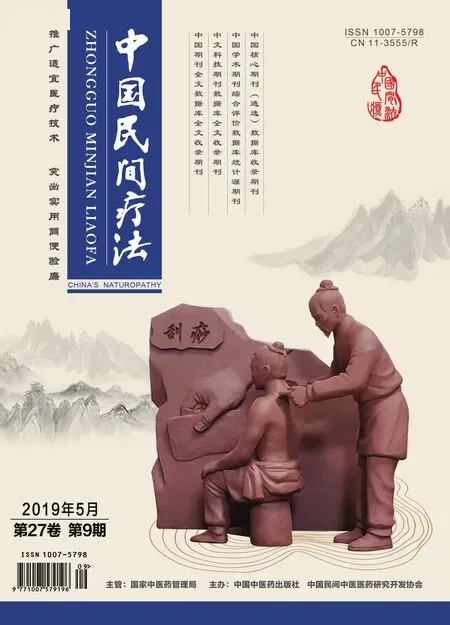劉光珍治療糖尿病腎病臨床經(jīng)驗(yàn)
張艷華,邢建月,閆夢苗
(山西省中醫(yī)藥研究院,山西 太原03000)
劉光珍教授現(xiàn)任山西省中醫(yī)院副院長,為山西省名醫(yī),中西醫(yī)結(jié)合腎病專家,山西省優(yōu)秀專家,國優(yōu)專家,全國百名優(yōu)秀青年中醫(yī)專家,全國優(yōu)秀中醫(yī)臨床人才。劉光珍教授致力于中西醫(yī)結(jié)合腎臟病臨床、科研、教學(xué)工作近30年,中西醫(yī)理論深厚,臨床經(jīng)驗(yàn)豐富,尤對糖尿病腎病的辨證論治獨(dú)具匠心,理論造詣深遠(yuǎn),臨床療效突出。在全國“腎病專業(yè)領(lǐng)域”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和學(xué)術(shù)地位。劉光珍教授提出用益氣養(yǎng)陰、清熱祛濕、活血化瘀法治療糖尿病腎病,開創(chuàng)了糖尿病腎病治療的新思路、新方法,使糖尿病腎病的治療取得突破性進(jìn)展,同時將活血化瘀法應(yīng)用于其他腎臟病的治療,也取得了較好的療效。
糖尿病腎病是糖尿病患者最主要的微血管病變表現(xiàn)之一,臨床特征為蛋白尿、漸進(jìn)性腎功能損害、高血壓、水腫,晚期出現(xiàn)嚴(yán)重腎功能衰竭,是糖尿病患者的主要死亡原因之一。
目前,對糖尿病腎病分期如下。①Ⅰ期:以腎小球高濾過率和腎臟肥大為特征。這類糖尿病腎臟受累的初期改變與高血糖水平一致,如果血糖控制,此期部分患者可以得到緩解。此期無病理組織學(xué)損傷。②Ⅱ期:白蛋白尿正常期。本期病理表現(xiàn)為基底膜增厚,系膜區(qū)基質(zhì)增多,腎小球?yàn)V過率多高于正常并與血糖水平一致。③Ⅲ期:持續(xù)微量白蛋白尿期。尿白蛋白排出率為20~200μg/min,腎小球?yàn)V過率開始降至正常。腎小球的病理改變較Ⅱ期加重,此期可以出現(xiàn)腎小球結(jié)節(jié)樣病變和小動脈玻璃樣變。患者血壓輕度升高,此期降壓治療可選用血管緊張素轉(zhuǎn)化酶抑制劑(ACEI)或血管緊張素Ⅱ受體阻滯劑(ARB)。④Ⅳ期:臨床糖尿病腎病期。大量蛋白尿,約30%的患者可出現(xiàn)腎病綜合征表現(xiàn),腎小球?yàn)V過率持續(xù)明顯下降,腎小球的病理改變?yōu)榈湫偷腒-W結(jié)節(jié)。進(jìn)入此期后,病情往往進(jìn)行性發(fā)展,臨床治療困難,水腫較嚴(yán)重,對利尿藥反應(yīng)差。⑤Ⅴ期:腎功能衰竭期。尿蛋白減少,尿毒癥癥狀明顯,胃腸道反應(yīng)較重,腎小球硬化,腎臟濾過功能進(jìn)行性下降,腎功能衰竭。
糖尿病腎病發(fā)病機(jī)制非常復(fù)雜,概括來說,起始于糖代謝障礙所致的血糖異常,在一定的遺傳因素及一些相關(guān)的獲得性危險因子的參與下,最終啟動體內(nèi)細(xì)胞因子網(wǎng)絡(luò),導(dǎo)致身體重要臟器的損害。損傷腎臟即為糖尿病腎病。
劉光珍教授在治療糖尿病腎病中積累了豐富經(jīng)驗(yàn),并有獨(dú)到見解,現(xiàn)總結(jié)如下。
1 主要病機(jī)
糖尿病腎病在中醫(yī)文獻(xiàn)中,既屬“消渴”,又歸屬于腎病范疇內(nèi)的“水腫”“尿濁”“脹滿”“關(guān)格”等,病機(jī)則以腎虛為主,初期精微外泄,久則氣化不利,水濕內(nèi)停,甚則濁毒內(nèi)蘊(yùn),臟氣虛衰,易生變證,總屬本虛標(biāo)實(shí)。以多飲、多食、多尿?yàn)榈湫桶Y狀,有上、中、下三消之分,從臟腑辨證以肺、脾、腎為病位,從陰陽屬性觀察以陰虛燥熱、氣陰耗傷為多見,然亦有屬陽虛、濕熱、血瘀者。消渴病在病因、病機(jī)、病位及臟腑陰陽辨證上,雖有上述之分,但它們之間往往相互關(guān)聯(lián),故在辨證中應(yīng)加以注意。發(fā)展至糖尿病腎病,則多以下消為主,陰虛燥熱往往已發(fā)展為氣陰兩虛,乃至陰損及陽。并由消渴早期的以虛為主的證候,發(fā)展為虛實(shí)并重、因虛至實(shí)的虛實(shí)夾雜證。如陰損及陽、津液輸布障礙,水飲內(nèi)停而水腫、小便不利。久病入絡(luò),脈絡(luò)瘀阻而為血瘀證,故治療當(dāng)虛實(shí)兼顧。但由于本病總以陰虛為本,燥熱為標(biāo),故縱然至陰損及陽,亦當(dāng)慎用溫燥,以免更傷真陰,而使燥熱愈甚,形成瘡瘍、煎厥等變證。
2 治療大法
本病總以氣陰兩虛為本,燥熱血瘀為標(biāo),治以益氣養(yǎng)陰、清熱祛濕、活血化瘀為大法。
2.1 益氣以黃芪為首選 黃芪與滋陰藥相配,有益氣生津之功,可有效治療糖尿病的氣陰兩虛。現(xiàn)代研究也證明,黃芪有一定的降糖效果[1]。黃芪與補(bǔ)血藥當(dāng)歸配伍,可益氣生血,現(xiàn)代研究表明,二者聯(lián)合應(yīng)用有減少尿蛋白、增加血白蛋白水平的功能[2]。黃芪與活血藥配伍,能益氣活血,顯著改善微循環(huán),緩解糖尿病神經(jīng)病變。黃芪單用或與利水消腫藥配伍,可治療氣虛水腫,為治療氣虛水腫的要藥。參芪地黃湯中六味地黃滋陰補(bǔ)腎,加參芪意在加強(qiáng)補(bǔ)氣之力,為現(xiàn)代腎臟病醫(yī)家所喜用[3]。
2.2 注重滋陰補(bǔ)腎 本病陰虛為本,久病及腎,發(fā)展為下消,但治療時仍需時時注意肝腎之陰。若單純看到糖尿病腎病的水腫而過用溫陽利水藥,則陰液更傷,燥熱愈增,往往導(dǎo)致病情迅速加重。
2.3 活血化瘀貫穿始終 糖尿病腎病的本質(zhì)為廣泛的微血管病變,糖尿病患者由于胰島素分泌不足或分泌延遲,導(dǎo)致微循環(huán)障礙,毛細(xì)血管管腔狹窄,血流緩慢,循環(huán)瘀滯,微血栓形成和微栓塞產(chǎn)生,造成組織缺血、缺氧,加重視網(wǎng)膜病變和蛋白尿的發(fā)生。中藥在改善血流變學(xué)異常方面具有優(yōu)勢。微血管病變患者多表現(xiàn)為舌質(zhì)紫暗或有瘀斑或舌下靜脈迂曲,屬中醫(yī)血瘀證。運(yùn)用活血化瘀法治療此類病證可獲得較好療效。
2.4 清熱祛濕為糖尿病腎病的重要治法 濕熱之邪與氣陰兩虛互為因果,濕為陰邪,易阻滯氣機(jī),損傷陽氣;熱為陽邪,耗傷陰液,且壯火食氣;脾虛不能運(yùn)化水谷與水濕,腎虛不能蒸化津液,致水濕內(nèi)停,濕郁久可化熱,故濕熱與氣陰兩虛互為因果。濕熱形成主要與胃、三焦、膽、大腸、膀胱密切相關(guān)。三焦主決瀆,膽與三焦共為少陽,為水火運(yùn)行之道路;大腸主傳導(dǎo)水谷糟粕;膀胱為“州都之官,津液藏焉”,均與水濕相關(guān)。故疏肝利膽、通達(dá)三焦、通利膀胱、清利大腸,成為祛除糖尿病濕熱病邪的重要途徑。
3 分型證治
3.1 肝腎陰虛 主癥:微量蛋白尿,浮腫較輕,口干欲飲,易饑多食,心煩失眠,尿頻,便秘,急躁易怒,面紅目赤,心悸怔忡,頭暈?zāi)垦#嗉t、苔黃,脈弦數(shù)或弦滑數(shù)。治法:養(yǎng)陰清熱。用藥:生地黃、熟地黃、牡丹皮、女貞子、枸杞子、知母、天花粉、黃連、麥冬、赤芍、丹參等。
3.2 氣陰兩虛 主癥:輕度浮腫,蛋白尿,腰膝酸軟,疲乏無力,頭暈?zāi)垦#瑹岫嗪梗p目干澀,視物模糊,大便秘結(jié),舌紅,苔薄白,脈沉弱。治法:益氣養(yǎng)陰。用藥:黃芪、白術(shù)、茯苓、女貞子、麥冬、天花粉、五味子、山萸肉、生地黃、知母、赤芍、丹參、紅花、桃仁等。
3.3 脾腎兩虛 主癥:腎功能異常,臨床蛋白尿,小便頻數(shù)或清長,或渾濁如脂膏,納呆,疲乏無力,面色蒼白,腰膝酸軟,或少尿,肢體浮腫,舌淡胖、苔薄白,脈細(xì)代滑。治法:健脾補(bǔ)腎,利濕化濁。用藥:黃芪、蒼白術(shù)、土茯苓、薏苡仁、石韋、茯苓、白茅根、赤芍、丹參、杜仲、狗脊、車前子、冬瓜皮、大腹皮、砂仁等。
3.4 陰陽兩虛 主癥:血尿素氮、肌酐明顯升高,大量蛋白尿,精神萎靡,形寒肢冷,大便偏稀,陽痿,遺精,面色無華,倦怠乏力,面目浮腫,腰酸耳鳴,舌淡、苔白,脈沉遲或沉細(xì)無力。治法:滋陰助陽、化瘀泄?jié)帷S盟帲菏斓攸S、山萸肉、女貞子、枸杞子、黃芪、當(dāng)歸、牛膝、杜仲、狗脊、薏苡仁、白茅根、石韋、土茯苓、丹參、赤芍、大黃、砂仁、生姜。
4 典型醫(yī)案
患者,男,68歲,主因間斷乏力、口渴、多汗10余年伴雙下肢浮腫8個月于2017年10月8日就診。患者糖尿病史10年余,發(fā)現(xiàn)蛋白尿8個月,近一年注射胰島素治療,空腹血糖控制為9.8 mmol/L,尿蛋白持續(xù)弱陽性,偶爾尿蛋白(+~++),腎功能正常,血壓正常,血脂正常。刻下癥:倦怠乏力,腰膝酸軟,煩熱多汗,耳鳴,口干口苦,小便多泡沫,大便秘結(jié),舌體瘦,舌質(zhì)暗紅,有瘀點(diǎn),苔薄黃,脈細(xì)數(shù)。遂來我院就診。實(shí)驗(yàn)室檢查:空腹血糖控制為9.8 mmol/L,尿蛋白(+~++)。辨證分析:患者消渴病久耗傷氣陰,且病程日久,窮必及腎,終致腎陰虧耗,氣陰兩虛,氣虛不能固攝精微,機(jī)體失于濡養(yǎng),故見倦怠,乏力;脾氣虛不能攝精,腎虛不能泌別清濁,上為煩熱多汗,下為精微外泄;腎陰虧虛,腰為腎之府,腰失所養(yǎng),故見腰膝酸軟;腎開竅于耳與二陰,腎虛故見耳鳴;陰虛火旺,灼傷陰液,機(jī)體失于濡養(yǎng)故見口干、口苦;舌體瘦,舌質(zhì)暗紅,有瘀點(diǎn),苔薄黃,脈細(xì)數(shù)系氣陰兩虛、濕熱瘀阻之舌脈。診斷:消渴(氣陰兩虛、濕熱瘀阻證);治法:益氣養(yǎng)陰,清熱祛濕,活血化瘀。處方:黃芪15 g,白術(shù)15 g,枸杞子15 g,女貞子15 g,丹參30 g,赤芍15 g,黃芩片10 g,石韋30 g,薏苡仁30 g,杜仲15 g,生龍骨、生牡蠣各30 g(先煎),熟地黃12 g,山萸肉10 g,土茯苓30 g,牡丹皮15 g,墨旱蓮12 g,砂仁6 g(后下),浮小麥15 g,桃仁15 g,紅花15 g,川芎15 g,焦三仙各15 g,14劑。水煎服,每日1劑,早晚空腹溫服。西藥繼予胰島素治療,并囑其采用優(yōu)質(zhì)低蛋白、低鹽、低糖飲食,慎起居,適勞逸,避風(fēng)寒,暢情志,防感冒。
二診:服藥后,患者癥狀有所減輕,乏力減輕,尿中有泡沫,大便正常。實(shí)驗(yàn)室檢查:尿常規(guī):蛋白質(zhì)(+),效不更方,14劑,水煎服,每日1劑。
三診:服藥后,患者癥狀大幅好轉(zhuǎn),乏力消失,精神食欲好轉(zhuǎn),尿中有少量泡沫,大便正常。實(shí)驗(yàn)室檢查:空腹血糖控制為7.8 mmol/L。尿常規(guī):蛋白質(zhì)(±),繼予上方為主,略有加減。堅持守方治療3個月余,定期監(jiān)測血糖、尿常規(guī)、尿微量白蛋白、24 h尿蛋白定量,繼予中藥補(bǔ)腎益氣養(yǎng)陰、清熱祛濕、活血化瘀,以鞏固治療,隨訪6個月病情穩(wěn)定。
按語:該患者患消渴病,久病傷及氣血陰陽,日久及腎,終致氣陰兩虛,腎陰虧耗,先天稟賦不足,脾胃虛弱,氣血虧虛,易感外邪,耗傷氣陰故感乏力、倦怠;脾氣虛不能攝精,腎虛不能泌別清濁,上為表虛自汗,下為精微外泄。本案中以黃芪益氣為君,黨參、白術(shù)健脾益氣為臣,川芎理氣,山萸肉、熟地黃、山藥、墨旱蓮滋陰為使藥。患者為本虛標(biāo)實(shí)之證,氣虛之體夾有血瘀之證,故以赤芍、桃仁、紅花活血化瘀。諸藥合用,隨癥加減,邪實(shí)得祛,正氣得復(fù),病終告愈。在該患者的治療過程中,劉光珍教授以補(bǔ)腎健脾養(yǎng)陰、活血化瘀為治療大法,并采取守方活法的治療原則,根據(jù)臨床證候的變化隨癥加減,獲得了較好的臨床療效。
5 小結(jié)
劉光珍教授治療糖尿病腎病,辨病與辨證相結(jié)合,活血化瘀法貫穿治療全過程,注重早期治療,截斷病勢,治病求本,補(bǔ)腎健脾,同時配合降糖、降壓、調(diào)脂綜合治療,中西醫(yī)結(jié)合治療,可明顯緩解糖尿病腎病病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