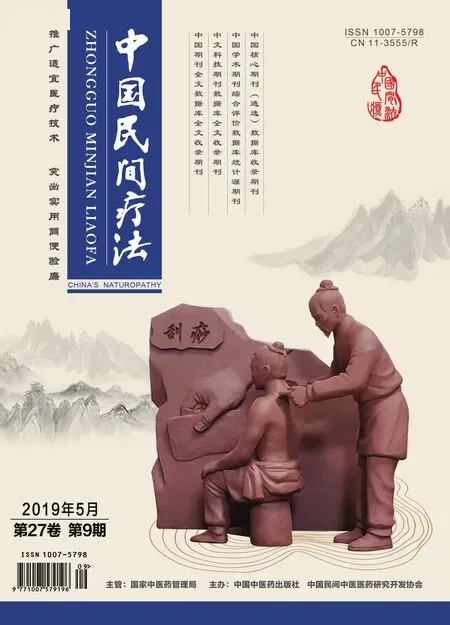從治療痞證論半夏瀉心湯的“魅力”
孟慶鴻
(天津中醫(yī)藥大學(xué),天津301617)
痞滿是臨床消化系統(tǒng)方面極為常見的證候。《素問·異法方宜論》載“藏寒生滿病”,最早提出對痞滿病因認(rèn)識。而仲景先師則是創(chuàng)立諸瀉心湯治療該種疾病,半夏瀉心湯既是治療寒熱錯雜痞證的基礎(chǔ)結(jié)構(gòu),也是后世醫(yī)家應(yīng)用最為廣泛的名方,無論是基礎(chǔ)研究,還是臨床實踐,半夏瀉心湯都是治療脾胃系疾病的“寵兒”,下面談?wù)勊摹镑攘Α薄?/p>
1 何為痞證
痞證是指由于無形邪氣內(nèi)陷于心下,影響中焦脾胃升降功能,使氣機痞塞,以心下痞塞不舒,按之柔軟,不硬不痛為特征的一類病證。患者常常自述“胃口堵得慌”,同時以手觸診,按壓無硬包或腫塊。《傷寒雜病論》第151條載:“脈浮而緊,而復(fù)下之,緊反入里,則作痞,按之自濡,但氣痞耳。”本條介紹了痞證的成因及證候特點,“脈浮而緊”說明寒邪在表,汗發(fā)可解,然誤用下法,引表邪入里,客于心下,影響中焦脾胃正常的升降功能,造成痞證。“按之自濡”提示病邪非有形之邪。“氣痞”說明痞的病理性質(zhì)是氣滯,故治療應(yīng)注意調(diào)節(jié)氣機。
2 治療痞證的思維之“美”
中醫(yī)是建立在樸素的辯證思維和取類比象的世界觀之上的,因此認(rèn)識疾病、診斷疾病與治療疾病均是通過不斷地觀察,取象于大自然,運用古樸的辯證思維去理解、分析其發(fā)生發(fā)展規(guī)律。痞證是由于邪氣影響中焦脾胃氣機的斡旋功能,導(dǎo)致脾氣不升,胃氣不降,中焦氣機停滯。故運用取類比象的思維方式,可以將痞證與生活中的下水道堵塞現(xiàn)象進(jìn)行類比。下水道堵塞時,當(dāng)引起堵塞的異物形狀、體積較大時,通常采取化學(xué)溶解或者物理打碎的方式,減小其體積,使下水道得以疏通;若引起堵塞的異物形狀、體積較小,但數(shù)量較多時,在潤滑的同時可以對其施加相反方向的力量,破壞異物與下水道之間形成的較為穩(wěn)定的平衡,以達(dá)到疏通的效果。針對痞證,《傷寒雜病論》提供兩種治療思路,與這種生活中的疏通方法極為相似。前者適用于無形邪熱留擾上焦,入里不深的痞證,以大黃黃連瀉心湯等治之。后者適用于邪氣入里傷及脾胃,脾胃虛弱,寒熱錯雜,以半夏瀉心湯等治之。同時這種思路也促進(jìn)了后世溫病學(xué)派的發(fā)展,正如葉天士所說:“微苦以清降,微辛以宣通”[1],使辛開苦降法有了更廣泛的臨床應(yīng)用。
3 半夏瀉心湯的組方之“美”
半夏瀉心湯是筆者最喜歡的方劑,其方藥組成具有極大的魅力。全方以半夏為君,力專消痞散結(jié),又善降逆止嘔。臣以干姜溫中散寒;黃芩、黃連泄熱開痞。然中虛失運,故方中又佐以人參、大棗補脾益氣,以甘草補脾的同時調(diào)和寒熱之藥。正如《素問·陰陽應(yīng)象大論》所說:“寒氣生濁,熱氣生清。清氣在下,則生飧泄;濁氣在上,則生脹。”本方剛好針對飧泄與脹同在的疾病,以半夏與干姜之辛升清,以半夏、黃芩、黃連之苦降濁。《素問·至真要大論》曰“寒者熱之,熱者寒之”,以半夏之溫、干姜之熱療寒,以黃芩、黃連之寒療熱。四藥相伍,方顯寒熱平調(diào)、辛開苦降之功。同時以人參、大棗、甘草之甘補脾胃之虛。后世將此法稱為“辛開苦降甘補”之法。綜合全方,寒熱互用以和其陰陽,苦辛并進(jìn)以調(diào)其升降,補瀉兼施以顧其虛實。
寒熱之藥相伍是本方的魅力所在,仲景先師極為擅長將藥性完全不同的藥物配伍以治療各種疾病,如麻杏石甘湯中辛溫的麻黃與辛寒的石膏相伍,以治療風(fēng)寒之邪入里化熱、邪熱壅肺之證候,宣肺以疏風(fēng),清肺以解熱,二者相伍能很好地恢復(fù)肺的宣發(fā)肅降功能。而本方則是寒藥與熱藥相伍,模擬人體中焦氣機升降,以辛溫、辛熱之藥象天,熱生清,辛味助清氣上升;苦寒之藥象地,寒生濁,苦味助濁氣下降。一升一降,形成了一個小宇宙。若人體這個大宇宙運轉(zhuǎn)失常則可以用小宇宙帶動大宇宙運行,幫助大宇宙恢復(fù)正常的軌跡。此外,寒藥與熱藥可形成相互制約關(guān)系,脾主升,胃主降,若升陽太過則燥胃陰,降濁太過反傷脾陽,仲景先師考慮于此,故采用寒熱相伍的用藥模式。
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在仲景先師原方中甘補藥量最大,提示本證的實質(zhì)為本虛標(biāo)實之證,雖以半夏為君,辛開苦降,直接消痞散結(jié),是全方最關(guān)鍵的用藥,但仍以人參、大棗、甘草補益胃氣為根本,恢復(fù)脾胃功能才能從根本上解決痞滿證候,達(dá)到“以補為瀉”的目的。正如尤怡在《傷寒貫珠集》所說:“痞者,滿而不實之謂。夫客邪內(nèi)陷,即不可從汗泄;而滿而不實,又不可從下奪。故唯半夏、干姜之辛,能散其結(jié),黃連、黃芩之苦,能泄其滿,而其所以泄與散者。雖藥之能,而實胃氣之使也。用參、草、棗者,以下后中虛,故以之益氣,而助其藥之能也。”此外,筆者認(rèn)為應(yīng)用半夏瀉心湯不必局限于寒熱錯雜,只要中焦氣機升降失常即可使用。仲景先師在原書中沒有提到寒熱錯雜的問題,寒熱錯雜是后人根據(jù)《金匱要略》中“嘔而腸鳴,心下痞者,半夏瀉心湯主之”推斷而出。試分析,濁氣在上,胃氣不降即可引起干嘔或者嘔吐,清氣在下,脾氣不升即可引起腸鳴,濁氣本屬陰,然而上屬陽,在上郁久則從陽化熱;清氣本屬陽,而下屬陰,在下積久則從陰化寒,因此寒熱錯雜是氣機失常日久所致。
4 半夏瀉心湯的應(yīng)用之“美”
半夏瀉心湯的魅力不僅局限于精妙絕倫的配伍特色,而且在臨床應(yīng)用中常受到中醫(yī)名家的青睞,可見其在治療痞證上發(fā)揮著巨大的療效。下面我們一起學(xué)習(xí)古今名家如何靈活應(yīng)用半夏瀉心湯治療各種復(fù)雜的痞滿證候。
4.1 古代名醫(yī)葉天士運用半夏瀉心湯的案例賞析《臨證指南醫(yī)案卷四·吐蛔·席案》中的患者“脈右歇,舌白渴飲,脘中痞熱,多嘔逆稠痰,曾吐蛔蟲”[1]。葉天士認(rèn)為這是“伏暑”(夏季感受暑濕邪氣,感而不發(fā),至秋冬季發(fā)作的急性外感熱病)。濕熱邪氣自里而發(fā),濕熱相裹,阻滯中焦氣機,出現(xiàn)脘痞等諸多證候,故葉天士選擇半夏瀉心湯治療,然而此處一個“議”字點明了并不以它為主方,而是用它投石問路,觀察藥后反應(yīng)。患者飲半夏瀉心湯以后出現(xiàn)“胸中稍舒,逾時稍寐,寐后嘔吐濁痰,有黃黑之形”。然后他解釋到“大凡色帶青黑,必系胃底腸中逆涌而出”。因此病位不在心下,故不能再用半夏瀉心湯。本則醫(yī)案運用半夏瀉心湯體現(xiàn)的是以其入手治療痞證,然后觀察其反應(yīng)確定下一步的診療方案,這種思路與《傷寒雜病論》第156條(對于誤下所致的心下痞,仲景先師首先用瀉心湯治療,藥后痞不解,再針對“渴而口燥煩,小便不利”使用五苓散行水,水液通行則痞滿自消)所體現(xiàn)的原則是相同的。
4.2 當(dāng)代名家劉渡舟運用半夏瀉心湯案例賞析 患者,女,49歲,湖北潛江人。主訴心下痞塞,噯氣頻作。嘔吐酸苦,小便少而大便稀清,每日三四次,腸鳴轆轆,飲食少思。望其人體質(zhì)肥胖,面部浮腫,色青黃而不澤。視其心下隆起一包,按之不痛,抬手即起。舌苔帶水,脈滑無力。劉老辨為脾胃之氣不和以致升降失序,中夾水飲,而成水氣之痞。處方:清半夏10 g,干姜3 g,黃連片6 g,黃芩片6 g,黨參片9 g,炙甘草6 g,大棗12 g,生姜12 g,茯苓20 g。連服8劑,則痞消大便成形而愈[2]。
按語:患者為肥胖體型,故素體為痰濕內(nèi)盛型體質(zhì),在飲食、情志或外邪等致病因素刺激下,使中焦脾胃升降功能紊亂,水飲中阻,故產(chǎn)生了痞滿的證候。胃氣上逆,故見嘔吐酸苦、噯氣頻作;脾不升清,故見大便頻數(shù)及稀清;同時脾不運化,水飲內(nèi)生,故見飲食少思、面部浮腫;而寒邪與水飲相搏于腸道,故見腸鳴轆轆。心下痞塊是由于脾胃之氣壅塞不通、痰氣中阻所致,其“按之不痛,抬手即起”的特點與仲景先師描述的“按之自濡”不謀而合。此外,從方證相對的角度來看,“痞,嘔,腸鳴”剛好對應(yīng)“半夏瀉心湯證”。故劉老辨為水氣痞,以辛開苦降之半夏瀉心湯為基礎(chǔ)方消痞散結(jié),同時加入并重用生姜溫中和胃化飲,加茯苓利水滲濕,使水飲之邪以小便為出路,同時此處不可用車前子、滑石之類利小便,是因為其性苦寒,苦寒?dāng)∥福讉笟狻V薪贡咎摚龠M(jìn)苦寒之品,胃氣一衰則變生壞證。此處可見劉老心思縝密,用藥之精不得不讓人佩服!
4.3 筆者跟隨恩師天津中醫(yī)藥大學(xué)袁紅霞教授的1則醫(yī)案 患者,女,26歲,2018年9月16日就診。主訴:食后胃脘痞滿數(shù)年余。自訴因飲食不節(jié)等原因致胃中堵悶痞滿,伴有胃脘灼熱嘈雜感,15∶00~17∶00時明顯,噯氣頻繁,四肢寒涼,二便調(diào)。舌質(zhì)淡紅胖,舌尖紅中有裂紋,苔薄黃,脈弦細(xì)。以半夏瀉心湯加味。處方清半夏10 g,黃連片10 g,黃芩片10 g,干姜10 g,黨參片15 g,炙甘草6 g,淡竹葉10 g,生石膏15 g(先煎),麥冬20 g,大棗5枚,共7劑。水煎服,每日2次。復(fù)診:訴服上藥后胃脘痞滿嘈雜感均消失。隨訪至今,未見不適。
按語:患者因飲食不節(jié)傷及脾胃功能,中焦氣機升降失職,故見胃中痞滿,噯氣;氣機失常過久引起寒熱錯雜,故見四肢寒涼,舌紅苔黃;而熱象重,傷及陰液,造成胃陰虧虛,故見胃脘灼熱嘈雜感,舌尖紅中有裂紋,脈弦細(xì)。15∶00~17∶00時加重是由于陽明經(jīng)經(jīng)氣旺盛于申時,正邪交爭劇烈,故見癥狀加重。因此應(yīng)采取辛開苦降、消痞散結(jié)、養(yǎng)陰生津的治法,故袁師運用了半夏瀉心湯與竹葉石膏湯合方治療,取得了顯著的療效。袁師在治療脾胃病方面頗有建樹,極為擅長運用經(jīng)方治療疑難雜癥,曾提倡對胃癌術(shù)后患者運用半夏瀉心湯加減治療以減輕其痛苦,提高患者生活質(zhì)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