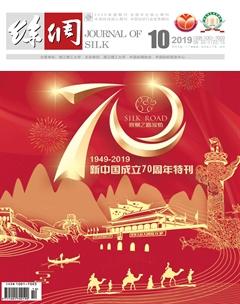理性的交往:中國絲綢服裝文化英譯與傳播策略
高歌 蔡欣
摘要: 文章依據交往行動理論的研究范式,以《紅樓夢》兩部英譯本中的相關絲綢服裝部分文本為例,從影響譯者判斷的時代變遷、社會關系、民族融合和復雜工藝等角度出發,探討中國傳統絲綢服裝文化的英譯以及對外傳播策略,揭示出交往行動理論的三個理性原則“真實性”“正當性”和“真誠性”,可以解決歷史和文化賦予絲綢服裝文化文本翻譯的難點和復雜性,能夠構建各文化主體間理性對話的機會,幫助中國傳統文化元素與現代產業結合,提升中國絲綢服裝文化在國際上的話語權。
關鍵詞: 理性原則;交往行動理論;絲綢服裝文化;《紅樓夢》;對外傳播
中圖分類號: TS941.12;H0-05 ?文獻標志碼: B ?文章編號: 1001-7003(2019)10-0122-06 ?引用頁碼: 101305
Abstract: This study, based on the research model of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action, via case study of excerpts related to silk costume from two English versions of the A Dream in Red Mansions, and from the aspects of change of time, social relations, national fusion and complicated process that influence translators judgment, aims to discuss the strategies for C-E transl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silk costume culture, and reveals that the three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rules of “Truth”, “Rightness” and “Sincerity” of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action are helpful to overcome the difficulties and complicacy in C-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silk costume culture writings due to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factors, construct rational intersubjective relationships among different cultures, boost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with modern industry, and promote the discursive power of Chinese traditional silk costume culture internationally.
Key words: rationality rules;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action; silk costume culture; A Dream in Red Mansion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中國自古以來絲綢文化底蘊深厚,是極具吸引力的“軟實力”。歷史上中華文明通過古老的絲綢之路對世界文明做出了重要貢獻,目前中國仍然是世界最重要的絲綢服裝生產和設計中心。在2017年中國服裝杭州峰會上,很多國內外專家都認為中國服裝業正在轉化市場競爭為合作,越來越多的中國品牌擁有全球“粉絲”,引領時尚消費。在這樣的新形勢下,大力翻譯和傳播優秀的中華絲綢服裝文化,對于提升中國服裝產業在國際上的話語權有著積極的作用。本文以哈貝馬斯的交往理論為哲學基礎,以《紅樓夢》雙英譯本[1-2]中的絲綢服裝翻譯文本為例,從交往行動理論翻譯觀的角度,嘗試通過理性的翻譯構想及文化思考傳播中國絲綢服裝文化,構建不同價值觀和文化內涵的人們之間的了解、尊重與借鑒。交往理論認為翻譯活動的目的不僅是語言轉換或者文本間互動,其核心目的是文化間的信息傳播與交流,其過程必須遵循平等對話的理性原則和方法[3],最終使不同的文化能夠在主體間尋求對客觀世界的共識,并產生相互認同感。
1 交往行動理論翻譯觀
交往行動理論的語言觀認為任何言語行為都是陳述部分和施行部分的結合[4]。翻譯也是如此,譯文是陳述部分,而譯者的文化立場、翻譯目的、審美傾向、個人喜惡、目標讀者的選擇定位等都屬于施行部分,這些施行部分的內容都會參與決定譯文的形式。施行層面完全是現實世界的理性體現,是譯者目的性、動機性和審美傾向的美學批判[5],翻譯不是譯者完全感性的自我解讀,而是理性交往的社會活動。譯者作為翻譯文本的構建者,要在原語和譯入語的語言規則與社會規范性中間做出解讀、平衡和調整,必須保持理性。交往行動理論構建翻譯標準的理性依據為三個有效性原則:真實性、正當性和真誠性。也就是說在翻譯中,譯者必須遵循知識的客觀性,陳述事實的“真實性”,否則完全任意的解讀會失去讀者的信任;翻譯中建立的交往關系一定是屬于社會世界的,譯者對原文和譯文的理解都要符合社會世界的準則和規范,對于社會中大多數人群來說是正當的,并具有普遍的有效性,這樣才能做到“正當性”;“真誠性”是指當原語與譯入語之間存在文化解讀空缺或者不確定性時,仍然可以依賴語言的定向性,也就是在原文的圖式框架內緊緊抓住其確定性的一面,在譯文中理性重建語境。
在文化傳播方面,交往行動理論翻譯觀認為,原語文化與譯入語文化之間沒有先進與落后之分,是主體之間的同等重要關系,譯者要為這種關系提供理性連接,構建起二者之間的橋梁。在中國傳統文化外譯中,譯者不能孤芳自賞,向譯入語讀者輸出與譯入語受眾的價值觀念和信息需求南轅北轍的譯本信息,更不能為了達到所謂“完美的譯文”而無視中國文化的深遠內涵。譯文不能逾越雙方的語言規則和社會規范的制約,譯者必須接納不同語言之間的合理碰撞,調動不同主體之間進行理性互動,實現各種文化的協調、平衡和發展,最終豐富人類文明成果。
2 絲綢服裝文化翻譯中的理性對話
哈貝馬斯認為“藝術作品具有敞開真理的潛能……以潛移默化的方式改變著人對世界的認知方式和自我理解方式,改變著自我同客觀世界與社會世界的關系,具有教化作用”[4]。因此絲綢服裝文化傳播也改變著外國讀者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理解和認同度,如果譯者能夠理性表達自身社會文化價值,并且理性反思他文化的價值,這種通過譯文達成的社會交往就是合理的。翻譯屬于美學批判的范疇,評價時要看標準是否合適,而非是否正確,絲綢服裝文化翻譯和傳播也是如此。
交往行動理論的核心哲學之一是在主體之間尋求對于世界共同狀況的了解,其對于構建國際傳播的新型交往路徑具有重要意義[6]。如今隨著傳播模式的轉型,傳播的主體由一元趨向多元。中國絲綢服裝文化對外翻譯和傳播也需要對本國語言和文化高度認同的同時,兼顧不同文化背景的國際受眾需求,以積極、理性的方式爭取國際話語權。任何一種文化的價值只能體現在與他人的交流中,與他文化的碰撞帶來自我及他人的認同,通過譯本進行文化傳播,使不同的文化能夠在主體間尋求對于客觀世界的共識,并產生主體間的相互認同感。只有秉持這樣的觀點,才能在翻譯過程中協調文化沖突,找到合適的傳播策略,使得各國文化在主體間理性流動和理性反思。
3 《紅樓夢》中相關文本的英譯和傳播策略分析
中國絲綢服裝文化歷史悠久,底蘊深厚,從織造、染色、印花、款式設計及文化意蘊等角度的翻譯都十分艱深。本文以《紅樓夢》兩個英文譯本(以下簡稱楊譯和霍譯)為例進行研究,探討中華絲綢服裝文化外譯的策略,協調文化交流中的碰撞。首先,曹雪芹由于其江南織造局的家庭背景,對于絲綢織造和絲綢服裝制品的研究造詣極深,《紅樓夢》中的絲綢服裝描寫顏色富麗,質料華貴,名目繁多,從服裝款式上的袍、褂、襖、裙等,到絲綢織造工藝上的縐、紗、絹、紈、絨、綃、緞、云錦、緙絲等,薈萃中國歷朝各代傳統絲綢服裝文化于一體,是中華絲綢之美的集大成者。其次,楊憲益和霍克斯是公認的翻譯大家,兩位的譯本都是譯學界難以逾越的高山,但是兩位從翻譯目的、文化背景、文化立場和個人偏好等很多方面都表現出迥然不同的譯者風格,在絲綢服裝文化的英譯上也表現出較大差異。因此,本文采用兩譯本中與絲綢服裝相關的片段,作為具體的分析對象,從交往行動理論的角度,探索中國絲綢服裝文化外譯過程中的理性交往策略,促進不同文化內涵之間的互動和借鑒。
有關絲綢服裝的文本有其特殊性,會有一些原因造成翻譯和傳播上的困難。本文從以下幾個難度較大的角度,來探討中國絲綢服裝文化英譯的策略。
3.1 時代變遷帶來的改變
在中國傳統的絲綢服裝中,很多元素隨著時代的變遷,在語言的表述方式上發生了很大變化,顏色詞就是其中比較典型的例子。中國傳統絲綢服裝中,顏色指稱詞種類繁多,很多指稱詞具有很深的時代和地域特色,其中一些表達在當下的服裝行業中仍然是慣用的表達方式,具有現實意義。但是對于如今的一部分業內外人士而言,由于時代變遷的影響,在理解其意義時會出現偏差。而且色彩指稱詞本身具有模糊性[7],有些指稱詞甚至不帶有基礎顏色詞,在翻譯上難度較大。
《紅樓夢》中曹雪芹將諸多異彩紛呈,名目繁復的顏色詞用在絲綢服裝描寫上,其翻譯難度顯而易見。比如第三回中描寫寶玉身著的絲綢褲子“松花撒花綾褲”中的“松花”色,與他穿著的綢面“白狐皮秋香色箭袖”中的“秋香色”:“松花色”霍譯“ivy-coloured”,楊譯“light green”;“秋香色”霍譯“russet green”,楊譯“yellowish green”。這兩種顏色都是中國傳統絲綢服裝印染上的常用顏色,翻譯難度大是因為這兩種顏色都沒有基礎顏色詞。對于現代人來說松花并不常見,因此連顏色大類都很難識別。松花色在古籍《玉紀補》[8]中被記載為松花綠色,可見是綠色系中的一種,而霍譯為“ivy-coloured”是與實際顏色有差距的。由于與秋季相關的顏色有很多,這給“秋香色”的翻譯帶來難度,《清史稿》[9]志七十八輿服二中有云:“康熙二十三年,定凡大典禮祭壇廟……禮服用黃色、秋香色……皇后冠服,凡慶賀大典……禮服用黃色、秋香色……”可見“秋香色”即清朝皇室至高慶典中常用到的一種黃色。楊將“秋香色”譯為“yellowish green”,霍譯為“russet green”,二者在顏色基調的翻譯上基本一致,黃綠基調符合“秋香色”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客觀本意。
類似的例子還有第三回中寶玉的“銀紅色撒花半舊大襖”中的“銀紅色”,與第四十九回中寶釵的“蓮青斗紋錦上添花洋線番羓絲的鶴氅”中的“蓮青色”:“蓮青色”霍譯“ivy-green”,楊譯“pale purple”;“銀紅色”霍譯“rose-coloured”,楊譯“bright red”。現代漢語詞典將“蓮青色”解釋為紫色系的一種,就這個詞而言漢語基礎顏色詞與實際顏色有差異。因此,楊譯為“pale purple”是準確的,霍譯的“ivy-green”與實際顏色有出入。“銀紅色”是中國傳統色彩名稱,是指淺淡的紅色中泛白,是非常柔和并不刺眼的顏色,染色的對象常為輕薄的絲綢面料,比如紗、羅、綢、綾等,與其字面意義“像銀子一樣閃亮的紅色”有所出入。清《鳳仙譜》[10]有云:“銀紅有深淡二種。深者如紅而稍淡,如霞紅而較深,又非杏紅,非芙蓉,別具一種色。其淡者粉地含紅,在有無之間,歷久不變,二種皆妙品。”可見深淡兩種銀紅皆不是閃光明艷的紅色。在第四十回中賈母對鳳姐說:“那個軟煙羅只有四樣顏色:一樣雨過天青,一樣秋香色,一樣松綠的,一樣就是銀紅的。要是做了帳子,糊了窗屜,遠遠的看著,就似煙霧一樣,所以叫做軟煙羅……”可見做帳子、糊窗子的“銀紅色”絲綢不可能是閃亮鮮艷的顏色。因此在這個顏色的翻譯上,霍譯的“rose-coloured”要比楊譯“bright red”更符合“銀紅色”傳統意義上的客觀本質。
以上諸多例子可見,霍偏向使用具有基礎顏色詞性質的自然名詞,有時再加上基礎顏色詞的策略來翻譯一些文化跨度很大的顏色指稱詞,這種翻譯方法借用了譯入語讀者熟悉的自然名詞的顏色,降低了閱讀難度;而楊偏愛使用表示色彩濃淡的修飾詞,加上基礎顏色詞的翻譯方法。盡管他們中只有楊憲益具有中國文化背景,但是二者對中國文化的認同度都很高,否則無法解釋霍克斯能夠苦心孤詣數十載從事這部鴻篇巨作的翻譯。因此在顏色指稱詞的翻譯上二者都在積極協調文化沖突,但是二人就顏色詞的翻譯上互有高低,都有與原文本不符的情況。“真實性”是交往理論的合理性原則之一,是譯者在翻譯中必須依據的原則。翻譯活動應該盡可能地呈現知識的客觀性,也就是對客觀世界事態與事實做出的陳述必須是真實的,任意地改變文本的真實性,就是犧牲掉了原文的內涵和文化意蘊,會造成知識信息的錯誤流動,帶來雙方文化之間更多的誤會。在傳統絲綢服裝翻譯中,由于年代的跨度大,很多元素的“真實性”與現代人的認知圖式有較大出入,因此譯者在翻譯之前必須尋根溯源,借助古籍考據其來歷和真實性含義,不可望文生義。
3.2 復雜的社會關系和深遠的文化內涵
服裝是社會關系的一個重要表現渠道,絲綢服裝材質昂貴,工藝復雜,體現出穿戴者的社會地位和身份名望。特別是清代,由于絲紡繡染等各種手工專業的進步,形成了炫耀財勢的繁瑣裝飾重于藝術表現的特點[11],服飾的材質和圖樣更加是人物社會身份和文化身份的體現。比如在第十五回,北靜王穿著的絲綢袍子是“江牙海水五爪坐龍百蟒袍”,其中:“江牙海水”紋,霍譯為“a ‘tooth and wave design”,楊譯為“zigzag wave patterns”。“江牙海水”紋,又稱“海水江崖紋”是中國的傳統吉祥圖樣,經常用于古代絲綢龍袍和高位官員服裝下擺。圖案的下部是斜向排列彎曲的線條,名曰水腳,水腳之上是波濤涌動的水浪,水中現出山石,伴有祥云點綴,蘊含福山壽海、盛世江山的宏大主題。這個圖紋體現出北靜王尊貴的地位和特殊的社會身份。霍將其翻譯為“a ‘tooth and wave design”,實際上這種圖案與“tooth”牙齒狀的紋樣相去甚遠;而楊譯為“zigzag wave patterns”,也只是想達到簡單的詞匯的對等,都沒有表現出原文的富貴美好意蘊。
像這樣的傳統絲質圖樣在當今仍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2014年11月10日,APEC領導人在出席北京舉行的歡迎宴會時,身著一系列展示中國新形象的中式絲綢服裝,就是采用“海水江崖紋”的設計,賦予21個經濟體山水相依、守望相護的寓意。中國國際廣播電臺英文網站“Chinaplus”將“江牙海水”翻譯為“a decorative pattern of the shape of a cliff and sea wave which were used in ancient Chinas imperial robes”,并進一步解釋為“the shape of a cliff and sea wave represents the 21 economies depending and supporting each other”。可謂因地制宜,既譯出了圖紋的尊貴祥和的意蘊,也傳遞出中國與世界各國建立和諧圓滿國際關系的美好愿望。
再如第八回中寶玉身穿的“秋香色立蟒白狐腋箭袖”,這種袍子綢緞面,白狐皮內襯,“立蟒”圖紋。“蟒”紋是明清代常用官服圖案,到了清代使用寬泛,很多官宦也會在禮服中使用,可見使用者的社會地位地位非富即貴。“立蟒”,霍譯為“writhing dragons”——翻滾的龍,而楊譯為“serpents”——大毒蛇。明朝沈德符《萬歷野獲編》[12]里有曰:“蟒衣為象龍之服,與至尊所御袍相肖……凡有慶典,百官皆蟒服……”可以證明,“立蟒”之圖紋的確為龍紋的一種,其寓意因富貴美好而影響深遠,傳世至今。因此,霍氏的翻譯兼具了傳遞中國文化圖式的“正當性”和“立蟒”的動態感,十分準確生動。楊譯的“serpent”在文化圖式上與“蟒”紋本身尊貴美好的寓意相悖,削弱了中國傳統絲綢服裝圖案的影響力。
中國絲綢服裝歷朝歷代都有很多極具特色的顏色、款式、工藝和創新,這些元素不僅停留在絲綢或者服裝的視覺領域,他們還承載著豐富的文化內涵和復雜的社會關系,很多元素在如今甚至重回到流行文化中來,煥發出新的生命。正因為如此,譯者在翻譯過程中,要更加關注譯文的“正當性”,似是而非的翻譯會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力。在必要的時候,對復雜的、內涵比較豐富的圖紋可以通過添加注解的方式,與讀者的社會世界進行溝通,借助雙方都能接受的概念和文化圖式,達到譯文最終的“正當性”,如果只是草草了事或者主觀猜測,不能正當傳遞作者的文化世界,也令讀者一頭霧水。作為譯者在深刻理解雙方文化的同時,應該耐心和理性地化解翻譯中文化上的障礙,只有這樣才能將中國絲綢服裝具有深層文化內涵的特色元素推廣到世界。
3.3 民族的融合
歷史上中國服裝文化見證了無數次的民族融合,這使得中國服裝具有多民族的特色,因此要使這些元素走出國門,在更大的空間創造新的競爭優勢,就必須克服翻譯工作的困難,達成跨領域、跨文化、跨語際的信息傳播效果[13]。具有民族特色的絲綢服裝不僅具有欣賞性,還具有很強的功能性。比如寶玉常穿的一種絲綢服裝——“箭袖”,在文中多次出現:“箭袖”,霍譯“a narrow-sleeved, full-skirted robe”, 楊譯“archer s jacket”。“箭袖”是指一種服裝款式,也稱馬蹄箭袖衣,是清代常見的服裝[11]。箭袖其袖口接出一個半圓形的袖頭,形如馬蹄遮住手背,起保暖作用,用于滿族同胞騎射狩獵,清代在禮節場合必須穿帶有箭袖的袍[14]。這是一種具有滿族和蒙族特色并且方便騎行和生活的款式,由于具有較強的使用功能,在清朝廣為流傳。在第三回中,霍將寶玉身著的“箭袖”譯為“a narrow-sleeved, full-skirted robe”,如果從功能的角度出發,“full-skirted robe”大擺袍肯定不是騎射的常服。而楊譯為“archer s jacket”,言簡意賅,不但將功能性和款式結合得恰到好處,而且找到了東西方的騎射手在衣著上的相通之處,也是東西方文化的結合點,遵循了雙方社會世界中的制約性,借助雙方都能接受的概念和文化圖式,自然地連接起作者與讀者迥然不同的文化世界,體現出很高的文化主體間意識和交往的“正當性”。
“褂”也是滿族人繼承其先人女真人和肅慎人的衣著特色之一,是一種穿于袍服外的短衣,衣長至臍,袖僅遮肘,便于騎馬[14]。第三回中王熙鳳穿著“縷金百蝶穿花大紅洋緞窄裉襖,外罩五彩刻絲石青銀鼠褂”和第五十一回中襲人的“青緞灰鼠褂”都是典型的清朝滿族貴族及其家眷的冬季常服,“刻絲”和“青緞”皆是工藝繁復,價格昂貴的絲綢面料,內襯動物皮毛,既有審美和御寒的功能,也是馬上民族權力和地位的體現。徐珂在《清稗類鈔》[15]中描寫皇帝的褂子時說:“一如常服褂而袖端平,前施掩襠,油綢為之……領用青羽緞……褂色用石青,長與坐齊,袖長及肘。”可見褂子的長度不會長于腰臀。對于“褂”,霍和楊有如下不同譯法:第三回中“褂”霍譯“jacket”,楊譯“cape”;第五十一回中“褂”霍譯“jacket”,楊譯“coat”。
“Cape”在牛津和韋氏字典中都被解釋為“a sleeveless outer garment that fits closely at the neck and hangs loosely over the shoulders,typically a short one”,可見是無袖短披風,僅領口系住,松散蓋肩,與中國傳統意義上的“褂”在功能上和長度上有相似之處,但是款式差別較大。“coat”牛津詞典解釋為“a thick outer garment worn outdoors, having sleeves and typically below the hips”,韋氏為“an outer garment worn on the upper body and varying in length”,可見“coat”為外出服,有袖,長短不定,以長過腰臀為多,與“褂”在功能上相同,長度有時類似。而“jacket”牛津詞典定義為“an outer garment extending either to the waist or the hips, typically having sleeves”,長及腰臀的有袖外出服,與“褂”在長度上相同,功能上也類似。因此,僅在這兩處“褂”的翻譯上“coat”與“jacket”要好于“cape”。滿族服裝曾經兩百多年興盛不衰,對中國近現代服裝的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很多絲綢服裝都有著滿族服裝的元素,為了保持和發揚這些珍貴的元素,在翻譯工作上要特別注重保留其款式和功能上的文化圖式。在采用歸化法翻譯時,切不可偏離文本原意,完全脫離原文化的限制,而是應該積極尋找文化之間的相通之處,理性遵循雙方文化的制約性,遵循交往的“正當性”原則,真正讓美好的民族服裝元素在主體之間流動。
3.4 高超而獨特的傳統絲綢服裝制作工藝
在工業化生產的背景下,如何宣傳和保持中國傳統服裝制作工藝曾經的輝煌,也是本文關注的問題之一。自動化的工業文明,帶來現代人觀念上的變化,中國傳統絲綢服裝工藝也不是始終一成不變的,也要與現代時尚相結合,為現代生活需要服務,挖掘參與現代競爭的機會。
中國絲綢根據不同織法工藝,品類眾多。《紅樓夢》中關于絲綢服裝工藝的描寫包羅萬象,織錦、刺繡、緙絲、金銀線等都有提及,但是很多織造和制作工藝之復雜艱深。對于世界上其他國家而言,都屬于文化空缺,因此在翻譯上做到語義上和文化上的對等都十分困難。比如第五十一回,襲人身著“桃紅百子刻絲銀鼠襖子”。根據蘇州緙絲博物館的介紹,刻絲即緙絲,始于隋唐,其織法是使用很多竹葉形小梭和木梳形撥子按花紋輪廓分塊制織,使織物上花紋與素地、色與色之間呈現一些斷痕,類似刀刻的形象,古人形容緙絲有“通經斷緯之像”。2009年中國的緙絲工藝就入選了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16]。緙絲主要有三種代表性英譯法:霍和楊都將刻絲譯為“silk tapestry”;《紡織術語》中英譯為漢語拼音的形式”Kesi”[17];中國絲綢博物館的緙絲展品譯為“Kesi tapestry”。牛津字典中將“tapestry”定義為:“Tapestry is cloth into which threads of coloured wool are woven by hand to make designs and pictures, used for covering walls and furniture.”意為提花裝飾的掛毯。盡管織布工具、使用的紗線、出現的年代、使用功能及文化功能都有所區別,但是緙絲與這種起源于西域的歐洲羊毛提花裝飾毯(tapestry)在“通經斷緯”的織法上,以及織法的起源上存在比較多的相同和相通之處[18]。在譯文的理性重建中,譯者以此為依據,將緙絲譯為“silk tapestry”或者“Kesi tapestry”是合適的譯法,在“tapestry”的基礎上加入“silk”或者“Kesi”,限定了對中國文化中“緙絲”的特指,有效地解決了文化空缺帶來的翻譯難題,遵循了理性交往的“真誠性”原則。當譯入語文化有空白時,譯者要充分利用文化間的相通部分,真誠尊重原文的文化圖式結構,將譯文構建在雙方文化中共通的確定性的因素之上,不應該在其空缺的或者不確定的因素上過度主觀發揮。
4 結 語
交往理論認為藝術具有改變人與世界,人與人之間關系的教化功能。只要遵循“真實性”“正當性”和“真誠性”的理性原則,通過相應的翻譯策略,中國傳統的文化形式和藝術作品可以在大跨度的文化交際中,與其他文化以主體間的形式信息流動,最大化地實現對外傳播效應。隨著全球社會要素不斷擴散和滲透,不同國家的絲綢和服裝產業人士之間會有越來越多的共同關注的業內話題,因此需要構建出更多的渠道彼此交流,需要多角度地平等理性對話。
基于交往行動理論,通過理性的翻譯策略,可以推動傳統絲綢和服裝制作工藝與現代生活和生產的再度融合,使傳統元素重回到流行文化中來,煥發出新的生命。可以幫助絲綢服裝業在新產品、新模式、新技術、新理念等各個方面走出國門,在更廣闊空間創造新的競爭優勢,將中國絲綢服裝具有傳統特色的元素推廣到全世界。
楊憲益與霍克斯兩位大家是文學翻譯界的巨擘泰斗,本文只是借助了兩譯本中與絲綢服裝翻譯相關的個別片段,梳理了粗粗幾個層面,難免會有管中窺豹之嫌,未來還需要進行更深入和全面的研究,任重而道遠。
參考文獻:
[1]CAO Xueqin. A Dream of Red Mansion [M]. Translated by YANG Hsienyi.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Press, 1978.
[2]CAO Xueqin. The Story of the Stone [M]. Translated by David Hawkes, John Minford.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73.
[3]呂俊. 何為構建主義翻譯學[J]. 外語與外語教學, 2005(12): 39.
L Jun. What is constructivist translatology [J]. Foreign Languages and Their Teaching, 2005(12): 39.
[4]哈貝馬斯. 交往行動理論[M]. 重慶:重慶出版社, 1994: 224-225.
JRGEN Habermas. Communication Action Theory [M]. Chongqing: Chongqing Press, 1994: 224-225.
[5]呂俊. 文學翻譯:一種特殊的交往形式—交往行動理論的文學翻譯觀[J]. 英美文學研究論叢, 2002: 352.
L Jun. Literary translation: a special kind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J].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ry Studies, 2002: 352.
[6]李欣人, 何明敏. 交往理論視閾下中國對外傳播理念重構[J]. 當代傳播, 2017(4): 24.
LI Xinren, HE Mingmin. Reconstruction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cation action theory [J].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s, 2017(4): 24.
[7]錢紀芳, 顧小燕. 色彩指稱詞的模糊性及其翻譯策略[J]. 浙江理工大學學報, 2008(6): 721.
QIAN Jifang, GU Xiaoyan. Fussiness of color referential words and relevant translation strategies [J]. Journal of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2008(6): 721.
[8]劉心缶. 玉紀補[M].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8: 178.
LIU Xinfou. Yu Ji Bu[M]. Beijing: Beijing Yanshan Press, 1998: 178.
[9]趙爾巽. 清史稿[M]. 長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5: 2063.
ZHAO Erxun. Qing Shi Gao [M]. Changchun: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5: 2063.
[10]趙學敏. 海棠譜鳳仙譜蘭蕙小史[M]. 北京: 當代中國出版社, 2014: 68.
ZHAO Xuemin. Feng Xian Pu Hai Tang Pu Lan Hui Xiao Shi [M]. Beijing: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2014: 68.
[11]沈從文, 王予 予. 中國服飾史[M]. 西安: 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04: 144, 152.
SHEN Congwen, WANG Xu. A History of Chinese Costume [M]. Xian: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4: 144, 152.
[12]沈德符. 萬歷野獲編 [M]. 北京: 文化藝術出版社, 1998: 22.
SHEN Defu. Wan Li Ye Huo Bian [M]. Beijing: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1998: 22.
[13]王宏, 劉性峰. 當代語境下的中國典籍英譯研究[J]. 中國文化研究, 2015(2): 70.
WANG Hong, LIU Xingfeng. The study of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under the context of contemporary times [J]. Chinese Culture Research, 2015(2): 70.
[14]陳東生, 甘應進, 周麗艷, 等. 清代滿族風俗與《紅樓夢》服飾[J]. 太原大學學報, 2006(3): 9.
CHEN Dongsheng, GAN Yingjin, ZHOU Liyan, et al. Manchus social conventions in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costumes in The Story of the Stone[J]. Journal of Taiyuan University, 2006(3): 9.
[15]徐珂. 清稗類鈔[M]. 北京: 中華書局, 2010: 6139.
XU Ke. Qing Bai Lei Chao [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0: 6139.
[16]范英豪, 周瑩. 基于市場開發與非遺保護雙重視野下的蘇州緙絲手工藝傳承[J]. 絲綢,2018,55 (10): 91-97.
FAN Yinghao, ZHOU Ying. The inheritance of Suzhou Kesi handicraft from the dual perspective of market development an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J]. Journal of Silk, 2018,55(10): 91-97.
[17]ULLA Cyrus-zetterstrom, XU Guohua. Textile Terminology [M]. Boras: Centraltryckeriet Ake Svenson AB, 1995: 44.
[18]孫佩蘭. 對緙絲起源研究中幾個問題的看法[J]. 絲綢, 1995(7): 47-51.
SUN Peilan. Views on some issues arising from the research of Kesis origin [J]. Journal of Silk, 1995(7): 47-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