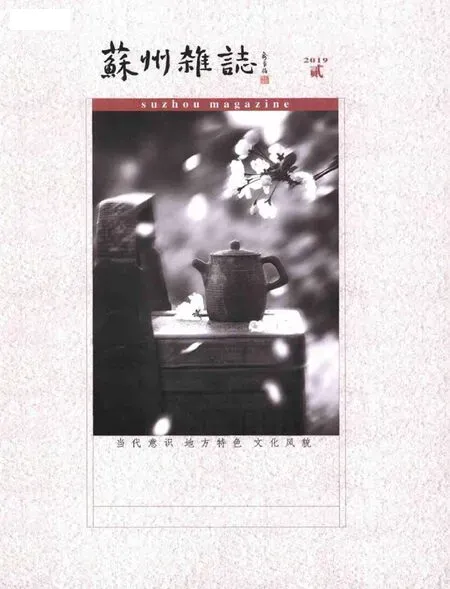林泉松風堪自洽
2019-01-10 03:42:33高萍
蘇州雜志
2019年2期
高萍
高士圖作為中國傳統(tǒng)繪畫中的經(jīng)典樣式,自魏晉始,直到明清,都是文人畫家們爭相傳模和不斷雕琢的對象。
所謂“高士”,概指博學多才、心性高潔、超塵脫俗的士子高人。他們活躍在無數(shù)的史籍傳記、詩詞繪畫、戲曲話本里,為一代代后學之人濃墨重彩地描述和傳誦著。《后漢書·逸民傳》序曰:“或隱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靜己以鎮(zhèn)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漢魏以來的高士選擇隱居是為了“求其志”,在繁亂的現(xiàn)世力求修得心靈的悠棲。到唐代隱逸之風的盛行和制舉制度的提倡,導致了以高士為題的詩歌的大量涌現(xiàn)。《全唐詩》中含有“高士”的詩詞百首有余,既有追憶魏晉竹林先賢,亦有思慕當時具名高士,但更多的描述并沒有具體所指。這種對高士形象的泛化,使“高士”的內(nèi)涵趨于外延,亦使高士題材的藝術形式變得更加多元。
美術史上的高士形象十分廣泛。不但描繪文人儒士、隱者逸客,也表現(xiàn)游方僧道、漁翁樵夫,更有高品位的仕女也常被納入高士圖的范疇。他們或相與交游、吟詩唱和,或聽琴品茗、坐而論道,亦或師徒授受、奇文共賞等等雅好和舉止,在千載之下的繪畫中被反復描繪著。《宣和畫譜》卷五《人物敘論》中,把高士題材的作品描述為:“精神有取于阿堵中,高逸可置之丘壑間者,又非議論之所能及,此畫者有以造不言之妙也。”將高逸之士與山水丘壑聯(lián)系在一起,以山林泉石的品質(zhì)比擬高士的品格,與詩詞一樣有“托物言志”的意味。……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