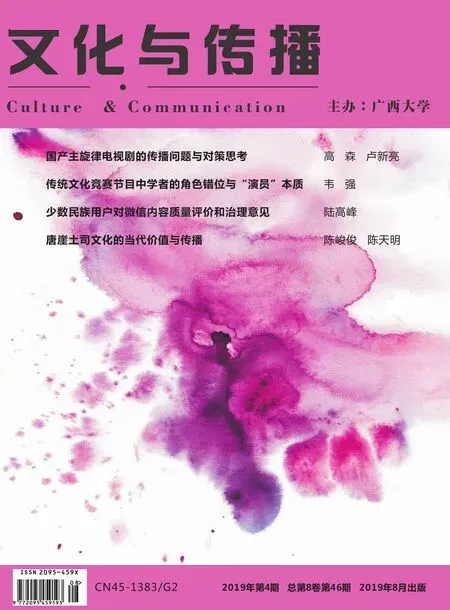《廣西婦女》戰時兒童觀之辨析:從抗戰“衛士”與文明兒童的“塑造”談起
潘 蓉
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戰時民族統一戰線的婦女組織——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婦女指導委員會誕生于此抗日救亡之際,該組織聚合了不少當時中國社會中的精英女性。①根據學者宋青紅2012年發表的博士論文《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婦女指導委員會研究(1938-1946)》,“新運婦指會總會及各分會廣泛吸收國民黨高官政要夫人、早期婦女運動者、婦女界名流、各行各業的婦女專家,國民黨、共產黨的婦女干部以及基督教人士參加。女性參與新運婦指會的組織工作,不僅僅因為其性別身份,也與其政治背景、身份地位密切相關。由于個人興趣愛好的差異,女性參與婦女新運工作的廣度和深刻不同,在新運婦指會內發揮的作用各異。參與新運婦指會的女性的廣泛的政治背景、身份地位,可見新運婦指會并不是一般的民間團體,也不是單純的官方婦女組織。”在1940年到1943年間,廣西分會出版的《廣西婦女》作為抗戰時期廣西最大的綜合性婦女報刊,扮演了號召廣西婦女團結抗戰、指導婦女運動的角色。
1962 年,Philippe Ar iè s《兒童的世紀》的發表啟動了兒童文化史的學術研究開端。然而在此扛鼎之作發表的20年前,戰時兒童問題已經在《廣西婦女》的傳播界面中被討論、實踐和探索著。從這些泛黃的新聞紙中,可以窺見過去與現在的兒童有著迥異的特點以及成人相應的不同對待之道。何以不同? Colin Heywood認為,“童年的確是社會建構物,會隨著時間而改變,而且在不同社會中的不同社會階層與種族團體也會有不同的童年概念。”[1]若延續社會建構觀,精英女性們將她們的兒童認識通過文字和印刷傳播給廣大女性群體的過程,雖不能完全說明戰時兒童歷史的全貌,但足以讓我們讀出一個時代兒童觀念和文化的側寫。
一、《廣西婦女》戰時“理想”兒童形象的呈現
(一)愛國主義的抗戰“衛士”
《廣西婦女》給予兒童的第一種理想形象是深具愛國主義意識的抗戰“衛士”形象,但他們并不是真的奔赴前線殺敵,而是承擔著宣傳動員大眾、營造統一抗戰氣氛的任務。如《桂林—孩子們的城》一文,描述了兒童在西南抗戰大后方的文化中心桂林市通過各種形式進行抗戰宣傳的情景:
當時桂林市街面上粘貼著各種兒童抗戰標語:“小朋友要學岳飛精忠報國的精神,不要學棄槍賣國投降的行為!”“大拳頭,小拳頭,一齊對準敵人漢奸的頭!”[2]署名為“各個不同名目的兒童團體小學校及青年救亡團體”的標語規劃了兒童學習的“偶像”,要求他們與漢奸樹敵。此外,兒童作為支持抗戰的行動者的“心聲”并非只粘貼在墻面上,還有直接的行動:
一輛宣傳卡車,裝載著二三十位小朋友,他們沿著桂林所有的街道作著流動的汽車播音宣傳,每到一個十字路口,卡車均停下來講演,唱歌,呼口號,唱相聲,打快板,每一場總匯集著二三百個聽眾……最使人感動的,就是在法政街口的地方,當宣傳完后,有一家人家特地買了很多的鞭炮來歡送我們,幾百位聽眾也異手同聲的鼓起熱烈的掌聲,這更鼓起了小宣傳員們戰斗的情緒,他們一點也不感到疲乏。[3]
在《廣西婦女》中呈現的理想兒童是充滿戰斗激情的、具有行動力和影響力的、仇恨敵人的宣傳衛士,并且不知疲乏地完美完成了激勵民眾抗戰的任務。文章還進一步地描述兒童在四月四日兒童節慶祝大會上的一幕,會場上設立主席臺,上面坐著許多由兒童擔任的“小主席”,按照類似于成人會議的流程,兒童的代表進行了一番“成人化”的講話:
大會的總主席——實驗小學的小朋友代表致開會詞:他提出了五點關于怎樣慶祝兒童節的意見:(一)全國小朋友要一致團結起來討伐汪逆偽組織,擁護蔣委員長抗戰到底。(二)小朋友要努力學習,武裝自己的小頭腦,不投降,不妥協。(三)努力幫助政府大人做各種抗戰工作,真正的負起抗戰中小戰士的任務來。(四)小朋友要集體生活及訓練身體。(五)要求政府及大人先生們改變對兒童不正確的認識,及改善教育內容和生活,并且,尤其要改善難童,童工,學徒,流浪兒的生活及教養。[4]
發言者是最典型的理想兒童的代表,年齡的幼小與話語的深度形成一種對比,他的“意見”表現出對于抗戰的認同,并履行呼吁同齡人參與抗戰的責任。抗戰“衛士”還主動弱化節日娛樂性、增強戰斗性。他們慶祝兒童節并非單純暢快地游戲,而是將節日慶典轉變為宣傳抗戰的場域,在“長官和大先生”的在場觀看下,“幾千個”兒童進行集體抗戰認同的強化。而這些行為令《廣西婦女》欣慰和推崇,因為擁有眾多抗戰“衛士”的土地才充滿光明和希望。
(二)“文明化”的兒童
《廣西婦女》對于兒童的期待,除了要他們扮演為抗戰宣傳的衛士,還要求他們順應當時國民政府發起的新生活運動的要求,拋棄不講衛生、粗野頑皮的形象,轉變為一個個具有現代文明觀念、衣著整潔、禮貌得體的孩子。作為廣西婦委會工作成果的證明,“文明化”的孩子最常出現在托兒所和教養院等社會機構中,內部環境及設施充滿干凈整潔的現代化氣息:
宿舍完全是新式的建筑……床鋪一律是架床,可以避免濕氣不生腳氣及瘡疥……澡堂廁所特別講究,澡堂有二十余間,都是新式的,可避免傳染病。廁所分男女各十余間,每日都有公役打掃,都施以石灰□□,且與各室隔□很遠,避免臭□氣蒸……醫藥衛生雖然不怎樣的完備,但也具了雛形……空氣新鮮,陽光充足,為一般大醫院所不及。[5]
被教養機構收容的難童、軍人子女與弟妹們有了許多改變,他們接受了種種規訓,生活變得規律刻板,如“兒童的飲食每日三餐,早晨七時吃粥,正午十二時及下午五時吃飯。”[6]經過訓練,一批衣著整潔、彬彬有禮、落落大方的文明兒童“誕生”了,人們看到這樣令人欣慰的情景:
兒童們一律穿著藍色制□制服,分別在各□位站著,不時向來賓們行敬禮,他們一個個都是精神活潑,笑容滿面的招待來賓……在療養室門口一排坐著幾個病孩,正在曬太陽,看見來賓,便一齊起立行禮。[7]三個四歲的小朋友……很自然地唱出這歌表示歡迎。他們的態度那么大方……大家都圍著他們不肯離開,唱完了歌,隨便的談著像很熟習的朋友一樣。[8]
對致力于促進新生活運動的精英女性而言,改造后的未來國民具有了惹人憐愛的品質。另一方面,《廣西婦女》稱,接受了文明教養的兒童表示自己比起家里更喜歡托兒所,且眾多婦女都想把孩子送到托兒所去。由此,《廣西婦女》驕傲地得出文明教養深受社會大眾歡迎的結論,進一步確立了文明化兒童的正當性。
總而言之,《廣西婦女》展現的兒童活動、兒童聲音和兒童意識,都是緊緊圍繞著新生活運動婦委會的工作職責,精英婦女在媒介中塑造了去異質化的“理想模型”,每一個兒童個體都必須飽含拳拳愛國之心,自覺歸入全民族抗戰的旗幟下,將自身與國家、民族利益捆綁。其二,兒童要接受成人的文明教養,脫離粗俗和不衛生、沒有禮貌的“惡習”。在這個過程中,《廣西婦女》努力形塑一種社會心態——只有將這些愛國符碼和文明印記刻寫到文化基因里的孩子不斷增加,才使成人有望得到安心、進步、欣慰與充滿希望的未來。與此同時,這種社會心態也形塑著兒童所處的生存環境。
由此引發筆者思考,社會上對于兒童的某種認知和對待方式不會憑空出現,是什么刺激了此種觀念的誕生?這些精英婦女的主張反映出的兒童觀念實質又是什么?
二、《廣西婦女》兒童觀之辨析
《廣西婦女》對于“理想兒童”的主張只是一種兒童觀的外顯表像,追溯其本質則要內化到一些理論核心,即這個時代中的精英婦女群體對于兒童觀念是怎樣的:兒童是否有別于成人?為什么要管理兒童?應該如何管理?
在回答上述問題之前,我們必須看到當時的社會背景中存在著三種直接影響兒童觀的動力——愛國情緒、政府推進新生活運動的文明化進程及女性主義思潮,這些社會動力直接影響著精英婦女的兒童觀念,下文具體展開解釋。筆者將《廣西婦女》兒童觀有別于他者的特點歸納如下:
(一)兒童有別于成人,但要激發其潛在的成人性
對于兒童本質的討論,西方存在一種兒童與成人二元對立的解釋,而這種對立被認為是社會建構的結果。如Neil Postman將這種對立歸因于印刷術的誕生,由于印刷術激發了人們的個人主義與對自我的思考,創造了文化人的世界,未具有文字閱讀能力的兒童因此被區隔在成人的秘密世界之外。[9]而Edward Shorter則認為,近代私人婚姻家庭才是構建童年的關鍵,由于中產階級和上流家庭生活的影響,關照兒童成為一種未來的投資,從而使兒童隔離出成人社會。[10]這種兒童被區別對待的現象,直到現在仍被視為是兒童社會地位提高的表現,一直影響到當代兒童的命運。
然而,熊秉真認為中國傳統觀念中,“孩童與成人固可代表社會上兩種不同的身份與角色,但更可能是‘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彼此交融,相互交替,可能始而復周,周而復始的一物之兩面”。[11]中國儒家倫理中的“善端”或“四端”均是起于一種人生觀,即每個嬰兒一出生,就有未成形的“成人”在體內,日后的教養就是為了栽培其內在的成人。而當孩子成長為成人,其心中仍存在著孩子的影子,并不會完全消失,故而中國道家有“復為嬰孩”“返老還童”之說。這種觀點提供另一種視角,即兒童與成人是合而為一的,并不是完全對立的生理概念,只是在不同階段或不同的個體中體現“兒童性”更強,或者“成人性”更強。
回到《廣西婦女》,其雖沒有直接談論兒童與成人區別存無的論述,但可從一些文本進行相關詮釋。首先,與成人相較兒童易受傷害,流離失所的難童和將士子女弟妹要被注意收容和教養,“從各戰區流離轉徙或尚在戰區中呼號待救之兒童,當不在少數,這個工作,正亟須我們去展開,要作為當前的一個中心任務。”[12]
因此,從這個層面上看,兒童是區別于成人需要額外照顧的。但這種照顧僅是提供給他們身體的庇護,精神上則與成人同在。這表現為《廣西婦女》認同加速兒童潛在成人性的出現,戰爭的殘酷、敵人的威脅應直接展露給孩子們而非加以粉飾。不像在電影《美麗人生》(La Vita è bella)中的橋段那樣,身處納粹集中營的父親為了保護兒子的童心,一直欺騙他殘酷的集中營生活只是一場游戲。《廣西婦女》的兒童觀中,并沒有區隔成人于承擔戰爭烽火的一端、使兒童被保護于歲月靜好的另一端。如前文所述,兒童反而被塑造為抗戰宣傳員,兒童節慶祝大會去娛樂化而增強其戰斗性,都是讓兒童直面戰爭、承擔與成人同種責任的體現。在這個層面上,兒童與成人的邊界是模糊的。
(二)兒童管理突出守護國族的功能主義
Philippe Ariès認為,中世紀家庭注重家族的榮耀和延續性,家庭價值高于個人,而現代家庭注重個人主義和隱私,強調個人主義和子女的獨立存在,所以教養目的發生功能性轉變,從家族榮耀為重轉向子女成長為重。[13]傳統中國管理兒童觀念也一直存在功能主義基礎,熊秉真研究認為,傳統中國儒家和理學程朱一派的幼教理想強調子女教育要從幼年就開始,教育是為了維護儒家社會規范,到明清時期則轉變為以考取功名榮耀家族為重。
而在《廣西婦女》的報道中,除了具有愛國和文明化意識的兒童形象被尤為突出,兒童存在的意義也被直接袒露。“新時代的兒童,在中華民國是太寶貴,太偉大了……新時代的兒童們,將會運用他們的聰明智慧,隨著他們年齡的長成,從政治,從經濟,從文化,從任何部門,把他們所有的力量,供獻給民族國家,供獻給人類。”[14]可見,兒童的珍貴在于其身上象征著國族未來的屬性。正是出于守護民族“希望”的初衷,《廣西婦女》強調提高兒童民族意識和整體素質:“要使他們知道,仇人是日本帝國主義,要回到家鄉,要找父母,必須把日本鬼趕出中國領土去,除了以這種民族意識教育之外,還要教以各種技能,使他們將完全教育,以達到有了強健的身體,才能做偉大的事業”[15]那些不參與不重視兒童教養的思想行為等同于損傷民族肌理,如廣西婦委會開辦嬰兒托育所受挫時,她們批駁道,“……顯現出社會人士對于這項重要工作是怎樣的漠視而不肯給予幫助”[16]此外,還強調保障兒童教育是出于安撫前線后方的考量,如“寄語前方的抗戰將士,和戰區的難童父母,你們的兒女,在桂林教養院是的,衣食住教是得到了很好的所在,你們安心殺敵吧……”[17]
可見,《廣西婦女》對兒童形象選擇、兒童象征意義、兒童社會功能、兒童教養作用等方面的論述都基于兒童社會角色的“功能性”,個體的獨特個性基本是不重要的,此種兒童管理觀念凸顯著愛國主義的邏輯和價值觀。
(三)婦女與兒童關系天然緊密,但社會應分擔管理責任
熊秉真認為,中國兒童歷史中的兒童管理呈現“上層到下層”和“私到公”的拓展過程。從宋以后,由于議幼學者不斷,編印教材增多,幼教不斷發展,越來越多的兒童被納入教育體系,接受幼教的兒童從上層階級子弟延伸到工商及中農家庭孩童,“一步步把家庭中重要而一向最固定的成員——幼齡兒童——從私人的領域逐漸脫離出來,成為家庭之外的團體(眾人或社會)或制度(學校或教育)關懷用力的對象。”[18]而傳統兒童管理中,女性不僅負責生育,也承擔家庭中一定的教養責任。很多中國士人都有識字之母課兒的經歷,他們入私塾后,母親繼續負責幼教的加強和輔助,如放學之后督促晚讀。
而《廣西婦女》則延續了兒童管理由家庭氏族向社會公共轉移之趨勢。戰爭環境中,許多家庭支離破碎,兒童原本的家庭教養無法維持,父母難以充當兒童的第一管教人,這些流離失所的孩子的管教職責轉移到教養機構,政府又進行賦予管教權力的確認。與此同時,婦女充當兒童管教的角色又呈現新的特征。首先,傳統觀念中婦女與兒童之間的緊密關系仍天然存在。如《戰時婦女工作與兒童問題》一文稱,由于母親比父親更為體貼、細膩、周到,兒童更信任和親近母親,“婦女與兒童的關系實在比男子對兒童的關系要密切得多”[19],但正因為婦女對于兒童的影響非常大,如果母親的知識水平和素質不高,就會阻礙孩子提升個人素質及參與抗戰救亡運動。
另一方面,婦女也被要求從兒童教養中解放出來,相對稀釋對兒童的管教權力。背后的現實矛盾是,由于要擔負兒童的教養責任,戰時婦女無法全身心參加服務工作。但在愛國主義情緒的主導下,精英婦女期待廣大女性作為社會服務和后方抗戰的有生力量,減少母職而投入社會領域。因此,《廣西婦女》非常支持和期待建設保育院、托兒所、教養院等公共機構,分擔傳統母職。
筆者認為此觀念與該時期女性主義思想的引進有關。如《廣西婦女》刊登了柯侖泰《新婦女論》的書評,文章認為蘇聯已經消除對婦女的一切不平等的道德觀念,蘇聯的托兒所制度是值得借鑒的。“婦女獲得勞動的權利,還要將婦女從為社會生育孩子的任務中解放,就要將母性的煩累,從婦女轉移到集團,子女的保育、教育由家庭轉向社會”[20]可見,西方女性主義將女性從兒童管理中解放的理念也被《廣西婦女》征用,成為宣揚其兒童管理設想的一種有力佐證和思想來源。
三、小結
本文的研究源于兒童文化研究中的一個面向,即相信兒童和成人相處之道是多元的,看待兒童“較合理的做法是將不同社會不同團體的童年文化史主題扯在一起,呈現它們合縱連橫的狀況,維持一種童年變幻莫測的社會建構形式”[21]由此,筆者通過婦女報刊對中國近代戰時兒童文化細部進行了一次探索,發現《廣西婦女》致力于建構愛國救亡、投身抗戰、文明有禮的戰時兒童形象,這些在文本中的兒童沒有當代孩子的天真浪漫,而是與成人一樣面對戰爭的殘酷、充滿對敵人及汪偽的怒火。由此可見《廣西婦女》所代表的精英女性的兒童觀念:她們認為兒童在生理上區別于成人,需要額外地教養和保護,某種程度上要區別對待,但又希望他們像成人一樣地抗戰;她們對兒童教養的重視,是出自兒童身上的抗戰力量,出自兒童作為文明化國民的未來希望,而非兒童本身就是可敬的生命和個體;她們承認婦女與兒童的天然母子情誼,但又覺得二者傳統上的教養捆綁關系既耽誤兒童成長又影響婦女投身社會服務,于是提出成人對兒童教化應從家庭轉移到社會機構,鼓勵女性從傳統母職中解放,投身社會工作和抗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