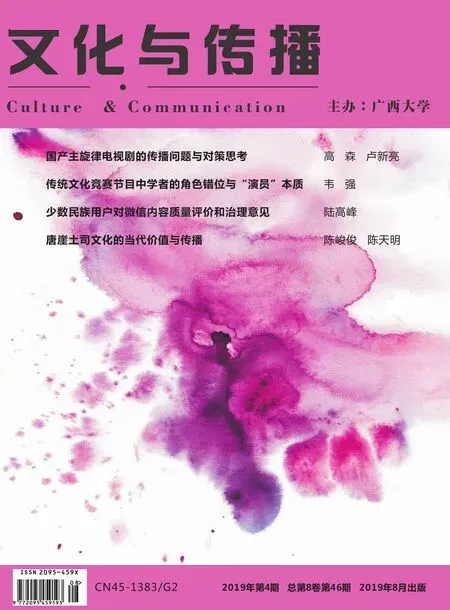宗璞《紅豆》新論
——從《北歸記》反觀《紅豆》創作成敗
張 磊
十多年前,有人發問,《紅豆》“今天續寫,該如何續寫?”[1]這一期盼如今成為現實,耄耋之年的宗璞先生在“南渡”“東藏”之后,歷經血與火考驗的“西征”,終于“北歸”,回到生養她的燕園,創作出《北歸記》。細讀《北歸記》,我們發現《北歸記》與《紅豆》某種程度的聯系,甚至可以說《北歸記》是宗璞先生對《紅豆》的重寫。《紅豆》是宗璞的成名作,也是她早期代表性作品,《紅豆》一問世,便引起較大的爭議。時隔半個多世紀,我們將《紅豆》與宗璞先生最近出版的《北歸記》對照來讀,能更準確地把握《紅豆》創作的成敗。
一、《紅豆》與《北歸記》的關系
《紅豆》是宗璞先生的一篇短篇小說,創作于“雙百”方針提出之后,發表于1957年《人民文學》第7期。《北歸記》是宗璞先生《野葫蘆引》第四部,部分章節載于《人民文學》2017年第12期。兩部作品相隔六十年,細讀兩部作品的文本,我們有一個有趣的發現,《紅豆》中的人物關系和事件在《北歸記》中都能找到對應的影子,兩部小說在一些細節上簡直是如出一轍。
1.主題相似
關于《紅豆》的主題,“謝冕同志認為‘紅豆’就是一段戀愛往事的追述。”[2]而另有人反駁道,“作品并不單純是寫一個戀愛故事,而是企圖通過江玫和齊虹的戀愛事件,表現青年知識分子怎樣經歷著曲折痛苦的道路走向革命。”[3]這兩種觀點具有很強的代表性,不過很多年后,宗璞特意指出她創作《紅豆》的初衷:“在我們的人生道路上,不斷地出現十字路口,需要無比慎重,無比勇敢,需要以斬斷萬縷情絲的獻身精神,一次次做出抉擇。祖國、革命和愛情、家庭的取舍、新我和舊我的決裂,種種搏斗都是在自身的血肉之中進行,當然十分痛苦。”[4]宗璞的這一說法在《紅豆》文本中也得到證實,小說講述的便是青年女大學生江枚人生的抉擇,她是追隨愛情和齊虹一起離開祖國去美國留學,還是留下來踩著父親的腳印,建設全新的中國?經過一番痛苦的內心掙扎,江枚最終決定拋棄了愛情選擇革命。《北歸記》也寫了一個關于人生十字路口抉擇的故事,抗戰勝利后明侖大學師生北歸,回到北平,他們都面臨著兩種命運的抉擇。明侖大學的校長秦巽衡為了“向國府做一個交代”[5],不得不離開他終身為之奮斗的明侖大學;孟樾為了尋得一張安靜下來能做學問的書桌,毅然拒絕南京政府的邀請,留下來守衛明侖大學,等待新的歷史時刻的到來;嵋為了照顧年老的父親,放棄與未婚夫在美國團聚的機會,留下來迎接新的生活……可見,兩部小說的主題在某種程度上是相似。
2.人物和情節相似
作為一篇短篇小說,《紅豆》篇幅較短,情節較為簡單,明線是江枚與齊虹的愛情,暗線是江枚參加進步活動,成為一名革命工作者。小說中兩條線索相互交織,相互凸顯,最終革命戰勝愛情成為主線。《紅豆》的人物關系也較為單純,主要有四個人物,江枚、齊虹、肖素以及江枚的母親,以及未及露面的江枚的父親。小說以江枚視角展開,江枚是一位具有小資產階級情調的女大學生,齊虹是江枚的戀人,是革命線索的對立物,是資產階級代表性人物符號的象征,是江枚前進的絆腳石;肖素是江枚的室友,也是江枚革命路上的引路人,是進步符號的象征;而江母則是一枚籌碼符號,江母站在哪邊,江枚的天平就會傾向哪邊;而未曾出場的江父無疑是壓死駱駝的那最后一棵稻草,他莫名其妙的死因促使江枚做出人生命運的抉擇,舍棄愛情留下參加革命工作。
《北歸記》雖然是一部長篇小說,但情節較為單純,它繼承了“野葫蘆引”前三部的基本線索,寫抗日戰爭勝利后,孟樾一家及明侖大學師生北歸后的生活。小說由孟樾這一代知識分子轉向嵋、弦子和莊無因等伴隨著抗戰成長起來的新一代知識分子身上,重點刻畫他們面臨人生兩種命運前途的抉擇。《北歸記》人物眾多,但宗璞以嵋為中心,通過嵋的視角,將讀者帶入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末北平即將解放大背景,詳細地敘述了蕓蕓眾生的心態和選擇。圍繞著嵋,宗璞講述了一個與《紅豆》類似的愛情故事,嵋放棄了與未婚夫莊無因出國團聚的留學機會,留下來照顧年邁的父親,迎接新的生活。相對《紅豆》,《北歸記》視野更為開闊,人物眾多,關系也更為復雜,但《紅豆》中的人物都能在《北歸記》一一找到對應物符號。江枚對應的是孟嵋(即孟靈己),齊虹對應的是莊無因,革命的引路人肖素轉換到《北歸記》中成了眾多的人物群像,如嵋亦師亦友的晏不來,嵋同宿舍好友季雅嫻,江母則轉化成嵋的父親孟樾,江父的失蹤更是源自宗璞父親馮友蘭的一段人生經歷。1934年11月,馮友蘭從蘇聯和歐洲歸來,被國民政府的秘密警察以莫須有的罪名逮捕,然后不做任何解釋無罪釋放。馮友蘭的這一人生經歷在宗璞的《野葫蘆引》中,演繹為孟樾因為幾篇宋史文章,被國民黨當局莫名其妙的逮捕又無緣無故的釋放。兩組人物在性格上亦非常相似,江枚和孟嵋都是天真活潑可愛的女大學生,愛好文學,喜歡音樂,傾向進步力量;齊虹和莊無因都是高冷的大帥哥,而且不怎么關心政治,都沉靜在自己的物理世界中;肖素和晏不來以及季雅嫻傾向革命,向周圍的朋友和同學宣傳進步思想,秘密參加革命工作;江母和孟父都屬于謹慎小心之人,但他們都同情革命。兩部小說還有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女主人公名字都帶有“Mei”的字(這是作家有意為之,還是有什么外在原因?),而且都是單親家庭(《紅豆》中江父失蹤,未及露面;《北歸記》前幾章寫到孟母,但后來因病去世。)。
不過,相比《紅豆》,《北歸記》容量更大,視野更開闊,立場更客觀,為我們全方位、立體地展示了中國兩種前途交替時的時代背景,眾多的人物在大時代變化時復雜的心態和對人生命運的選擇。在某種程度上說,《紅豆》是《北歸記》的一個片段,《北歸記》是在《紅豆》的基礎上進行了擴寫和適當的改寫。
二、從《北歸記》反觀《紅豆》創作的成敗
《紅豆》和《北歸記》主題相似,人物和情節也較為相似,如果我們現在將《北歸記》作為參照物,《北歸記》就像一面鏡子,反射出《紅豆》創作的成敗。
1.主題先行,功利性較強
宗璞創作《紅豆》時僅二十八歲,處于人生的青年階段。青年人感情充沛,充滿激情,但功利性較強。《紅豆》感情真摯,激情四溢,帶著一股淡淡的憂傷,同時也殘留著宗璞本人生活的影子。仔細考查宗璞的所有作品,她小說中的女主人公在很多方面與宗璞經歷和思想狀況有著驚人的相似,特別是大時代交替時個人的遭遇。抗日戰爭勝利至北平和平解放這段生活對于當時處于青春期的宗璞影響深遠,她先后二次以這段生活為背景,創作了《紅豆》和《北歸記》,可見這段生活在宗璞內心里留下的印跡。宗璞一家在大時代交替之際,選擇留下來迎接新生活,她的父親馮友蘭還受命于危難之際,作為清華大學校務委員會主席,維持清華大學秩序,等待著新政府的接收。然而作為從國民黨統治下走出來的知識分子,馮友蘭仍然“用舊經驗了解當時的新事物”,“反應也必然是錯誤的”[6],與新政權必然產生隔膜,所以馮友蘭以“言論行動錯誤實多”為理由,“請辭去一切職務”[7],馮友蘭一家也因此從清華大學的權利中心走向邊緣。如果說這些對于生性淡泊的馮家人來說,微不足道,影響甚微。但在隨后的歷次批判中,馮友蘭作為資產階級唯心主義哲學的學術代理人,不斷地受到批判和斗爭,成了宗璞一家人的噩夢。在宗璞的記憶中,“三十多年來,從我的青年時代起,耳聞目睹,全是對我父親的批判。父親自己,無日不在檢討。家庭對于我,像是一座大山壓在頭頂,怎么也逃不掉的。”[8]馮友蘭個人遭遇對于一直深愛著父親的宗璞來說影響肯定是巨大的,宗璞急于想改變當時一家人所處的尷尬地位,她想用小說贊美新生的政權,好為自己和家庭正名,表明對新生活的態度。豈止只有宗璞這樣做?當年很多作家紛紛發文表達對新政權的擁護,如胡風創作了《時間開始了!》,向新生活獻禮;郭沫若創作了一百零一首“百花詩”,以示對“雙百”方針的贊賞與擁護。因此,宗璞創作《紅豆》有一定功利性,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另外,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提出后,當時的政治環境相對較為寬松,文學創作上也涌現出一股反映人性思潮的作品,相繼出現了劉賓雁的《在橋梁工地上》、流沙河的《草木篇》、鄧友梅的《在懸崖上》等作品。受此精神鼓舞,宗璞嘗試著用宏大敘事和階級分析的方法講述了一個極具個人話語特色的小說《紅豆》,作為其在新生活的亮相。這部小說具有一定的功利性,主題先行。“當初確實是想寫一個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怎樣在斗爭中成長,而且她所經歷的不只是思想的變化,還有尖銳的感情上的斗爭,是有意要描寫江玫的感情的深厚,覺得愈是這樣從難以自拔的境地中拔出來,也就愈能說明拯救她的黨的力量之偉大”。[9]這雖是宗璞在非常時期的被迫表態,但時隔多年宗璞仍重申,“那時候信仰是很真誠的,尤其在年輕人的心目中。不止是年輕人,像我父親,我的父兄輩,他們在思想改造的過程中,都是很真誠的。”[10]可見這一表態并不完全是違心,應該是作家發自內心的真實想法。這一點在宗璞《紅豆》小說文本中也得到驗證,作家將女主人公江枚置身于兩種命運的抉擇中,即在愛情與革命之間做二選一的抉擇,江枚理智戰勝情感,決定與齊虹分手,留下來參加革命工作。這樣類似的選擇在《北歸記》中也多次出現,但宗璞淡化了革命因素,突出愛情,還把這種選擇與信仰和追求聯系起來。宗璞在六十年前因為主題先行,不得不讓江枚放棄那段至死不悔的感情,而在六十年后的再創作,宗璞聽憑心的召喚,讓她筆下的女性選擇了愛情,并為愛情走向革命。為什么會出現這兩種截然不同的選擇,顯然是受那個時代氛圍影響,主題先行導致的結果。
另外,為了讓江枚的選擇變得合情合理,作者嘗試著用階級分析的方法,人為地將江枚和齊虹設計為兩個對立的階級,江枚為具有小資產階級情調的革命工作者,而齊虹則為資產階級的大少爺,兩個階級水火不相容,矛盾不可調和,歷史趨勢是無產階級必定取代資產階級,作家也是依據這一趨勢,將齊虹塑造成頹廢、脾氣暴躁沒落的人物,江枚與齊虹分手,也就符合歷史發展趨勢。而《北歸記》,宗璞抱著如果不寫,“總覺得對不起那一段歷史,對不起書中人物”[11],“寫下去是我的職責”[12]的使命感,不再持有階級論,而是強調一種人本情懷,試圖還原歷史的本相,人與人之間也變得也相對單純和簡單,上至大學教授,下至販夫走卒,在人格上都是平等。所以,衛葑和凌雪妍以及弦子雖然家庭出生不同,但也能相愛,生活在一起。
2.敘述分裂
由于家庭出身的緣故,宗璞有一股強烈的“原罪”感,她急于想獲得一種身份認同,以修復因家庭出生與主流話語之間的裂痕。“她倉促地將愛情與革命設置為尖銳的對立狀態,以期完成身份的救贖……想在思想上改造自己的急切、為自己的身份正名的焦慮,體現在文本之中的是先行的時代主題與壓抑的個體話語之間的矛盾與沖突。”[13]那個時代創作要求寫重大題材,寫工農兵生活,走大眾化路線。而這種創作方向恰是宗璞的軟肋,宗璞的創作視野相對比較狹窄,她聚焦于知識分子的愛恨情仇和人性魅力,寫他們人生的抉擇。這顯然與那個時代創作要求相矛盾,體現在《紅豆》中,“主觀意圖和客觀效果不一致,想要達到的和實際達到的有很大距離,甚至是背道而馳的”[14],使小說敘述呈分裂狀態。《紅豆》有兩套敘述話語,一是表現民族和革命的宏大敘述話語。革命者肖素引導女大學生江枚參與學生運動,參加革命活動,最后肖素被捕,江枚全身心的投入革命懷抱,成為一名革命工作者。這是作家主觀上想表現的敘述主線;二是表現個人情感生活的私人話語,敘述江枚與齊虹的感情糾葛。這是作家主觀上想表達的敘述副線。宗璞用宏大的革命敘事取代個體敘事,用革命情懷取代個體情感,然而宗璞的意圖最終無法實現,客觀上主線和副線顛倒,敘述分裂。
之所以出現這種敘事分裂,是因為宗璞很多作品都有她個人的生活影子。她無意識間將自己的經歷和思想投射到作品人物身上。宗璞青春期那段經歷對她影響太深了,甚至至死不忘那段生活經歷,正如《紅豆》中江枚對齊虹的感情一般,“忘掉他——忘掉他——我死了,就自然會忘掉。”[15]“對于宗璞來說,她性別身份的有效范圍很窄,似乎只限于個體的情感生活,性別經驗產生的范圍也集中于情感生活。”[16]這似乎有一定道理,敘述生死不渝勿忘我的愛情是宗璞小說的一個母題,如《長相思》,秦宓與魏清書因大洋阻隔,四十年長相思;如《朱顏長好》,林慧亞因戀人琦滯留大洋彼岸求學,終身難以相見。這種難以割舍的感情可以說是《紅豆》中江枚與齊虹感情的延續,但這種情感也只能在新時期書寫,《紅豆》是萬萬不能直抒胸臆的,所以宗璞設置一條革命線索,讓江枚最后走向革命。宗璞的意圖是用革命敘述主導情愛敘述,讓革命線索成為小說的主線,但由于宗璞那份情還是無意識地釋放在小說文本中,導致敘述的分裂。
3.概念化敘述
宗璞曾說過,“戴錦華說我是“本色”作家,我覺得挺對,從我開始寫這篇作品(指《紅豆》),就不是自己給自己規定一個什么原則,只是很自然的,我要寫我自己想寫的東西,不寫授命或勉強圖解的作品。”[17]這一說法不免有點片面,任何作家的創作都受制于他所生活的時代,都無法逃脫他所生活那個時代對于個體的桎梏,宗璞也不例外,她有時不得不寫自己不想寫的東西,創作按照那個時代意圖“勉強圖解的作品”,如《桃園女兒嫁窩谷》,這是宗璞的一篇另類作品,寫的不是知識分子題材,而是農村題材,宗璞本人甚至不愿意將這篇小說收入她的《風廬短篇小說集》。主要原因是“一方面是它當時要表現的是社會主義改造,覺得這種思想和現在不大對頭,另外一方面覺得它和我大部分創作好像是兩回事:我忽然寫起農村來了”,追本溯源“主要是思想改造的產物”[18],這篇小說深深地打上那個時代烙印。
《紅豆》是宗璞特殊年代的產物,難免留有那個時代的印跡,即概念化敘述。概念化敘述表現之一是只有武斷的結論,缺乏形象的敘述。小說一般是通過人物形象的刻畫,或者對完整事件的敘述,來表現一定的社會生活,而不是以片面的結論或者概念化的論斷堆砌,得出一個概念化的主題。一部優秀的小說即使出現了論斷和結論,也是對人物的行為和事件具體敘述中,自然而然得出的結論。《紅豆》有很多概念化的論斷,沒有敘述,沒有佐證,沒有旁證,也沒有因果來源。如,江枚從練琴室出來,在路上偶遇齊虹,回到宿舍躺在床上的江枚,陷入遐想。而就在這時,作家突然寫道,“她非常嫌惡那些做官的和有錢的人”[19],按照正常的邏輯,下面作家應該敘述江枚為什么會“嫌惡那些做官的和有錢的人”?然而作家沒有做任何交代,這倒顯得江枚是一個仇富恨官的偏激狹隘的人。又如,正在和江枚親密接觸、濃情蜜語的齊虹,突然毫無征兆地說,“那我真愿意!我恨人類!只除了你!”[20]一個生活在福窩子里的資本家的大少爺,要風得風要雨得雨,他干嘛要“恨人類”,總得給一個具體的理由吧?甚至江枚也反問齊虹,“我只是奇怪,你怎么能恨——”[21]可惜,作家什么原因也沒說。還有,江枚與齊虹爭吵后,小說寫道,“就在這個時候,江枚也一天天明白了許多事。她知道少數人剝削多數人的制度該被打倒。[22]”江枚怎么“一天天明白了許多事”?她是親身親歷弄明白的,還是從肖素推薦給她的那幾本書上面知道的?這些小說沒交代,這些話本來也是那個時代的套話和口號。《紅豆》類似的概念化敘述還有很多處,這里就不一一列舉了。
《紅豆》概念化敘述表現之二是對齊虹形象的塑造上。小說一進入江枚的回憶中,齊虹便出現在讀者眼前:“他有著一張清秀的象牙色的臉,輪廓分明,長長的眼睛,有一種迷惘的做夢的神氣。”[23]兩個人可以說一見鐘情,江枚還因為齊虹沒能夠看自己一眼,而感到“很遺憾”。齊虹看起來有點高冷,在自己所學的物理領域有很深的專業造詣,而且愛好音樂,特別擅長彈鋼琴,又具有淵博的文史知識。可是在江枚接受肖素灌輸的幾天革命思想后,齊紅則在很多短時間內“從一個有人文主義涵養的風度翩翩的年輕人轉型成為一個死守愛情、甚至于有點不近人情的男人。”[24]齊虹的性格前后有明顯的分裂,“從敘事后果看,作者似在迎合某種具有威懾力的、左翼文學成規背后的政治觀念,這種觀念實際上就是階級出身決定論”[25],這也是因為作家主題先行所決定的。作家一方面寫竭力寫齊虹具有“做夢似的”氣質,寫江枚是如何愛齊虹,另一方面又不斷地抹黑齊虹。齊虹到江枚宿舍看望江枚,得知江枚去參加游行示威,暴跳如雷,不僅砸碎了門房的玻璃窗,還扔掉了帶給江枚的禮物,齊虹簡直是毫不講道理的暴君。這些還不夠,作家還讓肖素站出來直接指責齊虹,罵“齊虹的靈魂深處是自私殘暴和野蠻”[26],說他“真是自私自利的人,什么都不能讓他關心”[27]。從小說創作的角度上看,肖素在自己室友江枚面前妄自評價江枚的男友,她應該用具體的事實來向江枚證實齊虹是一個“自私自利的人”,而肖素好像根本沒有用事實向江枚證明齊虹的為人,僅僅在口頭上泛泛地非議了一番齊虹,可以說肖素簡直在污蔑齊虹。不過,《北歸記》中的莊無因性格較為統一,他雖然外表顯得高冷,不愛說話,但溫文爾雅,至始自終內心里愛著嵋,而且心懷愛國之志,主張科學救國,形象正面,性格完整。
如果齊虹真的像肖素認為的那樣“自私殘暴和野蠻”的人,他怎可能冒著危險一直留在北平等待江枚回心轉意,與他一起出國留學?直到解放軍快要進入北平城,他才不得不乘機離開。臨行前,他還試圖說服江枚和他一起走,甚至萌發了搶江枚一起走的打算。有意思的是在《北歸記》中,莊無因留學和嵋分手之際,也產生了搶嵋一起走的想法。“莊無因道,‘我想把你抱上車,和我一起走。’嵋喃喃道,‘我想你和我一同回去’。”[28]同樣的情景,在宗璞不同時期的兩部作品中再現,而宗璞的寫法卻迥異,齊虹殘暴自私,莊無因脈脈含情,兩者差異巨大,完全是因為宗璞創作《紅豆》是受到那個時代創作上公式化概念化的影響。宗璞在刻畫齊虹形象時存在概念化簡單化問題,齊虹的形象“不僅不豐滿,還有人為丑化之嫌。”[29]
三、小結
《紅豆》是特殊年代的產物,與《北歸記》相比,《紅豆》被打上深深的時代烙印,如創作上主題先行,敘述分裂,且存在概念化等問題。但我們不能因此否定《紅豆》存在的價值和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它價值在于寫了一段至死不悔的愛情,寫了愛情的甜蜜和多變性;與同時代的其它作品相比,《紅豆》相對來說較少受公式化概念化寫作的影響,且游離了當時的創作規范,寫出了人性的復雜性和社會的多樣性;與“百花文學”相比,《紅豆》更有深度,更有生命力,《紅豆》中的愛情也一波三折,讀起來讓人唏噓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