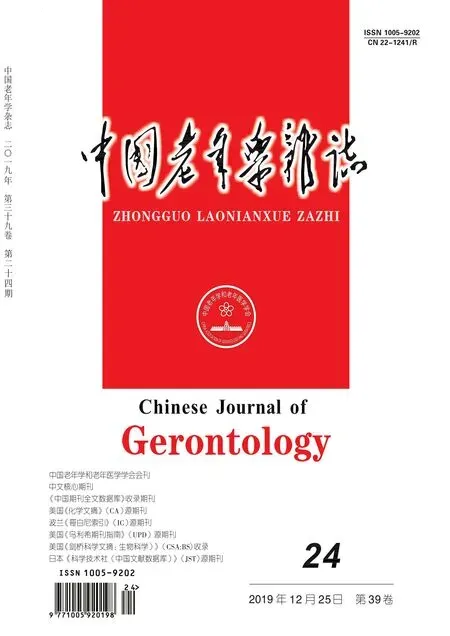大黃-桃仁藥對及其類方現(xiàn)代藥學研究和臨床應用
樂音子 曾莉 顏帥,
(1蘇州市中醫(yī)醫(yī)院,江蘇 蘇州 215009;2南京中醫(yī)藥大學)
大黃-桃仁是著名的活血藥對,經(jīng)常同時出現(xiàn)在外科活血化瘀方中,始于張仲景《傷寒論》的抵擋湯、抵當丸與桃核承氣湯,還常見于《金匱要略》中的鱉甲煎丸、大黃庶蟲丸、大黃牡丹湯、下熱血湯,二藥配伍,剛?cè)嵯酀幧倭#瑢H胙郑沧嗥蒲e、下瘀血之功,常用于治療瘀熱互結的各種病證〔1〕。現(xiàn)代研究表明大黃中主要含有蒽醌類、酚類、鞣質(zhì)類、氨基酸、多糖類等多種成分,其中蒽醌和鞣質(zhì)類成分的生物活性顯著〔2,3〕。基于大黃-桃仁藥對在外科臨床的廣泛應用,本文從藥理學角度對近年來該藥對及其復方制劑的臨床應用進行系統(tǒng)歸納整理,以擴大大黃-桃仁藥對在外科臨床的適用范圍,同時奠定該藥對治療外科臨床急腹癥的理論研究基礎。
1 大黃-桃仁配伍后的有效成分
大黃-桃仁藥對配伍使用歷史悠久,二者功效隨其配伍比例不同而有所差異,顏永剛等〔4〕研究大黃-桃仁藥對不同配比對大黃中10 種成分〔大黃酚-1-O-葡萄糖苷、大黃素-8-O-葡萄糖苷、蘆薈大黃素、大黃酸、大黃素、大黃酚、大黃素甲醚、沒食子酸、(+)-兒茶素和番瀉苷B〕提取量的影響,與大黃對照組(大黃-桃仁1∶0)比較,大黃-桃仁藥對不同配比的(5∶1、5∶2、3∶2)樣品中隨著桃仁比例的升高,大黃中10 種成分提取量逐漸減低;而在大黃-桃仁配伍比例為1∶1時,樣品中大黃的〔大黃酚-1-O-葡萄糖苷、大黃素-8-O-葡萄糖苷、蘆薈大黃素、大黃酸、大黃素、大黃酚、大黃素甲醚、沒食子酸、(+)-兒茶素和番瀉苷B〕提取量達到最低值;進而改變大黃-桃仁配比分別為(2∶3、2∶5、1∶5)時,大黃中的沒食子酸、(+)-兒茶素、大黃酚的提取含量顯著升高,整體變化呈“U”型趨勢。研究認為上述大黃有效成分的變化可能與桃仁含量增加改變?nèi)軇┫到y(tǒng)的酸堿度或極性環(huán)境,其具體作用機制還需更深層次的研究去佐證。
2 大黃-桃仁配伍藥對的研究進展
2.1抗炎、改善微循環(huán) 膿毒癥是創(chuàng)傷、燒傷、休克、感染等臨床危重患者的嚴重并發(fā)癥之一,也是誘發(fā)休克、多器官功能障礙綜合征的重要原因〔5〕。隨著對其發(fā)病機制深入認識,凝血系統(tǒng)作為膿毒癥的發(fā)生關鍵角色被世界范圍內(nèi)專家學者所認同〔6〕。依據(jù)膿毒癥的臨床表現(xiàn)(寒戰(zhàn)、高熱、凝血和神志異常),中醫(yī)學認為膿毒癥應歸屬到“外感熱病”、“傷寒”、“溫病”范疇〔7〕,內(nèi)毒素是引起傷寒、溫病的致病因子。歷代醫(yī)案中常用大黃與桃仁配伍,如張仲景《傷寒論》中的桃核承氣湯等;如劉彥琴〔8〕利用桃仁-大黃活血化瘀之功效,以桃仁承氣湯為主方防治內(nèi)毒素引起的大鼠彌散性血管內(nèi)凝血,發(fā)現(xiàn)加味桃核承氣湯可能通過提高內(nèi)毒素致大鼠血漿抗凝血酶及蛋白C活性,抑制核因子(NF)-κB活化,減少腫瘤壞死因子(TNF)-α分泌從而有效減輕內(nèi)毒素引起的大鼠休克和急性肺損傷,為大黃-桃仁在臨床應用提供可靠的理論依據(jù)。麥藍尹等〔9〕觀察大黃及其分別與枳實、黃連、牡丹、桃仁和甘遂配伍后對小鼠足腫脹的抗炎作用,研究結果表明大黃-桃仁藥對配伍后顯著降低致炎小鼠血清一氧化氮(NO)和丙二醛(MDA)含量,提高其超氧化物歧化酶(SOD)活性;然而與地塞米松組相比較,大黃-桃仁配伍后對小鼠足腫脹度抑制率在五組藥對中最低,分析可能的原因與桃仁水提取物(桃仁多糖)抗炎藥效成分含量低所致,上述研究表明中藥進行配伍后其化學成分、物質(zhì)基礎及藥效作用隨之產(chǎn)生變化,具體機制仍需進一步研究。顏永剛等〔10〕觀察桃仁-大黃藥對脂多糖所致蓄血證大鼠模型,篩選大黃-桃仁藥對的最佳配比大鼠的逐瘀瀉熱作用,研究結果表明大黃-桃仁(1∶1)顯著降低平均體溫、全血黏度和紅細胞聚集指數(shù)及纖維蛋白原(FIB)含量,同時該課題組皮下注射腎上腺素加冰水浴法復制急性寒凝血瘀大鼠模型,大黃-桃仁藥對(2∶3、1∶1、3∶2)均能改善大鼠的全血黏度、血沉、紅細胞聚集指數(shù)、血漿凝血酶原時間、部分活化凝血活酶時間、凝血酶時間、血漿纖維蛋白酶含量等凝血相關指標,以1∶1改善較優(yōu),與上述研究類似,大黃-桃仁藥對逐瘀-瀉熱的作用機制及其有效成分還需要研究。分析大黃-桃仁藥對(1∶1)中的有效成分,發(fā)現(xiàn)三個鞣質(zhì)〔沒食子酸、(+)兒茶素、表兒茶素〕、五個游離蒽醌(蘆薈大黃素、大黃酸、大黃酚、大黃素、大黃素甲醚)及共計8種成分以沒食子酸成分較為明顯。吳瑩等〔11〕采用線栓阻斷法復制右側(cè)大腦中動脈缺血/再灌注損傷模型大鼠,實驗研究表明沒食子酸可縮小缺血再灌注損傷大鼠的腦梗死面積及含水量,增加尼氏小體數(shù)目,降低腦組織中MDA水平,上調(diào)SOD水平改善腦缺血再灌注損傷,其作用機制在于減輕腦組織尼氏小體損傷、抑制神經(jīng)元細胞凋亡及減輕再灌注后腦組織中的氧化應激損傷。
2.2調(diào)節(jié)免疫、抗腫瘤 大黃瀉熱祛瘀;桃仁活血破血,逐瘀通絡;二者相使為伍逐瘀通絡、瀉熱破血功卓;陳艷君等〔12〕以大黃-桃仁藥對為基礎方觀察大黃蟄蟲丸聯(lián)合宮頸癌術后同步化療的近期臨床療效與安全性,比較用藥后治療效果、生存質(zhì)量和免疫功能改善情況及不良反應;研究結果提示大黃蟄蟲丸聯(lián)合宮頸癌術后同步化療有助于提高免疫球蛋白免疫球蛋白(Ig)M、IgG和T淋巴細胞亞群CD3+、CD4+、CD4+/CD8+水平,除此之外,明顯降低T 淋巴細胞亞群CD8+水平,且毒副反應明顯優(yōu)于單純化療組,能夠有效改善術后宮頸癌患者的生存質(zhì)量。
2.3保肝抗纖維化 肝纖維化指肝組織內(nèi)細胞外基質(zhì)成分過度增生與異常沉積,導致肝臟結構或(和)功能異常的病理變化過程〔13〕,就其病因病機及發(fā)病過程,應隸屬于中醫(yī)“肝痹”范疇。劉旭東等〔14〕基于內(nèi)毒素角度在肝纖維化發(fā)生發(fā)展過程中的作用,構建肝纖維化大鼠模型,予以大黃-蟲膠囊(含大黃-桃仁藥對)灌胃,結果發(fā)現(xiàn)大黃-蟲膠囊可顯著降低血清谷丙轉(zhuǎn)氨酶(ALT)、谷草轉(zhuǎn)氨酶(AST)、轉(zhuǎn)化生長因子(TGF)-β1和脂多糖(LPS)水平,首次從抑制內(nèi)毒素血癥角度進一步驗證了大黃-蟲膠囊保肝降酶、利膽退黃的抗纖維化的新的機制,為從內(nèi)毒素角度研究大黃-蟲膠囊抗纖維化機制奠定了基礎。鐘偉超等〔15〕復制酒精性纖維化損傷模型,用大黃-蟲丸進行干預,結合肝組織病理學檢查和肝功能指標,綜合評價大黃-蟲丸對肝纖維化的防治作用,研究表明大黃-蟲丸可能通過調(diào)節(jié)白細胞介素(IL)-6、干擾素(IFN)-γ、TNF-α 和IL-10 等炎癥因子的水平,抑制肝星狀細胞的活化,減輕肝臟的損傷與凋亡改善肝臟的膠原沉淀從而促進肝纖維化恢復。除此之外,針對纖維化天津醫(yī)科大學團隊〔16〕構建2 型糖尿病大鼠模型,采用分子生物學技術探究不同時期抵擋湯(含大黃-桃仁藥對)干預通過對 TGF-β / Smads 轉(zhuǎn)導途徑、CTGF和AngⅡ表達水平的改變情況從而影響血管纖維化的機制。
2.4抗術后粘連性腸梗阻(AIO) AIO是因多種因素(腹部手術、感染、異物)引起的腸管粘連導致腸腔內(nèi)容物滯留腸管,臨床常常表現(xiàn)為腹脹、腹痛、惡心、嘔吐,肛門停止排氣、排便等癥狀,是臨床腹部外科常見的急腹癥〔17〕。40%上的腸梗阻由于術后腹腔粘連引起,其中75%為粘連性小腸梗阻〔18〕。在美國每年執(zhí)行超過 35萬粘連松解手術操作,造成超過96萬天的護理和23億元醫(yī)療費用,影響患者的生活質(zhì)量,給政府帶來沉重的醫(yī)療負擔〔19〕。傳統(tǒng)觀點認為反復發(fā)作的AIO多數(shù)需要通過手術解除梗阻,數(shù)百年對AIO防治有多種方法與策略,但即便是創(chuàng)傷小的腹腔鏡手術亦難逃“手術-梗阻-再手術-再梗阻”的惡性循環(huán)〔20〕。上述直接明確AIO形成機制和防治策略的研究仍需現(xiàn)代專家學者積極探索。中醫(yī)學認為粘連屬于中醫(yī)學“關格”、“腸結”等范疇,早在《醫(yī)貫》已有相關論述:“關者下不得過也,格者上不得而入也。”目前中醫(yī)學認為術后損傷腸絡,滲液為痰,溢血為瘀,痰瘀內(nèi)積,腸腑氣血痞結,壅而為實,通降失和,痛、吐、脹、閉諸證叢生,日久結成有形之物而發(fā)病,其中氣滯血瘀是AIO的病理基礎〔21〕,治療上以活血化瘀、通里攻下、攻補兼施為原則。吳峰等〔22〕臨床觀察發(fā)現(xiàn)口服大黃-桃仁類方(桃核承氣湯)能明顯緩解AIO 患者腹痛、腹脹癥狀,促進胃腸功能恢復,降低白細胞和C反應蛋白(CRP)、TNF-α 水平,加速病情恢復,降低中轉(zhuǎn)手術概率。呂兵兵等〔23〕回顧分析970例粘連性腸梗阻病例均在常規(guī)治療基礎上,給予中藥復方大承氣湯(含大黃-桃仁藥對)胃管注入,其中 618 例患者未行手術治療治愈或好轉(zhuǎn),相關實驗研究表明大承氣湯降低不完全性腸梗阻大鼠模型血漿及小腸組織二胺氧化酶(DAO)、MDA和SOD濃度,減輕細菌移位和內(nèi)毒素吸收,改善小腸黏膜屏障功能防治粘連性腸梗阻〔24,25〕。為預測和辨識大黃-桃仁主要活性成分群及治療粘連性腸梗阻相關的潛在靶點,今后可采用網(wǎng)絡藥理學的方法分析、預測大黃-桃仁的功效物質(zhì)和治療AIO配伍機制。
3 結 語
大黃-桃仁作為臨床常用的活血化瘀類中藥藥對,在臨床不同配比前后的組分差異提示中藥藥對配伍后藥理作用與中藥劑量變化、各組分之間的物理化學反應息息相關。基于超高效液相色譜-三重四級桿串聯(lián)質(zhì)譜(UPLC-TQ-MS/MS)對大黃-桃仁藥對配伍后不同功效進行組分含量變化和藥物代謝動力學實驗研究,為后續(xù)研究大黃-桃仁協(xié)同用藥的合理性的深入提供科學依據(jù)和標準,對明確其物質(zhì)基礎為其臨床有效復方的二次開發(fā)和應用提供了理論支撐,并有利于擴大其臨床應用范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