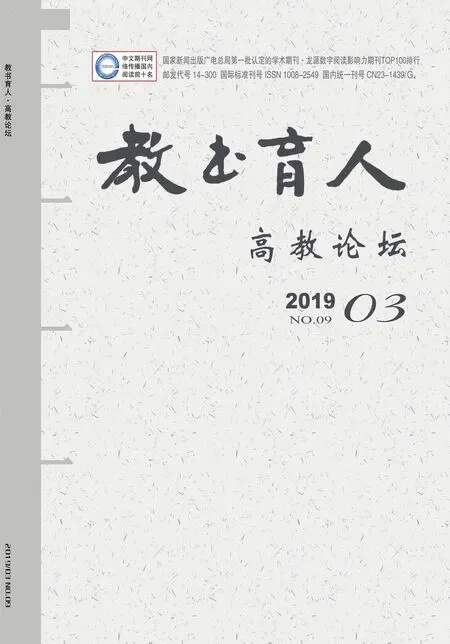教師資格認證國考制度下師范生專業使命感的異化
姜亞洲(紹興文理學院教師教育學院)
一 問題的緣起
在世界范圍內,提高教師質量的重要舉措之一是實施教師資格認證制度,意在在于通過教師資格認證,保證教師在入職之時即具備教育教學要求相關素養和能力。典型如美國,在其教分權制的教育制度下,以州為認證主體,實施多形式多渠道且層次分明的教師資格認證制度,同時開展大量的教師考試研究以提高教師資格認證的效益。2010年后,我國對教師教育的重視程度前所未有,各項改革舉措源源不斷地出臺。順應通過教師資格認證來提高教師質量的國際潮流,我國從2012年起試行教師資格認證全國統考,2015年后則全面實施全國統考,反映了提高教師質量的迫切需求。
長期以來,我國的教師教育由專門的師范院校實施,師范生畢業即直接獲得教師資格證書。自推行教師資格認證國考制度之后,通過教師資格考試成為師范生最重要的學習目標。如何使課程設置更為合理,讓師范生獲得相應的教育教學素養,是師范院校所要考慮的核心問題;對于師范生而言,如何在通過教師資格考試、獲取教師資格證書的同時,使自身的各項能力得到提高是最重要的問題。然而因教師資格認證考試的重要性,師范生在校學習時的專業使命感出現了異化:專業學習轉向片面應試。本文擬探討師范生使命感異化的表征及根源,并嘗試提出解決之道。
二 我國師范生專業使命的演變及其特征
專業使命意味學習本專業時所應承擔的知識和能力發展責任,本文所謂專業使命感,是指大學生在學習本專業時,對自身通過專業學習應達到的專業水平的認知和期許,明確學習本專業時作為專業學習者的所應承擔的角色責任。由此,師范生的專業使命感是師范生在進行教師教育專業學習時,對自己所應達到專業水平的期許和對自身角色責任的認知。
我國專業的師范教育從清朝末年開始舉辦。在效仿日本師范學校的辦法的基礎上,1897年南洋公學創辦師范院開啟先河,其后在京師大學堂中開設“師范館”,正式實施高等師范教育。此時對于師范生的要求主要是糅合了傳統的“以吏為師”的特征,同時吸收了近代西方師范教育的思想。如在師范生的專業要求中更多強調傳統道德方面的內容,認為“師范生為中、小學堂表率之資”。[1]不難看出此時師范生的專業使命主要在于提高自身的道德修養,在學業要求方面并沒有提出有別于其他專業的獨特使命。
1912年之后,我國的師范教育改弦更張,對師范生的專業要求從道德品質擴展為審美、公民責任、教育教學能力以及自學能力等諸多方面。如民國初年教育部頒布的《師范教育令》中規定,師范生須“謹于攝生、勤于體育、富于美感、勇于德行、愛國家、尊法憲、獨立博愛、趨重實際、具高尚志趣、悟施教之方、有自動學習能力”,[2]體現了對師范生將來從事教師職業的專業要求。換言之,在此階段,師范生的專業使命除了成為合格的公民之外,需要具備高尚的品德、高雅的情趣等個人修養,同時應提高自身的教育教學能力和自主學習能力。
新中國成立后,我國頒布了針對各級師范院校的《師范學校規程》,主要特征有兩個:一是強調思想政治教育,二是強調專業知識的系統性學習,之所以具備這兩方面的特征是來自于蘇聯凱洛夫教育思想的影響,即課程設置全為必修,強調專業系統性知識學習,過分強調課程內容與中學課程的對應。[3]在此背景下,師范生的專業使命首先是具有社會主義思想的學習者,其次是學習各科專業知識,這正是“學高為師、身正為范”的理念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體現。
在2010年之后的各項教師教育改革舉措中,有重大意義的是教師專業標準的頒布。教育部于2012年頒布了幼兒園、小學和中學教師專業標準,明確要求“各地各校……要依據《專業標準》調整教師培養方案,編寫教育教學類課程教材,作為教師教育類課程的重要內容”。《專業標準》所規定的“師德為先、學生為本、能力為重、終身學習”四大基本理念,賦予了師范生新的專業使命。簡言之,在當前教師教育改革的大背景下,師范生具有了成為“教育者”“研究者”和“終身學習者”的多重使命。
由此可知,從我國專業的師范教育產生至今日的教師教育改革高潮,師范生作為未來“教育者”的專業使命包含高尚的道德水準和專業的教學能力,且在當下與世界教師教育發展接軌的背景下,作為“教育者”的專業使命被賦予了新的時代內容,師范生所應具有的專業使命感當以促使自己成長為專業的“教育者”為核心。
三 教師資格認證國考制度下師范生專業使命感異化的表征
在各級教師專業標準的指導下,我國的教師質量監控有了依據。由此,教師資格認證理應成為提高教師教育質量的利器。然而,在教師資格認證考試和求職時的入編考試“兩座大山”的重壓之下,師范生的專業學習淪為“應試學習”,為通過教師資格認證考試,師范生將自身成長為“教育者”的專業使命感異化為“應試者”和“教書匠”。通過對Z省和G省兩所師范院校師范生的調查,發現此專業使命感的異化有如下三種表征:
從課程學習來看,師范生根據對應試是否“有用”來進行判斷和抉擇,其結果是對于教師資格考試涉及的課程情有獨鐘,對于增強教師專業意識的課程意興闌珊。目前教師資格考試考核科目按照教師的專業知識與能力結構來劃分,分為綜合素質和教育知識與能力兩類,中學教師則因學科本體性知識的要求而增加學科知識與能力考試,采用紙筆測試和面試相結合的形式。可以說此類考試科目的劃分涵蓋了各級教師專業標準所規定的內容,然而紙筆測試的方式卻使得這些內容由記誦就可掌握。此外很多師范生甚至認為,教師教育課程與“國考”內容接軌應該是教師教育課程改革考慮的重點問題。由此本應在專業學習過程中通過閱讀、討論和研究而增強專業意識的課程逐漸熏陶淪為勉力強記,各類教師資格考試專用教材和培訓班大行其道即是此方面表征最直接的體現。
從能力訓練來看,師范生熱衷于面試所需模擬教學技能的訓練,忽視對教育情境的體悟、教育教學研究等方面能力的提升。教育教學本是一種情境化很強的職業,正如范梅南所言,“教育的本質更主要的是一項規范性的活動”,因此教學不僅僅是“指導技術、組織技巧和診斷能力”,[4]而是通過大量的教育情境觀察和實踐形成自身的實踐性知識。在當前教師資格認證考試中,對師范生的教育教學能力考核通過10分鐘的模擬教學來測試。師范生為了通過教師資格面試,借助技術設備如微格教學等,不斷地進行模擬教學訓練。這種訓練可以提升臨場的表演效果,然而調查結果表明,經過細致預設的模擬教學訓練反而對師范生本人的教學實踐存在負面影響——師范生在教育實習階段親自執教時,過多的預設往往會對課堂教學的順利實施以及所教學生的有效學習造成阻礙。實際上已有研究指出,因為教學技能考核而催生的模擬教學訓練,具有極強的“工具理性”,使師范生成為教學技能的附庸,[5]其必然結果是教學技能表演為主的“教書匠”成為專業使命,傷害了師范生作為未來“教育者”的本體性使命。
從專業理想來看,謀求獲得教師資格證書和通過入編考試成為師范生的專業理想,對作為“教育者”“研究者”和“終身學習者”的專業使命卻有所忽視。如上所述,師范生在課程學習和能力訓練方面都圍繞著應試進行,因而對于從事教師職業的專業理想必然會以應試為基礎。特別是師范生作為“研究者”和“終身學習者”的專業使命,需要通過大量的教育研習能力及自主學習能力的提升來實現,這是以閱讀、討論和課堂觀察等為基礎。在師范生的專業使命感異化為“應試者”的情況下,快速通過考試是最主要的專業使命,在理解學生、促進學生的發展等方面的專業理想則有所削弱。
四 教師資格認證國考制度下師范生專業使命感異化的根源
以上所指出的師范生專業使命感異化的種種表征,反映了當前教師教育的困局。之所以出現如此困局,在文化土壤、制度設計及行動者自身等三方面都有其根源。
在文化土壤方面,通過教師資格認證考試的壓力使應試教育觀念蔓延到大學階段。長期以來,應試教育是我國教育難以根除的痼疾,批判者認為應試教育片面追求學生對學科知識的掌握,其“本質是反教育”。[6]然而應試教育所承擔的社會流動功能及其潛在的社會資源分配功能,使學習即為應試的觀念根深蒂固。本來應試教育是基礎教育階段存在的問題,但在實施教師資格認證國考制度的背景下,因為通過考試的重要性,使得在這一文化土壤上滋長起來的應試觀念蔓延到大學階段,造成了師范生專業使命感的異化。
在制度設計方面,我國的教師資格認證考試缺乏應有的靈活性。教師資格認證的本意是通過考試來鑒定師范生是否具備從教的知識與能力,此鑒定方式本應與師范生的培養過程緊密結合。長期以來我國教師教育模式是通過專門的師范院校實施,學生自入校起就已經選擇了師范專業;而美國德國等西方國家的教師是由綜合性大學培養,學生在大學學習中期才去選擇是否將來從事教職,即便如此,由于其實施的教育分權制,美國的教師資格認證的渠道更多元,方式也更為靈活,證書分類也更多。[7]我國對教師資格認證實行國家統一考試,因其對于從事教職的準入性質,使這一手段會成為衡量師范生學業水平的重要標準,如此師范生的專業使命感形成的基礎是通過教師資格認證考試。
在行動者自身方面,我國師范生自我發展的可能路向比較狹窄。一般來說,師范生的就業去向都是從事教職,因此對師范人才培養質量的考核中,有一項重要的指標就是從教率。而且從入學起就已經確定職業方向的師范教育,在培養過程中塑造了師范生較為清晰的未來工作自我,研究證明,“一個清晰、容易想象的未來工作自我形象才能對未來指向的行為(如主動職業行為)提供目標性指引以及行為驅力。”[8]如此,師范生將自己的學習與未來教職緊密聯系時,通過教師資格考試自然而然地成為其重要使命。
五 師范生專業使命感的回歸之途
要促使師范生的專業使命感由“應試者”和“教書匠”向“教育者”回歸,再構教師教育的價值向度,根據以上分析,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首先,明確教師資格認證考試作為評價方式的準入功能,弱化對教師教育的評鑒功能。雖然通過教師資格考試是教師教育人才培養質量的表現之一,但是此項評價考核的是記誦和表演能力,有礙于師范生形成成為“教育者”的專業使命感,且教師專業標準規定的研究能力和終身學習能力并不能有效鑒定,因此教師資格認證考試只應作為評價教師教育機構是否滿足基本要求的評價手段。教育部于2017年頒布《普通高等學校師范類專業認證實施辦法》,規定“通過第二級認證專業的師范畢業生,可由高校自行組織中小學教師資格考試面試工作……通過第三級認證專業的師范畢業生,可由高校自行組織中小學教師資格考試筆試和面試工作。”[9]解讀文件可知教師資格認證開始由終結性的國考開始轉向形成性的學習過程考核,此方面的肇因已經開始剔除。
其次,開拓多渠道、多層次的教師資格認證。配合師范專業認證工作,對參加教師資格認證考試的非師范考生,應制定修習師范類專業課程的要求,規定其所學的課程與學時,如此才能使其接受師范專業熏陶,在教育教學實踐方面規定最少實踐學時數,同時探尋替代學分的辦法。此外適度增加教師資格證書的級別和時限,以滿足不同地區、不同時段對教師人才的需求,如此即可幫助師范生告別應試,回歸作為“教育者”的專業使命感。
在師范生的未來工作自我方面,滿足師范生自我發展多樣化的需求,準許師范生能夠建立多樣化的未來工作自我,并能在大量師范院校綜合化發展的背景下,為之提供滿足此類需求的課程與教學資源。毋庸諱言,師范教育的目的在于培養卓越教師,但在目前社會向多元化、個體化變遷,師范生在四年的專業成長過程中可能會因個性、家庭以及對社會的認知等因素的影響,改變未來工作自我,教師教育理應有滿足此類生涯發展需求的渠道和資源。如此,在多元選擇背景下最終依然選擇師范專業的學生,必將以成為“教育者”為自身的專業使命,如此師范生的專業使命感即可回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