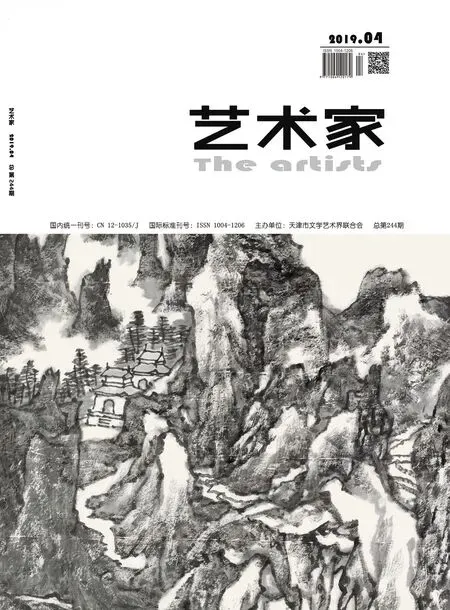淺談當代水墨畫特殊技法的運用
□王 迪 王馨晨 吉林藝術學院
當今社會工藝文化的滲透與影響越來越深入和廣泛,多元化的經濟體制影響著文化上的多元化趨勢,這個各方面都先進的百家爭鳴的時代為中國水墨畫的發展提供了一定的物質與思想基礎。面對多層次的審美要求,人類想要自由翱翔天地的心理態勢不斷增強。隨著文明與科技的進步,人類對過去許多深不可知的事物有了全面的認知,從而獲得了與前人截然不同的感受。為了追求藝術上的真正自由,前人的筆墨技法與傳統的繪畫語言便不能夠表達今天社會的思想情感,所以新的富有個性的語言和表現方法——特殊技法應運而生。
特殊技法的最大特征就是多元、自由。特殊技法的使用使水墨畫材料的特性被徹底釋放出來,“扎染法”的畫面層層變化,其效果有的類似冰裂紋,有的更像是圖案;“縐紙法” 的畫面往往會出現一些意想不到的痕跡,呈現一種特殊的肌理效果,如劉大昌先生就是縐紙皴法畫家;“腐蝕法”“水沖法”常用于寫意中如畫雪景及特殊處理;“紙筋法”的畫面會顯現出一些變化自然的淺白線條,因為是劉國松所創,故又稱“國松紙”;“水拓法” 即唐代范陽山人所創的“墨池法”;“滲透法”的畫面上的痕跡斑斑駁駁宛若山林,頗具意趣;“巧借紋理法”與“實物拓印法”的形式大體相同,都展現了生活中的自然之美,反映了真實物體的紋理樣貌;“撒鹽排遣法”“吸收沉淀法”的畫面上的斑駁痕跡有的像被蟲蛀的葉子,有的則好似所繪物體本身的紋理。特殊技法為水墨畫注入了勃勃生機,在運用新技法創作的作品中,其特性以及所具有的獨特審美感染力,是人們在創作和欣賞藝術作品時所不容忽視的[1]。
在傳統技法中,以“皴法”“墨法”最為基礎。皴法因為在國畫技法中專講畫山石的方法,所以明代汪珂玉也稱其為“皴石法”。皴法的種類有很多,小斧劈皴表現山谷嶄然的石頭山;披麻皴表現土石摻雜、山形渾圓而較少棱角的土石山;馬牙皴多用于大青綠色著色的勾勒山水上;解索皴就像一團糾結的繩頭,表示山的脈絡紋理。皴擦本身具有一種獨立的生命力,充滿豐富生動具體的變化,是繪畫中的一種肌理表現手法。墨法分為干、濕、濃、淡、黑五種,就像音樂擁有不同的音節,墨色也講究層次,濃淡分明,不過墨的音符是靠水來調節的。
隨著文人畫的發展,除了我們所了解的傳統筆墨技法外,也出現許多其他不同的工具和技巧。例如,破墨、潑墨、積墨、宿墨、焦墨等墨法。破墨之說始于南北朝,是對蕭繹的《山水松石格》提出的一種技法,是指對前一種效果加以破壞形成的一種新效果。明代李日華形容王墨所創的潑墨特點是:“潑墨者用筆微妙,不見筆徑如潑出耳。”潑墨法后被近現代畫家張大千繼承并大量運用。積墨效果具有極大地豐富感;宿墨因為失去了新鮮的光彩,在拖裱后還會滲畫出墨圈;焦墨常被拿來提醒畫面死板不精神的地方。另外,還有宋趙希鵠在《洞天新錄》中記載米芾作畫所用工具:“南宮戲墨不專用筆,或以紙筋,或以蔗滓,或以蓮房,皆可為畫,紙不用膠礬,不肯在絹上做。”清方薰在《山靜居畫論》中有:“畫云人皆知烘熳為之,勾勒為之,粉渲為之而已。古人有不著筆處,如見空濛叆叇,蓬勃無際之為妙也。張彥遠以謂畫云未得臻妙,若能沾濕絹素,點綴清粉,從口吹之,謂之吹云。又陳惟寅與王蒙斟酌畫《岱宗密雪圖》,其雪處以粉筆夾小竹彈之,得飛舞之態,仆嘗以意為之,頗有別致。”宋代畫家韓拙的“墨分陰陽”之說以及“水暈墨章”“沒骨”“渲染”“運水”等多種墨法,可見墨的任務是完成明暗起伏關系[2]。
水墨畫在構思、構圖、造型、筆墨、色彩等方面都面臨著革新,對待傳統我們要有發展的眼光,要時刻注意克服“守舊”的弱點。正確的態度是重視、不迷信、敢于創造。創造是時代的要求,也是水墨畫藝術本身的要求。
特殊技法與傳統技法的區別顯而易見。傳統技法講究“骨法用筆”,主張“書畫同筆同法”,要有書法的筆墨味道,作畫要“意在筆先”,落筆之前最終效果在作者心中就已“胸有成竹”。由于在“筆墨”上給予了極大的關注,一般作品的成品都“筆精墨妙”,具有傳統的美感。特殊技法在運用時產生的效果偶然性很大,具有變化多、自由度大的特點,制作手法大幅度地突破了“筆墨”束縛,大有“意在筆后”的韻味。特殊技法效果中的制作之美取代了傳統意義上的“筆精”,但墨、色之奇妙、美妙依舊存在,特殊技法基本可以應對任何藝術表現的需要,這就是蘇東坡所說的“神與萬物交,智與百工通”吧。對于“筆墨”效果而言,特殊技法雕琢痕跡很少“不類人為,宛若天成”,表現出現代人的手筆,具有強烈的現代感,它與物質世界中的許多現象和饒有意味的形式很接近,特殊技法是極其富有天趣的表現形式。特殊技法具有大匠大鑿的品格,運用特技而達到最高境界則可“遺去機巧”而“意冥玄化”,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水墨畫重表現,重主觀感受,帶有很強的感情色彩,當畫家用傳統的筆法表現不出其特有的感情與思想時,就會創造出許多新畫法。藝術要講感情,有真情流露才能流傳下好的作品。畫家的靈感和意境的創造是離不開技巧的表達的。對這些特殊的新技法,有人獨具慧眼給予熱情肯定,也有人將其視若發揚和中國畫的珍寶,更有人嗤之以鼻認為這是歪門邪道。我們借助這些工具創造出來的新技巧并非想炫耀創新的特殊技法比之前有多精妙,也不是想表達繪畫只要注重技巧就可以了,而是要以更有力、更自由、更恰當的手法表達作者的主觀情感。當然,表達作者情感單靠創新技法是不夠的,我們也需要在漫長的學習過程中加強基礎訓練,培養好我們的造型能力、審美與形象思維能力、畫面形式構成與把握整體和諧的能力以及思想修養等多個方面。我們對特殊技法的探索、開拓與創新絕不應為民族虛無主義所左右而愚蠢地割斷歷史,也不應拾西方現代派之牙慧而至西化,西化并不意味著現代化。因為前人使用的技法已不足以表現后世畫家的個人情感和思想,所以為順應歷史發展的潮流創造出的新技巧是時代的必然。凡筆墨不能表達者,必另創技法另辟蹊徑,這就是大滌子所謂的“是皆智得之也”。
結 語
古今中外的每一代人都在為情緒的自省和盡興尋找著恰當的語言。禪宗畫用墨色來表達“無色”的精神;馬蒂斯則寧可被人成為“野獸”也創造著他獨特的“安樂椅”,我們抱著老祖宗留給我們的遺產當然也更不能夜郎自大墨守成規,在這個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年代自然要探索、開拓、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