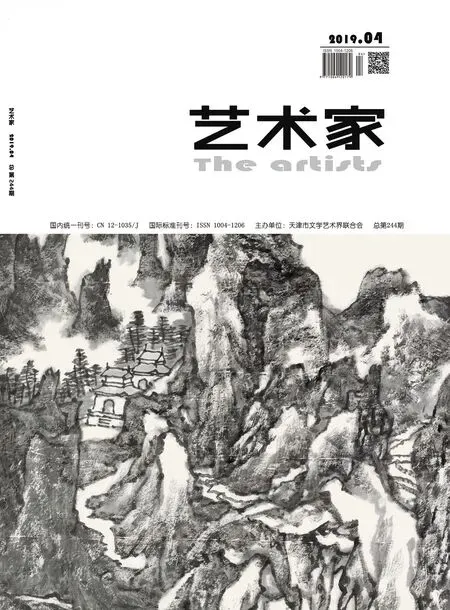弗洛伊德視域下凡·高畫作的藝術真實性及其人文情懷展現
□宋河潤 四川音樂學院
一、弗洛伊德視角下的凡·高個性剖析
弗洛伊德的理論有個前提,即所有藝術家都是精神病患者。大多數精神病患者受困于精神癥的外部表現,如瘋癲或自殺,凡·高就是其中之一。但這個結局不是一開始就確定的,而是如多米諾骨牌一樣,經歷了從口唇期到生命結束全部階段未能被修復的創傷而造成的。但弗洛伊德認為,藝術家與其他受困于精神癥的人不同,他們通過創作藝術作品尋找到了一條重返心智正常和健康的道路,其精神分析學說由心理結構、人格結構和潛意識三個部分組成。
心理結構可以進一步分為意識、潛意識和前意識三個部分。“意識”是人們認識自身和環境、處理日常事務的部分,具有推理、想象和思考功能;“潛意識”是心理活動較深層次的部分,包括人的原始本能和各種欲望,在被壓制后不斷尋找出路;“前意識”則位于前兩者之間,是指沒有被意識注意,但可以回憶起來的經驗。人格結構則分為自我、本我和超我三個部分,凡是被“自我”視作難以接受的東西,都會被“本我”和“超我”的規束下壓抑,然后積淀至無意識領域。弗洛伊德認為,藝術的功用在于使藝術家與受眾受到壓抑的本能、欲望得到“補償”或變相的滿足,藝術具有解決潛意識與意識之間沖突的作用。他在《心理分析導論》中寫道:“我們相信,文明在生活需要的壓力下,以刺激的滿足為代價得到創造;我們相信,文明在相當程度上被不斷重新創造,既然每一個剛剛進入人類社會的個體為了整個社團的利益,一再犧牲這種滿足。[1]”
郁火星對此解讀為:藝術同樣誕生于刺激和文明之間的沖突,表現為調節個人和社會的關系。如果說夢境僅僅表現了潛意識的內部沖突,藝術則將這種沖突提升了一步。因而,藝術研究中的心理分析方法試圖發現作品中偽裝的潛意識欲望,找到隱藏的心理因素。不管藝術作品的表現如何單純和傳統,心理分析方法都將展示隱藏在作品表面下的種種因素。
因為出生在夭折哥哥忌日的那天,凡·高一直蒙受“一個死去孩子的替代品”的陰影。在決心成為畫家前,他涉足過藝術品拍賣,做過職員和老師,還“短暫而尷尬”地擔任過傳教士,卻屢屢不被家庭接受甚至排擠,這使他既懼怕與人交往,又渴望人情溫暖。他對世界的渴望與現實世界的冷漠回應之間產生著劇烈的沖突。他在兩者之間不斷求索,尋找著精神和靈魂的出口,其將一部分矛盾傾注在了色彩濃烈的畫布上,另一部分的矛盾卻始終無法得以安放,最終以悲劇收場。他自己說:“幸運的是,我的心不再渴望任何豐功偉業,所有我在繪畫中想得到的,只是熬過這一生的一種方式。”就弗洛伊德理論而言,個體后期人格發展中的障礙與早期矛盾得不到解決以及早期心靈創傷有直接的關系[2]。
如果以弗洛伊德的理論看藝術本源,柏拉圖所說的理式世界是真實的。藝術作為對模仿理式世界的感性世界的模仿也是真實的。康德所說的“生命本體的沖動”強調了創作主體的重要性,是真實的。亞里士多德認為,藝術家應當“按照事物本來的樣子去模仿”,即藝術創作應表現事物的本質,而非其看上去的樣子,這也是真實的。回到弗洛伊德的理論上,藝術作為潛意識的升華,同樣是真實的。人類意識的表現總是被打上潛意識的標記。
二、凡·高繪畫技法的漫長積淀和對人文情懷的凝視
凡·高并非為印象派而生。事實上,直到1885年4月,他才在給提奧的信中提到,據說有個叫印象派的畫派,但我對它知之甚少。他積淀繪畫技法的時間十分漫長,因為沒有接受正規的學院派教育,其技法和風格也基本是自己探索出來的,參考書包括約翰·馬歇爾的《藝用解剖學》和巴格爾的《木炭畫聯系》。前期畫了大量的素描、鋼筆畫、木炭畫,在經過了一年多素描強化練習后,他才開始接觸油畫和色彩,甚至連調色盤和水彩的用法都是跟安東·莫夫學到的。搬到海牙后,他沉浸于研究不同媒介上的技術細節以及透視、色彩、光線、陰影等,以大量素描練習的底子開始了早期的水彩和油畫創作,學習如米開朗琪羅、丟勒、雷斯達爾、范戈因、卡拉莫等大量名家的繪畫技法和風格。
在練習和嘗試的過程中,凡·高一直保有著自己近乎匠人的藝術觀念:“人必須要經過長期艱苦的努力,才有可能觸碰到藝術的本質……藝術需要不顧一切地執著和持久的觀察。”這期間,他在社交上處于孤立狀態,但卻安之如飴地寫道:“研究畫面透視帶來的樂趣,遠勝于與人交流。”
關于他人文情懷凝視的萌芽,在其1880年7月寫給提奧的信中可以窺見。在其中,他表達了堅持創作的決定:
換羽期對于鳥兒來說,就像人類面對逆境或者不幸一樣。你可以選擇留在痛苦中,也可以由此脫胎換骨,重新做人……如果你能體諒一個人獻身于繪畫研究,就要理解熱愛讀書和熱愛倫勃朗一樣神圣,我甚至認為這兩種熱愛相輔相成。所以你追求的是什么?人的外表是否能反映他的內涵?也有另一種人,盡管他們的內心被強大的渴望所驅使,但現實不可改變,他們無能為力,就像被囚禁了一樣,所處的環境缺乏創造所需的土壤,使他們無所作為。
這封信詮釋了凡·高內心“潛意識”和“意識”的沖突,以及“本我”和“自我”之間的拉扯。他將自己比作換羽期的鳥,“本我”和“潛意識”渴望將“靈魂里的火”釋放出來,但“意識”和“自我”卻如牢籠一般囚禁著自由之精神。這個牢籠還將偏見、誤解、無知、假意的羞恥等感覺相互拉扯。弗洛伊德認為,藝術家的創作也同夢一樣,是無意識欲望在想象中的滿足[3]。對于“三個我”之間不斷求索中的凡·高來說,一定要與自然、土地和在其上勞作的人們緊密相連,“以一種宗教式的熱忱過著農民的生活”,才能為自己的精神找到處所。這自然造成了他對底層民眾入木三分的刻畫,以及富有人文情懷的凝視。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我愿用我的作品來表達一個怪人,一個無名之輩內心的所思所念。”
在海牙居住直到回到父母家中的這段時間,他創作了無數以底層勞動人民為主體的畫作。他畫搶著買彩票的人群,窮困潦倒的人們節衣縮食買彩票,希望獲得拯救。他認為,這種對現實悲慘境遇的反抗非常莊重。他游走在街上觀察拾荒者和從沙丘中刨土豆的人們。他整日待在紡織車間里,畫織布工和紡羊毛的女工。他甚至這樣描述院部護工的妻子:“她看起來無足輕重甚至渺小,這讓我心中涌起了強烈的愿望,來畫著如灰塵覆蓋的微草般的女人。”也許,他對這些底層人物的凝視結果和對自己的期待是一樣的,就算身處困境,人生灰暗,他也不愿意,也不應該被看成一個不幸的人。
三、凡·高畫作中深刻的藝術真實性
凡·高對藝術真實性的探索,印象派以明亮的色調和革命性的技術在巴黎聲名鵲起,這兩件事幾乎是同步發生的。他從那個“教學體系產出的作品單調、死氣沉沉、乏味至極”的安特衛普學院憤而出走,輟學后意外來到巴黎,結識了印象派的核心人物。
在創作《吃土豆的人》時,他盡全力為其注入了生命,認為:“如果把農民肖像按慣例畫得光滑無瑕就不對了。能讓人聞到培根味、煙味、蒸土豆的味,那才絕妙。”隨著他投入的越多,就越覺得農村生活讓人著迷:
“要是我筆下的人物看起來很美,那我倒要絕望了。我才不想讓它們看起來僅僅達到學術上的正確……米勒和萊爾米特才是真正的畫家,他們畫的從來是不是事物原本的樣子,不是經過簡單觀察分析后的客觀事物。他們,米勒、萊爾米特、米開朗琪羅,畫的都是他們感受到的事物。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可以畫出這種不準確,比如偏差、修正或者改變真實,然后讓畫成為一個謊言,這么說也行,但是那一定會比絕對的客觀更公正。”
從弗洛伊德的理論來看,那些“學術上正確”的畫是被壓抑、被社會道德過濾后的表現。而“讓畫成為一個謊言”,改變真實,讓情感和對自然的感受指引繪畫而非照相復刻正是其藝術真實性的表現。在去往法國后,他見到了包括浮世繪在內的多種繪畫風格,更找到了遠“比客觀更公正的”藝術真實性。
結 語
弗洛伊德把藝術既作為本能的升華,又作為對本能的補償,而創作的幻化是由人類共存的幻化性演化而來的,這種精神替代是基于所有人內心所共通的一種情感。也正因如此,凡·高創作的藝術真實性得以映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