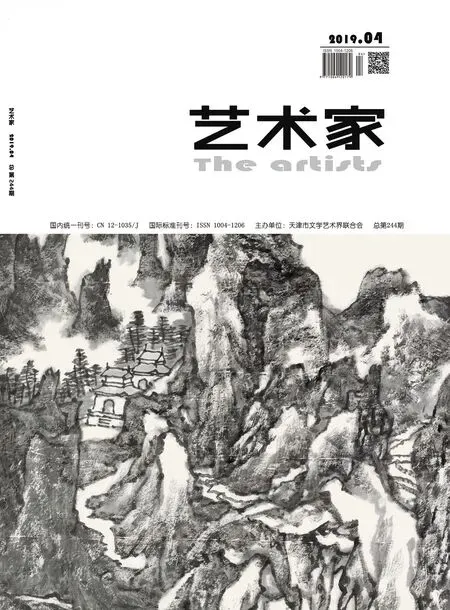盧龍大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中的飛天藝術與唐代莫高窟飛天的淵源
□楊敬依 燕山大學
飛天藝術在現代藝術研究中頗受關注。盧龍陀羅尼經幢中的飛天形象由于年代久遠,且地理位置較為偏遠,所以前人沒有系統地整理過它的藝術形象特點淵源,導致這一形象的歷史淵源項不完整。這造成在未來的修復和保護中容易對原飛天形象的藝術特點造成不必要的損失,因此,將盧龍陀羅尼經幢中的飛天藝術形象的歷史淵源確定化是未來經幢保護中必不可少的工作。
一、盧龍陀羅尼經幢的飛天藝術形象特點
盧龍陀羅尼經幢坐落于盧龍縣城內,因幢體刻有大佛頂尊勝陀羅尼經文而得名大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其高10.35米,上飾蓮瓣,下琢重檐,挑懸角鈴,間鐫飛天。飛天一詞源于佛教,佛教認為飛在天上的神就是飛天。后人將佛教中的天歌神和天樂神合為一體,稱為飛天。此幢飛天紋飾有8個面,每面飛天的上衣下裳、動作扭姿各有不同。經過多年的風雨侵蝕,飛天紋樣略有風化的跡象,導致有的飛天面部的眉眼特征已經模糊,但整體的形態動作仍保存完好。
盧龍陀羅尼經幢的飛天為單個造型,沒有形成連續式構圖,8個飛天都坐在云彩上,身體蜷成C字形,披帛圍繞周身,有的手托蓮花,有的身纏披帛,頭部扭動各有不同。
二、從歷史角度,與敦煌莫高窟飛天的異同
敦煌壁畫初期受西方影響,飛天多裸露上身,后來受本土影響,飛天才漸漸有了上衣。在唐代,飛天面型豐滿圓潤、體態婀娜多姿。這種美具有強烈的時代感,反映了當時人們的審美訴求,展示了大唐盛世下整體的雍容華貴之美,這也成為整個大唐時期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的主要藝術特征,同時說明飛天形象更加本土化,適應本土的審美趣味。
反觀盧龍陀羅尼經幢,據《盧龍縣志》記載:“經幢始建于唐高宗儀鳳元年(676 年)……明萬歷二十八年(1600 年)又經歷了一次大規模的修繕。”這就說明在盧龍陀羅尼經幢創建之初,飛天形象呈現更加本土化的飛天創造特點,同時由于莫高窟的藝術類型較之其他零散的洞窟更為豐富,所以在唐代得到了著重發展,一度成為當時整體藝術風格的標準。所以,盧龍陀羅尼經幢中的飛天從歷史角度來講,受到了當時主要藝術導向的莫高窟飛天的影響。
三、從現在看,與唐敦煌莫高窟飛天的異同
唐代敦煌莫高窟的飛天形象更加追求個性化,初唐時期的飛天刻在龕的兩邊,像是要巡視人間,這種與人間聯系在一起的手法渲染出初唐時期的世俗風格。到了盛唐時期,整體風格的裝飾性更加明顯,飛天大多以蓮花為中心旋轉飛翔,晚唐時期的飛天飛舞時不再排列成隊,而是聚集在一起。其臉型長圓,胸飾瓔珞,上著披巾,下穿長褲。不同于初唐和盛唐時期,晚唐時期的飛天多著半袖緊身衣,同時增加了絡腋。絡腋在《大唐西域記·印度總述》中有描述,指纏繞于腋下的衣著配飾。裙紋流暢、飄逸、貼體,面料同長裙質地,柔軟飄逸,飄帶成水波紋卷曲狀,與長裙飄擺游弋,同披帛交相輝映。
盧龍陀羅尼經幢中的飛天形象的共同特點是臉型較長,略呈“C”形;梳高髻,面部已風化模糊;上身著緊衣,垂墜飾,下著長褲,褲腰外翻,腰帶長垂,身飾披帛,于頭后呈環形,長飄于體側;雙臂外展,左手持蓮花,右手多側舉。由此可以看出,盧龍大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中的飛天形象與唐代莫高窟的飛天在面容、上衣下裳、披帛裝飾類似,可見當時修筑時或有共同的參照體,或以對方為參照體。因莫高窟的飛天具有連續性,飛天形象的轉變隨著年代的變化而變化,而盧龍陀羅尼經幢只有八個立面,且建造時間比莫高窟晚,所以應是參照了唐莫高窟的飛天形象。
四、盧龍飛天特點偏向唐莫高窟的原因
(一)地理原因
唐代莫高窟屬于飛天發展鼎盛的地域,盧龍陀羅尼經幢建造時工匠們不能憑空捏造,莫高窟開鑿于敦煌城東南25公里的鳴沙山東麓的崖壁上,前臨宕泉,東向祁連山,隨著絲綢之路的發展,唐代的莫高窟較其他石窟發展更為鼎盛,故建在晚唐的盧龍經幢應是學習莫高窟的唐風飛天造型。
(二)經濟要素
盧龍的陀羅尼經幢在晚唐屬于永平府境內,永平府西護京師,是連接京城與山海關的要沖地區,自古以來便是兵家必爭之地。永平府古城位于永平府的中心地區,古時就是重要的政治經濟中心,由于經濟較發達,能實時把握藝術形式的演變,所以,建造時便能追隨當下風尚,緊隨莫高窟的唐風。
盧龍縣的大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中的飛天藝術形象源于唐代莫高窟的飛天藝術形象,這不僅使修復經幢飛天有了更具體的參照對象,同時也填補了北方飛天藝術的類型。飛天這一形象在不同地區的表現實際上反映了印度、中亞和中國等不同地區的傳統與特色,為以后的藝術創造性提供了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