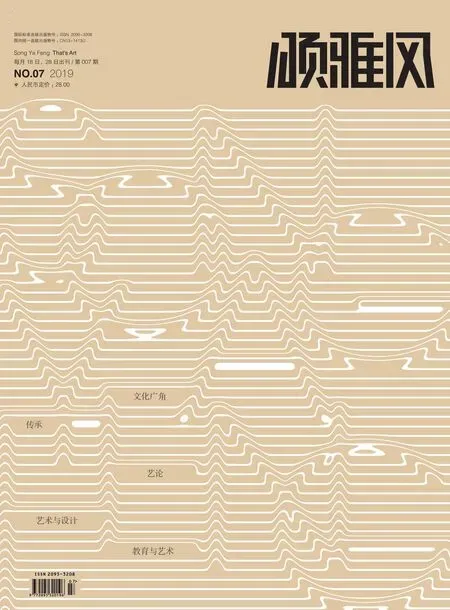西北“花兒”的藝術欣賞
◎洪金枝
一、西北“花兒”概述
(一)“花兒”的特點
在經過了長時間的發展之后,“花兒”呈現出來許多不同的特點。首先,流行區域較廣,在西北的甘、青、寧等區域都廣泛流傳著這一類型,與其他民歌之間產生了強烈的對比,既不像信天游流傳于陜北,也不像爬山調流傳于內蒙,“花兒”更多地將地區限制打破,突破了民族的制約,在漢族、回族、東鄉族、土族、撒拉族以及保安族等民族當中廣泛流傳;其次,內容包羅萬象,盡管花兒的內容以情歌為主,對婚姻以及男女愛情進行了精彩描述,但是同時也包含更為豐富的內容,包括天文地理、民族人物、歷史事件以及神話傳說等,無所不包;最后,花兒的曲調新穎別致,對于花兒的曲調來說,既區別于藏族、土族以及撒拉族等少數民族,同時也與中原漢族的民歌有著很大的區別,將壯闊雄偉的西北山河呈現出來,有著豐富的曲令,在傳統民歌當中十分罕見。
(二)“花兒”的分類
對于西北“花兒”來說,大致上分為河湟花兒與洮泯花兒兩種類型。河湟花兒主要流行于甘肅河州和青海湟水兩地,也可以稱其為少年,傳播范圍與影響力都要大于洮泯花兒,因此在各個民族之間都受到了喜愛;河湟花兒自身的特點主要為曲調豐富,同時以抒情為主,文辭優美而樸實,整體結構十分嚴謹。而對于洮泯花兒來說,包括岷縣花兒以及蓮花山花兒,在甘肅省康樂與和政縣的流傳比較廣泛,不過經過分析其唱詞、音調以及演唱的表現風格之后,根據其差異性又可以分之為“南路花兒”和“北路花兒”兩種。
二、“花兒”的藝術欣賞
在長期的歷史發展當中,“花兒”的流傳十分廣泛,同時也有著很高的文學性與藝術性,表現出來濃郁的地方色彩,在中國的民間歌謠當中別具一格,成為了十分珍貴的口頭文學遺產。
(一)靈活多變的比興手法
在民歌的演唱當中,比興是一種十分常見的表現手法,在西北“花兒”當中的應用更加廣泛。對于“花兒”的創作者來說,大多為情感馥郁之人,在唱詞的時候,往往是即興發揮,呈現出一種質樸的表現形式。比如在“一對的鴛鴦像鳳凰,它落在梧桐的樹上;尕妹的模樣像月亮,賢良著就像個孟姜”當中,作為一首典型的愛情“花兒”,通過鴛鴦與鳳凰兩種形象來起興,在進行氛圍渲染的同時,更好地表達出濃艷纏綿的感情基調。在“花兒”的比興當中,手法比較形象自然,同時音韻朗朗上口,采用一種人們喜聞樂見的方式,將比興手法與勞動人民的生活環境結合起來,在領略自然美的同時,感受到勞動人民所具有的淳樸與率真。
(二)豐富多彩的曲令與高亢的旋律
“花兒”的曲調豐富多彩,比較典型的撒拉令3/4(如“一對的鴿子朝南飛,大豆花開開是虎張口”)、水紅花葉葉令(如“十二個駱駝馱面哩,好一座青山霧拉了”)、 軟三令(如“咔啦啦洋火十三響,花鹿兒翻山吃草尖”)、酸把黎令(如“酸把黎熟了者沒入味,青石頭青蘭石頭蘭”)、青海水紅花令(如“鳳凰展翅者三千里,楊六郎把守在三關口”)、上山令(如“三間的大缸里家什多,山上的熟地丟荒了”)、尕連手令(如“白大布涼棚嫌白了,白龍馬甭者鞭子啦打”)、三閃直令(如“青銅的煙瓶烏木的桿,柳樹的栽子我栽了”) 等幾十種曲調, 而且都是四句式和六句式,句式押韻。“花兒”曲調高亢、清脆悠長、激越而優雅,悲壯處慷慨激昂如鐵馬金戈;哀婉處如泣如訴,似落花流水,悲壯者為之憤懣,哀怨人為之抽泣。河州型花兒曲令的整體基調偏向于悲劇色彩,渲染憂傷是其主要手法,通過將高亢的情緒與悠長的聲音結合,展現出一種壓抑而沉悶的沖擊感,仿佛在限制著情感的激烈爆發。這種獨特的情感來源于西北地區獨特的自然環境,同時在特殊的經濟生活與社會矛盾下,各族人民借助“花兒”的藝術形式,完成了自己心中的情感抒發,他們經歷過苦難,品嘗過辛勞,這些經歷都將化為沉重的憂傷,而熔鑄進民歌“花兒”之中。
結語
“花兒”是我國的一項重要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在西北地區廣泛的流傳,同時憑借自身重要的價值,成為了西北之魂。“花兒”作為一種傳統的民族音樂,其自身融合了漢族、回族以及藏族等等民族的音樂形式,同時將各民族對于未來生活的無限憧憬反映了出來,屬于我國傳統文化藝術當中的瑰寶。在我國的民間歌謠發展當中,“花兒”的藝術特點十分明顯,憑借自身別具一格的藝術特點,成為了民間文學藝術中秀麗多姿的藝術瑰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