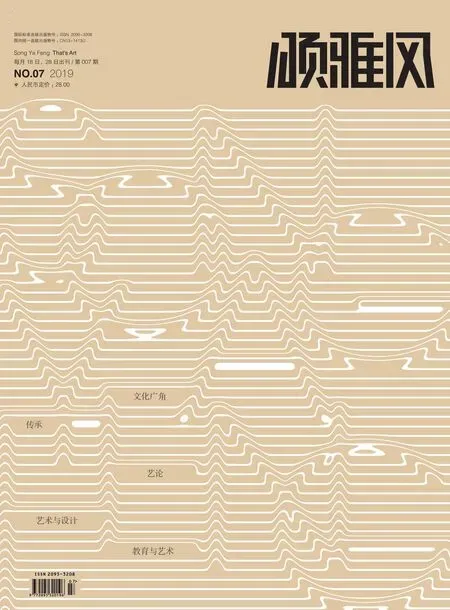從《我與地壇》看散文寫作的真情與濫情
◎侯小麗
《我與地壇》是作者在苦難病痛中生活的嘔心之作。作者史鐵生在青年下鄉時就發現疾病,后雙腿殘疾靠輪椅生活,病痛的折磨讓他一度消沉,活動范圍的局限使得附近的地壇成為他常去之處。幽靜的地壇,殘酷的現實,對個體情感和生命意義的冷峻思索,使作者思想超越了個體命運的挫折和苦難,進而感悟生命的永恒和宇宙的不息,使得此文超越了一般的抒情述景散文,成為浩瀚篇章中的奪目明珠。在借物抒情甚至是“借物歌德”類散文主導的年代,《我與地壇》無疑是另類,使人們恍然原來散文還可以這樣寫。
《我與地壇》1991 年發表,一些散文選本與小說選本都將此文列入,經過一段時間沉淀后才被大家公認為是散文。這與大散文的興起、散文題材的多樣性更廣泛多少有些關系。擅長寫小說的史鐵生很清楚小說的寫作可以虛構,而《我與地壇》傾訴的是作者的所思所感、所見所聞,作者是按散文的思路來寫作發揮的,如果按小說去對待顯然與作者的寫作意圖完全兩樣。這就是寫作時“虛”與“實”的不同,《我與地壇》是作者將多年來的經歷、思索用飽含情感、直指心靈的文字展現,只有散文才是展現真情實感的合適載體。
1949 年后的整體文學創作是被束縛后的平庸,思想解放后最先噴薄的是詩人激情的頭腦,小說家當仁不讓地跟上。“傷痕”帶動了老一輩作家的反思,巴金在經歷過苦難后深刻反思,呼喚人性,從而引發了一場寫真實、說真話的散文革命。“假大空”的所謂散文沒有了市場,讓散文一下子就找準位置開始復蘇。但這種復蘇短暫而單薄,很快被當時此起彼伏的文學熱潮掩映,直到《文化苦旅》橫空出世掀起的熱潮讓文化散文成為散文的主流,也讓散文由文學配角成為主角,經濟市場的及時回應讓更多作者加入到散文的寫作中。
同時期賈平凹提出“大散文”推動了文化散文的創作。賈平凹的大散文一說不僅是指題材廣泛,還意指境界大。題材廣泛自不必說,散文創作早已跳出楊朔式特殊時代散文的窠臼,轉而進入到百花齊放春滿園的熱鬧場面,一些擅長寫小說、詩歌等文體的作家閑暇之余也筆耕散文,讓散文創作爭奇斗艷。名家大家用老練深厚的寫作技巧在謀篇構思、文字精巧方面讓文化散文創作的厚度和高度不斷增強。但文化散文以及國學熱的浪潮,讓一些缺乏底蘊的人紛紛跟風,為賦新詞強說愁,鉆進故紙堆里搜羅掃蕩,市面上充斥了不少掛著“文化”游蕩的散文作品。大散文對散文文體要求的寬松化讓理論界及一些作者自覺性的試圖“規范”散文文體落空。散文成了筐,筐里東西裝雜亂了就需要整理,會發現許多文化散文已經泛濫到“濫情”的程度了。這種過于追求大題材與大感情的文章往往能引起崇拜知識的青年讀者共鳴,但理性讀者在表象的亢奮過后卻發現沒有多少回味的內容,尤其是眼中總是充斥這種除了人物、情節不同,敘事方式雷同卻缺乏個體體驗和心靈滲透的文化散文會產生審美疲勞,人畢竟不能持續亢奮。許多名家的文化散文,一味用過度抒情的筆法堆砌編排史料,通篇文章以個人偏好為導向高歌猛進。更可怕的是諸多文化散文成了“文化陷阱”,缺乏考證的史料、對歷史人物尤其是政治人物不假思索的褒貶,很容易落下硬傷,被人指責。
散文究竟要不要回歸真情,答案是必要的。在1980 年代林非先生針對一段時期以來的散文“假大空”現象提出了真情實感論,引起了關于散文真情實感的討論,真情實感被當作散文的本體性要求給散文創作帶來理論導向。當然任何一種理論的提出總有質疑者,孫紹振老師就對真情實感論提出強烈質疑。林非先生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提出真情實感論是及時而必要的,有進步意義,對這個觀點林非先生并沒有過多進行深入闡釋,多年后他也感到遺憾。文學創作與理論沒有終極真理,在不斷的實踐、質疑中碰撞后再回首思索,會去重新理解真情實感論。文學作品是作者主觀意識思索后按照一定文體規范通過文字來表達所思所想,這決定了文學作品存在主觀性,不能狹義地將真情實感定義為客觀再現,即使是報告文學也存在藝術加工。對散文創作的真情實感關鍵在“情與感”的真,可以虛構但不能虛偽,可以夸張但不能夸大。這種虛構與夸張要限制在寫作技巧性的范疇,寫作者如果主觀不能掌控虛構與夸張的度,那不如直接去構思小說或者詩歌。
什么是經典文章?經典文章就是可以讓人讀許多遍,若干年后依然可以回味,能帶給人美感的文章。經典需要時間的沉淀選篩,各種評獎及選本評選的文章通常是按官職、名氣排序,這樣的所謂“經典”只能蒙蔽許多素養不高的愛好者。而讀《我與地壇》時會被張弛有序、開合穿插的步調帶動進入的精美畫面,讀完余味悠長,掩卷長思,這才是經典的精妙處。當年被認為篇幅過長,如今對比有些大而無當、長而拖沓的文化散文,《我與地壇》就愈顯精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