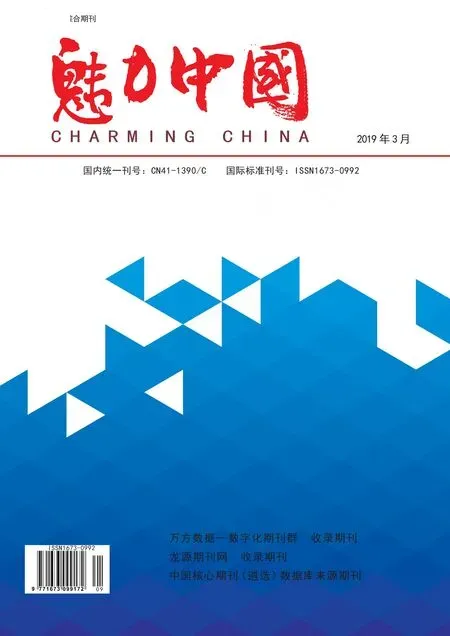歷史書寫之敘事模式探析
阮佳妮
(寧波大學人文與傳媒學院,浙江 寧波 315211)
就“歷史書寫”一詞而言,其本身就存在一定的矛盾性。首先,歷史一詞,在更多人的理解中,即為史實,就是客觀而真實的存在。而書寫一詞,即是一種話語,在話語權的背后往往蘊藏著主觀性和感情色彩。故不免有人認為,歷史書寫其本質是一種矛盾形容法。塞爾托認為,“可以對歷史書寫的可操作性出發,從主體問題加以審視,即敘述性的話語以及人更值得我們深思”。[1]若要探索這種矛盾,就得深入探討話語與事實之間的關系,也就是探究歷史書寫的主要模式——敘事。
在歷史與書寫的十字路口,法國歷史學家保羅·韋納對其有著別具一格的理解:寫歷史更像是寫小說。在《人如何書寫歷史》一書中,韋納經過多方分析論證,指出歷史學家的工作更像是小說家,并主張建立一種超越文本與材料的新型歷史觀。在韋納看來,歷史學家在書寫時,會在事件真實性的基礎上,將敘事故事化、生動化,以期達到自己想要的最佳效果。歷史學家就像是那些故事的訴說者,精心編織著以人為主角的真實事件。而在此意義上,歷史就像是一部真實的小說,生動精彩,引人入勝。但是,歷史并不是存在與認識的簡單混合體,其可以憑借敘事從而獲得無限的更新。
當代美國學者帕特里克·格里在《歷史、記憶與書寫》一書中,有兩篇論文談及歷史書寫。其中,《多重中世紀:競爭中的元敘事及對講述過去的競爭》一篇中主要是對元敘事形態和改造中世紀話語的方式做了探討。格里認為,“歷史學因此完全失去其指稱性,它的敘事只不過是權力和欲望的論述。所有的元敘事都無可救藥地是與過去的斷裂,被永遠關在語言的牢籠里”。[2]筆者認為,此觀點頗為偏激,把敘事中的權勢與利益因素無限放大,以致于抹殺了過去的真實,認為歷史學的敘事被語言本身的局限所禁錮。語言作為一種表達方式和溝通手段,使敘事得以與過去相連接,并產生一定的效應。敘事是在基于過去真實性之上,充分發揮語言的魅力,獲得自由而不是禁錮。盡管,敘事會受到強烈的欲望支配,或多或少表現出一定的傾向性,但這并不足以腐蝕其價值性。
美國學者海登·懷特在 1988年發表的《書寫史學與視聽史學》一文中,認為,“無論是視覺上呈現出的影像歷史,亦或是以文字為載體的書面歷史,都不能真實‘映射’所有事件。即使以微觀歷史的嚴格要求限定之,都不能保證是絕對真實的歷史表現。因為,任何一種書寫歷史都與電影再現的制作相似,必定要經過濃縮、移植、象征和評定的過程”。[3]最后得出結論,盡管在敘事中存在一定的虛構性,但書寫史學依然可以明確地表現出事件的原因和結果。賈維認為,在歷史學家將“事件”信息轉化為“事實”的過程和目的中,較少對真實事件進行“描述性敘事”,而主要是歷史學家的“辯論性結果”。“事件一旦發生,歷史事實中就會不自覺地包含對事件的描述,即通過行為的預測描述出來。而任何對過去的描述是否‘充分’,取決于歷史學家選擇一種怎樣的觀念。”[4]這種說法,首先承認了歷史書寫會無法避免地包含“描述性敘事”。后又否定了書寫中摻雜著大量的描述性,認為歷史學家的“辯論”使其趨向真實客觀。在書寫中,歷史學家觀念之搖擺與歷史敘事之起伏緊密相關。同時,強調歷史書寫不是單一性的,其背后蘊含著歷史學家們在時勢下多元的思想結晶和價值取向。
為了正確理解歷史書寫,分清事實的敘事和虛構的敘事兩者之間的差異是非常必要的。路易斯·明克、阿瑟·丹圖、海登·懷特、保羅·利科等學者都已在其論著中論證說明,敘述是歷史書寫最為重要的認知工具之一。盡管敘事是歷史書寫的重要模式,但這并不能說歷史書寫就完全等同于虛構,歷史學家就能夠無的放矢,隨意構畫。懷特認為,“敘事始終是、且將一直是歷史書寫的主導模式”。[5]克羅齊就曾說過,“沒有敘事,就沒有獨特的歷史話語”。[6]塞爾托認為,“在歷史書寫中,在其分析和操控的結果中,虛構走到了盡頭。敘述是對過去的呈現,它是一個不受到權力限制的領域”。[7]若把視線聚焦于歷史書寫理論,可以發現其核心并不在于運用先進科技探索過去的真相。因為即使運用超先進的科學技術,也無法完全“復原”歷史真相,使歷史完美“重現”,只能是無限地接近真相。
在當代中國,敘事與書寫之間的關聯性不斷延伸,互動性不斷增強,演繹出了公眾歷史書寫和公眾口述史學。與傳統史學相對的公眾史學的興起,意味著人們開始關注到擁有歷史話語權的個人,開始意識到歷史文本生產中的敘事性功能。歷史書寫在新時代下找到了全新的應用路徑——公眾史學。小歷史書寫提倡的“人人都可以書寫自己的歷史”,完全突破了舊時的禁錮,開辟了史學一片新的天地。國內已有越來越多的學者投身到歷史書寫的研究中,從事于小歷史書寫的實踐中。中國的公眾史學已逐漸形成一股學術思潮,期望它能在不久的將來以獨樹一幟的姿態立于史學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