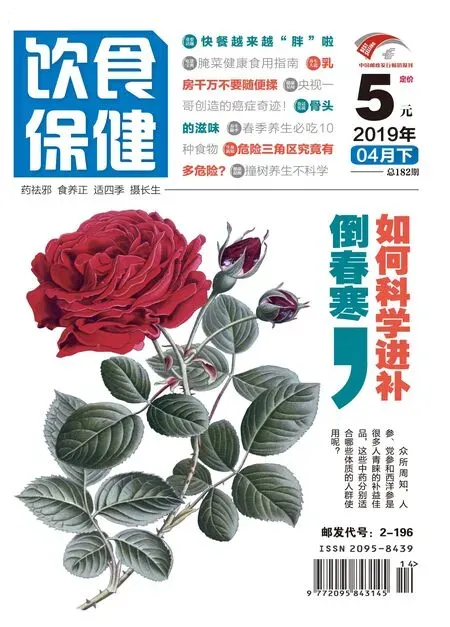骨頭的滋味
2019-01-13 03:02:14
飲食保健
2019年8期
臘骨頭的香味,雖然多年未曾重逢,但至今思之,猶自口有余香。有句順口溜說的是:“肉管三,湯管七,骨頭要管二十一。”什么意思呢?原來彼時老百姓的生活緊張,縱使是在“天府之國”的四川,物質亦匱乏至極,乃至于吃肉都不叫吃肉了,叫“打牙祭”。鄉人以為,比較可口的肉,其實只能解三天的饞,而煮肉的湯則可解七天饞,最厲害的要數骨頭,只要啃幾根,就可以21天不必再打牙祭了。這當然是一種夸張的說法,不要說21天,就是每天啃幾根骨頭,恐怕也無法給長年食菜咽糠的腸胃抹上一點可以滋潤的油星。
不過,這都是遠去的舊事了,而今時代變了,骨頭的滋味也在變,這就像那篇著名的《芋老人傳》中的書生一樣,落拓時的書生,吃幾塊芋頭也有如品到了上味,等到位居高位時,山珍海味都吃厭了,那芋頭也遠不如從前好吃了。其實,芋頭還是從前的芋頭,只不過位置變了,胃口也跟著在變,時勢使之然也。
西南地區的鄉下——尤其是在山高林深的山區,百姓人家是有做臘骨頭傳統的。宰殺年豬時,上等精肉都劃成了條狀,或是送到市場上去出售,或是饋贈親朋好友。余下些腸腸肚肚和零亂的骨頭骨架,全用一口夏秋時腌鹽菜的陶制水缸給胡亂盛了,再加入大量的鹽汁。待如此漬泡十來天后,取出來一件件地用棕葉搓成的繩子拴好,一長溜地掛在廚房土灶的上方,與臃腫的豬肚豬肺相比,臘骨頭顯得格外修長。在接受了一日三餐做飯時跳出灶堂的煙火熏烤半個月之后,這臘骨頭也算是功德圓滿了。……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