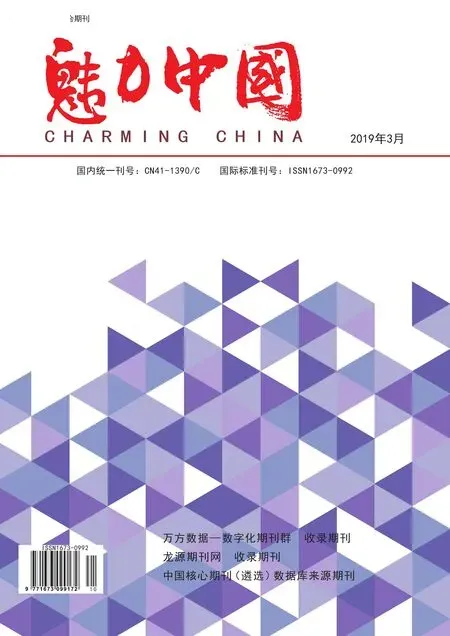檢察機關司法警察的職能定位
王玥琪
(吉林司法警官職業學院,吉林 長春 130062)
前言:隨著我國暴力抵抗檢察機關執法案件的增多,如何對檢察機關司法警察的職權進行界定與規范,如何協調檢察人員、普通民眾之間的關系,成為檢察機關文明執法的關鍵。通過制定完善的司法警察工作規范,對不同群體所應擔負的行政責任、刑事責任進行明確,能夠實現對司法警察職權與外在形象的維護。
一、司法警察職權的法律解釋與現行規定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警察法》第2章第2條規定:“人民警察包含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警察,以及人民檢察院的司法警察。人民警察在依法履行職務過程中,其所施行的一切職權受到法律保護。”這一法律從法律層面,明確司法警察屬于人民警察的法理地位,但并未對檢察機關司法警察的職責、權利等,作出具體規定。
而《人民檢察院司法警察暫行條例》(以下簡稱《暫行條例》)這一通知,則從司法警察隊伍建設、職權行使,對司法警察任職條件、法律職責等作出具體規定,主要內容如下:(1)《暫行條例》第1章第3條:司法警察具有維護社會法制、人身安全、人身自由與合法財產,保障檢察工作秩序的職權。《暫行條例》第1章第6條:司法警察要以《憲法》及其他法律為最高準則,堅守公正廉潔、嚴格執法的行為規范,從而實現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發展目標。(2)《暫行條例》第2章第7條:司法警察在經人民檢察院批準后,可執行參與搜查、傳喚、拘傳和協助執行等職權,也有權對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押送、提解、看管,并保證法律文書的準時送達。
因此從司法警察的法律職權、任務執行方面來看,其通常負責犯罪案件的警務保障、組織管理等工作,包括采取強制手段制止違法犯罪行為,使用警械、武器制服犯罪嫌疑人,以及強行帶離存在暴力、威脅行為群體的權利。雖然以上法律法規對司法警察的職能權利,進行了性質定位與職權配置,但在具體涉事案件的解釋方面,仍舊面臨著司法界定、司法解釋的模糊問題,司法警察能夠行使的職能較為狹窄,難以滿足現代社會的檢察執法需求。
二、目前檢察機關司法警察職能定位存在的問題
(一)司法警察職能定位模糊、權利狹窄
針對以上法律法規條款可以看出,司法警察在依法對刑事案件、犯罪案件處理過程中,具有使用警械、使用武器、強制手段,對涉事主體暴力、威脅、違法犯罪行為進行制止的權利。但采取何種強制措施、如何采取強制措施?以及在怎樣情況下將犯罪嫌疑人可以強行帶離現場,如何使用武器或警械,使用武器所產生后果有誰負責?因此對于司法警察多種職權的行使,缺乏明確的職能定位、法律支持,導致司法警察在刑事搜查,以及嫌疑人檢查、詢問、勘驗時,存在司法職權的認定、執行難題。另外,當前《暫行條例》規定司法警察具有法律文書送達的職能,這與司法警察的工作性質存在沖突,其在職權行使過程中也面臨重重困難。
(二)司法警察職能定位與實際案例的差距
現行《人民檢察院司法警察暫行條例》,主要從大方向上對司法警察職能作出法律規定,但并非所有有關司法警察的法律條款,都與現實司法案例存在完美契合,這是司法警察職權行使面臨的主要問題。《暫行條例》規定的司法警察8項職能權利,并不能在刑事搜查、公訴人出庭,或者犯罪嫌疑人提解、押送與看管中得到有效實施。也就是說,司法警察在依法行使職權時,很容易由于司法職權界定不清、自身操作不當等,而造成司法警察、涉事主體之間的行政糾紛,這會大大弱化司法警察在犯罪案件參與中的職能與權利。
三、檢察機關司法警察職能權利的立法策略研究
(一)制定明確、細化的司法警察職能權利法律規范
在司法警察職能權利的規定與實施過程中,全國人大法工委要依據不同犯罪案件、刑事案件的實際情況,對司法警察警務工作任務、執法內容進行分工明確,盡可能設置具有實用性、細化的職能權利法律規范,以保證多種搜查、傳喚、安全保衛、提解、押送、看管等警務工作的順利執行。例如:在《暫行條例》司法警察職權的補充條款中,可以對不同職責履行主體、職責履行方式進行規定,來有效確立不同司法警察人員的職責權利。然后再根據犯罪嫌疑人的主體行動,進行提解、押送、看管、安全保衛等職權的法律規定。
(二)強化檢警分離后司法警察的監督職權
隨著我國檢察人員、司法警察職權的分離,《人民檢察院司法警察暫行條例》等法律法規,在司法警察職能權利的規定方面,要去除有關檢察人員司法決定權、批捕權、回避權等權利的內容,增加與司法警察行政相關的監督職權。對于那些不適合檢察行使的行政職權,可以交由司法警察部門進行專門承擔與管理,這不僅有利于司法警察編制的建設與管理,也有利于司法警察、涉事主體之間司法糾紛的解決,減少司法傳喚、搜查中不必要的矛盾沖突。同時《暫行條例》中需要補充,只要司法警察發現犯罪嫌疑人提審、押送、看管等環節,偵查人員存在違法、不規范執法的行為,都可以向上級領導反映情況,來有效保證司法警察監督職權的行使。
結語
司法警察作為檢察機關職權行使的監督人員,需要依據《人民檢察院司法警察暫行條例》等法律條款,進行司法警察隊伍、司法警察職能的規范化建設,才能推動司法檢察工作的順利進展。通過對現有司法警察職能法律條款、《暫行條例》等的修改與補充,可以對司法警察的搜查、傳喚、安全保衛、提解、押送、看管等職權進行改革,加入具有明確司法屬性、職能定位的法律制度,這樣才能實現司法警察職權行使的實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