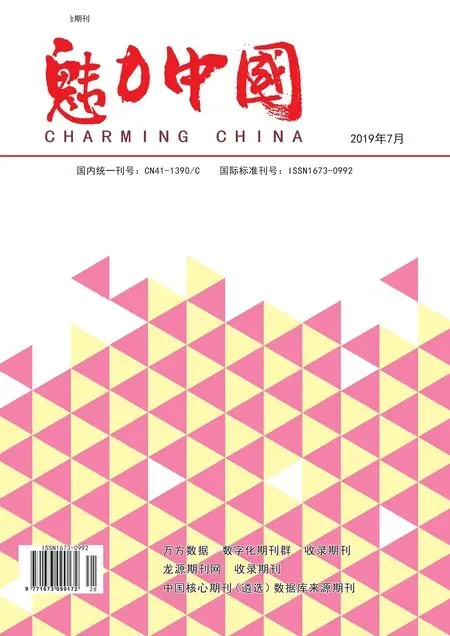講好中國故事
——從中國文化符號到中國話語
熊璨
(北京師范大學,北京 100088)
一、引言
習近平總書記在“2.19”講話中提出,“落后就要挨打,貧窮就要挨餓,失語就要挨罵”1。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國家之間文化交流日漸頻繁,我國也愈發(fā)關(guān)注中國國際話語權(quán)的爭取。然而,在目前的國際文化交流中,主流話語權(quán)仍掌握在少數(shù)西方發(fā)達國家手中,中國文化仍更多處于一種“有理說不出,或者說了傳不開”2的尷尬狀態(tài),這本質(zhì)上是一種文化失語。正如曹順慶先生所言:“長期以來,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理論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話語,長期處于文論表達、溝通和解讀的‘失語’狀態(tài)”3。早在“五四”時期,中國文化失語的危機便已埋下,我國近百年來的文化自卑和文化自戕形成了“言必稱希臘”4的學術(shù)風氣。在西學東漸的過程中,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地位愈發(fā)弱勢,因此言說自我的權(quán)利和空間不斷被迫壓縮。而如今,中國文化失語現(xiàn)象愈發(fā)廣泛,不但泛濫于上世紀“西學東漸”的潮流中,也逐漸顯現(xiàn)在二十一世紀“東學西漸”過程中。
中國至今尚未走出“失語”困境,而這一困境甚至比上個世紀的情況更為復雜。21世紀以來,全球化進程加速,世界各地逐漸出現(xiàn)的中國文化熱,讓我們恍惚感覺“失語癥”似乎已被完全治愈。目之所及,中國文化符號頻繁地出現(xiàn)在世界各地,在生活方面,中國制造、中國城、中餐廳遍地開花;在藝術(shù)方面,在全球上映的西方電影中也越來越多地出現(xiàn)了中國文化符號。這一切讓國人產(chǎn)生一種錯覺,仿佛中國故事已愈發(fā)引人關(guān)注,中國在國際上已擁有愈發(fā)重要的話語權(quán)。然而,是誰在講述中國故事?講述了怎樣的中國故事?這些都是需要我們關(guān)注和警惕的。
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guān)注到,在“西學東漸”的過程中,我們的話語空間越來越多地被西方擠占,“失語”問題不可小覷。在文學理論方面,已有多位學者嘗試從不同角度提出解決辦法。例如周憲教授從文化“合法性”的角度重新解讀“失語癥”等問題,并提出了中國文化的“重新傳統(tǒng)化”和“重新合法化”5;高迎剛教授認為我們應通過文藝批評實現(xiàn)文論理論研究和文藝實踐互動,從文藝實踐和文藝批評中尋找動力和資源,建立當代中國文論體系6;施旭教授則通過分析中國話語的特點,初步提出了一個系統(tǒng)的中國話語理論框架7。此外,從政治學和傳播學角度,也有多位專家展開討論,如陳曙光教授的《中國話語與話語中國》、田鵬穎教授的《在解構(gòu)“西方話語”中建構(gòu)中國話語體系》等文章,都在嘗試提出突破西方話語霸權(quán)、建設中國話語的辦法。
隨著東西文化之間的雙向交流互動愈發(fā)頻繁,建設與中國崛起進程相匹配的中國話語顯得刻不容緩。本文擬從“失語癥”視角出發(fā),梳理當下中國文化“失語癥”中的隱藏問題,并嘗試提出中國話語建構(gòu)的具體路徑。
二、中國文化符號愈發(fā)活躍,中國話語悄然缺席
在過去,西方人使用中國文化符號時,較多用于書寫他們眼中的東方故事,中國文化符號只是西方主流話語用于滿足其東方主義想象的工具,比如許多西方人對中國人的固有印象至今仍是以傅滿洲為代表的“黃禍”形象;在今天,西方則更多地使用中國文化符號描寫著西方故事,中國文化符號此時更像是西方文學的創(chuàng)作素材,任憑創(chuàng)作者將它涂黑描白,并在全球掀起巨大的影響力,而中國自己講述的故事卻聽眾寥寥。這一現(xiàn)象可以被概括為“在場的失語”,也就是說,中國文化符號在生機盎然的同時,中國的文化規(guī)則失語了。“語”即“話語” (discourse),并非指一般意義上的語言或談話,而是借用當代的話語分析理論(discourse analysis theory)的概念, 專指文化意義建構(gòu)的法則8,這些法則是指在一定文化傳統(tǒng)、社會歷史和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思維、表達、溝通與解讀等方面的基本規(guī)則, 是意義建構(gòu)方式和創(chuàng)立、交流知識的方式9。說得更簡潔一點, 話語就是指一定文化思維和言說的基本范疇和規(guī)則,范疇一般指文化中表層的部分,而規(guī)則是深層次的、能夠生成和支配范疇的部分10。
從這一角度出發(fā),筆者認為,雖然中國文化符號作為中國文化表層的范疇在海外大熱,但在這一狀態(tài)中,這些符號蘊含的深層文化規(guī)則卻是西方的,書寫權(quán)力也掌握在西方人手中。此時的中國文化符號只是包裹西方話語規(guī)則的皮囊,中國話語作為它原本的內(nèi)核早已不知所蹤。西方用他們的規(guī)則編織著中國文化符號,而中國話語規(guī)則在這一過程中則被過濾、剔除以致被逐漸邊緣化。
(一)中國文化符號日漸煥發(fā)活力
近日,美國迪士尼公司宣布正在籌拍的電影《花木蘭》中花木蘭一角將由女星劉亦菲出演,一時在海內(nèi)外廣泛激起討論熱潮。這并不是迪士尼首次使用中國南北朝民間樂府詩《木蘭辭》作為電影素材。1998年,迪士尼投入一億美元拍攝動畫片《花木蘭》,歷經(jīng)兩年制作后上映,該片全球票房超過三億美元,花木蘭以善良美麗、機智勇敢的形象被世界人民所熟知和喜愛。在成為迪士尼動畫片主角以后,花木蘭作為唯一一位沒有皇室血統(tǒng)和身份的“公主”,與白雪公主和灰姑娘(仙蒂公主)一同進入了“迪士尼公主”(Disney Princess)系列。自此,花木蘭不再只停留在電影中,而是與其他公主一起進入各大迪士尼主題樂園,與游客熱情互動,其形象也被制作成精美的服裝、玩具等走進人們的生活。
與影片上映同步,麥當勞公司在美國推出的限量版“木蘭”四川醬汁受到瘋狂追捧,供不應求,該款醬汁甚至成為一種情懷。在粉絲的反復要求下,麥當勞決定于2018年2月26日再次向全美麥當勞餐廳供應辣醬。影片及其所輻射到的行業(yè)所取得的成功和轟動效應令人始料未及,中國文化符號被包裹在美國動畫片中,向世界展示了其旺盛的生命力。
此后,嘗到甜頭的美國陸續(xù)在多部影片中大量使用了中國文化的符號。2008年,好萊塢動畫片《功夫熊貓》問世,故事發(fā)生地點明確設定在中國,短短一部影片包含的中國文化符號令人目不暇接。影片以寬銀幕規(guī)格拍攝,畫面因此呈現(xiàn)出中國國畫中留白的風格。不管是從思想上道家的“道可道,非常道”,禪宗的“頓悟”、儒家的“仁”,到建筑中的宮殿和園林,還是到武功招式中的拳法,到中醫(yī)的針灸、經(jīng)絡圖,再到日常生活中的麻將、長笛、面條、豆腐等等,中國文化符號貫穿了影片始終。通過大膽糅合以功夫和熊貓為主的中國文化符號,《功夫熊貓》最終取得超過6億美元票房的成績,更是獲得奧斯卡金像獎提名。之后,好萊塢趁熱打鐵,連出兩部續(xù)集,均獲得熱烈反響。
(二)中國話語規(guī)則難以有力發(fā)聲
中國文化的生命力讓我們不禁疑惑:如此受歡迎的文化,怎么能說它“失語”呢?其實細看之下,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雖然《木蘭辭》是中國的,《花木蘭》卻是美國的;雖然功夫、熊貓以及片中眾多文化符號都是中國的,但《功夫熊貓》卻是美國的。這并不僅僅表明故事的講述者有了變化,這更意味著故事的講述規(guī)則發(fā)生了根本改變。《花木蘭》從美國的文化視角出發(fā),把為父盡孝、為國盡忠的花木蘭重新詮釋為希望實現(xiàn)自我價值而勇敢參軍的女英雄。而《功夫熊貓》哪怕堆砌了再多的中國文化符號,其內(nèi)核也同樣是美國個人英雄主義,說到底,這都是黃皮白心的香蕉故事,也就是披著中國風外衣的美國故事。
以《功夫熊貓》為例,它看似是一只熊貓頓悟武功絕學,不怕犧牲,擊退邪惡勢力,最終保護家園的中國武俠傳奇;實際上它更多著墨于描繪一個有著諸如貪吃、逃避等世俗缺點的小人物,在看到自身的不足后仍然堅持夢想,最終進入精英階層的美國故事。同時,影片依然延續(xù)了“美式英雄主義”,這與美國漫威系列電影的主題并無二致。此外,片中也對中國儒家思想“天”、“命”等存在著一定的誤讀:具有最高智慧的烏龜大師在第一次見到熊貓阿寶時,便毫無來由地如同算命先生一般指定它是神龍大俠,并一直反復強調(diào)“這就是命運”、“從來就沒有什么偶然”,難免有故弄玄虛之嫌。儒家的“天命”與道家的“道生”都是強調(diào)生命由自然規(guī)律決定,并不是強調(diào)宿命,更不是推崇算命。因此,我們可以看出,片中大量的中國文化符號更多只代表中國文化的一些具體內(nèi)容,并不能代表中國文化規(guī)則。很遺憾,雖然中國文化符號充滿生命力,中國文化的規(guī)則卻深陷失語危機。
與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文化不同,中國文化規(guī)則是深受儒家、道家等文化影響的。西漢時期,在漢武帝采納了董仲舒提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漢書·董仲舒?zhèn)鳌罚┑慕ㄗh以后,儒學成為正統(tǒng)思想。儒學一個典型的特征便是“依經(jīng)立義”11。孔子并沒有留下一套系統(tǒng)的學術(shù)著作來書寫其思想理念,他的基本文化態(tài)度是“述而不作”,《中庸》也提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漢書·藝文志》)。也就是說,相比直接創(chuàng)作,孔子更傾向于講述和注釋先賢的優(yōu)秀文化遺產(chǎn)。但是,盡管孔子自稱“述而不作”(《論語·述而》),他的闡釋中依然體現(xiàn)出其“仁”、“禮”等重要觀念,可以說孔子的創(chuàng)作孕育于他的闡釋活動。后世學者深受這一理念影響,逐漸形成了“我注六經(jīng)”(陸九淵《語錄》)的普遍治學思路,通過為前人的經(jīng)典做注,表達或不表達自己的觀點。在教學上,孔子也多是言傳身教、循循善誘,引導弟子用包容的態(tài)度去感悟和思考。因此,孔子門下弟子對孔子思想的理解也各不相同,“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韓非子·顯學》)。在孔子逝世以后,弟子們逐漸形成八個不同的儒家派別,這也正是儒家思想兼容并包的體現(xiàn)。
盡管儒家思想的正統(tǒng)地位在西漢時期就得以確立,道家思想對中國的影響同樣非常深遠。道家思想用“道”來探尋人與自身、自然的關(guān)系。老子認為“道可道,非常道”(《道德經(jīng)·第一章》),主張規(guī)律和真理的不可言說性,提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道德經(jīng)·第二十四章》)、“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道德經(jīng)·第四十二章》),認為道是世間萬物的本源,任何事物都有陰陽兩面,陰陽在氣的作用下相互轉(zhuǎn)化,萬物便達到平衡的狀態(tài)。這一點在我國傳統(tǒng)醫(yī)學也就是中醫(yī)的理論中也有大量體現(xiàn)。此外,道家思想還包含“道法自然”、“無為而治”等許多重要內(nèi)容。
兩千多年來,儒家和道家學說相互影響、交織演繹,在人們身上逐漸發(fā)展出以含蓄、包容、謙遜、豁達為性格,以“微言大義”、“春秋話語”、“言盡而意無窮”為表達方式,以“虛實相生”、“清淡和雅”、“曠達超脫”為審美偏好,以“仁義禮智信忠孝悌節(jié)恕勇讓”、“上善若水”為處事原則,以“家國天下”、“天下大同”為抱負的民族特質(zhì)。
三、新媒介強勢助力,話語權(quán)重建可期
這些特質(zhì)流淌在我們的血液里,但可惜的是很多人已經(jīng)忘記了它的來源,我們并不明確如何去傳承和發(fā)揚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究其根源,是“五四”時期為挽救民族于危難的新文化運動幾乎打斷了中國文化傳承的經(jīng)脈。
(一)文言文媒介功能的失落
20世紀初,中華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關(guān)頭。提高民眾文化水平迫在眉睫,但由于那時書面語文言文和口頭語白話文的距離已經(jīng)很遠,大眾教育很難實現(xiàn)。于是,以陳獨秀、胡適、魯迅等歸國留學生為主的知識分子推動了白話文運動,白話文成功促使民眾受教育水平迅速提升,但文言文作為傳承中國文化的重要語言也被一并抹殺。同時,新文化運動提出打倒孔家店,中國古代文化被進一步全盤否定,西方事物、觀念、文化鋪天蓋地被引入中國。
這個過程為中華民族帶來新生,但我們的文化自卑情緒也同時蔓延開來,文化自卑不可避免地帶來了文化自戕,我們對西方開始盲目崇拜,主動斬斷與古代文化的紐帶,開始推行“以西釋中”的治學方法。這種現(xiàn)象幾乎一直延續(xù)到今天,這導致經(jīng)過多年西化的中國現(xiàn)當代文化與中國古代文化的隔閡甚至大于與西方文化的距離,中國大眾尤其是年輕一代學習英語的熱情普遍高過學習文言文,很多人可以輕松閱讀英文原著,但看不太懂文言文經(jīng)典作品。人們可能不清楚“道”的含義,但對“美國隊長”了如指掌。在文化領(lǐng)域,我們憑借不到一百年時間跟隨西方腳步發(fā)展所累積的成果,自然難以與西方進行平等對話,而作為文化傳承的重要媒介——文言文,此時已不再作為日常讀寫與交流的語言,反過來成為大眾吸收古代文化的隔膜,已經(jīng)難以再憑一己之力打通我們與古代文化的障礙,扭轉(zhuǎn)局勢。
(二)利用新媒介傳承中國文化
在中國文化符號日漸活躍的今天,我們需要抓緊機會,重建中國話語。但是,要想獲得與西方文化平等對話的權(quán)力,我們迫切需要打破我們與古代優(yōu)秀文化的隔膜,將文化傳承和發(fā)揚下去。
雖然文言文因?qū)W習門檻很高而難以快速普及,很難再次成為傳承中國文化的主要媒介,但社會發(fā)展到今天,我們有了更多可以助力文化傳承的新媒介,比如影視劇、網(wǎng)絡文學、游戲、音樂等等。在這個追求效率的時代,傳承文化最直接、快捷的辦法之一就是將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內(nèi)容化繁為簡,做到有趣、大眾化、接地氣,再通過新媒介實現(xiàn)大范圍傳播。換句話說,在大眾文化產(chǎn)品中有意識融入更多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內(nèi)容,并把產(chǎn)品做得有吸引力,能夠很大程度上為人們主動學習傳統(tǒng)文化搭建橋梁。這與新文化運動把文化傳播的主要媒介文言文改變?yōu)榘自捨挠挟惽ぶАH绻f當時我們因時代的需要無奈暫時放棄了傳統(tǒng)文化,那么現(xiàn)在我們就是因時代需要主動拯救傳統(tǒng)文化。
相比難度較高的文言文原著,大眾更容易被有趣的故事所打動,并因此更傾向于去主動探索、吸收故事輻射到的文化內(nèi)容。可以說很多人閱讀四大名著的原動力是來自于其同名電視劇,也有很多人從看《新白娘子傳奇》開始對中國傳統(tǒng)服飾、節(jié)日、宋史、中國民間故事、黃梅戲產(chǎn)生興趣并進行進一步學習,在宮廷劇火爆時期,有不少節(jié)目甚至借助劇情給大眾做了一次唐史、清史等正史的梳理。
相比需要花費較大精力才能理解的“文言文”,傳統(tǒng)文化植入影視劇、游戲、網(wǎng)絡文學等載體也更容易在大眾當中流行。值得慶幸的是,我們已經(jīng)著力在做相關(guān)的嘗試,《國家寶藏》作為普及我國文物、歷史、文化知識的新節(jié)目,已經(jīng)受到了不少的好評和推崇。我們要做的,就是繼續(xù)多花心思把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巧妙地融入這些新媒介,通過最大程度消除理解障礙,去激發(fā)觀眾興趣,并引導觀眾進行學習探索。通過文化傳播媒介的古今通變,我們可以更有力地夯實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群眾基礎,讓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真正成為大眾的文化,讓大眾去傳承和傳播,而不只是把傳統(tǒng)文化當作小眾專業(yè)人士的研究對象。
(三)利用新媒介傳播中國文化
通過這些新媒介,我們也更容易向西方大眾傳播我國傳統(tǒng)文化,而當西方更了解我們的文化底蘊和話語規(guī)則,甚至開始主動學習我們的文化時,我們也更可能獲得更強的話語權(quán)。如果不使用新媒介,閱讀理解每一本中國古代著作,都需要深厚的中文和歷史功底,這不僅對于中國大眾來說難度很大,對外國人難度更大。如果直接向海外推出中國古代著作,受眾群體會比較小,這很不利于中國文化走出去。因此,對新媒介的運用至關(guān)重要。
近年來,美國大眾文化利用新媒介強勢輸出,極大程度上鞏固并加強了其話語地位。在許多大眾心目中,不知不覺把美國代表的西方文化的規(guī)則和標準當做了我們的規(guī)則和標準。參考美國經(jīng)久不衰的肥皂劇《老友記》(《Friends》),美國在各個國家獲得巨大版權(quán)收益的同時,也向全球觀眾展現(xiàn)了美國青年的生活方式,這極大地吸引了全球觀眾開始主動探索、模仿美國文化更多方面,甚至成了不少海外年輕觀眾前往美國留學的初始動力。伴隨《老友記》的風靡,更多美劇也走進了海外觀眾的生活。在全球范圍內(nèi),出于對影視劇中美國文化的興趣,許多年輕人主動開始學習英語,閱讀原著,看原聲作品,吸收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文化,這對西方話語權(quán)的增強有重大意義。由此可以看出,使用新媒介是對外推廣本國文化,爭取國際話語權(quán)的重要途徑。
我國利用新媒介進行文化傳播較為成功的例子,過去有“功夫”電影,現(xiàn)在有網(wǎng)絡文學。借助功夫電影,李小龍、成龍等影星和中國功夫名聲大噪,許多西方人甚至以為所有中國人都會些武功,對東方力量產(chǎn)生崇拜之情;借助網(wǎng)絡文學,尤其是玄幻、仙俠等籠罩著神秘東方色彩的小說,大量海外讀者對中國文化產(chǎn)生了濃厚興趣。由于網(wǎng)絡小說中關(guān)于“道”、“佛”等中國傳統(tǒng)文化符號出現(xiàn)頻率很高,有網(wǎng)站成立專欄介紹中國的“道”、“陰陽”、“八卦”等內(nèi)涵,許多書迷甚至互稱對方為“道友”12。
但是,并非所有中國傳統(tǒng)文化在海外都有這么好的群眾基礎。因此,在新媒介中使用西方觀眾熟悉的中國文化符號,利用其親和力,將其與更多觀眾所不熟悉的中國文化相融合,不失為一個重要的文化傳播方式。現(xiàn)在風頭正勁的網(wǎng)絡文學恰好就是運用了這樣的方式,仙俠、玄幻等主題的小說因包含許多西方讀者熟悉的中國功夫,輕松獲得大批粉絲,但其中還有更多陌生的中國文化,這些文化則成為西方讀者了解中國的新窗口。為了方便粉絲們理解這些中國文化,小說翻譯網(wǎng)站不僅對出現(xiàn)頻率很高的中國的道教、武俠概念進行了解釋,也提供了很多中國俗語和成語的解釋,例如“生米做成熟飯”、“癩蛤蟆想吃天鵝肉”等,以方便讀者的理解,客觀上促進了中國文化的傳播。
在文化傳播上,我們還可以參考其他國家的做法:借助他國文化符號,宣傳自身文化內(nèi)涵。美國的《功夫熊貓》其實恰好就是借助了海外觀眾最熟悉的中國文化符號比如功夫和熊貓,并把美國的思想融入其中,在各國都獲得了非常廣泛的喜愛。這方面做得很突出的還有日本。日本動漫粉絲遍布世界各地,即便是在美國、歐洲這些存在著巨大文化和語言障礙的地方,年輕人也狂熱于日本動漫。但是,日本動漫并非只靠本土文化吸引海外觀眾。日本動漫首先是日本文化產(chǎn)品,會體現(xiàn)日本的價值觀和民族特質(zhì),但是單純靠本民族特質(zhì)并不容易讓海外觀眾產(chǎn)生共鳴,而在產(chǎn)品中加入多國文化符號,則更容易讓海外觀眾產(chǎn)生文化親切感,吸引觀眾,從而進一步增強日本文化傳播的效果。舉個例子,《圣斗士星矢》便是借鑒了希臘神話符號,使西方觀眾感到熟悉,潛意識中消解了觀看的畏難情緒,但它的內(nèi)核卻是日本武士道精神:斗士們?yōu)楸Pl(wèi)雅典娜而浴血奮戰(zhàn),可以說是日本武士的翻版。同時,片中也融入很多日本特色符號:櫻花、和服、便當?shù)榷嗵巸?nèi)容都在傳遞著鮮明的日本特色。通過對動漫的喜愛,粉絲們開始主動了解日本文化,學習日本文化,這對日本文化海外影響力的形成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
四、結(jié)語
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提出,要“堅定文化自信,推動社會主義文化繁榮興盛13”,要“深入挖掘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蘊含的思想觀念、人文精神、道德規(guī)范,結(jié)合時代要求繼承創(chuàng)新,讓中華文化展現(xiàn)出永久魅力和時代風采14”,要“推進國際傳播能力建設,講好中國故事,展現(xiàn)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15”。
我們的現(xiàn)狀是文化符號活躍,文化規(guī)則失語;也可以說我們的文化規(guī)則暫時失語,而文化符號愈發(fā)在彰顯其生命力,這恰好也為我們多年來的失語癥提供了治愈的良機。在國際文化交流越發(fā)頻繁的今天,我們不能再跟在西方國家后面亦步亦趨,更不能在國際社會上任由西方戲說中國故事。建設好國家文化、在國際社會上響亮發(fā)聲,不僅是中國向世界展示真實自我的需要,更是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經(jīng)之路。我們擁有五千多年的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近百年的文化自卑和自戕是時候畫上句號了。處在世界發(fā)展日新月異的新時代,打通與傳統(tǒng)文化的阻隔不僅意味著中國文化實力的顯著增強和中國文化特色的回歸,更意味著世界可以從此更好了解立體的中國,從而讓中國在國際社會擁有更強話語權(quán)。
在科技高度發(fā)達的今天,我們不必再為文言文退居二線而痛心疾首,新媒介已為我們提供了傳承、傳播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多種途徑。通過新媒介向大眾普及中國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不僅能夠讓大眾更加了解我們深厚的文化底蘊,更能夠增強國人的文化自信和自豪感,讓我們在國際文化交流中更有實力,也更有底氣。借助新媒介,參考他國文化傳播的方式,更好地讓中國文化走出去,讓世界了解中國文化、喜愛中國文化,則能為中國文化打造更好的國際環(huán)境,從而促成中國話語權(quán)更早的回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