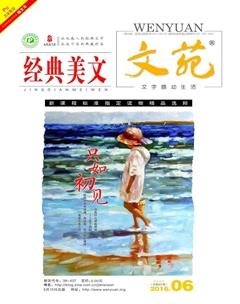蠶兒
陳忠實
從粗布棉襖里撕下一疙瘩棉花,攤開,把一塊綴滿蠶子兒的黑麻紙鋪上,包裹起來,裝到貼著胸膛的內衣口袋里,暖著。在老師吹響的哨聲里,我慌忙奔進教室,坐在課桌旁,把書本打開。
老師駝著背走進來,側過頭把小小的教室掃視一周,教室里頓時鴉雀無聲。
“其他年級寫字,二年級上課。”
老師把一張乘法口訣表掛在黑板上,領我們讀起來: “一六得六……”
我念著,偷偷摸一下胸口,那軟軟的棉團兒,已被身體暖熱了。我想把那棉團兒掏出來看看,但瞧瞧老師,那一雙眼睛正盯著我,我立即挺直了身子。
一節課后,我跑出教室,躲在房檐下,展開棉團兒,啊呀,出殼了!在那塊黑麻紙上,爬著兩條螞蟻一樣的小蠶兒,一動也不動。我用一根雞毛把小蠶兒黏起來,輕輕放到早已備好的小鐵盒里。再一細看,有兩條蠶兒剛剛咬開外殼,伸出黑黑的頭來,那多半截身子還卡在殼兒里,吃力地蠕動著。
上課的哨聲響了。
“二年級寫字。”
老師給四年級講課了。我揭開墨盒。那兩條小蠶兒出殼了吧?出殼了,千萬可別壓死了。
我終于忍不住,掏出棉團兒來。那兩條蠶兒果然出殼了。我取出雞毛,揭開小鐵盒。
哐,頭頂挨了重重的一擊,眼前直冒金星,我幾乎從木凳上翻跌下去。老師背著雙手,握著教鞭,站在我的身后。慌亂中,鐵盒和棉團兒都掉在地上了。
老師的一只大腳伸過來,一下踩扁了那個小鐵盒;又一腳,踩爛了包著蠶子兒的棉團兒。我立時閉上眼睛,那剛剛出殼的蠶兒啊……教室里靜得像空寂的山谷。
過了幾天,學校里來了一位新老師,一二年級分給他教了。
他很年輕,站在講臺上,笑著介紹自己: “我姓蔣……”捏起粉筆,在黑板上寫下他的名字,“我叫蔣玉生。”
多新鮮啊!四十來個學生的小學,之前只有一位老師,稱呼中是不必掛上姓氏的。新老師自報姓名,無論如何算是一件新奇事。
那天,我爬上村后那棵老桑樹摘桑葉,慌忙中松了手,摔到地上,臉上擦出血了。
“你干什么去了?臉上怎么弄破了?”蔣老師吃驚地問。我站在教室門口,低下頭,不敢吭聲。
他牽著我的胳膊走進他住的小房子,從桌斗里翻出一團棉花,又在一只小瓶里蘸上紅墨水一樣的東西,往我的臉上涂抹。我感到傷口很疼,心里卻有一種異樣的溫暖。
“怎么弄破的?”他問。“上樹……摘桑葉。”我怯生生地回答。
“摘桑葉做啥用?”他似乎很感興趣。“喂蠶兒。”我也不怕了。
“噢!”他高興了,“喂蠶兒的同學多嗎?”“小明、拴牛……”我舉出幾個人來,“多哩!”
他高興了,笑瞇瞇的眼睛里,閃出活潑而好奇的光彩,說: “你們養蠶干什么?”
“給墨盒兒做墊子。”我話又多了, “把蠶兒放在一個空盒里,它就網出一片薄絲來了。”
“多有意思!”他高興了,“把大家的蠶養在一起,擱到我這里,課后咱們去摘桑葉,給同學們每人網一張絲片兒,鋪墨盒,你愿意嗎?”
“好哇!”我高興地從椅子上跳下來。
于是,他領著我們滿山溝跑,摘桑葉。有時,他在坡上滑倒了,青草的綠色液汁黏到褲子上,也不在乎。
三天后,有兩三條蠶兒爬到竹籮沿兒上來,渾身金黃透亮,揚著頭,搖來擺去,斯斯文文地像吟詩。它要網繭兒哩!
老師把一個大紙盒拆開,我們幫著剪成小片,又用針線串綴成一個個小方格,把已停食的蠶兒提到方格里。
我們把它吐出的絲兒壓平,它再網,我們再壓,強迫它在紙格里網出一張薄薄的絲片來。老師和我們,沉浸在喜悅的期待中。
“我的墨盒里,就要鋪一張絲片兒了!”老師高興得像個小孩, “是我教的頭一班學生養蠶網下的絲片兒,多有意義!我以后不管到什么地方,一揭墨盒,就看見你們了。”可沒過多久,老師被調走了。他說: “有人把這兒的情況反映到上級那兒,說我把娃娃慣壞了!”
我于是想到村子里的許多議論來。鄉村人看不慣這個新式先生——整天和娃娃耍鬧,沒一點兒先生的架勢嘛!失了體統嘛!他們居然不能容忍孩子喜歡的一位老師!
三十多年后的一個春天,我在縣教育系統獎勵優秀教師的大會上,意外地碰到了蔣老師。他的胸前掛著“三十年教齡”的紀念章,金光給他布滿皺紋的臉上增添了光彩。
我從日記本里給他取出一張絲片兒來。
“你真的給我保存了三十年?”他吃驚了。
哪能呢?我告訴他,我中學畢業后,回到鄉間,也在那所小學里教書。當老師的第一個春天,我就和我的學生一起養蠶兒,網一張絲片兒,鋪到墨盒里。無論走到天涯海角,我都帶著踏上社會的第一個春天的“情絲”。
蔣老師把絲片兒接到手里,看著那一根一縷有條不紊的金黃的絲片兒,兩滴眼淚滴在了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