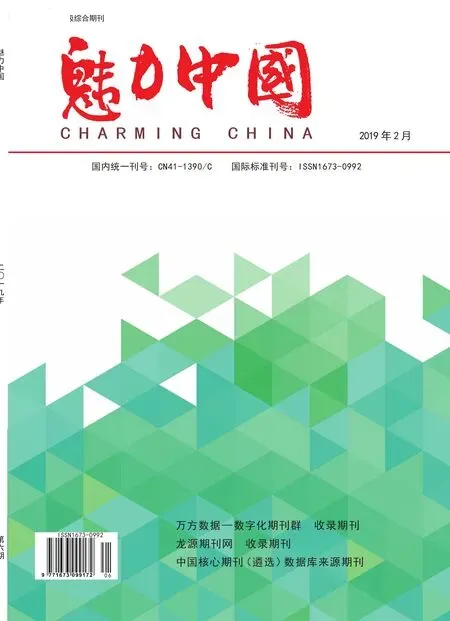從竇光鼐看諸城竇氏家族特點
胡金娣
(諸城市博物館,山東 諸城 262200)
明、清兩朝是中國世家文化發展的鼎盛時期,世家文化的載體是接代傳承的世家大族,諸城適宜的自然環境和繁榮的經濟基礎,成為世家大族形成發展的理想境地。而厚重的歷史底蘊和濃郁的文化氛圍,使這些世家大族傳承文化擁有了取之不竭,用之不盡的源泉。諸城出現了臧、王、劉、李、丁、邱、竇、張等名門望族。這些世家望族將內蘊豐厚的家族文化接代傳承,創新發展,涌現出眾多的文人名士,形成了獨具地方特色的諸城“名人文化”現象。名人文化的主體是文化名人,而文化名人多是世家大族中文化傳承的佼佼者。
諸城竇氏家族于明朝洪武年間由山海關遷來,竇光鼐祖上有多人出仕,但所任多為教諭、訓導之類低職微官,在諸城境內并不顯著,直至竇光鼐一輩,僅一人成為聲名顯赫的朝廷重臣,竇光鼐以其一人之力使家族聲望蜚聲海內,載于史冊。
竇光鼐(1720——1795),字元調,號東皋,世稱東皋先生,諸城西郭家埠村人,清中期著名學者。竇光鼐自幼聰穎,7歲能撰辭章,9歲應童子試,12歲作《瑯琊臺賦》,15歲中博士弟子員(秀才),17歲鄉試副榜,22歲中順天鄉試舉人,23歲進士。歷官翰林院庶吉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南書房行走、河南學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浙江學政、兵部左侍郎、順天府府尹、宗人府府丞、都察院左都御史等。其生平博覽群書,學問淵博,書法端正秀麗,風骨挺勁。傳世著作有《省吾齋詩文集》、《東皋詩集》等。
竇光鼐幼年家境貧困潦倒,竇光鼐在《先府君行狀》中對當時的困境作了較詳細的記述:“先王父方疾,即命府君分爨。及沒,府君力營喪葬,藏事,遂大窘。故分田僅四十畝,強半荒蔓,乃謀與四叔子光公并力耕墾,會秋大熟,乃能自存活。”即使竇光鼐步入仕途后,因奉行“持身嚴正”“清正廉明”的家訓,處世廉潔,所以其家境并未得到徹底改觀。其在《先太夫人行狀》中記:
不孝光鼐復蒙恩擢左中允,母以不孝年少荷主知,再三訓淬勉焉。然自是疾,洊至不能就養京師。山左值歲歉,家有薄田半荒蔓,不能給朝夕。不孝間縮俸郵寄,吾母必量分諸伯叔之匱乏者,而己食其糲,曰:“吾不獨飽也。”
此事清道光《諸城縣續志》亦有記載:“父卒時,以金賻者,悉卻之,曰:‘吾自翰林至京兆,未嘗受人財,豈以親歿為利乎?’久宦京朝,至饔飧不給,其清節尤為世所重云。”如此之清廉家族,有清一代,實為罕見。家境長期拮據是諸城竇氏家族的特色,而正是這一特色,向世人證明了,清正廉潔是竇氏家族世代相傳的族訓,亦是竇氏家族出仕的成員必須發揚的家風。
傳承家族文化,是維系一個家族興旺發展的重要措施,世家大族非常重視對后代的文化教育,竇氏家族盡管家境拮據,也從沒放松對子女的文化教育。竇氏的家庭教育具有自己的特點:幼小啟蒙,家館結,要求嚴格。
竇光鼐在《先太夫人行狀》中追憶母親對他們的教育:(光鼐)方學語,轍教之,識數百字。及六歲,從家大人館于翰林高云亭先生家。人謂母曰:“能離舍乎?”母曰:“男兒終不畜于家,何吝也?”家大人命不孝省親,逾一二時,母轍促之行。
從以上記載可知,竇光鼐的啟蒙教育是在家里,“方學語,轍教之,”第一任老師就是父親。竇光鼐的兒子竇汝翼等對此事亦有記載:“幼即聰穎,五歲隨先大父學,每課百余行,讀一兩回即能成誦。”至六歲時,跟著父親“館于翰林高云亭先生家。”
諸城竇氏家族除竇光鼐外,再也無人進入高官階層,即便是竇光鼐,最終也以四品銜告退。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狀況呢?筆者認為,這與竇氏家族的家風有密切關系。竇氏家族以持身嚴正、剛直不阿為做人的準則,進入仕途后,所反映出的個性是:清正廉明,嫉惡如仇,堅持正義,不懼犯上。因為他們不顧忌得罪旁者,不會阿諛奉承,所以他們在仕途上就會遇到很多坎坷,難以得到升遷。
竇光鼐的性格從各方面都能體現出來,其在《先府君行狀》中記:“及不孝居翰林,亡弟光鉞方從府君治舉子業,有傳言不孝持論好異者,府君手書責之,寄《家訓》一卷以為警。其明年,府君至都,見不孝所為文字,喜曰:‘所見近正矣!人乃以為異,顧汝與人議論好勝,宜亟除。’”從此記載可以看出,竇光鼐的性格剛直好勝,已經得罪了不少人了,連父親都聽到了傳言,對他進行勸阻。對于竇光鼐的性格,王賡言評價云:“憨直,不可干以私。任京兆時,力遏權貴,鋤吏民之不法者。視學浙江,參地方一官貪黷,幾罹不測,公矢志不回,卒能申其意,浙人至今感之。”
王賡言《東武詩存》中記載:竇光鼐為官多年,上深知其學識淵博,詔為太子太傅。一日,講《書·堯典》篇,太子之左股疊動,勢如顫然。竇正色曰:“為人上者,曷其奈何弗敬?”太子乃肅敬竇教綦嚴,欲使其《書》旨純粹,文治乃光華也。而太子苦不能耐。乾皇忽起溺愛之心,親自舉步,至御書房中,謂竇曰:“太子系儲君,功課宜少寬貸。”竇曰:“師嚴然后道尊,且《書》以道政事,《書》理洞曉,政治乃光昌。欲為明君,當自力學始。”上曰:“力學為天子,不力學亦為天子。”遂偕太子以出。甫至門外,竇厲聲曰:“力學為堯舜天子,不力學為桀紂天子。”上惡其抗言不遜,置若罔聞。回至宮中,默坐沉思,深是竇言,自悔言之不謹,失尊師重儒之道。遣親王某代為遜謝,復令太子入校,而竇之教法如初。后高宗晏駕,太子即位,年號嘉慶。因力學有年,而敷政無缺,得稱明君。人咸曰:“竇公固良師,高宗亦明君也。”
上文所記之事,在諸城民間亦流傳甚廣,家喻戶曉,并演繹成數個不同的版本。在這里我們既看到了竇光鼐身上透出的剛正不阿的峻厲家風,也看到了其體現出的竇氏家族重視教育的傳統。
諸城竇氏家族無論在經濟、政治和官宦方面,與境內其他豪門相比,顯得頗為寒微。其經濟狀況自始至終處于結據狀態。正是這種平民的境況,培養出了竇氏家族質樸、善良、和睦,和處事低調的傳統。嚴格的家教與剛直不阿的家風,是竇氏家族傳承中的重點所在,剛直不阿的家風始終貫穿于家族的傳承中。從竇光鼐身上我們可以看出諸城竇氏家族的鮮明個性和特點,竇氏家族熏陶出了竇光鼐一代名臣,并使其家族流芳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