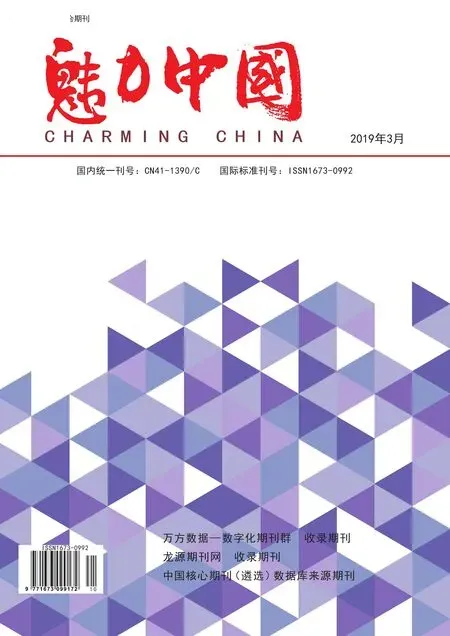魯迅與契訶夫小說藝術的比較分析
曾燾 李有 陳星行
(四川成都 武警警官學院,四川 成都 610213)
一、契訶夫小說的情節特征
在契訶夫的作品中結局的表現主要有兩種模式。模式一:具有意外效果的結局。這種帶有幽默感的驚喜的結局會給我們留下深刻的印象。例如他的早期散文《演說家》、《馬姓》、《蠢貨》、《乞丐》、《無題》等。模式二:“無結局”,也就是沒有盡頭的結局。契訶夫成熟時期的作品很少會直接表現人物與周圍環境發生碰撞后的結局,這種碰撞就像是一種不可避免的災難。通常,他會停止對災難邊緣的敘述,不會花所有的精力在悲劇的完整性上,而是會在日常生活或瑣碎的事務中表現悲劇。
時間越長,契訶夫越是意識到需要擺脫“結局”的影響.傳統意義上的“結局”也就是主人公或是結婚,或是被射死,再不會有其他的可能。然而契訶夫最終創作出了不同往常的結局模式。作品《帶狗的女人》正是典型的契訶夫第二種結局模式的例子。正當復雜的情景和巨大的矛盾暴露出來時,作者停止了敘述,并沒有給故事的主人公設定一個結局,而是把這個謎題拋給了讀者。這正是契訶夫成熟時期小說創作的特點。俄羅斯學者康福德首次詳細的闡述了這種方式,并將這種創作方式稱為“開放式結尾”。從這也可以看出契訶夫是多么的重視結尾的設計。契訶夫這種結尾的創作和他自身行為的一些基本原則也有很重要的聯系。這種方式基于客觀事物描寫和主觀判斷的原則,轉移核心矛盾就是為了讓讀者有機會更加深入的思考。這和極筒主義原則有很緊密的關系。許多這些情節結構特點中的原則與魯迅作品的藝術結構特點具有相同點。
二、魯迅小說的情節特征
魯迅作品的獨特性和深厚民族性是得到社會普遍認可的。他和世界上所有偉大的作家一樣,都是由本民族的文化孕育出來的。魯迅的早期創作受到了19世紀歐洲和俄羅斯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直接影響。眾所周知,這種創作手法最顯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它在社會歷史運動和發展的背景下概述了一個人的性格和他精神世界的特征,強調了個人的社會屬性,人的性格變化也是受到社會的影響而產生的。這種暴露社會現象的創作題材在俄羅斯19世紀現實主義作家的作品中被表現得尤其鮮明。具有鮮明的現實主義精神,廣泛的社會生活方面的內容和對社會制度的披露,正是魯迅的第一部作品與19世紀俄羅斯現實主義文學的相似特征,這也是表現出二者聯系的重要標志。
與契訶夫不同的是,魯迅總是在思考周圍的社會環境,專注于創造一個典型的人物。其作品的情節構圖是基于人物角色性格的創造和內心世界的展示。說到典型人物,我們首先想到作品《阿Q正傳》中鮮明的人物形象阿Q,他已經被認為是世界文學史上不朽的角色之一。法國著名作家羅曼·羅蘭在讀完這個故事后很欽佩地說:“這是真正的藝術,接連不斷的反諷和阿Q哀愁的表情將永遠留在我的記憶中。”在刻畫人物的過程中,魯迅“真實的重現了當時的時代背景和人們所處的社會環境,展現了人物行為的大背景。”在《阿Q正傳》中沒有單純的背景描寫,所有內容都融合在角色的描寫中,這種描寫方式讓人深刻地意識到環境和角色有機地結合在了一起。此外,角色內心世界的解剖也是表現性格的重要手段之一。
三、魯迅和契訶夫小說的敘述手法
在契訶夫的作品中,第一個人“我”,經常扮演主角和敘述者的角色,例如在《我的一生》、《匿名氏的故事》、《醋栗》、《在別墅里》,《套中人》,《太太們》等等。但是契訶夫總是保持自己和‘主人公’之間的距離,永遠不會讓這個“我”成為一個能夠隨時審判所有事情和所有人的法官。契訶夫本人指出需要區分作者和敘述者。但是魯迅和契訶夫的作品在第一人稱的運用上存在差異。在魯迅的作品中,第一人稱“我”通常可以代表作者本人或與他觀點接近的人。作品《狂人日記》的結論是,中國五千年的文明不過是‘吃人’的歷史,是作者想要通過這個故事傳達的核心思想。
魯迅也愛第一人稱敘述。但他的第一人稱“我”卻具備天真獨立,生動活潑的性格特點。在每一個“我”中,讀者都能夠清楚地感受到作者的感受和情緒,這是因為魯迅本人對自己的要求很高。他說:“我的確時時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更無情面地解剖我自己,發表一點,酷愛溫暖的人物已經無論是誰,只要在中國過活,便總得常聽到“他媽的”或其相類的口頭禪。”因此,可以相信魯迅故事中的第一人稱敘述者代表著一個與作者本人觀點非常相似的人物。因此,作者對敘述者的批判和諷刺的態度可以被認為是作者本人或與他相似的人的“解剖”。契訶夫和魯迅的第三種敘述類型一一不是主人公,也不是陳述、觀察者,而是一個站在故事敘述之外的無所不知的作家,敘述事件。當然,這種第三人稱敘述的方法也是最常被使用的。
契訶夫和魯迅都是現實主義作家,他們的象征主義都是分散在各個故事中的,如人血饅頭(《藥》),墓碑上的花環(《明天》),辮子(《彷徨》),長袍(《孔乙己》)。阿Q是民族劣根性的象征,他的各種惡習,和性格缺點如“精神勝利法”,以及其他一些愚蠢的思想觀念,被認為反應了中國的國民性,是民族在近代落后的根源。值得注意的是,魯迅的象征形象主要來自安德烈耶夫。魯迅寫道:“在安德烈耶夫的作品中保留著嚴肅的現實,有深度且描寫很細致,印象派和現實主義在他的作品中是和諧的,除了他,沒有人能夠消除內在世界和外部現象之間的差異,展現靈魂和肉體的統一。”盡管他的作品具有象征主義的氣息,但仍然不缺乏現實主義。”象征手法的運用并沒有改變魯迅現實主義的創作風格。反而增強了現實主義的泛化能力。這也揭示了魯迅與契訶夫作品之間的關系。他們都不是象征主義者,但卻廣泛使用了一種現實主義可以接受的文學象征手法。這是另外一點可以證明兩個偉大作家相似性的例證。
四、結束語
契訶夫終其一生反對庸俗主義,魯迅則終其一生反抗封建專制主義。看起來差別很大,但事實是,他們的這種斗爭和批評,都屬于政治活動領域,屬于生活的倫理和文化方面,這使得它在尋求真理方面具有普遍性和持久性。契訶夫和魯迅都是生活在本世紀后半葉的轉折時期,處于本國文學發展的高峰時刻。他們的作品與社會變化密切相關,這一點進一步深化和擴大了作品的社會意義。比較契訶夫和魯迅的作品,不僅讓我們有機會了解到俄羅斯經典作品對中國文學的影響,還可以看到兩國文化是如此的相近,以及這兩位偉大藝術家在創作基因和創作原則上的相互聯系。任何杰出的文化創造不僅有助于豐富民族文化傳統,也豐富了世界文學寶庫它提升了整個人類文明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