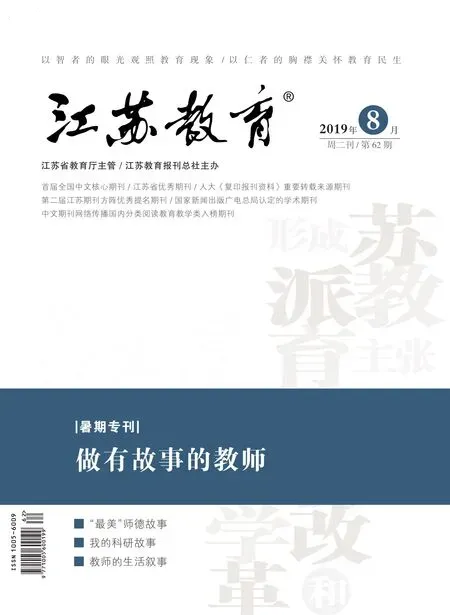科研工作最講認真
彭 鋼
我一生的正式職業就是從事教育科研工作,經歷和積累了很多有意思、耐尋味的故事。這里我講三個故事。
故事一:黃埔一期
我20 世紀80 年代初大學畢業后進入江蘇省教育科學研究所工作。當時也就是一個糊里糊涂的“菜鳥”,對教育的認識和理解一片空白,對教育科研更是一無所知。1985 年初,當時的上海市教育科學研究所舉辦了首屆面向全國的教育科研方法培訓班(后來得知,這是全國最早的實證研究方法的培訓班),很榮幸領導派我去參加了這個培訓班。江蘇一共有四人參加:南京市教科所的負責人陶志明、常州市教科所所長朱川彬、徐州市教科所所長張夕吾,后來我們把這個班戲稱為“黃埔一期”。
這個班一共15 天,培訓的內容主要是實證研究的“三法兩工具”,即觀察法、調查法、實驗法、教育測量、教育統計,再加上一些其他先進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實踐。對我們每一個人來說,這些內容都是完全陌生而新鮮的。我們住在華師大二附中的學生宿舍,每個房間住8 人,上下鋪,每天上午聽課3.5—4 個小時,下午聽課3小時左右,晚上我會把白天的聽課筆記對照教師所發的講課提綱和講義完整地梳理一遍。課程安排得很滿,學習生活非常緊張,但我從來沒有聽到學員叫苦喊累。
在這個培訓班上,我有幸認識了顧泠沅,他發明了本土方法——“經驗篩選”,成功地運用教科研提升了青浦的數學教學質量,后來成為中國教育科研的大家;認識了創造“茶館教學法”的育才中學的段力佩校長,他的講課極富啟發性和煽動性,很吸引人,下面掌聲雷動;認識了青年才俊鐘啟泉,他給我們講了完全不同于“茶館教學法”的掌握學習,我第一次聽到了“教學過程控制”的概念,知道了通過“診斷性測驗”“形成性測驗”“總結性測驗”達成教學目標的科學教學理論。后來布魯姆1989 年到中國上海來,目標教學(掌握學習)風靡了全中國,一直到現在影響仍然很大。
15 天的培訓回寧后,根據穆嘉琨所長的要求,我把課堂筆記全部整理出來,約有5 萬多字,發表在當時的《教育科研動態》上,拿到了我工作以后的第一筆稿費180 元(當時我每個月的工資只有56 元)。更為重要的是,這深刻地影響了我。在我的全部職業生涯中,可以說最為關注的就是方法,運用最為自覺的是方法,講課最精彩的也是方法。后來我當了17 年的規劃辦主任,對學校承擔項目最為有效的指導也是從方法角度(包括廣義的方法設計)。聽說所謂的“基于證據的研究”成為一種新潮,我很納悶:怎么還會有不基于證據的研究,實證方法給出的就是一種收集證據、分析證據、處理證據、表述證據的思路和方式。教育學研究的證據不像犯罪學那么難以采集,幾乎遍地都是,問題是你得運用學界承認的合法、規范、有效的方法去采集證據。現在回想起來,這15 天的認真學習及回寧后的認真總結,奠定了我職業生涯的重要基石,具有極高的回報率。
故事二:如東“創業教育實驗”
1989 年在北京召開了面向21 世紀的國際圓桌會議,會議提出了“三張證書”(“學術證書”“職業證書”“創業證書”)的新理念。1990 年我們在毛家瑞副所長的領導下,承擔了聯合國教科文亞太地區辦事處“創業教育”的項目研究。該項目選擇了如東縣兩個鄉的成人教育學校進行實驗。選擇的理由很簡單:項目要求在弱勢地區的弱勢群體中進行,當時的成人教育針對的都是學歷層次較低的農民,更重要的是當時的如東教育局局長嚴仲清高度重視科研,還有一個強大的教科室能夠支撐研究。
我們幾乎每月去一次如東:從南京的下關碼頭坐一個通宵的船到南通碼頭下,再從南通坐2 個小時的汽車才能到如東。每次去都做一樣的事情:考察調研實驗學校,與基層同志現場研討,商量下一步的實踐重點和操作策略。這樣持之以恒地堅持做了三年實驗,從成人教育領域擴展到職業教育領域,再擴展到基礎教育領域,從如東縣擴展到通州、泰興、江寧,從江蘇走向全國,走到聯合國教科文的東京會議和泰國會議。在全國核心刊物上發表論文幾十篇(在《教育研究》上就發表了課題組關于創業教育的5 篇文章),出了“創業教育”兩套叢書,我個人則完成了兩部“創業教育”專著,后來該項目獲得第二屆全國教育科研成果二等獎。目前創業教育已風靡全國,成為教育研究尤其是高等教育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我們可以驕傲地宣稱,最初的創業教育文獻均來自20 世紀江蘇省教科所的項目研究所發表的文章。
現在回想起來,當時省教科所的一批年輕人所具有的“非凡”的研究勇氣,真的可以說是“無知無畏”。我當時在省教科所的情報研究室擔任副主任(主要負責編輯內刊《江蘇教育研究》),當毛所長把這個任務交給我的時候,我連想都沒想就答應了,根本就沒有想過其中的艱難險阻。而共同承擔這個項目的我的年輕同事蔡守龍、丁偉紅、馬維娜等人,也是無所畏懼、勇往直前。當然,更為重要的是認真、勤奮、執著、頑強的態度和精神。當時的我們太認真、太勤奮了,幾乎每個人都把自己所承擔的項目研究工作放在了首位,幾乎每個人都在分工中做到了優異和極致。
在當時的中國,可以說“創業教育”只是一個理念和口號,完全是理論與實踐研究的空白。唯一的文獻是教育部教育發展中心的王一兵撰寫的面向21 世紀的國際圓桌會議的紀要,在此紀要中,他將英文enterprise education 翻譯成企業家精神教育,而我們經過反復商量,直接就翻譯成“創業教育”,并一直沿用至今,這是最值得我們驕傲的成就之一。在這樣的背景下,本土性、原創性的實踐創造,即如東縣的實驗成為理論創新的重要源泉。幸運的是,我們不僅創造了實踐,而且創造了新的理論話語和理論模型(盡管還粗陋)。前些年東北師大某教授忽然造訪,他寫了一本《中國創業教育史》,其中一章的文獻運用了大量我們研究的資料(公開發表的),與我和馬維娜相談甚歡,大概是認為找到了創業教育研究的“祖宗”。
當然,高人指點也十分要緊。當時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副所長滕純聽說江蘇南通高度重視教育科研,如東有個馬塘小學教育科研轟動全國,有個著名校長曹玉蘭很有水平,一定要來看看,于是我陪他去了南通和如東。他聽了我匯報創業教育的研究,讓我去申報全國教育科學“九五”規劃項目,后來果然申報成功;又建議我們進行創業成功和創業不成功的比較研究,并在此基礎上建構“創業教育模型”,為理論建構提供了重要的方法指導。創業教育研究可以說是我職業生涯中最重要的研究,也是最有影響的研究,為我今后領銜做大規模的項目研究奠定了基礎。
故事三:塔城師范的“科研”
1997 年春節后我作為改革開放后的第一批援疆干部到了新疆,于是我在位于祖國西北邊陲的塔城師范學校工作了三年。一年后,我終于爭取到分管教學和科研工作。
在一次我所主持的內地學校考察學習的交流會議上,教師們幾乎一致的觀點引起了我的高度重視和警覺:內地學校除了辦學條件好、收入高以外,教師水平和教學水平并不比我校高。于是我運用廣義的方法,設計了開展課堂教學研究的三部曲:一是調研課堂教學,二是建立分析框架,三是開展科研培訓。
1998 年春節一開學,我就用自己的方法開始大規模的課堂教學調研,根據教務處提供的教師名錄和課程表,在漢族教師中圈了30 人作為聽課對象,總共聽了80 節課,與執教者進行了隨機交流和訪談,并按我自己的研究框架對收集到的數據和案例進行分析處理。于是在全校教師大會上做了第一次報告,用翔實的數據和案例表明我校課堂教學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引發了全校性的“地震”,基本摧毀了他們教學自我感覺太好的錯誤觀念。
接著,我在研究和分析教育部師范教育司組織全國專家打磨出來的師范教育精品課的研究基礎上,提出了好課的分析框架。十節課來自學校統一購買的錄像,據圖書管理員說購回后放了幾年,壓根就沒有人借過、看過。我調出了這十節課,對著錄像反復觀看、反復研究,包括美術課和音樂課,并在此基礎上提煉出好課的基本框架和基本標準,并以這十節課為例,給全校教師講“什么是一節好課”,以便在觀念層面建立起“好課”的基本概念。這次講座再次引發全校性的轟動,開始有教師主動向我承認,北京、上海、江蘇的師范教育確實水平比他們高,說明他們開始建立新的參照體系和公認的、統一的比較標準,而不再憑感覺、靠想象了。
征得校長蘇志樸的同意和支持,我準備在全校培訓教師,給學校留下教學研究和科學研究的種子。于是我出了一張試卷,一共三道題目:一是原文摘錄一段你最喜歡的教育家的名言,說一說喜歡的理由;二是通過調查和訪談的方式,盡可能客觀地向你教的學生征求教學意見和建議,描繪出你自己的教師形象;三是在此基礎上,明確自己教學中存在的問題,提出改善教學、提升教學的方向。我還在全校“揚言”,只要能夠提交自己的試卷,就可以來接受我的講課和培訓。這是一場全校教師的開卷考試,在這15 天中可以嘗試各種辦法去完成試卷。可以說這是一次難度很高的作業。據說全校每一個教師都做了這三個題目,但最后完整做完試卷并有勇氣提交試卷的只有37 位教師(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真實呈現自己需要勇氣)。但我已經很滿意了,我知道這一舉措,已經發揮了讓每一位教師去認識自己的教學工作、研究自己的教學工作、判斷自己教育教學成效、思考自己如何改進和提升教學的應有作用。
我在研究和分析這37 位教師的試卷時,發現了很多感人的細節和文字,發現了教師的職業良心、教師對學生的愛、教師迫切的學習愿望、教師追求更好的教學的強烈需求,還發現了有可能成為好教師但先前完全沒有進入我的視野的人選。我深感驚喜,深受教育,同時十分不安。這使我認識到,對教育教學的認識和理解,不僅需要科學更需要人文,不僅需要所謂的理性更需要有對人性的把握和寬容,不僅需要科學方法更需要有對人的深切關愛。于是我重新準備了一次全校講座,以這37 份試卷為基本數據和典型案例,重建教師的教學信念,重建教師成為好教師的信念,重建教師成為專家的信念,同時告訴教師不能通過自我感覺、自我想象、自我陶醉去尋找教學成效和自我形象,而應通過與學生交往、通過課堂中的學習行為、通過反映在學生身上的學習成效和成長來“迂回”和反射。
這樣我開始了每周一次的教師培訓旅程。每次我講一個半小時,留下半小時集體討論。第一次上課坐了滿滿一教室的教師,還有很多的民族(主要是哈薩克族)教師,讓我深感意外。我最后一次授課是1999 年的深冬,雪下得很大很大,講課結束后我與聽課教師在學校教學樓的雪地里合了一張影。回南京后,這張照片一直壓在我辦公桌的玻璃臺板下,想他們了就推開桌上的書看一眼照片。
這一年半的每周一次講課,養成了我堅持每天閱讀、每天備課的良好習慣,不然就沒得講,不然就不可持續。新疆的三年,也是我一輩子閱讀最為廣泛、最為深入的三年,為回到南京從事更高要求的科研工作進行了充分的知識和學養儲備,也養成了我竭力去理解教師、傾聽各種不同聲音、與教師一起討論、共同交流、深度探討的習慣。新疆的三年,更養成了我將復雜的概念和理論用自己的話語進行通俗表達的習慣,特別是在講課內容的選擇上,一定要與教學實踐關聯度大、教師容易感興趣的主題和方式來進行。每一次上課,都為下一次備課提供了研究、思考的空間和選擇。我面對的重大挑戰是,既要讓他們能夠學到一些最基本、最“管用”、最有啟發性的理論,又得緊密結合教學實際和教師自身實際,這就需要我不斷地調整自己的認識和理解,然后再具體實施,而絕不能一廂情愿,同時更不能放棄原則,遷就現實和后進。
三個故事講完,回到題目的理解上。第一層意思是說一種工作的態度,即始終保持著一種“認真”狀態:認真學習、認真籌劃、認真觀察、認真記錄、認真分析、認真處理、認真表述,體現著一種嚴格、審慎、專注的精神;第二層意思是說科研要根據真實的狀況,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這里的“真實”包括了“實際、實情、實理”,其中尤其不能忽視“實情”,科研工作需要不斷地通過與“真實”的互動,逐漸逼近“真相”;第三層意思就回到了科研“求真”的本質,這樣一種“真”可以說就是追求“真理”,即真相、真實背后的規律、原理甚至意義和價值,也可以稱之為“真正”。于是我發明了一句話,科研工作只認“真”不認別的,總結起來就是:科研工作最講認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