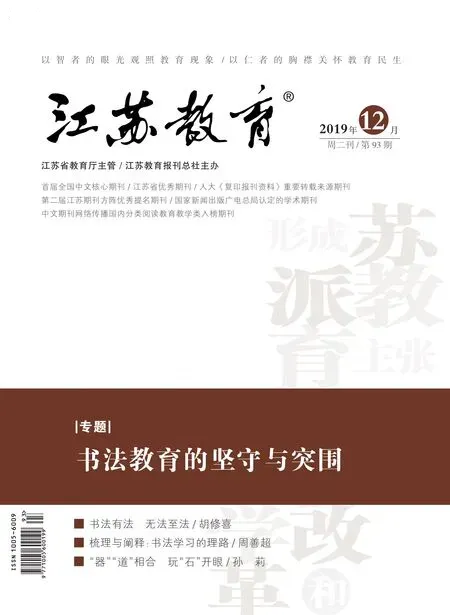梳理與闡釋:書法學習的理路
周善超
教育部《關于中小學開展書法教育的意見》和《中小學書法教育指導綱要》兩份文件頒布以來,書法教育在中小學校園得到了極大的推動,教師學習書法的熱情空前高漲。然而,光靠感性的熱情遠遠不夠,就像現(xiàn)在社會上很多學書法的人一樣,開始時興致很高,有的“筆性”也很好,但往往學習了一段時間以后,進步就不明顯了,甚至停滯不前。這是怎么回事呢?筆者認為這主要是沒有真正理解書法學習的“理路”。對此,筆者做一些梳理和闡釋。“理”,即原理、規(guī)律,也就是說,學習書法是有規(guī)律可循的,有它自身的、內在的原理;“路”,即路數、路徑、方法、體系,也就是說,學習書法是有路徑的,我們要在堅守“理”的基礎上尋找“路”的突圍。
一、楷書學習的理路
楷書種類繁多,風格各異,是書法史上一個十分龐雜的大家族,有的人學起來不注重方法、路徑、規(guī)律以及原理性的東西,往往“朝碑暮帖”“朝顏暮褚”,結果頭緒紊亂,路徑混濁,顯得很盲目。究其失敗原因是沒有去梳理書法史上楷書的風格體系和筆法傳承的脈絡。
那么,怎樣來梳理它們的風格類型和筆法體系的脈絡呢?中國美院王冬齡教授在其《書法篆刻》中說,楷書從風格上可分為兩個系統(tǒng),一是南北朝碑刻,其中尤以北魏碑刻最為著名,史稱“魏碑”;二是唐代碑刻,又稱唐楷。唐以后的楷書宋之蘇東坡,元之趙子昂均有所建樹,到了明清幾乎無著名碑版可言,然小楷卻卓有成就。所以,楷書可分為魏碑、唐楷、小楷三種類型。當代著名書法家黃惇教授曾提出中國書法史上楷書、行書的體系問題。他認為,從書法審美的角度看,中國書法史上的楷書可歸結為三個體系,即晉楷一系、魏楷(魏碑)一系和中唐楷書一系。我們深入想想就會發(fā)覺,上述兩位專家實際上正是為我們提供了明晰的學習楷書的三條路徑,這三條楷書路徑無論從哪一條開始學習都可以,但不能今天寫“鐘王”(鐘繇和王羲之),明天臨“顏柳”(顏真卿和柳公權),后天學“二爨”(《爨龍顏碑》和《爨寶子碑》),所謂“朝碑暮帖”。無論在哪一體系上學習,都應集中時間,集中精力,大量臨習這一系統(tǒng)內的碑帖,盡量做到搞懂搞透,各個擊破,待到某一體系楷書的技法(筆法、結字、體勢等)掌握了,鞏固了,再考慮學習另一個體系的楷書,或者學習其他書體。
筆者認為,學書應該從主流書風學起,這對于初學楷書者尤為重要。中國書法史上魏晉楷書一系應為主流書風,它肇于“鐘王”而流被后世,從釋智永到“初唐四杰”(歐、虞、褚、薛)無一不奉“鐘王”書法為圭臬,直到元之趙孟頫、明之文徵明等仍然全面?zhèn)鞒小扮娡酢币吕彙_@種由文人書家?guī)熗绞谑埽鄠鳎诠P法和審美意蘊上與“鐘王”一脈相承的楷書體系稱之為魏晉楷書一系。因此,從鐘繇——“二王”(王羲之、王獻之)——智永——“初唐四杰”(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趙孟頫——文徵明……魏晉楷體系非常明晰,且大多以小楷為主,中楷次之。從這條筆法傳承的脈絡上看,即元朝倪瓚的小楷、明朝王寵、徐渭的小楷都可以納入其中。因此,這是中國書法史上楷書諸體系中的主流,是學習楷書的正脈、大道,也是學習楷書的最佳理路。
魏楷即魏碑楷書,是北魏碑版及與北魏前后書風相近的碑志、石刻書法的總稱。嚴格意義上講,這是一種未成熟的楷書,其用筆與魏晉一系楷書大相徑庭,它的筆畫有明顯的刀刻、斧鑿之痕跡,初學者往往捉摸不透其筆法特征,甄別不出其優(yōu)劣,所以筆者并不主張學書者一開始就從魏楷學起。然而這種楷書恰恰又具有雄渾樸茂、恣肆爛漫、自然天成的特征,成為中國書法史上具有獨特個性的審美典型。清代已降,書壇碑學中興,書家“無不口北碑而寫魏碑”,碑學大家金冬心在《魯中雜詩》里說“恥向書家作奴婢,華山片石是吾師”。到了晚清,以何紹基、趙之謙、康有為等為代表的書家把魏碑書法推到了巔峰。即使到了近、現(xiàn)、當代,魏碑書法在整個書壇仍占有重要一席,其成績卓越者眾。大家可從那些魏碑名家的成功案例中得到啟發(fā)。所以筆者主張已具備了一定書法基礎的教師再來寫一寫魏碑也是很有必要的,它對豐富筆法、拓寬視域、提高創(chuàng)作水平和審美鑒賞能力都大有裨益。魏碑中的佳品如《張猛龍碑》《鄭文公碑》《龍門二十品》《石門銘》《二爨》等都可以選擇臨摹學習。
至于唐楷,這里主要指中、晚唐楷書(初唐楷書如虞世南、褚遂良等書家,從筆法上講,仍應歸入晉楷一系),其代表書家為顏真卿、徐浩、柳公權。
很大一部分人學習書法是從唐楷(“顏柳”)入手的,但從專業(yè)角度講并不利于以后的發(fā)展。當然,把“顏柳”當作學書基礎是可以的,但有了基礎以后就一定要學會“變”。因為顏、柳楷書用筆上最大的特點是起、收筆處重提按、多頓挫,小動作很多。尤其是“鉤”畫還出現(xiàn)了“三角鉤”“鵝頭鉤”等描頭畫角的華飾現(xiàn)象。若長期練習這種筆法,形成習慣,對過渡到行書學習非常不利。晚唐的柳公權,其筆法森嚴,結構緊斂,與魏晉那種崇尚質樸、自然、率意的書風相去甚遠。宋朝大書家米芾在《海岳名言》里講:“顏魯公行書可教,真(書)便入俗品。”他還說:“柳與歐為丑怪惡札祖,其弟公綽乃不俗于兄……”一針見血地指出了歐、顏、柳諸家楷書在用筆上存在的弊端。誠然,學習唐楷作為起初訓練運用筆墨的能力是可以的,但它于筆法上的弊病是顯而易見的,即很難用來打通與魏晉楷書之間的筆法通道,更不用說用這種筆法去寫行草書。也正因如此,中晚唐楷書在其后的宋、元、明歷代書家中幾乎沒有什么傳續(xù)。因此,對于長期系統(tǒng)學習書法的人,筆者并不主張把中晚唐楷書作為學習書法的主要取法對象。
二、行書學習的理路
(一)行書筆法體系
談到學習行書,人們自然就想到王羲之的《蘭亭序》。是的,王羲之是中國書法史上偉大的書法家,他的代表作《蘭亭序》被后人尊為“天下第一行書”。千百年來《蘭亭序》一直是人們學習行書的不二法帖。然而,學習行書并非只知道王羲之及其《蘭亭序》帖就行,仍然要厘清書法史上整個行書體系及其筆法發(fā)展的脈絡,因為王羲之以后的唐、宋、元、明歷朝書壇名家輩出,大師林立。行草書體系浩瀚而冗繁,在學習過程中很有必要對其進行梳理。按照行書筆法的演變脈絡,行書可分為三大風格體系,即“二王”行書體系、顏真卿行書體系和魏碑行書體系。
1.“二王”行書體系。
“二王”行書體系是以王羲之及其子王獻之為代表的包括釋智永、虞世南、褚遂良、李邕、陸柬之、楊凝式、米芾、蔡襄、趙孟頫、文徵明、董其昌、王鐸等書家在內的筆法代代相傳、風格一脈相承的行書體系。
從筆法和體勢上看,王羲之行草書具有平正和欹側兩方面的風格特征,后來的書法家在這兩方面各有取舍,各有所長,于是中國書法史上造就了王羲之書法的兩大分支,即:(平和一路)王羲之——釋智永——虞世南——陸柬之——蔡襄——薛紹彭——趙孟頫——文徵明等;(欹側一路)王羲之——王獻之——李世民——李邕——楊凝式——米芾——祝允明——王鐸等。以上是“二王”行書在后世的傳續(xù),到元明時已形成了一整套龐大的“二王”行書體系。
從學習角度講,我們認為,在“二王”行書體系中,先學平正一路的,后學欹側一路的比較合乎常理,然而這也并不是絕對的。應該指出,在“二王”體系的諸多書家中,無論從哪一家學起都行,也就是說,可以直接學“二王”,也可以間接學“二王”;可以由前人(“羲獻”)往下觀照后人,輻射后人;也可以由后人向上追溯前人,理解前人,從而逐步達到學習的目的。學習“二王”行書若按照這樣的理路進行,就是找到了學習的門徑,效果一定很明顯。
2.顏真卿行書體系。
顏真卿行書史稱“顏行”。顏真卿是繼王右軍之后的我國書法史又一座高峰,堪與王右軍比肩。探索顏真卿行書的本源,實際上仍屬于“二王”一系,這里之所以將它另立門戶,主要因為它能在傳統(tǒng)筆法中揉入篆籀筆意和強烈的外拓體勢。我們從《中國書法史》《歷代書法論文選》等專業(yè)書籍上也常常會讀到顏書有“篆籀氣”的評論。顏真卿書法能“納古法于新意之中,出新法于古意之外”,變傳統(tǒng)的“折釵股”為“屋漏痕”筆法,這是顏真卿在用筆上的一大突破,一大創(chuàng)新。他的書法對后世影響極大,五代的楊凝式,宋代的李建中、“宋四家”(蘇軾、黃庭堅、米芾、蔡襄),以及晚明的傅山,清代的劉墉、翁同龢、何紹基等個個得魯公書法之真諦。“魯公三稿”被后人奉為學習行書的典范之作,其中《祭侄文稿》更是被尊為“天下第二行書”。
3.清代魏碑行書體系。
清代魏碑行書簡稱“魏行”或曰“碑行”。清代魏碑行書體系是中國書法行書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清代碑學興起后,文人書家“無不口北碑而寫魏碑”,他們紛紛將魏碑用筆和結體融入“二王”行書或“顏行”之中,進行大膽融合嘗試。他們在行書的那種雋永、飄逸的風格中摻入碑銘書法的質樸、雄強之氣,讓二者有機結合,從而產生另外一種審美情趣。清代的何紹基、趙之謙、康有為、沈曾植、吳昌碩,現(xiàn)代的沙孟海、陸維釗、蕭嫻以及當代的王鏞、孫伯翔等都是這方面的杰出書家。
(二)楷、行、草諸體之間的銜接過渡
有了一定楷書基礎的人,總想早日進入行書階段的學習,因為行書更具實用性和藝術性,有人把寫行草書說成是毛筆在紙上“跳舞”,說明行草書更容易抒發(fā)性情。那么學了楷書后如何朝行書上過渡呢,它們之間是否有內在的聯(lián)系?當然是有的,比如說,學“二王”行書之前可先從褚遂良的楷書《雁塔圣教序》《大字陰符經》或趙孟頫的楷書如《膽巴碑》《三門記》學起,接著選擇釋智永的《真書千字文》或虞世南的《汝南公主墓志銘》、陸柬之的《文賦》等行楷書墨跡臨一臨,然后可上溯至王右軍的行書《圣教序》《蘭亭序》諸帖,最后可迂回至“宋四家”的行書上來,“宋四家”不僅可以上承晉、唐,還可以下啟元、明。這是一個很好的學書軌跡,因為它們在筆法上是一脈相承的。若在這樣的軌道上行進,就等于上了書法學習的“快車道”。而那種“只知顏柳,不曉褚薛,無論鐘王”的狹隘思路顯然是不夠的。路子對了學起來事半功倍,反之,則事倍功半,甚至會“南轅北轍”。倘若學了顏、柳之后直接去寫行書《蘭亭序》《圣教序》或“宋四家”,不但不能順利過渡,反而會因不見效果而喪失學書的信心。
學行草亦然,如唐代草書大師懷素的《自敘帖》,可謂草書之典范,后人學草書無不受其影響。可學了《自敘帖》后直接去臨習晚明張瑞圖、黃道周等人的行草書就很難一下子上手,原因是《自敘帖》幾乎全用“使轉”筆法,圓筆中鋒,筆線洗練,這是懷素用筆的一大特色,而張瑞圖、黃道周等行草書卻有過多的“翻折”用筆,特別是張瑞圖的用筆,方折緊束,下筆尖利橫撐,顯露鋒芒,凡行筆改變方向處,都用翻折筆鋒,棱角凌厲。清代梁巘說:“張二水書,圓處悉作方勢,有折無轉,于古法為一變。”這樣,我們就明白了懷素的草書與張瑞圖、黃道周等的行草在用筆上的差異了。初學者是很難在二者之間找到契合點的,若要硬著頭皮去寫,這就說明學習不講究“對路”。而應該用心琢磨,仔細研究,掃清書體之間的筆法障礙,找到書家之間技法相互貫通的秘籍,才能收到良好的學書效果。
三、隸書學習的理路
社會上學習隸書的路徑很多,有的先學楷書再學隸書,有的先學篆書再學隸書,也有的直接從隸書入手。還有些稱之為“魔鬼訓練營”的書法培訓班對隸書的訓練方法更是千奇百怪,高招百出。而本文提出隸書學習的“逆推法”,對于中小學書法教師來說,也相當于一種“準專業(yè)”書法訓練。
先簡要地來梳理一下隸書的發(fā)展脈絡:隸書萌于秦而成于漢。最初的隸書叫秦隸,也叫古隸。西漢早期的隸書也屬古隸范疇,如出土于湖南長沙的《馬王堆簡帛書》、山東臨沂的《銀雀山漢簡》等。西漢宣、元帝時期的簡牘已充分展示隸書的成熟形態(tài),一般把出土于河北的《定縣漢簡》視為隸書成熟的標志。然隸書的全面繁榮和鼎盛時期在東漢,集中體現(xiàn)在各種摩崖石刻和碑碣書法當中。東漢以后,三國兩晉仍然有隸書的余跡,自南北朝起到后來的唐宋元明則是隸書的全面式微期,盡管唐時也出現(xiàn)了幾位隸書名家,如史惟則、韓擇木,但放在整個隸書發(fā)展史上來觀照仍顯得暗淡無光。直到清代以降,因大興碑學,隸書迎來了其發(fā)展史上的又一個高峰,出現(xiàn)了鄭谷口、金冬心、鄧頑伯等一批隸書大家。民國時期,隸書創(chuàng)作成就不高。當今書壇,隸書呈繁榮之象,有崛起之勢。
縱觀2000 多年來的隸書發(fā)展史,可謂泱泱大觀。我們學習之,當從何學起?這里,筆者提出隸書學習的“逆推法”,供大家參考。“逆推法”類似于數學分析推理中的“倒推法”。落實在隸書學習中就是打破常規(guī)的“從平正到險絕、從規(guī)范到奇崛”的“上坡訓練法”,而是“從險絕到平正、從奇崛到規(guī)范”的“下坡訓練法”。書法專業(yè)的技法訓練課一般是按照篆書—隸書—楷書—行草這樣的課程安排的。正是如此,我要講的“逆推法”就是指教師在具備了一些篆書基礎的前提下提出的。
隸書該從那一塊碑學起、或從哪一片簡牘學起更好?是從清隸學起,上追秦漢;還是先學秦隸,下啟漢碑好呢?
筆者認為先從《石門頌》學起,這對于有過篆書的基礎的人來說比較容易上手,因為《石門頌》用筆與篆書一脈相承,圓筆中鋒書寫,捺畫沒有明顯波磔,點畫沒有廟堂碑刻那樣精細,法度也沒有廟堂碑刻那樣謹嚴、肅括,只是體式上較篆書由縱式變?yōu)闄M式,其核心的東西(筆法)并無變化,所以學起來與篆書會自然對接。有了《石門頌》的基礎后,再去摸一摸另一塊摩崖《楊懷表記》,開始也不必為其爛漫、斑駁、蒼古之象所迷惑而不知所措,因為作為《石門頌》的姊妹篇,《楊懷表記》的筆法直接《石門頌》而來,其體勢、風貌很相近,屬寫意一路的隸書。通過一段時間的練習自然會覺得《楊懷表記》和《石門頌》一樣疏朗灑落,雄肆樸茂,自然天成,妙趣橫生。當然,若沒有篆書的功底,沒有《石門頌》的基礎,一開始就直奔《楊懷表記》,方法也是不足取的。《封龍山頌》盡管不是摩崖刻石,但它同樣具備摩崖的特質,其筆法源于《楊孟文頌》《石門頌》和《楊懷表記》,中鋒用筆,鋒芒內斂而體勢奔放,極富篆籀筆意。然比起《楊孟文頌》,《楊懷表記》更加有氣勢,波磔也更加明顯。清楊守敬評《封龍山頌》曰:“漢碑氣魄之大,無逾于此。”學書者在學《石門頌》《楊懷表》《封龍山頌》諸石的同時,對《西峽頌》《郙閣頌》也可有所涉獵,而且很有必要接觸,作為“漢南三頌”(石門、西峽、郙閣)在筆法、結字、氣格、整體風貌等方面都有諸多相同點,可以作為此時隸書的同一風格類型加以考察,研習。此外,像前秦的《廣武將軍碑》、東晉的《好大王碑》等都可在這一時段學習、參考。
學習了《石門頌》《西峽頌》諸碑后,筆者認為緊接著應學漢碑碣中那些方整厚重、古樸雄強一路的隸書,如《衡方碑》《張遷碑》《肥致碑》《鮮于璜》等,這些碑碣盡管不是摩崖,但風格特征與《西峽頌》相類,但此時必須明白,這些碑刻里的有些字起筆、收筆、波磔等已由原來的圓轉用筆變?yōu)榉秸塾霉P,這是非常關鍵的一步。當學到《鮮于璜碑》《張遷碑》等碑刻時,大家對于隸書就覺得熟悉了很多,似有老朋友重逢的感覺,興致隨之而來,思路隨之清晰,學起來就顯得很輕松。訓練中,《張遷碑》盡管是放在方拙、厚重、雄強一類的漢碑中,然比起《衡方碑》《郙閣頌》諸碑,它卻算是一塊很精致的碑碣,一般會將它與《曹全碑》對照起來學習。對比二碑,其筆法:一方一圓;其結體:一勻整一舒展;其線質:一厚重一飄逸;其風格:一質樸一妍美。由于易于比較,便于體會,所以學此二碑進步自然會很快。而作為廟堂之碑,還有許多與《曹全碑》一樣精致、典雅、華美的其他碑刻,如《禮器碑》《乙瑛碑》《華山碑》等,因此學書者學了《曹全碑》之后再學這些碑刻,就會不知不覺進入了精美絕倫的漢碑世界。這時,當我們回過頭來看看當初選擇那些爛漫、放蕩、奇崛一路的摩崖石刻作為隸書入門范本,會有豁然開朗、柳暗花明之感。隸書學習的脈絡一下子打通了。
當然,對于一般的書法愛好者而言,從《石門頌》《楊懷表記》《西峽頌》到《衡方碑》《張遷碑》《鮮于璜碑》再到《曹全碑》《禮器碑》《華山廟碑》的學書之路顯然是不可取的。首先,其最大的障礙就在于筆法,為了表現(xiàn)篆隸書線條的“金石氣味”,其“圓筆中鋒”“裹鋒澀筆”的運用就需要好長時間單獨練習;其次,摩崖石刻作為寫意性書法,沒有森嚴的法度和既定的規(guī)律可循,初學者難以一下子抓住其要害,所以只有亦步亦趨,按部就班,從平正、規(guī)范一路的漢碑學起,爾后再學雄強、古拙、險峻一路的,所謂先學平正,再求險絕。因此,對于初學者來說,本文提出的隸書學習的理路顯然是反其道而行之的。而這種“逆推法”運用于具備一定篆書基礎的人來說是完全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