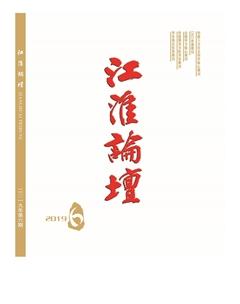新鄉賢參與鄉村振興研究
周丹丹
摘要:鄉村振興是新時期鄉村社會秩序的重建和全面振興。在鄉村振興的實施過程中,新鄉賢是一個重要的參與和推動力量。重返費孝通在討論鄉土重建時的理論視野,重思費孝通有關鄉市相輔相成、鄉土人才反哺鄉里、雙軌政治等問題的論述,有助于我們更為深刻地理解新鄉賢的身份再生產及作用再生產,并認識新鄉賢參與新時期鄉村振興的路徑及意義。
關鍵詞:費孝通;新鄉賢;鄉村振興;鄉市相成;雙軌政治
中圖分類號:C912.82 ? ?文獻標志碼:A ? ?文章編號:1001-862X(2019)06-0028-006
十九大報告提出的“鄉村振興”戰略是新時期中國鄉村全面重建與振興的整體性綱領和發展戰略。鄉村振興的三大核心要素是人才、資金和土地,其中,人才要素尤顯關鍵。當代鄉村人口大量流失,導致鄉村勞動力不足、技術人才短缺,人才要素成為新時期鄉村振興的短板,遏制了鄉村振興戰略的深入實施和開展。
2015 年中央一號文件《關于加大改革創新力度加快農業現代化建設的若干意見》指出:“創新鄉賢文化,弘揚善行義舉,以鄉情鄉愁為紐帶吸引和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鄉建設,傳承鄉村文明。”2016 年出臺的“十三五”規劃綱要明確提出要“培育新鄉賢文化”,即“以鄉情為紐帶,以優秀基層干部、道德模范、身邊好人的嘉言懿行為示范引領,培育新型農民,涵育文明鄉風”。2018年1月,改革開放以來第20個、新世紀以來第15個指導“三農”工作的中央一號文件發布,題為《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 2018年的中央一號文件強調:“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必須破解人才瓶頸制約。要把人力資本開發放在首要位置,暢通智力、技術、管理下鄉通道,造就更多鄉土人才,聚天下人才而用之。”而“以鄉情鄉愁為紐帶”的新鄉賢,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中的重要鄉土人才。中央一號文件進一步明確了新鄉賢的基本類型及服務鄉村振興事業的方式,“鼓勵社會各界投身鄉村建設。建立有效激勵機制,以鄉情鄉愁為紐帶,吸引支持企業家、黨政干部、專家學者、醫生教師、規劃師、建筑師、律師、技能人才等,通過下鄉擔任志愿者、投資興業、包村包項目、行醫辦學、捐資捐物、法律服務等方式服務鄉村振興事業”。
鄉賢是中國傳統社會結構的有機組成部分,是溝通國家權力與基層地方民眾的積極力量。鄉賢文化由此成為中國傳統地域文化的重要因素,并形成一套完整的地方文化系統,與國家的“大傳統”形成有效互動。在中國當代社會轉型和治理轉型的時代環境中,在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社會背景下,如何對鄉賢文化這一傳統文化形式進行創造性的現代轉化,使其植根并契合當下的時代背景和鄉村振興的發展趨勢,進而促進新鄉賢參與實施鄉村振興,這是我們面臨的挑戰。
早在上世紀40年代,費孝通在《鄉土中國》《鄉土重建》等一系列著述中,就深切地將關注的目光投向中國鄉土。費孝通為我們描繪了一幅幅鄉土中國的側影,展示了鄉土文化的諸多面相,并進而通過對“損蝕沖洗下的鄉土”[1]352的現實關注和理論分析,強調地方人才的重要,建構了中國傳統“雙軌政治”的概念和理論體系,并提出如何進行鄉土重建的思路。
隨著當前新鄉賢文化的興起,學界已有不少相關研究和論述,從各種角度探討新鄉賢的內涵和作用[2][3]、新鄉賢與鄉村治理的關系[4][5]、新鄉賢參與鄉村振興的作用和路徑[6][7]等。這些研究明晰了新鄉賢的概念和內涵體系,并充分挖掘了新鄉賢參與鄉村治理的作用,探討了新鄉賢與鄉村振興的關聯。但已有研究較少從費孝通對鄉土重建的思考中進行理論的對話和深化,并以此為視域考察新鄉賢如何參與鄉村振興。本文將從費孝通早年的敏銳觀察和分析中探尋新鄉賢參與鄉村振興的內在邏輯脈絡及基本路徑,加深我們對費孝通鄉土重建思想的認識,進而反思新鄉賢文化對鄉村人才振興的啟示。
一、城鄉之間的新鄉賢
鄉村振興著眼于打破城鄉二元格局,建立城鄉之間人才、資本和產業的流通和互惠,進而破除城鄉之間的結構化、制度性壁壘,實現城鄉一體化協調發展。費孝通對鄉村重建的論述中,基于城鄉整體化的視角,將鄉土中國與都市相關聯,提出“鄉市相成論”,[1]313進而在城鄉有機關聯之中探討鄉土人才對鄉村建設的作用。這一深刻的認識對我們探討新鄉賢參與鄉村振興問題頗具啟發作用。
1.鄉市相成
20世紀40年代,費孝通在一系列論著中系統描述并分析了鄉土中國的諸多面相和特征。在以農業為主的傳統社會,傳統儒家文化的差序格局作為基本的社會規范和倫理特征,建構了一種基于鄉土鄉情的社會結構和鄉土共同體。而費孝通所處的時代,正處于這種共同體發生劇烈變遷之際,他結合自身所處的社會現實,描繪了都市興起和鄉村衰落的過程,提出基于產業互補、鄉土人才回流的鄉土重建。
費孝通鄉土重建的理論基點是基于整體論的城鄉相輔相成思想。費孝通深刻認識到,中國的城市與鄉村是無法分割的整體,用他自己的說法就是“鄉村和都市本是相關的一體”,也即鄉市相成論。但是,近代中國的社會現實卻是都市不斷興起,而鄉村日漸衰落,中國經濟呈現“都市破產鄉村原始化的狀態”[1]315。在中國漫長的歷史時期,鄉村和都市大體呈現一種相輔相成的格局,“鄉村和都市應當是相成的,但是我們的歷史不幸走上了使兩者相克的道路,最后竟至表現了分裂。這是歷史的悲劇。我們就不能讓這悲劇再演下去”[1]315。鄉市相克是鄉市相成的反面,即將鄉村和城市對立起來,在都市興起的同時,產生了各種遏制鄉村發展的因素,鄉村發展所需的有形及無形資源全部被都市吸納,鄉村與都市之間有機的產業和消費循環鏈條被切斷,尤其是近代,中國鄉村自給自足的農業和手工業生產模式遭到西洋工業的致命性沖擊。鄉土工業在第一輪與“西洋都市機器工業競爭”中敗下陣來,“貧窮跟著鄉土工業的衰落侵入鄉村”,[1]369緊接著鄉土工業的勞動力也被吸附進都市,更直接導致鄉村經濟的癱瘓。
如何使“鄉市合攏”,這是費孝通著力思考和力圖解決的問題。在提倡都市化的同時,“不應忽視了城鄉的有機聯系”,[1]361要恢復城鄉之間的有機循環以解決城鄉危機。“在都市方面的問題是怎樣能成為一個生產基地,不必繼續不斷地向鄉村吸血。在鄉村方面的問題,是怎樣能逐漸放棄手工業的需要,而由農業的路線上謀取繁榮的經濟。”[1]318費孝通從產業發展及生產、消費鏈條等經濟和貿易的角度進行了思考。此外,他更痛心疾首地反思了鄉土人才流失給鄉村發展帶來的致命影響。
2.從鄉到城
鄉土人才從鄉到城而不再返鄉,進一步造成了“損蝕沖洗下的鄉土”。鄉土社會被“損蝕沖洗”的過程,費孝通類比于李林塞爾用“采礦”描寫的美國田納西河區域:一塊地種了幾年棉花后就把地里的養料耗盡了,再加上河水的沖洗,導致土質日益變壞,作物不長,加之森林遭受砍伐,大雨之后,水流一路把膏腴之地沖洗侵蝕。經過這樣沖洗的土地,最終變為荒區。[1]352-353
這種耗盡一切養分的發展和增長,最終導致的鄉土衰敗,需要一個極其關鍵的要素即人才來復原。費孝通著重強調的人才力量正是鄉土社區里成長起來的本地人。“除非鄉土社區里的地方人才能培養、保留、應用,地方性的任何建設是沒有基礎的,而一切建設計劃又必然是要地方支持的。”[1]353
鄉土人才無法留在鄉土,而是沿著由鄉入城的路徑流入城市。費孝通辟專章談到“回不了家的鄉村子弟”問題,并從歷史比較的角度來分析。他和潘光旦先生分析了915個清朝貢生、舉人和進士的出身,發現其中一半來自鄉間,也就是說,當時人才的分布并不是集中于某一固定區域或某一固定階層,“原來在鄉間的,并不因為被科舉選擇出來之后就脫離本鄉”[1]357。費孝通認為,“人和地在鄉土社會中有著感情的聯系,一種桑梓情誼,落葉歸根的有機循環中所培養出來的精神”[1]355,“中國落葉歸根的傳統為我們鄉土社會保持著地方人才”[1]357。這種感情的聯系和傳統曾經為鄉土社會保持著地方人才,一個人功成名就,也不忘根本,他對鄉土具有一種責任。
但這種傳統在近代被割斷,“鄉土培植出來的人已不復為鄉土所用”[1]358,當時的大學生畢業找不到工作,青年失業現象嚴重,而他們鄉村的家也回不去。一方面的原因在于,價值觀念已經發生變化,鄉村與他們產生隔膜;另一方面的原因則在于,大學教育和中等教育都沒有培養鄉土社區人才,他們所學的一套來自西洋的知識體系,無法找到一條對接的通道將之運用到鄉土社會。最終,“鄉間把子弟送了出來受教育,結果連人都收不回去”[1]358-359。
其結果便是,“以前保留在地方上的人才被吸走了;原來應當回到地方上去發生領導作用的人,離鄉背井,不回來了。一期又一期的損蝕沖洗,發生了那些渣滓,腐化了中國的社會的基層鄉土”[1]358。本土人才外流,不僅造成鄉土建設所需的人才匱乏,還導致了鄉村地方權力的變質。
這就是費孝通所言鄉土社會的被“損蝕和沖洗”,以前植根鄉土的人才被吸走,本可回到鄉土的人才卻又回不來,鄉土不斷受到人才外流的損蝕,鄉土文化和鄉土傳統也日漸稀薄。就當下而言,留不下的城市和回不去的鄉土成為大量城市流動人口二元悖反的生存現狀。受制于城鄉戶籍制度的屏障,以及公共資源配置不均等和公共服務供給不足的限制,由鄉進城的人即使有心回歸鄉土,也無力承擔回鄉的成本;而勉強留在城市從事服務業、建筑業和制造業的大量外來者,更是處處被邊緣化和底層化。這些徘徊于城鄉之間的打工者,在當前的政策激勵下可被納入返鄉農民工回鄉再創業的考量之中。而大量來自鄉村,在城市從事科教文衛、服務政府部門或自己成功創業的商業人士等,正是鄉村振興所需的新鄉賢力量。
3.由城返鄉
鄉土人才由城返鄉涉及必要性和可行性兩方面的問題,這在費孝通論述鄉土重建問題時都是重點關注的。就其必要性而言,前文論述中已經涉及,在此重點闡述費孝通談到的可行性問題。
首先,在情感方面,鄉土人才由城返鄉具有可行性。“返鄉”是一種人和鄉土之間的基本感情聯系的表達,也是中國人落葉歸根的一種情愫。家鄉是一個人出生和成長的地方,承載著一個人對故土的最深的眷戀,也飽含著一個人與家人之間的情感和回憶。中國人對故土的這種情懷,能內在持久地發揮作用。因此,從古至今,回鄉報效鄉土和父老兄弟都是中國人不斷返鄉的原動力和情感基點。費孝通正是基于對鄉土中國的深切理解,從中國人的內在情感結構和文化心理入手,提出了這種人地情感連接作為鄉土人才由城返鄉的最基本也是最深層次的原因。
其次,在填補地方領袖人物匱乏方面,鄉土人才由城返鄉具有可行性。地方領袖人物是地方社會認可、在民間具有相當威望并領導民間社會活動的代表人物,他們往往因其人格魅力、領導才能、威望度和認同度、社會資本、知識資本、物質財富及人際關系資本等方面的原因,獲得民間社會的推崇。
費孝通舉了他在英倫所見的一個實例,來說明當時地方領袖人物的匱乏及其應對。“以往那種貴族、鄉紳、牧師等人物現在已經失去了被人民尊重的地位,但是在英國鄉村里卻有一種人在擔負過渡性的領袖責任。我稱他們的責任是過渡性,因為依我看來,將來鄉村社區里自會生長出新的社會重心和新的領袖人物來的。現在那些過渡性的領袖是從都市里退休回去的醫生公務員、學者和富于服務心的太太們。這些人并不是從鄉間出身的,他們的職業也不在鄉間,但是退休到了地方上卻成了地方自治的機構中的重要人物了。”[1]348
在此,費孝通談到了幾個問題,其一是傳統鄉村權威的失勢和瓦解;其二是過渡性鄉村權威的出現;其三是過渡性鄉村權威的基本構成;最后,暗含的一層意思是,未來由過渡性鄉村自治領袖到鄉村自身權威的再建構。我們可以將之稱為費孝通所設想的地方領袖人才過渡計劃,該計劃很好地解決了過渡人才從何而來的問題。費孝通在此列舉了“從都市里退休回去的醫生公務員、學者和富于服務心的太太們”。細加辨析,可以發現,這類人與當前所提倡的新鄉賢具有吻合之處。雖然費孝通強調,在英國,這類人并非本鄉本土人士,但在中國語境中,我們完全可以找到本鄉本土出生的此類人士返鄉擔任過渡領袖。結合我國在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對新鄉賢進行的明確身份界定,即從鄉到城的“企業家、黨政干部、專家學者、醫生教師、規劃師、建筑師、律師、技能人才等”,我們發現,費孝通在中英比較之中,已經獨具慧眼地發現這類新鄉賢在重建鄉土中大有用武之地。此外,費孝通更為深刻地提出,過渡計劃的目的是培育鄉村社區自身的領袖人物,即未來的鄉土領袖孵化。
最后,搭建鄉土人才返鄉以后對接鄉土的“橋梁”,使鄉土人才由城返鄉具有可行性。鄉土人才如何返鄉,實際上是鄉土人才如何對接鄉土的問題。費孝通觀察到畢業大學生無法回到供養他讀書的故鄉,由此引發他思考對接“橋梁”的問題。費孝通的這一思考,可謂從制度層面、體制機制層面探討鄉土人才由城返鄉的問題。鄉土人才由城返鄉是一個涉及城鄉公共資源配置、公共服務供給、城鄉戶籍制度、城鄉教育和醫療制度等人、財、物多方面的系統工程。費孝通當時的思考已經涉及大學及中等學校教育體系及教育培養目標的問題,“一個鄉間出來的學生得了一些新知識,卻找不到一條橋可以把這套知識應用到鄉間去;如果這條橋不能造就,現代的教育,從鄉土社會論,是懸空了的,不切實的”[1]359。
二、雙軌政治:新鄉賢參與鄉村振興的路徑及作用
費孝通在論述鄉土重建的問題時,提出了社會學界一個相當經典的概念,即“雙軌政治”。如何理解費孝通談到中國歷史上的權力關系及社會結構時所構建的“雙軌政治”,尤其是,如何結合當前新時期新鄉賢文化來重新理解這個概念,對深入理解新鄉賢參與鄉村治理的路徑及作用頗具啟發意義。
1.雙軌政治
費孝通對鄉土重建問題的思考,由現狀入手,又從中國傳統深入,參乎西方實例,最后反思并建構重建理路。在這一脈絡和路徑之中,深入中國傳統是為了厘清中國傳統權力關系和社會結構,看清當時中國鄉村基層社會正在發生的變化,即基層行政之僵化。費孝通從中國傳統的政治結構中析出了政治的雙軌,即自上而下的軌道和自下而上的軌道。在古代中國,國家權力由自上而下的軌道傳導,而在縣域以下的地方基層社會,自上而下的權力往往會發生轉換,其中,鄉紳階層在溝通國家與地方、將地方民意上傳至國家層面發揮著重要作用。
專制皇權往往在“自上而下的單軌上開快車”[1]337,而中國政治傳統中的無為主義和自下而上的政治軌道,可以避免單軌上的“火車”開得太快,這正是自下而上的政治軌道的重要作用。“自上向下的單軌只筑到縣衙門就停了,并不到每家人家大門前或大門之內。”[1]338在此,費孝通發現了“縣衙門到每家大門之間”這最為有趣也極其重要的“兩門”之間地帶。在中國政治軌道和政令傳達的體系中,我們表面上所見往往是自上而下的政治軌道執行政府的命令,但是,“一到政令和人民接觸時,在差人和鄉約的特殊機構中,轉入了自下而上的政治軌道,這軌道并不在政府之內,但是其效力卻很大的,這就是中國政治中極重要的人物——紳士”[1]334。至此,我們看到,中國古代雙軌政治的重要節點和轉換點,落在一個獨特的群體即士紳群體身上。
近代以來,“政治的雙軌實際都已淤塞”[1]354,這可以從雙軌的兩個方面來看。從自上而下的路線看,中央雖然一步步將行政機構深入地方,“筑下了直達民間戶內的軌道,而實際上卻半身不遂”,[1]354地方官員的徇私舞弊和地方公務的腐敗不堪讓自上而下的軌道擁堵不暢;而從自下而上的軌道看,情形更堪憂,傳統社會中由士紳階層發揮的溝通基層社會和國家之間的軌道早已蕩然無存,“上通的軌道影子都不見了,以致連以往‘道在師儒時代的無形軌道都覺得值得回念了”[1]354。
2.新鄉賢的再生產:身份重塑
伴隨著中國傳統社會結構的解體,中國的士紳集團作為一個群體整體性地退出了歷史舞臺,雖然中國士紳的文化心理及文化表征在某種程度上仍然存在。在費孝通所分析的雙軌政治中,士紳群體在歷史上溝通上下、庇護鄉里的作用也不再結構性地存在。
新時期,在國家政策的感召下和鄉村振興發展戰略的鼓舞下,各地新鄉賢文化被制度化地再生產。
首先,通過一系列推選制度,產生新的身份,制度化地再生產新鄉賢的身份。以山東鄒城唐村鎮為例,唐村鎮隸屬“孔孟桑梓之邦文化發祥地”的孟子故里——山東省濟寧市鄒城市,位于山東省中南部。唐村鎮深厚的鄉賢文化積淀,為新時代鄉村振興提供了豐富的資源。借助傳統鄉賢文化和鄉賢傳統,當地黨委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動新鄉賢文化建設,助力地方基層治理,振興鄉村發展。2013年以來,唐村鎮啟動了“儒風唐韻”新鄉賢文明行動,完善了相關制度,制定、出臺了《唐村鎮鄉賢推選實施方案》《“儒風唐韻”新鄉賢文明行動實施方案》等,建立了較為完善的新鄉賢選任、培訓和管理辦法。[8]
唐村鎮黨委書記G說:“唐村鎮結合實際,在包括老干部、老黨員、老教師、老醫生、退休工人,也包括為富亦仁的經濟能人中,通過群眾推薦、支部提名、黨委認定,全鎮共推選出35位新鄉賢。”(GS訪談)當地鄉賢的代表人物,茲舉數例:QRS,中共黨員,某國企員工,退休后回鄉,擔任村紅白理事會長;PYK,某國企員工,當地潘氏家族傳人,積極參與家族文化的傳承和保護,搜集整理古賢史料;QQC,中共黨員,鎮退休干部,參與鎮志和村志編撰;WZZ,中共黨員,鎮退休干部;GRZ,中共黨員,鎮退休干部;LWP,某公司經理,鎮商會會長;GCS,醫生;LDR,中共黨員,退休教師;YRK,中共黨員,小學校長。
其次,通過一系列政府工作和活動,不斷強化新鄉賢身份的內涵。如,唐村鎮為讓新鄉賢落地生根,當地黨委、政府抓住新鄉賢工作的六個落點:一是聚鄉賢傳家風,二是聚鄉賢轉村風,三是聚鄉賢惠民生,四是聚鄉賢促發展,五是聚鄉賢保平安,六是聚鄉賢助黨建。由此,唐村鎮將新鄉賢與鄉村文化存續、鄉風村風建設、民生工作、經濟發展和黨建工作等一系列工作緊密結合起來,確保新鄉賢的再生產得以順利進行。
此外,唐村鎮還結合當地文化傳統,為新鄉賢賦予古代鄉賢文化之內涵。唐村鎮鄉賢傳統古已有之,如明代潘榛即為鄉村賢達的代表。為此,唐村鎮重整潘家祠堂,打造新鄉賢文化的陣地,先后建成了鄒魯鄉賢館、潘榛圖書館、王爐村鄉賢館等展示場所。在鄒魯鄉賢館中,陳列著從孔孟到潘榛共16位古代鄉賢、唐村鎮各姓氏家訓、10名新鄉賢事跡及184戶鄉風文明戶代表。古代鄉賢文化和新鄉賢事跡的公開展示,不僅重塑了這些人作為新鄉賢的身份意識,而且強化了當地人對新鄉賢的認可和贊同。
再次,通過傳統儀式的再生產,不斷加強新鄉賢身份的傳統文化內涵。中國古代傳統儀式的再生產也進一步重塑和豐富了新鄉賢的角色,如當地對鄉飲酒禮的挖掘和再造。鄉飲酒禮是中國古代的一種飲食禮儀,盛行于周代,一般由鄉大夫主持,目的在于考察賢能或敬養老人。[9]鄉飲酒禮也稱為鄉禮。甲骨文中“鄉”字形為兩人圍著盛有食物的食器跪而對食,以此表示一個群居的團體,后世鄉飲酒禮與初民同居共食具有密切關聯。[10]孔穎達認為,鄉飲酒禮的舉辦一般有四種情況,其一為“三年賓賢能”,其二為“鄉大夫飲國中賢者”,其三則為“州長習射飲酒”,其四為“黨正臘祭飲酒”。考察《周禮》所載:“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考其德行,察其道藝……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興其眾寡,以禮禮賓之。”鄭玄注曰:“謂合眾而尊寵之,以鄉飲酒之禮,禮而賓之。”[10]唐村鎮對鄉飲酒禮進行了成功的挖掘和恢復,并請新鄉賢參與鄉飲酒儀式的展演。在儀式再生產的同時,為新鄉賢角色注入了傳統鄉賢文化的要素,并強化了他們自身對新角色的認同。
3.新鄉賢的再生產:作用重塑
新鄉賢的再生產重塑了新鄉賢群體在鄉村的作用。在費孝通的雙軌政治中,以往缺失的自下而上的軌道,通過新鄉賢的再生產,在國家正式行政機構的末端和民眾之間,架構了新的橋梁。
首先,新鄉賢有助于黨委、政府凝聚鄉村民眾共識和基層民眾力量,化解矛盾糾紛,助力鄉村振興的發展。鄉村振興戰略是在黨委和政府的引領和指導下開展的鄉村建設和鄉村發展,新鄉賢群體在黨委、政府與基層民眾之間游走,有助于政令的上傳下達和雙方的溝通交流。如,在唐村鎮,鄉賢工作在支部的領導下展開,新鄉賢對支部工作起到了很大的幫助作用。在王爐村村民墳地遷挪和建設公益墓地的工作中,村支書找到新鄉賢商量,兩位新鄉賢通過半個月的努力,做通了群眾的思想工作。新鄉賢往往在宗族或鄰里中享有威望,通過親緣、地緣和人緣等優勢,大量的矛盾糾紛能被新鄉賢在基層解決。又如在西顏村收麥子期間,其中一家因為誤收了鄰家的一壟麥子,結果兩家人相持不下,新鄉賢用自己家的麥子先頂上,然后通過評理,化解了鄰里矛盾。[8]220正如當地領導人所說:“新鄉賢是德治的一種手段,少了行政的強約束、弱溝通、硬治理,更多的是鄉賢參與下的強溝通、軟約束、善治理。一年來,新鄉賢的作用不斷得到發揮,越來越成為黨委政府眼中的‘德高望,村干部身邊的‘好幫手,群眾心里的‘自己人。”(GS訪談)
其次,新鄉賢有助于形成新的鄉村地方權威,推動鄉村振興的發展。費孝通談到,鄉村發展需要有本土民眾的組織化力量來對接外來資源,鄉村地方權威的缺失,或鄉村地方權威黑惡勢力化,都極大地影響了鄉村基層民眾力量的正常發揮,導致民間的組織化受阻。按照費孝通的地方領袖人才過渡及孵化計劃,新鄉賢作為過渡型的鄉土地方領袖,有助于培育和孵化本鄉本土的地方權威,助力鄉村振興的實施。
再次,新鄉賢有利于導入鄉村發展資源和渠道,助力鄉村振興的發展。不少新鄉賢作為事業有成、榮歸故鄉的人士,或具有一技之長、或熱心鄉里,自身具備鄉村發展所欠缺的信息、技術、文化、資本或市場資源。當新鄉賢返鄉之時,他們攜帶的這些資源在很大程度上將成為助力鄉村產業發展、市場拓展或科教文衛振興的發動機。鼓勵和引導新鄉賢帶著技術、資本下鄉,同時通過相關的政策法規和制度保障新鄉賢和地方民眾雙方的利益,將實現二者互惠雙贏的局面。
三、結 語
重返費孝通幾十年前在鄉土重建問題中的諸多思考,我們發現,新時代鄉村振興的諸多話題早已被他論及并有相當成熟的思考。而費孝通對當時鄉土社會整體現狀的擔憂和對未來的設想,于今仍然發人深省。
伴隨國家對新鄉賢文化的大力倡導,在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過程中,新鄉賢在推動鄉村振興方面大有可為。返回并接續費孝通對鄉土人才和鄉村社會結構的思考,我們能更清晰地認識新鄉賢在當代新的鄉村秩序和鄉村政治格局中的地位,以及新鄉賢發揮作用的渠道和意義。
總體而言,重返費孝通鄉土重建的視野是為了克服并超越他曾擔憂的問題,為當前的鄉村振興提供更多的理論關照和可能路徑。新鄉賢作為費孝通在雙軌政治中著力最多的士紳階層的現代轉化,其地位及其所承載的時代和社會意義與以往頗有相似之處,但也有根本不同。在理論與現實之間,在費孝通的思考與當下的社會情境之間,我們需要更深刻地理解并認識新鄉賢在新時代被再生產的社會意義,并在鄉村振興的過程中,積極促進新鄉賢作用的發揮。
參考文獻:
[1]費孝通.鄉土重建[M]//費孝通文集(第四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
[2]張兆成.論傳統鄉賢與現代新鄉賢的內涵界定與社會功能[J].江蘇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4):154-160.
[3]胡鵬輝,高繼波.新鄉賢:內涵、作用與偏誤規避[J].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1):20-29.
[4]顏德如.以新鄉賢推進當代中國鄉村治理[J].理論探討,2016,(1):17-21.
[5]楊軍.新鄉賢參與鄉村協同治理探究[J].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2):48-52.
[6]高萬芹.新鄉賢在鄉村振興中的角色和參與路徑研究[J].貴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3):127-134.
[7]王國燦,金潔霞.鄉賢文化是鄉村振興的重要軟實力[J].統計科學與實踐,2018,(6):61-63.
[8]高勝,邵澤水.讀孟子 ?做鄉賢[M].北京:團結出版社,2017.
[9]晏青.鄉飲酒禮起源新探[J].孔子研究,2018,(2):65-71.
[10]姚偉鈞.鄉飲酒禮探微[J].中國史研究,1999,(1):12-22.
(責任編輯 吳 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