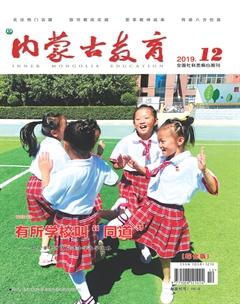有所學校叫“同道”
魏晉

坐火車從呼和浩特到包頭,進入包頭東河區時,鐵路的北側呈現出一片赭紅色的樓群,這樓群和樓頂上的大字“北梁南區”異常醒目。
嶄新的同道小學就隱藏在這片嶄新的樓群里。
雖然今日之北梁與昔日之北梁在地理上已經毫無關聯,但人們沿用了這個名字,因為,北梁,是一頁歷史;北梁,也是一個符號——城市棚戶區代名詞。
棚戶區原本不是棚戶區,它是包頭歷史文化的發祥地,學界素有包頭“根在東河,魂在北梁”之說。從殘存的四合院,精致的磚雕、影壁,足可以想像當年的繁盛。北梁,有濃厚的走西口文化遺跡——晉陜風格的民宅,街巷交錯,召廟林立,參差十萬人家,假如從康熙年間算起,它已有300多年的歷史。
歷史走進新世紀,北梁的簡陋與寒酸,北梁的“貧民窟”面相,與高樓林立、街衢縱橫的其他地域形成鮮明對比:清末民國時期的青磚灰瓦建筑與上世紀60—80年代的臨時建筑擁擠在一起。弱勢群體多,人居條件差,70%的人沒有固定收入,900個人才平均一個公廁,三代同堂住十幾平方米的陋室。現代城市功能嚴重匱乏,街巷狹窄彎曲,百年老院里擁擠著簡陋的臨時棲身建筑……
據稱,包頭市北梁棚戶區是當時全國城市中面積最大、人口最多、最典型的連片棚戶區。
2011年,北梁被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特別關注”,他說:“不能讓城市一邊是高樓大廈,一邊是棚戶區”“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此后,李克強兩度深入北梁棚戶區,推動了一個全國最大的棚戶區改造項目;棚戶區一個光屁股的孩子頑皮地從舊立柜里鉆出來的鏡頭出現在《新聞聯播》中……
□“同道小學”背后的世界
去包頭市東河區的同道小學采訪,原本是源于它的科學教育比較出色:從自媒體或其他渠道,隔幾天就可以看到他們科學課和科技社團活動的小視頻。
不料采訪過程中萌生出一個更大、更深刻,也更沉重的話題——棚戶區的改造,僅僅是居住環境的改善嗎?怎么給他們的孩子一個大致均衡的教育環境?如何通過教育這個杠桿撬動社會公平正義的車輪,從而阻斷貧困的代際傳遞……
2016年才開始招生的同道小學,既是城市棚戶區改造的產物,也是為實現社會“教育均衡,起點公平”而努力的模板。
李鎮西在《我想辦一所沒有特色的學校》中曾說:我們面對的是好多學校不喜歡的孩子——當地失地農民和進城務工人員的子弟。面對這些孩子,我們就不是什么“特色”,而是一個個具體的難題:有的孩子為什么上課心不在焉?他上課為什么聽不懂?有的學生為什么要輟學打工?孩子的家長為什么不愿意來開家長會?怎樣才能讓學生享受學習的快樂?如果考不上高中,他將來能夠做什么?怎么讓一部分聰穎的孩子最大程度地獲得知識,最大限度地提升能力,最大限度地得到發展乃至極致……
同道小學似乎也面臨這樣的難題。
有資料顯示:東河區登記在冊失業人員70%以上居住在北梁地區;東河區低保人員40%以上集中在北梁地區。這個數據背后的現實就是:家長受教育程度低,他們每天為生計而奔波,對下一代教育的關注度、期望值都會變得弱化和無奈。
段思明校長說:我們學校面對的就是窮人家的孩子,剛開始那兩年,家長有固定職業、固定收入的基本沒有,這兩年家長有固定職業和收入的才逐漸增多了了。
同道小學承擔著讓這個群體的孩子,從“優居”到“優教”的歷史使命。
□從“優居”到“優教”
北梁棚戶區改造分為南區和北區,北區的孩子到環城路小學巴東校區上學,南區的孩子到同道小學讀書。在“義教均衡發展”背景下誕生的同道小學就硬件而言,絲毫不差于任何“名校”。學校基建投入2300萬元,設備投入300多萬元。自2016年5月開學至今,已經招了4屆學生,24個班。學生數已經達到了1180人,到明年秋季,就是一所完整的六年制小學了。
學生彬彬有禮,見到校長和記者,一律問好,盡管有的自然,有的羞澀;大廳里陳列著的展板上是孩子們的“樹葉畫”,其造型的別致,想像的奇特,色調的搭配,落葉殘枝取舍的渾然天成,讓成年人都會感到驚訝。走廊里懸掛著主題為“北梁印象”的水粉畫,內容上全是兒童眼中的北梁,無意中為消失的北梁做了一份文化檔案:唱晉劇的旦角,戴著小白帽的回族老人,四合院的門樓,賣大碗茶的“伙計”……色彩、造型、構圖、用光,有夸張,有變形,居然在稚嫩中隱隱地見出印象派的風格。
段校長兩次問記者:我們的學生有沒有農村孩子的痕跡?
“基本看不出,偶爾有痕跡。”因為與學生的座談會變成了“警察式”詢問,原本很優秀、能在全國競賽中獲獎的孩子,卻拘謹和膽怯,反映著孩子們的內心還缺乏足夠的自信。
父母文化程度低、收入低,每天為生計而艱難地奔波。“改變孩子的不良生活習慣,就是文明化的過程,就是學校教育的責任之一。”段校長以及學校的老師們是這樣理解教育的要義的。
“學校就是想從最基本的小事抓起,如每周檢查一次個人衛生,曾發現學生沙眼率比較高,為什么呢?手洗不干凈,還老揉眼睛。于是就從洗手、剪指甲這樣的生活小事兒做起。”段校長說。
他講了個親歷的故事:一天早晨,一個女孩因沒剪指甲哭著不進校門,家長推搡著問:咋拉?指甲長就不能上課哩?后來還是一位女老師掏出指甲剪為她剪了,洗了手,才平息了“風波”。
這些孩子需要加倍的關愛!
同道小學的老師們對學生的熟悉程度是驚人的——記者一說起某個學生,段校長、劉霞書記和一些老師們都會脫口而出:“你說的是那個誰吧?哦,他家里是這么個情況……”
段校長送給我他們編輯的一本《同道故事》,上面收錄的全是老師們的教育敘事,有喜怒哀樂,有酸甜苦辣,有調侃詼諧。以后他們將每年編一本。時間長了,就成了一部教師和學校的成長史。
《同道故事》中記錄著的是故事,折射出的則是老師們的學生觀、課堂觀、學習觀……
杜曉娜老師,為了學生主動打招呼簡單的六個字,兩度流淚——我們班有一個拒絕說話的小男孩,不論是表揚還是批評,他都是低著頭,連眼神交流一下都不敢。發現他的不正常后,就利用家長會了解其中的原委。爺爺流著淚和我講述著他的不幸,而身為母親的我也流下了熱淚。從那一刻開始,我決定一定要親近他,要給予他關愛,不讓他覺得老師陌生、威嚴,每每和他說話時我都會摸著他的頭,或是摟著他的肩膀。有一天,他終于敢看著我的眼睛說:“杜老師,下午好!”
白雪老師為一個“追著給老師講題”的女孩而感動:大部分的孩子學習要老師督促去完成,可她卻督促老師聽她講題。有一天,我忙到沒時間聽她講題,她整整追了我一天,一下課就來問我是否有時間,講完后讓她回去上課,她嘟囔著說“我還想講幾道題” ……
馮帥的學生觀——學困生可能是自己比我們還痛苦的人。他們學習沒開竅,但有其他閃光點。有讀課文的聲音好聽的,有會縫縫補補、給布娃娃做件衣服的,有老實、憨厚熱愛勞動的……給他們一點時間,靜待花開吧。
劉苓老師的課堂觀——那節課,我原本想展示自己的 “風采”。無奈,本應成為我的“捧哏”的那些“熊孩子們”,卻非要來“逗哏”。怎么辦?把“展示”的想法放在一邊吧。我實在沒有精力去和一幫“熊孩子”搶風采,那就不妨讓我成為“捧哏”吧,把舞臺的“C位”讓出來。結果,課堂卻收獲了預料之外的精彩,孩子們的思維激發了我的靈感,我的即興發揮又促進了他們的探究,課堂中的對話讓我驚喜連連……
此外,董惠茹老師的教材觀、朱惠民老師 “善良的謊言”、喬沛文老師和“熊孩子”的斗智、從高中“下嫁”小學教語文的劉娜老師所經歷的學生向她道歉的故事……無不讓人感到,同道小學有這樣一個群體:雖然整體上有些稚嫩,但教育觀、學習觀、學生觀、評價觀卻甚為正確,這無疑對學生享受“優教”有了基本保障。
□“科技創新教育,重在喚醒”
小學的科學課程,在應試教育的背景下,極易被邊緣化。
當多數小學科學課開不齊、開不足,更談不上“開好”的時候,這所新生的小學居然把科技教育做得有聲有色:學生多次獲包頭市、自治區乃至全國的獎項,科學課不是僅僅掛在課表上“供檢查、參觀之用”,而是實實在在的每周兩節課。他們有個理念叫“科技創新教育,重在喚醒”。“喚醒”什么?用段校長的話說,就是“保護孩子們的好奇心和那種與生俱來的對科學技術的熱愛”,“讓科技興趣伴隨他們一生”。
建校短短的三年中,同道小學配備了科技教室、創客空間、勞技教室、電腦編程教室四個完備獨立活動場所,總面積達200多平方米。隨之而來的是多個科技社團的誕生,大量貼近學生的科學活動和競賽開展起來了——
2017年,學校開始建立科學實驗養殖室,培養了一批小小“飼養員”,陸生、水生、兩棲動物養了不少,其中白玉蝸牛居然培養出了第二代,大頭蟻培養出了完整群落。在養殖的過程當中,“飼養員”們學到了很多動植物的相關知識,見識了難得見到的螞蟻卵和白玉蝸牛卵,這大大激發了孩子們的科學興趣,還潛移默化地培養了他們的責任感和求知欲。讓學生敢自由思想,會發散思維,能持之以恒地探究感興趣的現實問題。不到兩年的時間,學校教師所帶學生在內蒙古最高規格的科技創新大賽中成績優異,躍居成為東河科技教育亮點校。
沒有專業的科學課教師,但這不能怪小學,而是我們師范教育體制導致的。高等師范院校培養了科學課師資了嗎?全國除湖南懷化師范學院設立了“科學教育系”外,其他高師一律空白,現在小學的科學課教師大都是由分科化的理科教師承擔的。
同道小學四位科學教師也是如此。
王斌,本科在內蒙古師范大學學的是美術教育,但自幼喜歡機械制造。當年還是小學生的他,鼓搗家里的“隨身聽”還發生了爆炸。可是父母竟沒有打罵他,反而鼓勵他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原本是學工科的料,后來學了美術,現在又愛上了人工智能。他曾在包頭市東河區組織過一個民間組織“愛迪生俱樂部”。
采訪時,他正在電腦前為下午的課《聲音的秘密》備課。現在他代美術和科學兩門課程,還帶著三個社團(航模、艦模、機器人),于是成了“美術老師中最愛科技制作的,科學教師中畫畫得最好的人”。
白玲玉,一個白白凈凈的年輕女教師,大學學的是生物學,現在代數學課和科學課。采訪那天,她在實驗室上了一節《物質的溶解比較》,學生的參與度甚高。
周老師,既是孩子的家長,又是學校科學課程的兼職教師。采訪那天下午,她上課的內容是《月相》。課堂上她把自己買的餅干分給學生做月相對比,餅干是夾心的,一黑一白,黑可以理解為天空,白可以理解為變化的月亮。可惜那餅干太干了、太脆了、太香了,雖實驗有成功的,有失敗的,但呈現的卻是課堂本來的面目,也等于告誡學生,科學實驗失敗是家常便飯,只有鍥而不舍,才能有所發現。
自2017年起,同道小學每年必參加的活動就是科技創新大賽。學生將生活中的好想法、小發明付諸行動,形成科技創新作品。第33屆科技創新大賽學校雖然僅有兩名學生參賽,但是分別獲得了包頭市一等獎、三等獎和內蒙古自治區二等獎的好成績。以賽促學,極大激發了學生參加科創活動的興趣。第34屆科技創大賽時,參加了其中的五個項目,每個項目均有獲獎,其中包含了2個自治區一等獎,5個自治區二等獎,3個自治區三等獎的好成績。記者采訪后不久,2019年包頭市第35屆科技創新大賽落下帷幕,同道小學的選手們成績斐然:包頭賽區,“青少年人工智能創意編程”四個一等獎;“青少年機器人創意比賽項目三個一等獎”;“科技創新成果”2個一等獎,3個二等獎;截稿時,又有兩位學生赴寧波參加全國第七屆青少年電子信息智能創新大賽……
在一年一年的參賽過程當中,孩子們獲得了很多課本以外的知識和能力,思維得到了發展。隨著獲獎人數的增多,更多的孩子愿意努力一試,科技輔導員水平也在不斷提高,陪著孩子們一起成長。家長的積極性也被調動起來了,多次獲獎的四年級的小男生馬端澤,今年暑假里父親帶著他去察右后旗觀看火山遺址,收集了火山石標本;學生王可也告訴記者:自己從小就喜歡科技產品和科幻電影與書籍,參加了社團后,不僅沒有耽誤學習,還感覺變得聰明了……
同道科技社團、人工智能編程社團、同道小講堂欄目及同道小科協都已成為推動學校科技普及工作的重要抓手,引領更多的學生熱愛動手動腦的科學探究。因此,2019年,在各級各類科技比賽中,同道小學鏈條式發展,多點開花,出現多項冠軍頭銜,成為內蒙古地區的佼佼者。
那天早晨,記者觀看了同道小學的 “學習準備型跑操”,規模大、全員參與,鏗鏘有力。起初以為無非是簡單模仿普通高中的跑操罷了,全國一窩蜂跟著衡水中學走。后來得知,這背后是有教育理念支撐的。
同道小學校長段思明的辦公桌上放著一本約翰·瑞迪和埃里克·哈格曼合著的《運動改造大腦》,書上面有不少處他的勾畫圈點。段校長說:是這部書啟示了自己——干了20年教育,從來沒有這樣深刻地認識體育和智育的關系,原來“運動后的知識學習效果更好”。于是,他安排了全校雷打不動“學習準備型跑操”,從一年級就開始。起始時,家長反對,怕累壞了自家孩子,如今卻成了學校的常規,學生體質增強了,冬季患感冒的、請假的少了;同道小學敢把體育課安排在早晨的第一、第二節。開始時,教師覺得反常而有異議,“哪有第一二節就上體育課的呢?學生剛運動完,怎么靜下心來上課?應該是上數學、語文課啊?”兩年下來,教師和家長一律認可了:運動,并沒有影響學習成績,反而提高了課堂的效率。
“同道”是個極好的校名,命名者一定是個厚積薄發、學養高深的人,它包含“道常為而無不為”“道不同不相與謀”“同道之人做同道之事”的意思,也包含著“讓不同家庭出身的孩子有相同的、相近的人生之路”的愿景。五年、十年、二十年,當同道的孩子們走向廣闊的社會時,他們或許會感喟:是北梁棚戶區的改造拓展了他們幾代人的生存空間,是同道小學的教育改變了他們的人生軌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