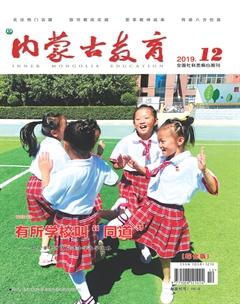面對抑郁,我們能夠做些什么?
陳薇薇

也許每個人在一生中都會有機會遇見“抑郁”——空虛、絕望,每天都被壓力和沮喪撞飛,陷入不良情緒的漩渦。壞心情就像沼澤,越陷越深,整個人如同在懸崖絕壁上漫步,隨時有墜落的危險。
一天,接到大學同學的電話,說她班里有個男生初一的時候成績是年級第一,到了初二開始嚴重下滑,現在不愿與人交流,因為胸口悶,幾次請假停課,且有自殺傾向。
鑒于同學的描述,我懷疑孩子是有抑郁情緒的。但是還有哪些具體表現呢?到底是普通的不開心,還是抑郁情緒?或者是抑郁癥?該去就醫還是只做心理咨詢?我認為首先要到專業部門做診斷,所以建議他去醫院做診斷之后,再決定是否需要心理咨詢。
兩周后,同學又聯系我,說家長已經帶孩子去過醫院了,診斷為抑郁癥,并且開始了藥物干預,但是效果不太好,家長想帶孩子做心理咨詢,她希望把這個孩子推薦給我。單憑心理咨詢,也許不能起到良好的效果,但是如果是認知療法和藥物治療相結合呢?
我很想試一試。
那天天氣很熱,說實話我第一次見到有如此嚴重抑郁情緒的孩子。一個又高又瘦的男孩,憂郁的眼神,背弓得和蝦米一樣,話很少,說話的時候眼睛不愿與人對視。在與孩子和家長做了簡單介紹之后,我讓他們簽了知情同意書,并開始和孩子進行一對一的會談。
“你有什么需要我幫助的嗎?”我問。
“沒有。”他說。
我努力表現得熱情、關心和關注,并向他介紹了保密原則。
“我理解你的感受,是在陌生人面前很難敞開心扉,還是覺得我對于你的問題無能為力?”
“因為陌生。”他淡淡地說。
“我看到爸爸媽媽送你過來的時候,眼神中充滿了焦急,他們希望我能幫助你什么呢?”
“他們希望我走出來。”
“‘走出來是什么意思?”我嘗試進一步具體化。
“就是和以前一樣。”
“我很好奇,以前的你是什么樣的?”
“學習成績很好,雖然在家不愿意說話,但是在學校或和同學們一起時也很開朗。后來我的成績開始滑坡,自己想放棄,也不想和別人說話,封閉自己不愿意出門。”
“這些變化一定讓你很無助很孤獨,所以你自己也試圖走出來是嗎?”
他點點頭。
“當時發生了什么讓你變化這么大?”
“沒有什么。”他說
“我想了解更多你正在經歷的事情,并幫助你,能和我講講放假之后你的每一天是怎么過的嗎?”
他搖搖頭。
我第一次遇見這樣的情況,每次學生來求助的時候,尤其是第一次,他們往往很健談,像打開的水龍頭一樣。而眼前的這個男孩子裹著厚厚的冰層,無法撬動。
如果這樣,不如來關注此時此刻吧,我想。“你剛才搖頭的時候在想什么?”
“我認為咨詢也許幫不到我。”他說。
“你認為‘咨詢也許幫不到你,這種想法,讓你有了什么感受?悲傷?絕望?”
“都有。”
“這確實讓人覺得沮喪。”我感覺到他有深深的無望感,并試圖讓他對咨詢建立信心,我接著說:“我曾經見過一些像你這樣有抑郁情緒的孩子,雖然當時他們也和你一樣,但是并沒有被問題擊垮,最終恢復得很好。我想盡我所能去幫助你,你愿意試一試嗎?”
“愿意。”
雖然僅有兩個字,我已經感到那瘦弱無力的身軀中透出的韌性。
“感謝你對我的信任,因為今天是我們第一次會面,所以我們今天的目的不是解決問題,我需要問你一些問題,了解你的一些事情,目的是搜集一些信息,并且做出初步的評估,可以嗎?”
“好的。”
“剛才我看見你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是覺得胸口悶嗎?”
他抬頭看了我一眼,“是的。”
“身體還有哪些地方不舒服?”
“胸悶、頭痛、睡不好覺。”
“多久了?”
“一個月了。”
“當時發生了什么,讓你身體出現了這些癥狀?”
他停頓了一會兒,搖了搖頭說:“并沒有什么。”
“你說原來性格很開朗,那時候應該有不少朋友吧?”
“是的,不過現在很少一起玩了。”
“為什么呢?”
“有一次,我和其中的一個朋友吵架了,后來他聯系其他人漸漸疏遠我。”
“除了他們,你還有其他要好的朋友嗎?”
“班里還有幾個,但是我現在很少和他們說話,也很少在一起。”
“我感覺你是很期待朋友的。”
“是的,我害怕被拒絕。”
“曾經有過這樣的經歷嗎?”
“有一次,我和班里的一個同學打招呼,但是他顧著和別人說話,沒搭理我。”
“當時很傷心難過嗎?”
他點點頭。
“當時有了什么想法讓你這樣難過?”
“我想他一定不在乎我。”
“你認為他不在乎你,很難過,那個時候你做了什么讓自己不那么傷心嗎?”
“我只是回到座位不愿意再和他說話了。”
“這樣做讓你好受些嗎?”
“并沒有,很失望,更不想和他們說話了。”
看來,對情境的回避強化了他的消極思維,并且變成情緒以及行為惡性循環的一部分。這種惡性循環加深了他的問題,使他更不想參加社交活動了。
我在紙上呈現了他的認知模式,希望可以引導他了解自己慣用的認知行為方式。并試圖解釋將如何用認知調試的方法對他進行工作。
“我們來看看你的思維如何影響你的情緒。你認為朋友不在乎你,有沒有什么證據可以證明你的這種想法?”
“沒有?”
“還有沒有其他可能?”
他把頭埋得更低了。
“有沒有可能是因為他沒聽見?”我說。
“沒有這種可能。”
“如果真的是這樣,你會怎樣看待自己?”
“不被喜歡,沒有價值。”
“因為同學沒有理你,你就是不被喜歡的?沒有價值的嗎?你的價值在于是否被別人喜歡?”
他一直沉默著。
“也許只是因為你現在的抑郁情緒,許多時候思考的并不是事實,當你發現想法也許并不是完全真實的時候,你會感覺好一些。”
為了及時獲得反饋,我接著問:“你會覺得我哪里講得不清楚或者不對嗎?或者你有什么想法和建議和我交流。”
“沒有,也許是這樣吧。”
他還是不太愿意敞開自我,一直在不停地喘息,我感覺他已經相當疲憊,所以想要結束這次會談,做最后的總結。
“所以,我今后將會和你合作,幫助你改變使你抑郁和焦慮的思維方式,你會學一些技巧,能夠更現實合理地思考問題,并為達到目標去積極行動,好嗎?”
“嗯。”他輕輕說了一聲。
咨詢結束后,我糾結于這個個案是否可以繼續再做下去。自己的意識中是很想做下去,因為對認知療法感興趣,所以很想證明自己掌握了多少,但是這個咨詢明明不應該再繼續做下去了。一是因為很難撬動這個孩子封閉的內心,二是自己對認知療法所學的理論與實踐結合經驗并不豐富,還不能解決這么嚴重的心理問題。其實做咨詢也要放下功利心。要認識到自身的局限性,不能為了滿足自己的欲望而利用來訪者。
幾天后我進行了回訪,家長說醫生建議由于孩子目前嚴重的抑郁情緒,交流能力有限,不適合做咨詢。因此和家長協商,咨詢就此終止。
這次的咨詢給我上了很好的一堂課,什么是有所為,有所不為。當終止咨詢的一瞬間我很輕松。若心中不能放下“貪嗔癡”就不能明心見性,真正灑脫。
其實這個個案不僅僅可以用認知療法,還可以嘗試人本主義或者后現代療法。做心理咨詢往往需要熟悉種種治療理論,不過每種理論都存在自己的優勢和局限性。有時候我們需要把各種理論和知識經驗整合,而這個整合的過程需要多年的學習,如果我們打算短時間內學會所有東西,一定會被混亂感和絕望感所淹沒,將不同的理論技術進行成功的整合,需要多年的反思、實踐以及對不同理論的讀物進行廣泛的了解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