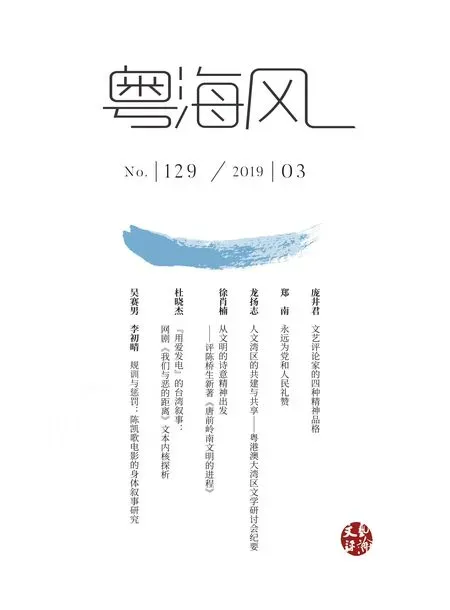惟能誠于人,方能誠于文:王干散文欣賞
文/劉根勤
王干,昔日的干兄,如今的干老,囑我為其散文作評論。
當真是榮于華袞,然而也絞盡腦汁。
這標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濃濃的古龍味道。
原話是西門吹雪說的:“唯有誠心正義,才能到達劍術的巔峰。”
西門吹雪,是古龍筆下的劍神。他的話,就是古龍的話。
這是古龍理解的劍道,濃郁的中國風。
西門吹雪說話的對象,是葉孤城。這是當時兩大絕頂高手。他們是生死決戰的主角,同時也是相互尊敬的對手。
這兩人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高冷,孤傲,像冰山一樣。
但西門吹雪有一個好朋友,也是葉孤城信任的人,就是陸小鳳。
陸小鳳不冷,很熱情,性格輕松幽默,有他的地方就有笑聲,武林中有名的人物,都喜歡與信任他。
熱情難得,真誠更難得。
陸小鳳能與西門吹雪交朋友,又能得到葉孤城的信任,他的本性,自然是真誠的。
同時,他的武功也是天下絕頂。
孔子說了:“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一個人,如果受人愛戴,他一定具備基本乃至高超的才能。
天下雖大,道理一樣。
環顧當世,王干,堪稱文壇的陸小鳳。
陸小鳳的特點,古龍迷無人不知,他的機智、武功、酒量、臉皮之厚和好色出類拔萃。他生性風流,好管閑事,喜歡喝酒,欣賞美女,更重情義。
熟悉王干的人都知道,這些特點,或者說優點,幾乎就是王干的鮮活印象:精力充沛,宣泄出來,表現就是極端的好奇,好學,好玩,斐然成家,自得其樂,推己及人,助人為樂,成人之美。
可以說,除了傳說中的“四條眉毛”之外,陸小鳳的特質,王干同時具備。
當年王朔戲謔的“文壇奔走相告委員會主席”,固然是對王干的善意形容,又何嘗不是陸小鳳在古龍世界的真實形象?
不恨王干不見古龍,只恨古龍不見王干,不然當浮一大白。
7月份,我收到王干惠贈的文集,煌煌11冊之巨。
滿滿的感佩。
所感動者,我認識王干,是在1999年,不經意間,20年了。
當時我作為南京大學歷史系研究生,卻有著濃郁的文學情結,經常跑到江蘇作協去跟一批師友聊天喝酒。那時別說微信,連手機都沒有,某天我經過創作室時,看到一位滿臉笑容的中年人,面前放著“王干”的字牌,主動進去攀談,結果一見如故。
王干大名,如雷貫耳。
說是中年人,當時他滿打滿算虛歲四十。便是到今天,他臉上還是容光煥發。
我老記得一段掌故:鐵木真14歲時,父親遇害,他流浪草原,4年間結識了許多英雄豪杰。其中一位老首領將自己的女兒孛兒帖嫁給了他,原因是:這孩子臉上有光,眼中有神。
王干出名,那是不可思議的早。
1980年前后,他已經是江蘇嶄露頭角的青年作家與評論家。后來他跟文壇大佬王蒙的傳奇對話,奠定了他在文壇的資歷與地位。
“二王”對話,是里程碑式的,不過那主要用于對普通讀者的介紹。
我個人對王干的認知,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汪曾祺,熟悉的人,都叫“汪老”。
可以說,汪老與王干,絕對的“情同父子”。
王干從來沒有這么說,但從他的文字中,這種評價絕非過譽。
汪老是性情中人,王干也是。
更重要的,他們都是里下河地區人氏。
這里文風鼎盛,鄉情濃郁。
我很榮幸,跟兩代文豪毗鄰。我多次在媒體與課堂上說,20世紀的中國作家,能夠接續中國傳統的,或者與國學有關的,只有汪老與金庸,汪老隱居京華,金庸沉潛香江,南北雙絕。
2000年初,我在南京聽過金庸講座,大俠才名冠世,但我深感難以溝通。那時汪老已經過世三年,每次撫讀其文,想見其為人,可惜無緣拜見。
但是結識了王干,這位汪老的嫡派傳人,也不枉了。
汪老當年有篇懷念業師沈從文的文章,標題是《星斗其人,赤子其人》,我覺得這個標題,用來形容王干的人與文,準確不過。不過汪老珠玉在前,我只好另起爐灶。
20年間,我和王干聯系不多,但心照不宣,見面就是大酒,然后就是大作相贈。
所佩者,20年后,王干威名與日俱增,創造力更是一騎絕塵。
文壇對王干的評價,大體上幾句話:說不盡,難以歸類。
文學之內,他是作家,寫散文,寫小說。
他是大名鼎鼎的評論家。改革開放40年,他與中國文學一起成長,是記錄者,更是參與者與推動者。
他還是享有盛譽的編輯,一代名編,策劃無數大型活動,推出無數經典作品。
他是青年作家的導師,優秀作家的知心朋友,還是里下河地區文學青年的偶像,是汪老大纛的接力者。
文學之外,他是個高級玩家。酒量大、酒風好,他的烹飪也是一絕,藉此會遍各界英豪。他的書法有底蘊,足球籃球都好,圍棋也不錯。當然這是我的看法。趙本夫說,王干的圍棋一般,但與那些圍棋國手比如常昊、羅洗河等人的對話,非常專業。
如此旺盛的精力與創造力,已屬罕見。他居然40年如一日,不能不說是奇跡。
11冊文集,洋洋灑灑,嘆為觀止。
最好玩的還是當他的面跟別人說起他的名字,每次都說:王干,本名,非筆名。
當年的干兄,現在的干老,容顏依舊,但受人尊敬與親愛,卻是與日俱增。
關于王干的記憶與觀感,滿滿的都是溫情與熱情。
文人相輕,在王干這里,是絕對不存在的。
王干身上,絲毫沒有新式文人的拘謹與清高,有的是滿滿的煙火氣。
文學于他,就如朋友,或者如一日三餐,不可須臾或缺。
又如蘇東坡作文,王陽明靜坐,不得不為,樂在其中。
此所謂良知與初心,正心誠意的典范。
但凡有血氣之人,見之無不感興,佩服。
王干跨界極廣,這里重點介紹他的散文。
《王干文集》中,有單列的《王干隨筆集》,也有散布于其他分冊中的各種美文,還有特別具有王干個人標記的博客文章。
這些文章,絕大多數發表于專業報刊,許多甚至是國家級的學術與輿論平臺,也有不少沒有發表的,但王干個人覺得珍而寶之,不吝與文壇內外的朋友們分享。
其實,正如王干本人的“難于歸類”一樣,他的文章也是如此。
眾所周知,王干在公眾場合,算是不善言辭的。多年前,他在南京大學舉辦過一次講座,我的老師錢乘旦教授主持的,他講金庸與王朔的那段小糾紛,語速很慢,笨拙而真誠,看得出他對南大師生的尊敬。
但王干在單獨溝通時,卻能做到邏輯清晰,節奏穩定。當時有一位我們同級的研究生“質問”他為什么當代文壇沒有大師。王干極有禮貌地說,大師并非當代就能評定的,他認識文壇上許多創作者,極有潛力,但是需要時間,他們需要時間來進步,讀者也需要時間來了解他們。提問者十分滿意。
講座畢竟是社會性的場合。或者并非王干所長。
王干的強項,是作家與學者的專有空間,是朋友們的酒席,是案牘與鍵盤。
不管寫論文還是散文,王干都是倚馬千言立等可取。真如蘇東坡所說的行云流水,行于所當行止,于所不得不止。
其他不說,只要統計一下他40年來的寫作數量,絕對在千萬字以上。而且高質量的寫作很多。研究王蒙、汪老如此,研究莫言如此,研究鐵凝、王安憶、池莉乃至后來的中生代、新生代作家,都能切中肯綮,深得理論界、評論界與創作界的共同認可。
如果按照現代的學術規范以及量化標準,王干的文學評論不一定能符合學院派學者的要求,原因就在于他的個人印記太濃。
王干的論文,帶有很強的詩性特征。他研究文學,他的研究,其實也是一種創作。
研究界的風尚,是文章要不帶煙火氣,超凡脫俗,四平八穩,不偏不倚。這是說的好聽,說的不好聽,就是沒有人味。科學研究或許可以如此,人文領域的觀察,恰恰最需要有溫度的作品。早有人說了,研究者或者評論家自己不會寫好看的文章,拿什么來研究與評論別人的文章?
大多數時候,文化界總是被學術八股把持,這是無奈的現實。
王干的出現,對主流的行文,幾乎是一種災難,或者說泥石流。但對作家,對讀者,卻是不折不扣的清流。
王干的出現,是文壇與研究界的幸運。
以他的才情與閱歷來寫散文,可以說是再合適不過了。
王干的故鄉是興化陳堡小鎮,位于里下河腹地。這片1.4萬平方公里的平原,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地處江淮之間,水網縱橫,水災密集,戰火頻仍,生活艱難,這里的人民卻靈性漫漶,不擇地而出,無往而不利。
傳說中“江北出高僧”,汪老佛性很重,這個熱愛生活的老頭兒,寫得出晶瑩剔透的《受戒》。早他兩百年的鄭板橋,脾氣很倔,但舉手投足都是才氣,美國大都會博物館便收藏了許多他的作品。
相比這些前輩,王干同樣才氣充沛,他更多了幾分入世的歡愉,他的單純與活力,讓人忘卻了他是一個文人。
然而他的確是一個文人,一個好玩、會玩更善待別人的文人。
《王干隨筆選集》精選了王干的隨筆50余篇。
我們挑選其中的一些篇目來分析。
《向魯迅學習愛》《老舍與說話》《汪曾祺與生活》《王蒙的N個春天》,這幾篇無疑要單列,尤其是后兩篇,充分體現了他對前輩的敬意。這兩人許他以忘年交,是他在文壇的伯樂。而這兩位大佬對文學與文學家的責任心與熱情,也在他身上得以延續。
汪老的小說好,散文更好,我最喜歡看他談吃的作品。那種輕松寫意,深得明清小品的精髓。王干得其三味。這對老少爺們可謂淮揚美食縱橫京城的雙璧。
如前所述,王干是玩家。隨筆中談玩或者說文體綜藝的,琳瑯滿目,蔚然大宗。這里只列舉幾篇,《論麻將的無限可操性》《閑讀圍棋》《圍棋的極限與境界——與常昊對話》《足球頌》《說譜》《偉大的嗓門報國無門》《武俠、灌水與大話》《貝哥哥的發型和縣委書記的帽子》。
王干身材不高,顯壯碩,足球踢得不錯,聽說籃球也是可圈可點,帶球突破三步上籃拿得出手。人人以為他好動,沒想到他動如脫兔,也能靜如處子。奮筆疾書就不說了,坐下來打譜或者揮毫也都煞有介事。
還是那句話,至情至性的人,做什么像什么。
特別有意思的是,王干對武俠小說尤其是金庸評價極高,他認為,金庸小說與四大古典名著相提并論毫不遜色。金庸去年剛去世,我不知道他之前跟王干是否熟識,有沒有聽到這些評價。他如果在天有靈,當為有這位知己而欣慰。
王干是頂級的文學評論家,也是優秀的社會與文化觀察者。
都說評論家其實是表揚與贊美家,王干證明了真實批評的存在。他的兩篇隨筆,嚴厲批評張藝謀的審美水準,說他是“審美吸血鬼”。
他對許多文化現象與事件,不但關注,而且持續關注。他寫了四篇文章談簡化字,《五十年內,廢除簡化字如何》《簡化字是資源匱乏年代的產物》《簡化字是盛世中國臉上的一顆痣 ——再說五十年內廢除簡化字》《簡化字是“山寨版”漢字——與王立群先生商榷》。從這些標題就可以看出,他的態度嚴肅且專業,他指出簡化字屬于“權宜之計”,但難以持久。他提出“廢除”的建議,但又不是一蹴而就,要從長計議。這都體現了他的責任心與專業性。
這些文章,冠以“隨筆”與“散文”的名義,其實比大部分高頭講章與官樣文章都更有內涵,也更有可行性。
這些文章,有兩大特點:一是信息量大,從文學到文化,從專業到社會,從歷史到當下,可以說是百年中國精神的全景掃描;一是性情充沛,作者的真誠、熱情與深刻,汩汩而出。
提到散文,不能不寫自己。王干的魅力,在于真實而鮮活。
汪老,與他筆下的蘇北、云南與北京,是20世紀中國文壇的絕美風景。
王干比汪老小了四十歲。他所處的時代,更恢弘,更精微,更熱烈。
因為時代的進步,尤其是交通與通訊的進步,王干的視野,比前輩更寬廣。
所以他寫生活,寫故鄉,寫居住與游歷過的城市,可謂最好的人文紀錄。
他寫魂牽夢縈的故鄉泰州,寫念茲在茲的江南古城,寫高屋建瓴的大國首都,都別有風味。
《泰州是誰的故鄉》《泰州有條鳳城河》《關于泰州美食的記憶》《個園假山》《江南三鮮》《明前荼、雨前茶與青春毒藥》《閑話南京》《北京的春(夏秋冬)》《在懷柔觀山》《小二、點五、涮羊肉》《男人居住北京的十一條理由》《如何進入重慶》 《過橋米線和菜泡飯》。
這些文章,光看標題就知道內容。但是真看進去,欲罷不能。因為王干的觀察與體驗能力,的確不同尋常。
他說男人居住北京的十一條理由,頗有可觀之處,關鍵是結尾來了一句,北京有我。令人忍俊不禁。
的確如此,“我”是世界的中心,“我”要不在北京了,北京再好,也只是回憶,而不是鮮活的“這一個”。
令我感佩的是,王干筆下的故鄉,如同母親的體溫,如同啟蒙老師的聲音,如同初戀情人的眼神,是他對這個世界的起點,也將是歸宿。
百年來,文人對故鄉,幾乎是一邊倒的“批判”,“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現在的網絡上,每到過年,都是一批學者文人如此。似乎不如此不足以顯示自己的孤高與冷傲。他們仿佛寓言故事中的某種人,總想提著自己的頭發,讓自己離開大地。
王干不然,他才名早著,游遍四海,從京城到老家,從達官貴人到販夫走卒,他無不傾心結納。
不是王干沒有遇到挫折,恰恰相反,他遇到的挫折并不少。他在一篇自傳體小說中,提到在老家鄉鎮中學從教時遇到的黑暗經歷,義憤填膺。
但正如一滴墨水污染不了江河湖海。王干筆下的故鄉,有情有義,活色生香,流光溢彩。
泰州市委書記韓立明女士寫了《泰州的海》,王干為之呼應,寫了《泰州的河》。兩篇文章,寫出了泰州人靈魂中的詩意、靈性與豪情,可謂聞弦歌而知雅意。
這篇文章發表在《泰州日報》上,國家級的《新華文摘》聞風而來,收錄了這篇文章。
王干對家鄉的深情,獲得了充分的認可。
這一點,他像極了蘇東坡:上可交玉皇大帝,下可交卑田院乞兒,眼見得世上無一個不是好人。
王干的散文好看,王干本人更好看。
還是那句話:惟能誠于人,方能誠于文。
最真的人,最誠的文。
期待王干創作生命長青,成為“干”,也就是實踐,行動,創作的王。
如此,文壇幸甚,故里幸甚,青年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