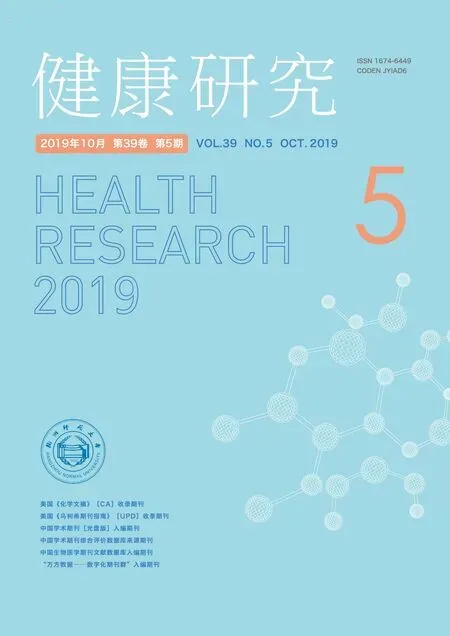系統性紅斑狼瘡合并開角型青光眼1例臨床分析及文獻復習
韓平陽,鄢巨振
(杭州師范大學附屬醫院 腎病風濕免疫科,浙江 杭州 310015)
系統性紅斑狼瘡(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SLE)為一臨床常見多系統受累自身免疫性疾病,好發于育齡期女性,發病機制與多種自身抗體形成相關。糖皮質激素(glucocorticoid,GC)為治療SLE的基礎用藥,根據SLE疾病活動度及不同器官受累,GC劑量及維持時間有所不同[1]。長期使用GC相關副反應已被臨床醫師所認識,包括骨質疏松、向心性肥胖、類固醇糖尿病、白內障等[2]。GC所致青光眼雖然已被認識,但仍未被臨床醫生所重視[3]。本文報道1例SLE患者在GC治療 4年后,出現雙眼繼發性開角型青光眼,因眼壓升高未及時發現導致雙眼不可逆視野缺損和視神經萎縮、丟失。
1 病例資料
35歲女性,因“確診SLE 4年,自覺左眼鼻側視野缺損2天”入院。患者4年前因鏡下血尿就診,當時實驗室檢查:ANA(+)(1∶100稀釋),U1RNP抗體(+),Sm抗體(+),SS-A抗體(+),SS-B抗體(+);抗心磷脂抗體(-);直接抗人球蛋白試驗(+);血紅蛋白101 g/L;血沉65 mm/h;超敏C反應蛋白(-);血生化:球蛋白55.5 g/L↑,白蛋白正常;免疫球蛋白G 39.6 g/L↑,免疫球蛋白E 151 IU/mL↑,補體C3 0.37 g/L↓,補體C4 0.05 g/L↓。胸部CT:雙肺散在肺大泡;B超:淺表多發淋巴結腫大,脾腫大。眼科檢查:雙側眼壓正常(右眼14.3 mmHg、左眼14 mmHg);曲光度數:右眼-5.00、散光-1.50,左眼:-4.50,散光-2.75;視野檢查雙眼均正常。診斷SLE、繼發性干燥綜合征,患者長期服用強的松5 mg/d聯合羥氯喹0.1 g/d治療。2年前因劇烈腹痛,診斷SLE并發急性腸系膜血管炎,GC加量至甲強龍40 mg/d靜滴,聯合來氟米特口服;癥狀緩解后GC逐漸減量,15個月前減量至強的松15 mg/d口服維持至此次入院;羥氯喹加量至0.4 g/d口服、未減量。半年前開始出現雙眼發紅、疼痛,間斷頭痛,抗生素眼藥水滴眼治療,未監測眼壓。2天前自覺左眼鼻側暗區,當地醫院測眼壓:左眼59.0 mmHg、右眼51.5 mmHg,視野檢查提示雙眼視野缺損,診斷“藥物性青光眼”,考慮羥氯喹所致可能性大,當日停用,同時予“布林佐胺+卡替洛爾+拉坦前列素”滴眼液降眼壓治療。第2日來我院眼科復查眼壓:左眼28.3 mmHg、右眼24.5 mmHg;屈光度數:左眼:-7.00、散光-2.25×168,右眼-6.75、散光-2.75×166;視野檢查左眼下1/2象限、右眼上1/4象限視野缺損;OCT檢查雙眼黃斑厚度無明顯異常,周圍神經視網膜厚度(RNFL)顯著下降,左眼為甚,提示視神經嚴重萎縮;前房鏡檢查提示為開角型。眼科診斷:雙眼開角型青光眼,建議繼續原眼藥水滴眼。追問病史,患者16歲開始近視,無青光眼家族史。結合患者長期服用GC及眼科檢查,診斷為GC繼發開角型青光眼。
2 討論
本文報道1例SLE患者,服用強的松>10 mg/d、持續2年以上,并發開角型青光眼,眼科醫生根據高眼壓導致視神經因缺血而丟失程度,推測其眼壓升高至少達半年以上。遺憾的是患者半年余來眼部癥狀雖多次向風濕科醫師反應,但均未引起重視。文獻報道[4]使用>7.5 mg/d的強的松或等效物、持續1年以上風濕病患者,開角性青光眼的發生率為19%,7.5 mg/d者發生率為3%;若早期及時發現并停用或減量使用GC,眼壓可于2~4周內降至正常,眼壓過高時可給予降眼壓藥物滴眼。Brock-Utne等[5]報道1例28歲女性SLE患者服用強的松5~30 mg/d,4年后出現開角型青光眼,給予毛果蕓香堿液滴眼并行左眼手術,后眼壓恢復正常。Zhang等[6]報道4例22~29歲SLE患者服用強的松>10 mg/d,持續3~10年后出現開角型青光眼,4例患者均有近視;基礎眼壓28~60 mmHg (平均46.5±11.1 mmHg),使用最大局部和全身抗青光眼藥物,眼壓仍不能控制,均行小梁切除術輔助鞏膜下絲裂霉素C治療后眼壓明顯下降,隨訪過程中眼壓控制在2.50±1.77 mmHg。
SLE本身及羥氯喹均可并發眼部病變。文獻報道SLE高度活動時可引起狼瘡性脈絡膜炎[7],脈絡膜滲出導致閉角型青光眼,給予激素及免疫抑制劑控制狼瘡活動后,眼部并發癥可隨之緩解。本例患者入院評估SLE病情處于穩定期,無明顯活動性表現,且眼科檢查提示開角型青光眼,不考慮SLE活動所致。羥氯喹所致眼部損害主要是由于藥物本身毒性作用損害視網膜感光細胞,出現視網膜色素上皮層的破壞[8],患者早期癥狀為視力下降、中心或旁中心視物遮擋,晚期可有視物變形與色覺改變;多數文獻報告顯示視網膜損傷均發生于黃斑區或中心凹旁[9]。2010年歐洲抗風濕病聯盟(EULAR)指南推薦[2]:SLE患者使用抗瘧藥治療引起的視網膜病變的發生率不高(0.5%),危險因素包括:年齡60歲以上、存在黃斑變性、視網膜萎縮、肥胖、肝腎功能不全、治療時間大于5年、羥氯喹日劑量在6.5 mg/kg以上或者氯喹日劑量在3 mg/kg以上。本例患者2013年初診時,評估均無上述危險因素,當時眼科檢查提示雙側眼壓及視野均正常;此次發病眼科OCT檢查提示雙眼黃斑中心凹區正常,視網膜損害主要發生在中心凹周邊區域,與羥氯喹片所致眼底損害表現不符。查閱相關文獻,最終考慮患者開角型青光眼與系統使用GC相關。
多項指南[2,10-11]提示GC所致眼部并發癥主要為白內障和青光眼,使用GC治療前需評估患者危險因素,進行基線眼部檢查。GC繼發開角型青光眼的高危因素包括[4,12]:存在開角型青光眼,糖尿病,高度近視,一級親屬有原發性開角型青光眼。已經存在青光眼的患者尤其敏感,46%~92%開角型青光眼和65%閉角型青光眼患者將會因暴露于GC而加重。本例患者有長期近視,5年前開始使用GC前雙眼屈光度數已明顯升高,屬于存在高危因素患者,但當時未引起重視。
多種途徑的GC用藥均可引起青光眼[12],包括系統性(口服和靜脈)、局部(眼和皮膚)、注射(眼周和皮下)、吸入和鼻部用藥。其引起眼壓升高的可能機制為:小梁網細胞含有高濃度的GC特異性受體,被認為在GC誘導高眼壓中發揮作用。GC可能進入小梁網細胞并激活這些受體,因而改變小梁網細胞基因的表達。這些改變可引起細胞外基質的改變,這些無定形顆粒樣物質在鞏膜靜脈竇內皮下聚集,使小梁網增厚、小梁網內空間減少,導致房水流出減少、眼壓升高。
GC所致眼部損害雖已有多項指南指出,但尚未被臨床醫師所重視。Carli等[3]的研究顯示:接受GC治療的170例SLE患者,平均隨訪時間11.5年中,20%患者從未接受過眼部檢查,余80%患者接受眼部檢查平均時間為6.25年;僅有33%的患者在接受治療1年內進行過眼部檢查;其中白內障發病率為39%,青光眼發病率為3%。Han等[13]研究也顯示在使用GC治療(強的松>7.5 mg/d×6 months=1350 mg)的37例患者中,風濕科醫師僅推薦了37.8 %的患者接受眼部檢查,其中6例有青光眼家族史的患者均未接受過眼部檢查。
綜上所述,風濕科醫師應重視GC誘導的眼部并發癥,使用GC前進行基線眼部檢查包括眼壓測量、白內障檢查等。對有并發青光眼高危因素患者需權衡GC使用利弊,同時定期眼科復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