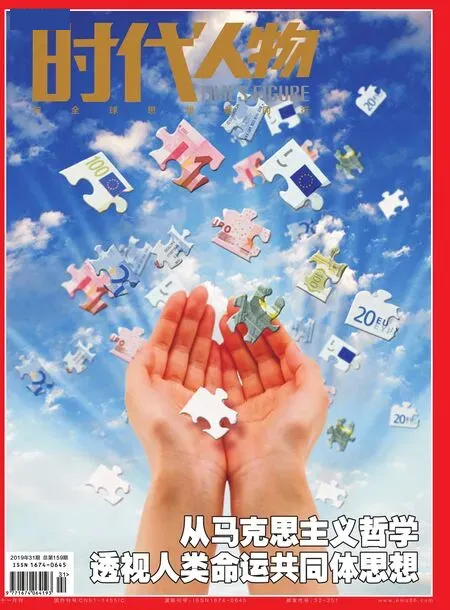漢至魏晉南北朝工筆人物畫“形神觀”探究
□文|楊靜遠
(作者單位:中央美術學院)
在文人畫興起之前,“寫實主義”一直是中國繪畫的傳統,方聞在《心印——中國書畫風格與結構分析研究》一書中指出:“14世紀,人們已經全面地掌握了繪畫的幻覺效果。元代的杰出畫家追求繪畫的超再現性(extrarepresentational qualities)。隨后,”不似“的觀念受到認真的探討。”[1]羅樾與方聞觀點相同,亦是將元代作為寫實與寫意的分水嶺。羅樾認為漢代至南宋的藝術是再現藝術,而元代之后則是拋棄了宋代客觀再現的傳統。因此,中國在文人畫興起之前具有寫實性意義的工筆人物畫其實十分發達。然而文人畫家認為“論畫以形似,見于兒童鄰”,也就是繪畫需要“逸筆草草,不求形似”。作為宋代著名的文人畫家,蘇軾將形似與兒童畫進行了比對,認為強調形式的繪畫是幼稚的作品,并認為繪畫要求“常理”。這種風格受到后世文人畫家的追捧,遂不求形似,以筆墨游戲作為抒發情感的對象在宋之后備受文人畫家的喜愛。
然而中國繪畫藝術從漢代開始就出現了對于“形”的追求,并與“神”結合萌發了中國工筆人物畫重要的范疇——“形神論”。從考古上看,中國的工筆人物畫的確至漢代已經成熟,馬王堆漢墓出土的T型帛畫即是明證。繪畫的成熟自然理論也得到了相應的發展,《淮南子.說山訓》中說道:“畫西施之面,美而不可說,規孟賁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亡焉。”該句中的“說”通“悅”,意思是:畫西施的面部,如果只是挺好看而不讓人賞心悅目,觀賞孟賁的眼睛,只是特別大看完不讓人害怕,這就是君形亡矣。此時劉安的《淮南子》中并沒有明確指出“形”“神”,而是以“君形”代替。所謂“君形亡焉”就是指畫人物時只有形似,而未有神似。此處所言之“神”即是指人的精神狀態。《說苑.反質》中有言:“精神者,天地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而各歸其真,故謂之鬼。”[2]《論衡.論死》中又言:“神者,伸也,伸復無己,終而復使。人用神氣生,其死復歸神氣。”[3]漢代對于人的精神是十分看重的,他們認為人的精神是人永恒的存在,因此就形成了魂魄與肉體的二元觀。而精神又是人生命的真正存在,因此神對于人來說是靈魂的象征,不死的象征。將神借用到藝術中來表現,即是將宇宙生命觀與藝術進行了結合。
雖然《淮南子》中論述了“形”“神”的概念,但是并沒有真正的指明出來,也沒有討論兩者之間的辨證關系,真正代表將中國工筆人物畫中“形神論”形成的是顧愷之。顧愷之十分注重人物畫,并認為人物畫是最難畫的,他說:“凡畫,人最難,次山水,次狗馬,臺榭一定器耳,難成而易好,不待遷想妙得也。”原因在于人物畫必須要畫的傳神,那么如何解決人物畫的傳神問題呢?他在《魏晉勝流畫贊》云:“凡生人亡有手揖眼視,而前亡所對者,以形寫神而空其實對,荃生之用乖,傳神之失矣。空其實對則大失,對而不正則小失,不可不察也。一象之明昧,不若悟對之通神也。”[4]在文中顧愷之提出了兩個概念,一是以形寫神,二是空其實對。那么何為“以形寫神”呢?其指人物的神態需要靠形來表現,如果形不準確,那么人物的神態就喪失了,即形是工筆人物畫的基礎,而神是工筆人物畫追求的最高目標,那么形與神就形成了一對辨證關系,兩者互相依存。那么在以形寫神的基礎上,他指出如果沒有神態,那么人物則是空其實對。所謂空其實對則是從三方面來討論的,一方面是從人物本身來說,如果人物空有其形,那么其神態即喪失;從第二方面來看,不僅僅需要的“對而正”,而且需要人物與人物之間的情感交流;第三方面就是要考慮人物與環境之間的關系,也就是需要有故事情節。漢代的繪畫多為“成教化,助人倫”之用,因此人物畫十分流行,顧愷之的《女史箴圖》《列女仁智圖》等都是以政治教化為目的的作品。那么故事情節就需要貫穿于作品之中,因此,人物與空間的關系自然成為需要考慮的問題。從“以形寫神”到對“空其實對”的否定其實表面了顧愷之對形神觀的提升,即由具體單個人物畫的創作方法轉向了對整體布局的把握上來了。因此,顧愷之將“空其實對”視為大失,那么“不空其實對”則是顧愷之對于藝術的整體追求。所以,神在顧愷之那里成為了藝術的最高追求,并與形形成了一對范疇,成為中國工筆人物畫的重要創作與品評標準。
那么如何才能做到以形寫神呢?顧愷之提出了首先要遷想妙得,也就是繪畫需要對客觀對象進行觀察,然后再內心中進行體驗與把握,也就是要把握好主客觀之間的關系。那么如何通神呢?顧愷之提出來了悟對通神,也就是在觀察的基礎上,要深入到人物內心,了解人物性格。因此,顧愷之十分注重人物眼睛的刻畫,畫完人物后他經常不點睛,需要觀察很長時間后才進行刻畫。
在顧愷之基礎上,謝赫將人物畫再一次進行了總結,提出來了人物畫品評的最高標準為“氣韻”。何為“氣韻”?謝赫在《古畫品》中說:“氣韻,生動是也。”也就是“氣韻”是人物畫中神態的表達。“氣”本為哲學概念,《黃帝內經》中提到:“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陰陽。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其九州、九竅、五臟、十二節,皆通乎天氣。”《淮南子.原道訓》:“氣者生之元也。”在中國古人看來,氣為宇宙萬物的本源,氣分陰陽,陰陽化而萬物生。所以氣帶有“生機”的意義。至曹植將氣引入文學藝術中后,“氣”一詞得到了廣泛的運用,那么氣的意義也得到了更廣闊的延伸。劉勰在《文心雕龍.明詩篇》說建安的詩是“慷慨以任氣”,鐘嶸在《詩品》中謂曹植的詩“骨氣奇高”。這明顯與魏晉時期興起的人物品藻有關。《世說新語.賞譽》:“王戎云:‘太尉神姿高砌,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外物。’”從此我們能看出來,人物品藻的興起,使得人們對于人物的觀察已不僅僅是形態,而是神采、風采、氣度等,也就是強調一種抽象的生命品質,所以氣就是人一種生命的精神品質。
“韻”并非形容繪畫的術語,而是與音樂有關。曹植《白鶴賦》“聆雅琴之清韻”,因此,韻”與強調內在抽象化的精神品質不同,而是形式所發生的音韻,給人以空靈的美感。
因此,氣韻就是從神與形似兩個角度闡釋的,“氣”形成了“生”,“韻”形成了“動”,也就是氣與生命精神氣質有關,韻與形式所產生的韻律動感有關,兩者的結合就形成了對形神論的探討。那么謝赫的“氣韻”與顧愷之的“以形寫神”有什么區別呢?顧愷之其實是從創作的角度討論的,而謝赫則是從品評的角度討論。雖然顧愷之提到了神的重要性,也能從中看到神也與傳統哲學存在關系,但是他并未有將人物畫提高到“道”的高度,而謝赫以“氣”為出發點,討論了氣在人物畫的意義,而氣本是宇宙萬物的本源,將宇宙萬物本源與人物畫進行結合討論,進一步形成了繪畫這一小宇宙與宇宙自然的大宇宙相統一的觀念,遂使中國傳統工筆人物畫形成了與道等同的高度。
注釋
[1][美]方聞,李維琨譯.心印——中國書畫風格與結構分析研究,上海書畫出版社,2016年版,第20頁
[2][漢]劉向:《說苑》,錄于[明]程榮纂輯:《漢魏叢書》,吉林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464頁
[3][漢]王充.《論衡》,錄于[明]程榮纂輯:《漢魏叢書》,吉林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850頁
[4]鄭午昌.中國畫學全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5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