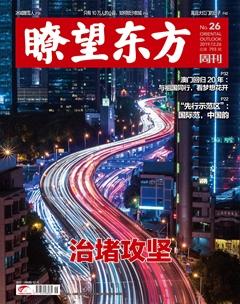人們為什么仍在讀路遙
劉佳璇
2019年冬日初雪之后的北京,天氣更加寒冷,一群人因為一個27年前離開的中國作家聚在一起。這個作家就是路遙——如果他還活著,在這個冬天會迎來自己70歲的生日。
為紀念路遙誕辰七十周年,2019年12月1日,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在北京舉辦了典藏版《路遙全集》發布會。
和路遙成長與成名的時代相比,中國社會如今已發生了巨大而深刻的變革,閱讀的媒介也有了變化。但在微信讀書App的總榜上,《平凡的世界》穩居前五,仍延續著它問世以來“國民暢銷書”的神話。
“拿起《平凡的世界》,千百萬的讀者會覺得這好像說的就是我的事,就是我的情感。”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李敬澤在發布會上說。
27年過去了,路遙的小說為什么能穿越代際的隔閡,依然被讀者們熱愛和感激?
平凡世界里平凡的人
著名作家陳忠實曾評價,在當代作家中,路遙最能深刻理解這個平凡的世界里的人們對中國意味著什么。
“他本身就是這個平凡世界里平凡的一個人,卻成了這個世界人們精神上的執言者,一次又一次裂變和升華,他的情感是充滿血肉的情感。只有看到這一點,我們才能破譯長篇小說《平凡的世界》里那深刻的現代理性和動人心魄的真血真情。”陳忠實說。
路遙的作品能在時代變化中保持活力,歸根結底還是真正關切了平凡人的命運和痛苦,并提供了一種超越苦難的精神力量。
路遙作品里主人公在陜北農村經歷的饑餓與貧窮,以及由此引發的文化自卑和想掙脫束縛的強烈愿望,他都真切感受過。青少年時期的路遙向往知識與藝術,同時也感知到,城鄉之間,人們接近知識與藝術時有著難易的差別:農村能上高小的孩子很少,農村孩子由于貧窮交不上糧,伙食也比城里孩子差;大部分農村孩子都因交不起一毛錢,而放棄去放映站看電影的機會。

路遙(右)在陜北農村走訪(姚宗儀/ 攝)
路遙只能在閱覽室和新華書店里拼命讀書看報,如饑似渴地了解陜北之外的世界。他在畫報上看到大城市、火車、輪船的模樣,在報紙上看到其他國家的名字,也知道了胡志明、卡斯特羅和航天英雄加加林。
1963年,路遙考上延川中學,但家人不同意他繼續求學,希望他回家,早日訂婚——這是當時陜北農村的普遍現象。在路遙的養父看來,修一孔窯洞、娶個婆姨,比繼續讀書更重要。開學那天,養父遞給路遙一把小镢頭和一條羊毛繩,要他上山去砍柴。
路遙接過小镢頭和羊毛繩,一走到山里就把它們扔進了溝里,獨自進了城。路遙后來回憶那次進城的心情:“感覺特別孤獨,就像一只小羊羔獨自處在茫茫雪原上那樣孤獨。”最后,是村干部借給他二斗黑豆換來了入學所需的報名費。
實際上,路遙有關貧窮、城鄉差別以及通過奮斗走出山村的記憶,也是很多中國人的共同回憶。
1982年路遙的《人生》發表后,引起了巨大轟動。小說主人公高加林在城鄉的夾縫之中,經歷了失戀與前途迷茫的痛苦,但始終保持著堅韌的奮斗精神。無論對當時返城的下鄉知青還是想要進城的農村青年來說,高加林的故事都能引起他們的情感共振。
在“城鄉交叉地帶”深耕
在創作代表作《平凡的世界》時,路遙計劃它的內容“將涉及一九七五年到一九八五年十年間中國城鄉廣泛的社會生活”。
路遙敏銳地捕捉到了這十年的特殊性。“這十年是中國社會的大轉型期,其間充滿了密集的重大歷史性事件;而這些事件又環環相扣,互為因果……”“我的基本想法是,要用歷史和藝術的眼光觀察在這種社會大背景(或者說條件)下人們的生存與生活狀態。”
和早期的創作相比,路遙已有意識地、理性地圈定了自己作品的題材范圍,那就是他所說的“城鄉交叉地帶”的生活,他發現了這片地帶“在我們整個社會生活中所具有的深刻而巨大的意義”。
即使熟悉這片土地,也經歷過故事發生的時間,路遙仍為全方位了解歷史發展的脈絡下了很大“笨功夫”。他曾將1975年到1985年的報刊翻遍,心中形成了十年間大到全世界、小到延安地區的事件年表;同時進行了大量“田野調查”或“體驗生活”的工作,尋找人物原型。
可以說,《平凡的世界》是將虛構的人物放在了非虛構的歷史之中,其扎實的現實主義手法在當時求新求異的文壇是一種“逆流”。1986年,《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完成后,大部分一流雜志和出版社婉拒了書稿。
然而,《平凡的世界》契合了社會轉折期一種新的趨向,即在個人意識覺醒的情況下,人們正重新考量城鄉二元結構之下的命運與前途。這在《人生》中已經初見端倪,而《平凡的世界》則是集大成的作品。
城鄉中國的奮斗手冊
和同時代很多農村出身的作家不同,路遙并沒有以“魔幻現實主義”或其他流行手法描述農村,在他的筆下,城鄉交叉地帶不是異化的、神秘的“他者”,人在這片土地上苦難的奮斗歷程也就格外真實。
因此,與在文學精英中遭受冷遇相映成趣的,是《平凡的世界》在讀者中的熱銷。這部小說再版數十次、銷售幾百萬冊,1991年獲得第三屆茅盾文學獎。直到現在,各類國內的閱讀調查之中,《平凡的世界》總是被讀者歸在“必讀經典”之列。
對于很多城市年輕人來說,幾十年前,他們的父輩很有可能是在《平凡的世界》的鼓舞下從農村走到城市扎根的。這些年輕人閱讀《平凡的世界》,也是閱讀父輩的奮斗史和心靈史。
很多評論家都認為,只要城鄉二元結構還存在,只要農村青年和小城青年跨越鴻溝的夢想還在,《平凡的世界》就不會過時。
《平凡的世界》最大的價值之一,是它有著一種強有力的勵志精神。
在這部小說中,主人公活得有尊嚴也有希望,在每一次重大打擊中都能獲得精神洗禮。基層青年需要尋找精神上的出路,路遙的作品起到了這個作用,為他們提供了激勵和慰藉。路遙作品的勵志性和時下的“雞湯文學”絕不相同,因為它應對的并非浮在表面的焦慮,而是深層次的痛苦。路遙一直思考如何面對現代與傳統的劇烈沖突,他筆下的人物也充滿了由此引發的心靈矛盾和痛苦。這是現代化進程里中國人的普遍感受,無論是生活在城鎮還是鄉村。
路遙的作品能在時代變化中保持活力,歸根結底還是真正關切了平凡人的命運和痛苦,并提供了一種超越苦難的精神力量。放在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背景下,他的作品可謂是城鄉中國的個體奮斗手冊。從這個角度去理解《平凡的世界》,也許更能懂得它問世三十余年仍在各大榜單“霸榜”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