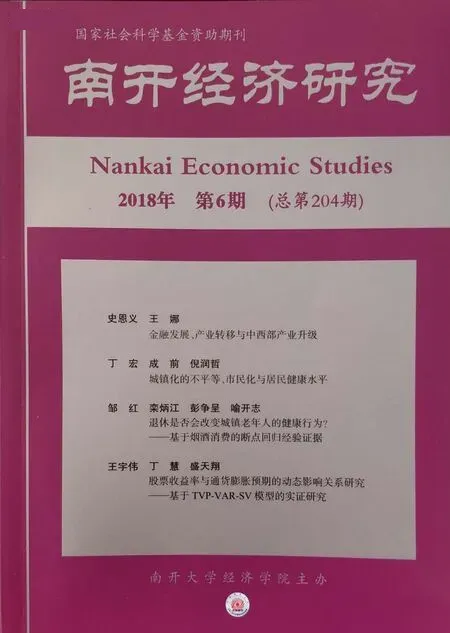為什么我們會虛偽?網絡時代的誘惑與自我控制
蔣軍鋒 崔露露 李孝兵
一、問題與意義
個體虛偽對應的行動(言行)動態不一致現象在網絡時代愈發讓人印象深刻。2011年轟動一時的廣東佛山“小悅悅事件”①http://baike.baidu.com/link?url=gxh0tOot9OX1tbEfTIQOB36hMjtwS-OGk5rojbxYAFpHfd9HldQgmzSxjmdDph Zaa7XLMHzwErgPPa-OF1xGkK。,最后被總結為“上網的人不上街,上街的人不上網”。顯然,上網的人不可能不上街,上街的人也不可能不上網,如此總結不過是以極度夸張的語言凸顯了我們言行的兩極:異口同聲譴責路人并且道德冷漠的上網者話語總是義正詞嚴,序貫而過漠然視之還無動于衷的路過者行為總是令人心寒。與之類似,當下我國的很多“(準)公共知識分子”,一方面在網絡公共平臺上慷慨激昂地抨擊既有體制(潛規則,文化),搶占道德制高點,另一方面卻利用既有體制(潛規則,文化)將從網絡平臺得到的聲名進行利益勾兌。這些“潔言污行,雞謙狼吞”的現代翻版,其公開宣稱的價值取向與現實行動之間發生直接沖突,通常被稱為虛偽。網絡的放大效應使得個體傾向于公開宣稱自身更高的道德準則(無論這種道德準則是用以約束他人還是自身),以搶占話語權和道德制高點;而實際決策過程中的個體往往更受制于其直接承受的現實利益與成本的誘惑,不得不偏離公開宣稱的信仰。社會網絡化下個體的虛偽行為與通常的虛偽存在何種區別?網絡規模的擴大、社會聯系的增多以及個體間利益關聯的增強是否會系統性地影響虛偽行為,這是相關研究面臨的重大挑戰。
不管類型如何劃分(Crisp和 Cowton,1994),虛偽的本質是行動與公開宣稱信仰間的不一致(Zamulinski,2015;Batson 等,1997;Naso,2006;Samuels,2009;Wagner等,2009)。人們之所以虛偽,原因在于其公開宣稱的信仰(或道德準則)可以提高個體的自我形象,具有工具價值(胡永輝、洪修平,2015)。通俗而言,虛偽就是行動不一(Batson 等,1999;Kris,2005):(1)對待自身與別人行動的態度不一致(第一類虛偽);(2)不同時點上自身行動之間的不一致(第二類虛偽)(Valdesolo和 DeSteno,2007;Rai和 Holyoak,2014)。虛偽行為背后有著復雜的道德動機:或許行動者處于一種認知失調狀態,又或許是行動者的一套自我防御機制,由行動者的價值觀所驅動。不管怎么樣,虛偽可以被認為是一種機會主義的適應性策略(吳寶沛和高樹玲,2012)。
與社會心理學不同,本文基于誘惑與自我控制來模型化虛偽行為所蘊含的動態不一致,把行動成本嵌入到決策者的個體直接收益中,形成決策者的誘惑效用(自身誘惑效用),進而扭曲個體直接收益與社會整體收益之間的線性關系,使得誘惑效用與由社會整體收益形成的規范效用之間的沖突成為可能。結合個體對規范效用與誘惑效用的綜合權衡,進而構造出誘惑與自我控制間的沖突來內生行為的動態不一致:當自我控制所帶來的規范效用的增加無法彌補自我控制所帶來的誘惑效用的損失時,決策者會選擇通常被認為是“不道德”的行動;相反地,如果自我控制所帶來的規范效用的增加足以超過與之相伴的誘惑效用的損失時,行動就會呈現出“道德”的特征。決策者所需付出的自我控制成本是決定虛偽是否發生的唯一因素,是否執行自我控制僅依賴于決策者所面對的誘惑與自我控制成本之間的比較,而無須借助于自我欺騙、不誠實或者道德弱點等概念。
誘惑與自我控制的理論框架凸顯了虛偽行為的社會屬性,行動集與行動的雙重選擇體現了虛偽行為的相機決策特征。決策情境界定了可行的備選行動集合,并且可以模型化為菜單A(Kreps,1979、1992)。本文引入兩種不同的排序準則對隸屬于菜單A中的行動進行排序(Gul和 Pesendorfer,2001;Noor,2011):基于社會整體收益的規范排序,代表社會規范或道德)和基于個體誘惑效用的誘惑排序。與Maccheroni、Marinacci和 Rustichini(2012)中個體決策僅依賴社會選擇函數或者個體選擇函數兩者之一所不同的是,自我控制模型中的個體試圖最大化由兩類效用函數構成的綜合效用。菜單A中最大誘惑元素的效用被構造為決策者所面臨誘惑的基準),刻畫了決策情境的特征,被定義為選擇x∈A時所面對的誘惑,被定義為不同行動之間的誘惑,則被定義為自我控制成本。行動之間的規范效用差異 P則給出了決策者實施自我控制之后帶來的規范效用的變化,不同情形下決策者行動的動態不一致(虛偽)就由自我控制行動帶來的誘惑效用損失與規范效用的變化之間的權衡完全控制。
與既有研究相比,基于誘惑與自我控制來解釋虛偽行為具有如下特點。首先,模型僅僅假設行動者是理性個體,將道德現象歸結為決策者的理性選擇,不僅假設簡單,結論穩健,更重要的是堅持了道德的理性基礎;其次,誘惑效用與規范效用形成的綜合效用體現了決策者社會屬性與個體屬性的復合,個體直接收益與社會整體收益間的線性關系表明了兩者的一致性,并使得社會整體收益變得可以操縱,誘惑效用中的直接成本則引入了兩者的異質性,突出了虛偽行為的社會屬性;最后,決策提前期與行動選擇的動態關系統一了決策情境與虛偽行為之間的關系,任何個體的虛偽總是可以在特定的決策提前期下被觀察到,自我控制模型可以預測個體虛偽行為的出現時點,因而也給出了模型有效性的檢驗途徑,從而使得“虛偽”變得可以操縱。
二、理論回顧
虛偽是社會行動與個體行動交互作用的演化結果,必然能夠為個體和社會帶來一定好處。如果完全消除虛偽,則個體之間的心理距離近乎為零,極易發生沖突,社會維持的成本會極其昂貴;如果完全虛偽,則人與人之間的信任為零,社會也將無以為繼(汪丁丁,2007)。在行動者“所說的”和“所做的”相互替代的框架中,個體公開“所說的”往往對應著較高的道德準則,在某些條件下,甚至只要做出某種道德姿態,行動者就可以避免潛在的懲罰(L?nnqvist、Michael和 Walkowitz,2015)。個體私下“所做的”一般來說都充分體現了行動者的自我需求。在社會心理學的旁觀者-演員分析框架中,行動的道德價值與自我效用兩者之間是高度沖突的:作為旁觀者的個體往往是高水平道德規范的堅持者,而作為參與者的個體往往體現出更多的自利特征,罔顧道德規范的要求。與此不同,也有研究指出虛偽之所以存在,是因為無論是行動者的“所說”還是行動者的“所做”,都是互補的。換而言之,言語是用來補償行動的(Brunsson,2002),公開宣稱某種道德規則,不過是行動者對自我形象的管理(Rustichini和 Villeval,2014;L?nnqvist、Irlenbusch 和 Walkowitz,2014),可以帶來潛在需求的滿足,行動者在行動后的有關言語選擇更能充分體現這一點。在某些情形下,僅僅是改變言語與行動的次序,都可以引起虛偽程度的變化(Barden、Rucker和 Petty,2005;Barden等,2014)。總而言之,虛偽行為中個體“所說的”與“所做的”都能為個體或者社會帶來一定收益,但這種收益會隨著時間或決策者所在具體環境而變化,個體行動是否虛偽,決策環境有著重大影響。
行動是否虛偽,首先取決于行動者看待問題的視角與道德標準。道德動機理論將個體行動分為道德正直與道德虛偽兩種截然不同的狀態,在道德意識缺乏或者情境壓力過大的時候,道德正直的行動選擇與出自于自利需求的道德虛偽所引發的道德失效是相同的,個體虛偽與否需要通過其它信息來加以判斷(Fellner和Lünser,2014),個體的自利特征也影響著虛偽行為是否發生(Rai和 Holyoak,2014)。行動者對道德采取視角的抽象程度(Lammers,2012)和道德標準的具體程度(K?rner和 Volk,2014)都影響虛偽行為發生的可能性:一旦個體采取比較抽象而無視行動具體細節的視角時,社會需求或者道德規范就是行動排序的主要標準,而當個體采取比較具體并更關注細節的視角時,個體付出的代價與收益的比較對行動的影響就會迅速變大,個體對社會或者道德標準的態度總是足夠明確(Kaiser和 Byrka,2015)。與之類似,具有某一組織成員席位的個體則更容易被組織的道德標準判斷為虛偽(Effron、Lucas和 O′ Connor,2015),是否具有組織的成員席位,帶來的是判斷者與行動的距離差異,這是虛偽與否的重要影響因素(Focella等,2016)。簡而言之,判斷者與行動收益間的聯系是否緊密,直接影響到判斷行動是否虛偽時所采取的道德標準。
廣為人知的解釋水平理論(Construal Level Theory,CLT)更清楚地體現了行動后果與決策關系遠近對行動選擇的影響。Xiao 等(2015)利用我國3所大學的768個樣本,證實了在低解釋水平上個體行動的選擇更多是基于功利考慮,自己決策與為他人提供建議兩者之間的區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釋為個體是否承擔行動的后果,兩種情形下呈現出效用推理的特征(或者說是效用最大化的特征)。作為解釋水平理論的具體運用,演員-旁觀者框架采用了作為演員與作為旁觀者的個體對同樣行動的不同判斷來解釋虛偽產生的原因。Hale和 Pillow(2015)分析了個體判斷他人與自身虛偽標準的不對稱性,個體對同樣行動是否虛偽的判斷高度依賴于這兩種角色在具體情境下差異化的解釋。顯然,這帶來了自我與他人在理論體系中地位的不對稱問題:凡是涉及決策者自身,決策者總會采取特定標準,這實質性地違背了社會中個體之間的平等原則(Fritz和Miller,2018),使得理論失去了一致性與嚴謹性。
為什么個體會選擇虛偽,并且行為會表現出動態不一致的特征?虛偽行為的不一致性如此明顯,有人認為其原因必然是個體的不誠實,或是自我欺騙,虛偽也總是個體的錯誤選擇(Rai 和 Fiske,2011)。虛偽究竟是個體的錯誤選擇還是個體的自利選擇,L?nnqvist、Irlenbusch和 Walkowitz(2014)指出虛偽的出現并不必然存在自我欺騙;基于貝葉斯分析框架與邏輯相似的滑坡理論,Rai和Holyoak(2014)認為自利才是虛偽出現的根本動因。最近研究表明,至少在某些情況下,個體公然的道德姿態就足以阻止社會或他人對其罪責的合理懷疑,進而免于對其先前行動的懲罰(L?nnqvist、Michael和Walkowitz,2015)。道德多元化工具的分析則認為個體內部不同的道德觀念可能造成了個體決策時的內心沖突,一旦引入在不同情形下所適用的道德價值觀,則可以顯著降低個體行動遭受到的虛偽指控(Graham 等,2015)。顯然,籠罩在虛偽上面的不誠實與自我欺騙的色彩慢慢被行動者的自利所代替,基于更多價值觀沖突的自利則可進一步增強虛偽行為背后決策者的理性,提高行動解釋框架的一致性。
三、基本模型
(一)社會網絡結構與均衡收益關系
利益相互影響的個體組成具有一定關系結構的社會網絡,總可以模型化為連通圖,由此定義了社會網絡N。所有個體組成網絡的頂點集合,元素數目n稱為社會網絡的階,表示社會規模;個體兩兩之間的聯系eij構成關系集合E( N),聯系數目表示對應社會的豐富或者緊密程度。可以將社會網絡N拓撲成以鄰接矩陣表示的圖(后文簡記為G):

社會網絡中任意個體i選擇行動xi都會產生兩個后果:(1)對自身收益產生影響;(2)對與其有直接聯系的其他個體j∈N的利益產生影響。不失一般性地,假設行動A引發個體i的直接收益發生單位變化,同時導致與自身有直接聯系的其他個體j的收益發生rij單位變化。假設社會網絡中利益影響是對稱的,則G中個體收益互動關系可以表達為如下的利益關聯矩陣R:

在社會對應的連通圖中,相互聯系的個體之間的影響總是可以持續進行,并且一直達到收益均衡。因此,個體行動引發的收益變化需要通過無窮步長的作用鏈才能充分顯示,個體行動對社會網絡收益的影響也總是表現為所有個體的收益改變。引入所有個體行動向量①盡管時間偏好與風險偏好兩者并不嚴格相等,但是在很多情況下不作區分也是可以接受的。有關時間偏好與風險偏好之間的關系以及兩者的分離參見系列文章:Andreoni J.,Sprenger C. Risk Preferences Are Not Time Preference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2,102(7):3357—76;Epper T.,Fehr-Duda H. Comment on"Risk Preferences Are Not Time Preferences":Balancing on a Budget Line[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5,105(7):2261-71;Miao B.,Zhong S. Comment on "Risk Preferences Are Not Time Preferences":Separating Risk and Time Preference[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5,105(7):2272-86。則社會網絡收益的改變可以刻畫為:

在個體行動選擇xe的作用下,所有個體行動所引發社會網絡的整體變化就是上述網絡乘數各分量的加總,即社會收益可以表示為社會網絡標量乘數:

如果乘數涉及到的矩陣滿足相應收斂條件,則兩種乘數可以分別表達為:


此時,社會網絡中任意個體之間的行為收益關系保持不變,任意個體收益與社會網絡收益之間的關系也保持不變,由此決定的個體收益和社會網絡收益都實現了均衡,定義均衡時的社會網絡收益為社會(網絡)整體收益,根據式(6)得:

由此,社會網絡中任何個體的直接收益與社會整體收益之間的均衡關系總可以刻畫如下:

由于需要討論的是個體行為的道德特征,一個損害社會收益的個體行為不會被納入到分析范圍中,因而總是假定個體行為收益與社會網絡收益之間的參數α大于 0,隨著決策者變化而變化,但不受決策者的行為選擇影響。參數λ為矩陣特征值,由社會網絡決定,矩陣特征值特征值按照升序排列,最小與最大特征值分別記為和特征向量記為,后文特征值與特征向量分別簡記為λi和。
(二)規范效用與誘惑效用
嵌入到社會網絡中的個體總是社會屬性與個體屬性兩者的混合體。通過個體直接收益線性變換所形成的社會整體收益保證了社會屬性與個體屬性的一致性,而嵌入個體直接成本形成的誘惑效用與社會整體收益形成的規范效用兩者之間存在著異質性,這使得虛偽行為對應的動態不一致性成為可能。
1. 規范效用與誘惑效用的分離
依據解釋水平理論,行動背景具體與否決定了行動選擇的解釋水平高低。如果行動背景不復存在,即將遇到的細節困難得不到決策者的足夠重視,個人即將付出的成本也將完全被忽視(K?rner和 Volk,2014)。將抽象視角或者解釋高水平推到極致,則行動選擇對個體帶來的具體影響完全不在決策者的考慮范圍之中,決策者將完全采用社會規范來看待行動之間的比較排序。簡而言之,隨著抽象程度越來越高,該行動需要個體付出的成本將會逐漸被完全忽略。按照 Noor(2011)的遠離(distancing)技術,當決策行動的后果與自身無關的時候,行動選擇體現了決策者的規范偏好。結合社會規范的無差異性,由于誘惑與自我控制理論中規范偏好的不變性,則由社會整體收益所決定的行動之間的相互偏好關系就滿足了誘惑與自我控制理論中規范偏好的不變性特征,因而我們把由社會整體收益所決定的行動排序稱之為規范排序(normative ranking),規范排序下各行動帶給決策者的效用稱為規范效用,特別地,由于社會規范與社會的一一對應關系,同一社會中所有不同個體從不同行動決策中獲取的規范效用是可以進行人際比較的。
與之相反,當具體背景凸顯時,個體行動選擇由低水平來予以解釋(Xiao 等,2015)。當具體背景更加清晰時,行動者會越來越重視行動選擇背后對個體收益與成本的影響。隨著個體對行動背后的成本與收益的考察越來越具體,成本與收益的考慮就會在決策者的行動框架中占據越來越多的分量。假設個體完全不考慮行動帶來的社會成本,而只考慮行動選擇帶來的個人收益與成本,將邏輯推到極致,則個體對行動的排序完全由行動選擇對自身直接收益與成本的影響來決定,此種情形下備選行動集合中行動之間的排序體現了個體的直接收益與成本的特征,我們稱之為誘惑排序(temptation ranking)。誘惑排序下各行動帶給決策者的效用稱為誘惑效用,可以為決策者提供短期的直接好處,由于誘惑排序與個體特征存在對應關系,即便在同一社會中,不同個體之間也不可加以比較。
2. 作為規范排序的社會整體收益
道德必然根植于社會整體收益,為社會中所有個體提供無差異的共同利益是社會規范出現的推動力與根本目的。社會規范是一個群體共同體的主要標志,社會規范的實施與權威依賴于其對參與其中的個體之間共同利益的維護(李國慶,2005)。社會規范通過影響個體的自我價值判斷來驅動個體的行動選擇,這意味著違背社會通常會給個體帶來自我否定的感覺,感覺到自己是不合法、不一致和不連貫的(Breakwell,1986;Kernis和 Goldman,2006)。作為社會規范的社會整體收益必定會引導個體協調自身收益與他人收益之間的關系,并解決如何看待社會長遠發展的問題。
從個體行動中得到的社會整體收益必然表現為具體個體得到的收益,決策者必須遵循社會規范將其納入到決策框架中。同一社會網絡中,同一社會規范要求個體處理好兩種關系:(1)自身利益和與自身有直接收益關聯的個體利益兩者之間的關系;(2)社會未來收益與當下收益之間的關系。在給定社會中,決策者對與自身有著直接聯系的個體利益的重視程度和對自身利益的重視程度之間的比值可以刻畫為社會折現率,一般而言,決策者對他人利益的重視程度不會高于對自身利益的重視,因而社會折現率不會超過 1,同時由于兩者存在利益關聯,折現率因而也不會小于 0。對于給定社會而言,社會規范是無差異的,因而在同一社會中對與自身有直接關系的個體的利益,個體對其的重視程度與自身利益的重視程度正是社會折現率(0,1 );由于總是可以調整時間跨度,社會未來收益與當下收益之間的關系在決策者看來依然可以表達為社會折現率①盡管時間偏好與風險偏好兩者并不嚴格相等,但是在很多情況下不作區分也是可以接受的。有關時間偏好與風險偏好之間的關系以及兩者的分離參見系列文章:Andreoni J.,Sprenger C. Risk Preferences Are Not Time Preference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2,102(7):3357—76;Epper T.,Fehr-Duda H. Comment on"Risk Preferences Are Not Time Preferences":Balancing on a Budget Line[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5,105(7):2261-71;Miao B.,Zhong S. Comment on "Risk Preferences Are Not Time Preferences":Separating Risk and Time Preference[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5,105(7):2272-86。。
在式(3)所給定的利益交互影響的社會網絡結構下,在決策者視野中,社會折現率q∈作用下的社會整體收益可以簡單表達為行動者收益的線性函數:

社會規范還會對不同時點之間的社會收益關系給出約束,對于無限持續的收益流的折現,總可以類似給出:

其中t表示時點,表示時點t上的社會整體收益。
社會折現率抽取了同為社會網絡參與個體之間的相同特征,用以協調個體與他人關系,以及協調現在與將來收益之間的關系:當社會成員對他人利益更加重視,社會未來利益在所有個體的決策權衡中占有更重要的位置,社會規范就會表現為更高的社會折現率。
3. 作為誘惑排序的個體誘惑效用
參與社會的單獨個體,除了與社會中所有其他個體具有共同特征之外,顯然還具有標志自身存在的獨特性。在效用決策框架中,這表現為個體必須考慮與他人不同而由自身承擔的收益與成本。顯然,只有對行動帶來的直接收益與直接成本進行綜合權衡,才能決定完全(實質)自利個體對備選行動集合中各行動選項的排序,因而可以定義誘惑效用為:

其中,表示引發個體直接收益為x的行動帶給個體的直接成本。
式(12)給出行動帶給個體的直接影響,這是個體完全只考慮自身直接收益而對行動進行排序的效用表示。同社會整體收益一樣,個體對自身效用也存在一個跨時折現的問題。在考察社會規范對應的社會整體收益時,個體通常會采取比較抽象、比較長遠的眼光來看待未來時點上的收益流;與整體社會相比,個體預期壽命要短得多,決策者在考察自身直接收益與成本變化時,通常會采取一個比較具體、比較短期的視角,因而可以在社會折現率的基礎上假定個體會引入一個附加折現率(0, 1),個體對未來時點上的收益流將采取折現率pq來予以處理,即:

居于社會中的個體具有雙重屬性:社會規范抽取了其作為社會成員不變性質的利益所在,個體自利抽取了其作為社會獨特個體的利益所在,只要兩者以恰當方式結合起來,就能全面刻畫社會中個體行動的完整屬性。社會折現率提取了同一社會中所有個體之間的共同性質,構成了不同個體之所以能夠結成社會的同一性;與社會規范所代表社會個體的共通性質與共通利益不同,個體自利則定義了個體在社會中的獨特性,顯示了社會構成的多樣性。相較于社會折現率,決策者審視自身直接收益與成本時,將會選擇一個較小的折現率,個體直接收益與成本對決策者個體的影響更為具體,使得作為個體的決策者采取更加務實的態度來對各種行動選項進行排序。因此,在某種意義上,同一社會條件下采取更高附加折現率的個體,通常意味著其更加看重未來,眼光也就更為長遠,在實際生活中則會表現為度量大,眼界寬闊。
(三)基于誘惑與自我控制的行動決策模型
作為社會網絡中的個體決策者,其行動選擇必須綜合自身的社會屬性與個體屬性,在規范效用與誘惑效用折中的基礎上采取自利框架進行決策。從社會收益的具體內容來看,社會網絡的利益影響鏈也作用于行動者自身,社會收益本質上也包含了決策者的間接收益,這使得決策者通常采取長遠視角來考察社會整體收益的變化。從個人的誘惑效用來看,關系自身的成本與收益要求決策者采取相對具體的視角來考察行動決策,這意味著決策者也需要采取短期視角來考察行動決策的取舍。綜合起來,將代表社會整體收益的規范效用與代表個體收益的誘惑效用同時納入到決策者的權衡中,既可以視為決策者對短期視角與長期視角的調和,也可以看成是其社會屬性與個體屬性兩者的復合。
1. 誘惑
高度依賴于個體特征的誘惑效用可以通過個體收益和與之對應個體成本差值的合適單調函數表達。誘惑排序 V中,稱備選集合A中引發的行動者個體i的最大效用稱為該行動集(菜單)的誘惑效用:

換言之,行動y∈A是行動集合中為決策者提供最大誘惑效用的元素,稱為集合的最大誘惑元素。如果決策者行動的驅動機制只有個體的短期視角,完全不顧及社會整體收益,其決策函數就會只有自身收益與成本的變動。那么,在最大化假設下,行動y就是決策者在情境A下的最優選擇。顯然,菜單的誘惑效用是唯一的,只依賴于備選集合中最大誘惑元素y∈A(Gul和Pesendorfer,2001)(但最大誘惑元素未必唯一)。

直觀地,誘惑就是菜單誘惑效用與決策者實際選擇得到的誘惑效用之間的差值。換言之,如果出于某種原因,決策者選擇了x∈A,則不得不放棄本來可以得到的最大誘惑效用。由于任何個體都遵循最大化機制,可以帶來最大誘惑效用的選項就構成了菜單A的誘惑基準。這樣構造的誘惑具有通常所言的情境依賴特征:同樣的行動選擇,同一決策者面對的誘惑依賴于其所在的菜單A,V ( A)越大,選擇相同行動的決策者所面對的誘惑就越大,這有助于刻畫決策者“從實際出發”的特點。
如果行動x1,x2∈A,類似式(15),我們可以構造同一菜單下兩個不同行動之間的誘惑。定義:

2. 決策機制
作為決策者的個體,會綜合考慮其行動的規范效用與誘惑效用,這體現為兩種效用的加和。考慮到決策的情境依賴性,引入刻畫決策情境特征的決策集合的誘惑效用,所以其決策形式可以變化為 u( x)-( y)。此時,決策函數不僅綜合了規范效用與誘惑效用,還體現了決策者的情境理性。由此,結合社會整體收益與個體誘惑效用,行動者的決策機制可以描述為:

滿足式(17)的決策機制綜合了社會整體收益與個體誘惑效用,不僅體現了決策者的社會屬性與個體屬性的復合,也說明了決策者采取了抽象與具體視角相結合的決策框架,同時還表明決策者總是長期導向與短期導向的混合行動者。決策函數還體現了決策者是情境理性的,不僅受到行動(成本與收益)特征的影響,還受到了行動集合(菜單的誘惑效用)的影響。不會隨最后選擇而變化,行動決策所依賴的效用就是( x)代表的兩類效用的折中取值,體現了決策者對社會整體收益與個體誘惑效用兩者的綜合考慮。
式(17)的形式體現了任意決策都是社會整體收益與個體誘惑效用兩者的復合驅動過程。為了顯示決策者對誘惑的抵制,將上式變形為:

由式(17)定義為選擇行動x∈A時決策者所面對的誘惑。相應地,決策者選擇行動,而沒有選擇能夠帶來最大誘惑效用的行動y∈A,通常認為決策者在這個過程中實施了自我控制,此時決策者付出的成本稱為自我控制成本:

為了更清楚的顯示社會-自我的復合,即決策者綜合考慮規范效用與誘惑效用,進一步凸顯決策過程中所面臨的誘惑以及付出的自我控制成本,引入x∈A與集合中最大誘惑元素y∈A兩者之間的規范效用差異:

上式刻畫了菜單中其他行動與最大誘惑元素之間在規范效用上的差異,決策者執行自我控制抵制誘惑帶來規范效用的變化。結合式(17)和式(18),決策者的決策機制可以描述為:

很明顯,此時的決策者是基于自我控制成本(損失的誘惑效用)與自我控制收益(得到的規范效用)兩者之間的權衡來選擇行動。為了保證決策者選擇之間的可比較性,上式實際將自我控制的收益與成本轉化為了社會規范作用下的比較,此時決策者行動的本質是其對社會整體收益的規范效用變動與代表個體誘惑效用的自我控制成本變動兩者之間的權衡,處于社會網絡中的個體行動選擇總是會考慮社會與個體兩者之間的權衡。
在同一情境中對兩個行動比較,依然可以按照式(21)通過形式變化直接寫出:

實際上,式(22)可以給出同一情境下兩個行動之間的排序準則:

在自我控制理論框架下,決策者通過執行自我控制來獲取社會整體收益,這表明社會整體收益的增加需要行動個體付出代價:自我控制成本。作為行動承擔者的決策者是通過權衡自我控制成本與社會整體收益來優化自身選擇,社會整體收益與決策者的自我控制成本是相互替代的,也是相互沖突的。決策形式(18)充分說明個體決策者的社會屬性與自我屬性兩者之間的沖突,說明了任何社會收益的獲取在本質上是參與社會網絡的個體付出;更進一步,式(18)、式(19)和式(20)使得行動者獨特的誘惑效用轉化為社會效用成為可能,建立了個體的社會屬性與個體屬性兩者之間的聯系。
四、虛偽行為的觸發
(一)不同解釋水平下的決策差異
不同解釋水平下個體決策行動的差異,一般被認為是對自己和他人采取不同道德標準的虛偽行為(第一類虛偽)。解釋水平理論認為處于演員或旁觀者的不同角色下的同一個體的行動選擇存在顯著差異:作為旁觀者的決策者在為他人提供建議時,傾向于選擇那些看起來道德水平更高的行動,而作為演員的決策者則傾向于選擇那些道德水平更低的行動;或者在解釋自身行動選擇時,總是強調行動選擇的困難,而在解釋他人類似行動選擇時,則無視行動選擇的成本。通常而言,高低水平下的行動差異也代表了虛偽行為中“說的”和“做的”不相一致:“說得好聽”通常也就是忽視了行動直接成本,而呈現出較高道德水平的行動選擇;“做得難看”則是因為看重行動的直接成本,而呈現出較低道德水平的行動選擇。
本質上,在不同解釋水平下,決策者從行動決策中得到的直接收益與付出的成本存在顯著不同:作為演員的決策者,必須承擔行動引發的直接收益與成本,相較于旁觀者,作為演員的決策者通常會采取更為具體、更為短期的視角來看待行動之間的權衡。在高水平下,決策者無需承擔決策行動的直接成本與收益,此時其效用完全由社會規范給出,不同行動之間的排序也就完全由規范排序所決定;而在低水平下,決策者必須承擔行動的直接成本與收益,此時效用則由社會規范與誘惑效用的折中給出,決策者必須對其所面臨的誘惑效用與社會規范效用進行權衡,不同備選行動之間的排序也就由自我控制與誘惑兩者共同決定,或者說由規范排序和誘惑排序共同決定。
假設在同一社會網絡下,某決策者的行動集合A中存在備選行動和,兩種行動直接收益與成本分別記為、、c ( x1)和 c( x2),由其所引發的社會整體收益變化則是和,假設在決策者處于高水平情況下,認為優于,這實際上意味著,不考慮行動直接收益與成本,社會規范視角下作為建議者的決策者存在:

作為建議者的決策者沒有面臨任何誘惑,因而也無需執行自我控制。在作為演員的決策者視角下,必須考慮行動選擇的誘惑效用。除了考慮行動的社會規范效用以外,決策者必須考慮行動的直接收益與成本,按照式(22)和式(23),兩種行動的排序則取決于:


(二)決策提前期引發的決策差異
虛偽行為的另一主要類型就是決策者自身行動的前后不一致(第二類虛偽),我們將其模型化為不同時點上行動的反轉。這種虛偽通常發生在如下情形:在對未來某一行動決策時,或者對未來行動進行許諾時,決策者的選擇通常表現出較高的道德水平,其行動更多地遵循社會整體收益對應的規范排序,即所謂的“口惠”;而在對當下某一行動決策時,決策者的選擇通常表現為較低的道德水平,其行動更多地體現了決策者直接損益的變動,表現出所謂的“實不至”。兩種決策的本質差異在于行動后果所發生的時間差異:高談闊論未來某種行動選擇時的決策者面對的是未來收益流與成本流,而實實在在地進行當下行動選擇的決策者卻必須直面立即發生的收益流與成本流。
不失一般性地,假設決策者面對收益流與成本流發生時間點不同的兩種情形:第一種情形是行動對應的收益流與成本會立即發生,我們記此種情形下行動發生的時點T0,此時的行動決策記為D0;第二種情形則是行動對應的收益流與成本在將來某一時點發生,決策與行動之間存在一定的時滯,我們記此種情形下收益流與成本流的發生時點為T=t,此時決策者的行動決策記為D-t;定義決策時點與行動發生時間之間的時滯t-0為決策提前期Tl。
一般而言,個體在面對未來才發生的行動選擇時,其選擇會更多地體現為社會整體收益所決定的社會規范特征,即對于D-t而言,行動排序更多體現了社會整體收益的特征:社會收益之間的比較決定了行動之間的排序。如果此時決策者的行動選擇為,被視為高道德水平的話,則意味著必須滿足假設,但由于此時的行動者還必須承擔行動帶來的直接收益與直接成本,根據個體決策的最大化機制,依據式(22)和式(23),必定存在:


這就意味著:

當決策者面臨著即期收益與成本流時,依據式(22)和式(23),不同行動帶來的綜合效用的比較則是:
只要滿足式(26),則決策者此時的行動選擇D0會轉化為x2。整個過程中,盡管在和D-t下,決策者面臨著完全相同的決策集合,但其最終的選擇剛好反轉,呈現出通常的道德虛偽特征:說得到而做不到。隨著行動(直接收益與直接成本)發生時間的逼近,決策行動越來越明顯地呈現出更加看重個體直接損益的“道德低下”的特征,事到臨頭的決策者也就當了“縮頭烏龜”。
綜合式(26)和式(29),只要決策條件滿足如下特征:

我們可以得到,在完全相同的決策條件下,即保持社會收益關系不變,社會規范效用與個體直接收益和成本不變,規范效用與誘惑效用對應的折現率與附加折現率不變,當決策時點與行動發生時點的時滯只要大于滿足式(30)的t,則決策者的最優行動選擇必然會呈現出動態不一致:最優選擇在某一決策提前期之后會發生反轉。如果加以道德評判,就會呈現出虛偽的特征:當面對著未來發生的行動選擇時,決策者會更加看重社會整體收益,其行動選擇更多體現規范效用的特征,看起來總是更加道德一些;而隨著時間的逼近,決策者面臨著當下行動選擇的時候,自身直接收益與成本的變化變得越發重要,行動選擇也就更多體現誘惑效用的特征,看起來總是顯得道德水平變得更低了,整個過程就會呈現出通常所謂的道德虛偽。
五、社會演變、個體特征和提前期與虛偽行為
基于誘惑與自我控制權衡決策機制,誘導出的虛偽行為本質是決策者因時而化的機會主義策略,也就是一種理性的相機決策。根據式(30),個體行動是否呈現出虛偽特征,主要依賴于刻畫社會特征參數λi、決策者個人特征p以及決策(提前期)特征Tl。
(一)社會網絡演變與虛偽行為
社會網絡演變總是表現為對應連通圖中連接邊E( N)或者頂點E( N)的變化,前者通常是被認為社會規模在增大,而后者則被認為是社會聯系變得更為緊密。在社會網絡G中,參與社會的個體相互間關系eij斷開,則意味著個體i和j的社會關系的減少,根據組合矩陣的相關理論,變化之后的網絡的最大特征值就會降低(Bramoull、Kranton 和 Amours,2014;Gantmacher,1959);而去掉個體vi以及與其聯系的所有合作關系之后,社會網絡的矩陣的特征值滿足關系(Gantmacher,1959)(此時鄰接矩陣的秩降低了)。另一方面,社會網絡的結構演變還可以來自社會中個體之間利益關聯程度的變化,從而引發社會網絡的利益關聯矩陣R的變化。根據矩陣運算,當利益關聯矩陣R的元素增大時,等同于社會折現率q增大,根據 Perron-Frobenius有關矩陣特征值與特征向量的討論,此時社會網絡矩陣的最大特征值λmax也會增大。簡而言之,社會規模的增大,社會聯系更加豐富,參與社會的個體之間的利益關聯更加緊密①社會折現率q的增大意味著可以在全體社會網絡成員中對于社會利益與未來利益取得了更大的共識,個體之間的相同看法增加了,因而可以說社會的同質性程度更高,多樣化程度更低。,意味著社會網絡對應的矩陣最大特征值λmax都會增大。
結合個體決策行動出現虛偽的條件式(30),考慮社會網絡的最大特征值λmax隨著社會規模增大、社會聯系增多和相互利益關聯更強的情形下對虛偽發生的影響,假定各類行動的直接收益與直接成本不發生變化而決策者的附加折現率p也不發生變化,如果社會網絡均衡狀態由其對應的最大特征值所刻畫(我們不考慮均衡狀態在不同特征值之間的變化),因為社會網絡演變而導致的λmax的增大,使得原來滿足式(30)約束的行動中總有一部分不再滿足約束,這意味著社會網絡的演變使得作為演員與參與者不同角色之間的第一類虛偽行為減少,而不是增多,社會整體變得更加重視社會規范,道德水平(定義為個體選擇更加重視社會規范效用)會表現出進步;而另外一個方面,就個體在不同提前期下的決策D0與D-t而引發的虛偽而言,虛偽發生的區間)顯然會隨著λmax的增大而增大,在這個意義上,意味著社會規模增大、社會聯系增多與個體利益關聯增強都會導致第二類虛偽更為頻繁發生。無論虛偽情形的發生是否會隨著社會規模、社會聯系與利益關聯的演變而在社會宏觀層面上發生確定性變化,但在微觀層面上,社會規范效用會隨著社會網絡的上述三種演變過程對個體決策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換而言之,更大的社會規模,更多的社會聯系以及更強的利益關聯,從總體上來看,會強化個體行動對社會整體收益所代表的社會規范效用的重視,規范效用對個體選擇的影響會越來越大,社會成員的選擇會呈現出道德水平越來越高的演變趨勢,而絕不會呈現出我們習慣性指責的“人心不古”或者“世風日下”的特征。
(二)個體特征與虛偽行為
盡管參與社會網絡的個體具有社會屬性與自我屬性的雙重特征,但個體間的差異只會在自我屬性上體現。決策者的社會屬性被社會折現率和規范效用所刻畫,從而形成決策者所使用的長期導向;能體現個體間差異的就是其對直接損益的態度:附加折現率p。現在我們分析隨個體特征變化不同個體虛偽行為發生的特征變化。
利用式(30),對于第一類虛偽行為,即不同解釋水平下的行動不一致,個體之間附加折現率的變化無法影響式(26)的成立與否,因而個體的差異不足以影響第一類虛偽行為的發生。但是,對于第二類虛偽行為,即選擇行動在時間上的不一致,則個體之間的附加折現率p差異就會直接作用于虛偽行為發生的可能:

式(29)說明隨著決策者的附加折現率變小,個體行動更加趨向短期導向時,滿足第二類虛偽行為的參數區間就更大,相同決策情形下發生動態行為不一致的可能性就越大。特別是,隨著社會規模的增大、社會聯系的增多與利益關聯的強化,個體之間行動導向變化(附加折現率的變化)就會導致虛偽行為發生的可能性在人際之間的差異越來越大。簡而言之,更為發達的社會(社會規模的增大、社會聯系的增多與利益關聯的強化),正如前節指出的通常會增大λmax,這會強化不同附加折現率個體之間虛偽行為發生可能性的差異:附加折現率不同(行為導向的長期-短期差異)的個體之間虛偽行為的發生差異會隨著社會網絡的發達而進一步強化。
(三)決策提前期與虛偽行為
對于道德虛偽相關的研究來說,存在著一個難以回答的問題:道德虛偽是否可以先驗識別?由式(30)可以知道,個體附加折現率p的差異會導致在不同社會網絡情形下個體行為動態不一致發生的區間差異。那么,這種差異是否允許一個從不虛偽個體的存在呢?答案是否定的。
只要滿足式(30),決策者就一定會出現虛偽行為。那么,是否存在某個參數無法滿足式(30)呢?這意味式(30)約束對應的區間一定是空集,這等同于要求:


這意味著個體視角會比整體社會更為長遠,更為看重未來收益,誘惑效用隨著時間的流逝比規范效用遞減得更慢:時間更遠的提前期,個體對自身收益與自身成本感受會更強烈。這顯然違背了通常所言的“渡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個人的收益與成本的權重通常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越來越低。因此,只要滿足假設p<1,則任何個體都會在一定條件下出現動態不一致,表現出虛偽的特征。
我們來考慮給定附加折現率p的個體虛偽行為出現的臨界條件:其最小的決策提前期。根據誘惑與自我控制兩者關系的判定式(23),個體對同一決策情境下的兩種行動排序無差異的條件:

可以求出決策者行動呈現出動態不一致的條件為:

由于式(26)成立,可以確定式(35)分子取值為負,又因為附加折現率,所以可以保證對給定附加折現率的個體來說,其行動決策反轉的最小提前期。最小提前期t0兩側的決策對行動和x2的排序剛好反轉:決策提前期小于t0的行動選擇與當下決策是相同的,此時的決策者并不會出現動態不一致,不會顯示出虛偽的特征;而在決策提前期大于t0的情形下,此時決策者的行動選擇與當前決策則是相反的,會表現出動態不一致,呈現出虛偽的特征。
由決策最小提前期t0與個體附加折現率兩者的導數(符號判斷利用了式(35))得:

面對“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恭謙未篡時”,如果堅持“壞人”和“好人”的兩分法,社會心理學必須堅持無限理性,在“流言日”和“未篡時”能夠不依賴決策者的行動來判斷何為“周公”,何為“王莽”,忽略與時間相關的有限理性對虛偽判定的關鍵作用,其對虛偽的解釋也無法檢驗。自我控制模型顯示,無論個體還是群體,被視為虛偽不僅依賴于規范效用與誘惑效用,還依賴于決策時點。在這種意義上,虛偽永遠與決策時點相關,沒有被視為虛偽僅僅是因為行為還沒有來得及反轉而已。
六、結 語
在社會心理學的解釋水平理論與經濟學的自我控制理論基礎上,針對虛偽行為中不同時點決策間的沖突,本文引入個體收益與社會收益兩者的線性關系來刻畫個體與社會間的一致性,同時嵌入行為成本構造誘惑效用與規范效用之間的潛在沖突,植入虛偽行為所蘊含的動態不一致性的根源。在此基礎上,基于誘惑效用與規范效用兩者的沖突,構建綜合效用最大化模型,利用直接收益-成本與決策提前期的演變對誘惑效用與規范效用的不同影響來誘導虛偽的機會主義策略特征,解釋了兩類虛偽行為的觸發,分析了相關變量對虛偽的影響。基于自我控制模型的解釋框架,綜合考慮了社會網絡中決策者的個體與社會屬性,強化了虛偽行為的社會特征,簡化了研究假設,提供了虛偽行為的經驗檢驗途徑,為虛偽行為提供了一個完全基于理性的解釋途徑。
在不同時點或者不同角色下,同一決策者行為選擇的動態不一致,被社會整體收益與個體誘惑效用兩者之間既相互一致又相互扭曲的關系所解釋。利益關聯確保了均衡狀態下個體收益與社會整體收益之間的線性關系,這提供了決策者的社會屬性與關注規范效用的動機;而行動成本的引入則扭曲了個體與社會兩者對行動進行排序的一致性,表達了社會中的個體獨特性,由此構造的誘惑效用因而具有了與規范效用相互沖突的可能。誘惑與自我控制間的權衡觸發了第一類虛偽行為,而誘惑效用與規范效用隨著決策提前期的變化而引發誘惑與自我控制之間的權衡則觸發了第二類虛偽行為。這為虛偽行為提供了一個基于多元(社會-個體)價值觀沖突的理性解釋框架,強化了虛偽行為的社會屬性。
社會網絡的演變通過改變社會整體收益與個體直接收益之間的線性比例來引發虛偽行為的改變。社會規模的增大,社會聯系的增多,以及參與社會個體之間的利益關聯增強,都會增大個體收益與社會整體收益之間的比例關系,從而引發宏觀層面上兩類虛偽行為出現概率的變化,但在微觀層面上,社會網絡的演變都會增大社會規范效用在任何類型行為決策中的權重。社會演變對虛偽行為的宏觀特征與微觀表現的影響再一次強化了虛偽行為的社會屬性,也體現了決策者的社會-個體復合屬性以及其間的沖突,并且表明傳統所謂的“世風日下”或者“人心不古”的道德判斷并沒有足夠的邏輯基礎。
個體行為導向的差異引發虛偽行為發生最小提前期的變化,任何比最小提前期更大的決策提前期都會引發決策的動態不一致,從而引發虛偽現象。最小提前期的存在使得個體決策的動態不一致成為可能,可以揭示主流社會心理學無法解釋的“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恭謙未篡時”現象背后的發生機制,為虛偽的自我控制解釋框架提供有效的檢驗方案。
進一步的研究應該關注以下三個方面。首先,社會網絡化過程中個體間收益的競爭和合作(或者是替代與互補)關系的變化特點。顯然,不同的利益關聯模式下,個體之間,個體與社會之間的利益分歧程度也不相一致,這會影響到行為選擇所對應的誘惑與自我控制成本;其次,在給定社會收益關聯的情形下,矩陣的不同特征值所對應社會狀態實現與否的決定因素。不同的特征值下虛偽出現的條件顯然不同,本文盡管給出了同一利益關聯矩陣對應的不同特征值的可能,但現實社會中的個體與社會整體收益之間的均衡關系究竟為哪一特征值所決定,這些因素因而也就決定了社會狀態下虛偽行為發生的概率;最后,個體行為選擇集合中不同行為的分布特征,換而言之,個體行動空間的構成。我們給出了虛偽行為隨著社會發展的相應變化,但這些推斷并沒有考慮到參與社會網絡個體行動集合中的行動分布特征,而行動在集合A的分布顯然也會影響虛偽在社會網絡演變前后是否會變得更多。總而言之,網絡關系復雜化引來了個體與社會關系的變動,使得網絡社會中虛偽發生的宏觀特征與微觀特征兩者的經驗基礎應該得到未來研究的更多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