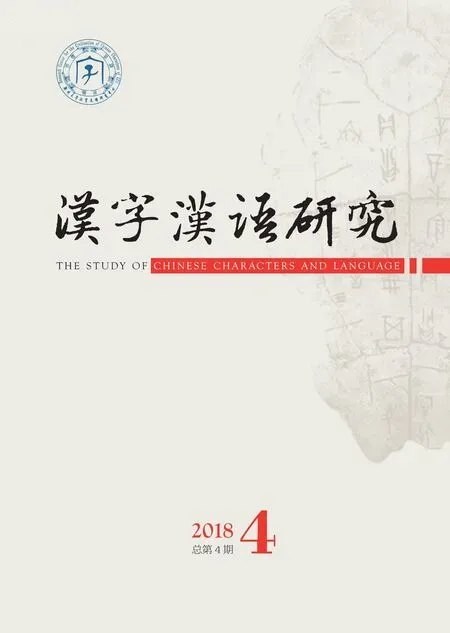“坐甲”新釋
李 輝
提 要 《左傳·文公十二年》“坐甲”一詞歷來訓釋有疑。本文通過對“坐”字在傳世、出土文獻中用法的梳理,排除其訓釋為“持、披”義的可能性;并結合出土實物和兵書文獻,將“坐甲”釋為 “著甲跪坐于地”的“坐陣”之法,乃古代一種臨敵備戰的隊列陣型;同時梳理“坐甲”在后世文獻中的用法。
1.“坐甲”訓釋梳理
《左傳·文公十二年》:“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關于“坐甲”一詞,歷來的訓釋似難以令人信服,目前的觀點主要有四種:
第一,“坐甲”為“未穿鎧甲而坐于地”。孔穎達疏:“甲者,所以制御非常,臨敵則被之于身;未戰且坐之于地。”竹添光鴻(2008:756)會箋訓釋大抵相同。第二,訓為“披甲坐于地”。惠棟(1991:37)補注: “昭廿七年《傳》云:‘吳王使甲坐于道。’《荀卿子》云: ‘庶士介而坐道。’故云坐甲。”沈欽韓(2016:183)、楊伯峻(2009:591)訓釋同。趙生群(2013:135)也認為“坐臥皆不離于甲”。第三,將“坐”訓釋為“手持、穿上”之義,通過“坐”與“挫”古相通用加以證明。“坐甲”則為“持甲”,指戰士準備戰斗。此觀點見于錢慧真(2011)。或直接將“坐”訓釋為“披”,“坐甲”即“披甲”。此觀點見于陳淑梅(1989)。第四,將“坐”訓釋為“積聚”,“坐甲”即“積聚鎧甲”,指發動戰爭之前的準備。此觀點見于吳柱(2016),主要根據《文選·左思〈吳都賦〉》中“坐組甲,建祀姑”李周翰注文“坐,猶積也”。
由上可見,前兩種觀點均將“坐”釋為“坐地”,矛盾點在于穿不穿鎧甲。而后兩種觀點都將“坐”訓釋為其他動作,因以后世之眼觀之,臨近戰斗坐于地上,實在是不合情理的,于是提出了種種反駁。乃至于將“坐”訓釋為“積聚”,把戰爭情勢的描寫都已經提前到戰爭動員準備階段了。
在討論之前,首先需要厘清的是“坐”的詞義及其主要用法。
由止息行為的動詞“跪坐”之義,自然可以轉為名詞性的“座位、席位”之義。止息行為又可以引申訓釋為“留守”之義。《左傳·桓公十二年》:“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杜預注:“坐,猶守也。”后世有“坐守”一詞。又或因《說文》古文字形像兩人對坐訴訟,“坐”又有“辨訟曲直”義,可引申為“因……獲罪”之義,凡此不贅述。“坐”之連詞、副詞義等,此處亦不需詳說。
先秦時期“坐”①“坐”這個詞乃斯瓦迪士100核心詞中的一個,表示人類的一種基本行為。“坐”表示“止息”行為的具體動作會因時代而產生變化,但在先秦時期,其核心的“止息”動作義是難以被沖擊的。仍較多使用其本義“跪坐”,如依其本義訓釋“裹糧坐甲”,則為“攜帶干糧,跪坐于鎧甲”。依照當時秦晉交戰,而晉軍準備以逸待勞的情況,斷然不可能讓士眾解甲而坐,此乃“待斃”而非“待勞”,顯然不符情境,故第一種觀點(即孔穎達與竹添光鴻)不可取。后人又因不了解先秦時期士兵鎧甲的性質,斷然否定士兵不可著甲跪坐于地,故只得從“坐”的訓釋上尋求突破。又因與《左傳·成公二年》“擐甲執兵,固即死也”形式上極為近似,“擐甲執兵”即“身披鎧甲、手握武器”,所以關于“坐”的訓釋形成了如下意見(即上文所言第三、四兩種觀點):①訓為“披”;②訓為“積聚”;③訓為“持”,引申為“穿、披”。
第一種意見,乃根據“坐”的本義為“坐靠于地”,引申為“憑靠”,再引申為“披、穿”,并列舉“因”之本義為席子而引申為“憑借”做例證。此種訓釋是錯誤的,一則“坐”引申為“憑靠”而訓釋為“披”,并沒有直接的文獻例證;二則用“因”的詞義引申為例證是
現試圖根據古代軍戎服飾的研究成果,結合出土實物及古代兵書文獻,重新考察“坐甲”一詞。本文將“坐甲”訓釋為“著甲跪坐于地”,特指出此乃“坐陣”之法,為古代一種臨敵備戰的隊列陣型。該陣型可攻可守,最常出現在固險據守的戰爭情勢下,以防守為主,可即刻轉為進攻。后世文獻中對于“坐甲”一詞的具體使用有差異,可引申為“披甲待敵”“武裝備戰”“全副武裝的士兵或軍隊”等含義。
2.“坐”訓釋為“持、披”或者“積聚”不妥
不恰當的,該例子中的“憑借”“趁著”詞義是逐漸虛化的,是詞匯化的過程。
第二種意見訓為“積聚”義,主要根據《文選·左思〈吳都賦〉》中“坐組甲,建祀姑”李周翰的注文“坐,猶積也”。其認為“蹲、坐”互訓,而“蹲”有積聚義,是故“坐”也有積聚義。此亦不可靠。一則“坐”訓“積聚”,只李周翰注文一見,或隨文訓釋。二則“蹲、坐”互訓是動詞義的止息行為。《廣韻·魂韻》:“蹲,坐也。”《玄應音義》卷六引《字林》:“蹲,猶虛坐也。”而“蹲”的“積聚”義來源則是“?”。《廣雅·釋詁三》:“?,聚也。”王念孫疏證:“蹲與?聲近義同。”因為不在一個詞義層面,所以“坐”訓“積聚”只一見,不足以為證。三則如果訓釋為“積聚鎧甲”,則和上下文語境相差較遠,已經將時間推到戰爭的動員準備階段,不符合當時情境。
第三種意見,訓“坐”為“持”,最后仍舊歸到“披”的含義上。錢慧真(2011)依據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挫,又為坐。《春秋考異郵》:‘清明者,精芒挫收也。’”認為“坐”與“挫”古相通,“坐”可假借為“挫”,“挫”有“持”義,故“坐”有“持”義。其主要依據以下三條例證:
(1)挫糟凍飲,酎清凉些。(《楚辭·招魂》)
(2)挫針治繲,足以餬口。(《莊子·人間世》)
(3)或行或隨,或歔或吹,或強或羸,或挫或隳。(《老子》第二十九章)
第一條例證,王逸注:“挫,捉也。……提去其糟,但取清醇。”此處的“挫”訓為“提取去除”義,和手中所“持有”某物,意義有別。第二條例證亦是如此,“挫針”乃是“捏針”,從“持拿”到“披、穿”仍有一定距離。第三條例證為今本《老子》第二十九章,“挫”可訓“搦”,而“搦”訓“持”,但是帛書《老子》甲、乙本該句均作“或培或墮”,高明《帛書老子校注》:“王本則誤‘培’字為‘挫’,……甲、乙本末句作‘或培或墮’,與傅、范本同,老子原本當如是。”檢閱簡帛:
(4)□□□□,或壞(培)或撱(墮)。(帛甲《老子·道經》)
(5)物或行或隋(隨),或熱【或吹,或強】或?,或陪(培)或墮。(帛乙《老子·道經》)
(6)物或行或隨,或熱(噓)或炊(吹),或強或?(挫),或伓(培)或隋(墮)。(北大漢簡《老子》)
由上面三則出土文獻材料可知,今本之“挫”或從上句誤抄而下,因為破壞了每句中相反對舉的情況,所以今本上句改為“或強或羸”。而上句之“挫”當用其本義“摧折”,正與“強”相對。是故此處引用今本老子之“挫”無法與“搦”通。而《通訓定聲》所謂的“坐”“挫”通,所舉例均不是嚴格的“持拿”義上的通用。并且目前簡帛材料中,“坐”與“挫”通假只如下一例(白于藍,2017:458),乃是與“挫敗”義相通,而非“持拿”義:
由此看來,將“坐”訓釋為“持、披”或者“積聚”,從訓詁的角度看都會存在一定的問題,并不妥當,因此我們仍要回到“坐甲”一詞的舊注上,考察其是否存在合理性。
3.著甲士兵可以跪坐
歷來對于“著甲坐地”這一行為的疑惑在于,鎧甲笨重堅硬,怎么可能讓戰士穿著鎧甲“坐”在地上呢?所以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先秦時期著甲士兵可不可以完成“坐”姿。
首先,先秦時期的鎧甲并不都是重裝甲。我國古代鎧甲所使用的材質,歷經了藤木甲、皮甲、青銅甲、鐵甲、紙甲,以及儀式性質的綿甲等材料。就材質密度而言,顯然青銅甲、鐵甲當較其他材質的鎧甲質量更重,但是如果戰爭時期軍隊全部裝備青銅甲、鐵甲,一是質量過重,對于士兵身體素質要求高,并且這樣的部隊機動性能很差,難以靈活作戰或者長途奔襲;二是如果全部裝備重裝甲,需要成熟的冶煉和鍛造技術,需要相當的國力支持。總而言之,春秋時期大量使用重裝甲是不現實的。皮甲比藤甲靈活,也比金屬甲輕便,亦有相當的防護性。最早皮甲實物是河南安陽侯家莊1004號墓出土的,湖北隨縣曾侯乙墓則出土了較為完整的皮甲。《周禮·考工記·函人》:“函人為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也就是說,在文公十二年,秦晉交戰之中,大量使用的或是皮甲,甚至戰士并不著鎧甲,那么也就不存在“笨重”而不可“跪坐”的問題了。
其次,是否因鎧甲的制式而不可“坐”?《周禮·考工記·函人》:“權其上旅與其下旅,而重若一。”鎧甲是分上下兩個部分的,以腰為界線。鎧甲具體的防護部位,又可以分為身甲、披膊、護臂、垂緣、膝裙、吊腿等,但是先秦時期,士兵的防護往往在腰以上的軀干部分(見圖1、圖2)。也就是說,當時士兵所穿鎧甲的制式也不會影響其做“跪坐”這一動作。其實,如果鎧甲過分限制了下肢的運動,那么士兵就很難進行戰斗動作以及行軍奔襲。

圖1①參看張衛星(2005:33)。

圖2①參看陜西省考古研究所漢陵考古隊(1994)。
東周時期出土的鎧甲標本,復原后有完整結構的為湖北曾侯乙墓(見圖1)、湖北荊門包山楚墓、湖北江陵天星觀楚墓等,其中身著鎧甲的戰士,完全可以“跪坐”于地。出土實物亦可證實這一點,山東臨淄山王村漢代兵馬俑坑就出土有跪坐姿勢的武士俑(見圖3)。

圖3②參看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2016)。圖中左右都是跪坐武士俑,身上著甲,前立盾牌。
4.著甲跪坐乃是“坐陣”戰法
既然春秋時期鎧甲所使用的材質和鎧甲自身的制式,均不會影響到戰士完成“跪坐”這樣的動作,那么討論“坐甲”一詞時,就不應當從這一角度去否定“坐”為實際“跪坐”動作的可能性。因此對于前兩種觀點“未著甲坐于地”和“著甲坐于地”,仍需要重新考慮,不應當直接否定。
孔穎達正義和竹添光鴻會箋均將“坐甲”解釋為“未著甲而坐于地”,是不恰當的。從秦晉兩國對峙狀況來看,既然晉國準備實行對峙消耗的戰術,雖然是以逸待勞,但沒有不做防備的道理;而且“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秦軍既然是偷襲晉軍,如若晉軍是“解甲而備戰”,秦軍肯定會一舉殲滅晉軍,所以從當時兩軍對壘的實際狀況分析,不應當是“不著甲而坐于地”。
從后世使用“坐甲”一詞的文獻看,釋為“解甲坐地”,也不符合邏輯:
(8)諸軍皆坐甲城下,欲以不戰降賊,佐獨勒所部,晨夜攻擊。(北齊魏收《魏書·李佐傳》)
(9)募兵出戰,至城門皆坐甲自守,恐城外有伏,乃燒城旁府署。(唐許嵩《建康實錄》卷十五)
如果想要以不戰而屈降敵人,總不會不穿著鎧甲吧?這樣恐怕是不會戰勝的。同樣,征集士兵出戰,在城門處防守,也沒有脫下鎧甲的道理。可見,孔穎達正義所解釋的“不著甲而坐于地”是不合適的。
第二種觀點“著甲坐于地”與第三種觀點“披甲、持甲”的主要矛盾在于是否“坐于地”(并且訓“坐”為“持、披”也是錯誤的,前文已經證明)。從常理而言,戰爭進行的時候是不應當“跪坐于地”的,但如果翻閱一些兵書文獻,就會發現“跪坐于地”這一行為是合理的,乃是古代戰前布陣的一種方式——“坐陣”。
《左傳·桓公十二年》敘述楚、絞之戰時說:“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大敗之,為城下之盟而還。”注云:“坐猶守也。”可以推測這是一種戰術方法。朱駿聲《春秋左傳識小錄》:“桓十二,楚人坐其北門。惠棟云:‘兵法有立陳坐陳行止之別,見《尉繚子》。’《傳》曰:‘裹糧坐甲。’又云:‘王使甲坐于道。’《司馬法》:‘徒以坐固。’皆是。”《晏子春秋·內篇諫下》:“晏子對曰:‘臣聞介胄坐陣不席,獄訟不席,尸坐堂上不席,三者皆憂也。’”由此可見,古代兵書文獻中應記有“坐陣”之法,與“立陣”相對應,具有不一樣的戰術功能。
《司馬法·嚴位》:“凡車以密固,徒以坐固。”《太平御覽·兵部》卷三百二十二:“凡車以密固,徒以坐固。”注文:“車卒眾則密陣,步卒眾則坐陣。”《尉繚子·兵令上》:“有立陣,有坐陣。……立陣所以行也,坐陣所以止也。”《吳子·治兵》:“圓而方之,坐而起之,……每變皆習,乃授其兵。”陳偉武(1995)指出此處的“圓”和“坐”均是陣名。施子美《施氏七書講義》:“常陳皆向敵,有內向有外向,有立陣有坐陣。……立陣所以行也,坐陣所以止也。立坐之陣,相參進止,將在其中。坐之兵劍斧,立之兵戟弩,將亦居中也。”曾公亮《武經總要》記載有“銜枚之法”:“后動有銜枚之法,待彼先動,欲戰之時,令軍中人臥旗,并銜枚坐陣,待敵先發,乃擂鼓大呼,進擊必勝。”劉寅《武經七書直解·司馬法》:“凡戰之道,等道義、立卒伍、定行列、正縱橫、察名實。”注文云:“凡卒伍之位,使在下之人分左右,孫子教女兵分左右隊是也。又使在下之人皆被甲而坐,若《春秋左氏傳》‘裹糧坐甲’是也。”
銀雀山漢簡兵書類文獻中也有相關記載。《孫臏兵法·威王問》:“孫子曰:‘鼓而坐之,十而揄之。’田忌曰:‘行陳(陣)已定,勭(動)而令士必聽,奈何?’”整理小組注:“坐,疑即坐陣之坐。”陳偉武(1996)同意該考釋意見。
由上述材料可知“立陣”與“坐陣”的區別,“立陣”主要是進攻陣型,而“坐陣”則為防守陣型。既是防守陣型,也必然是要“穿著鎧甲”的。這時候再來審視《左傳·文公十二年》的記載:“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就可以理解“不在軍事,好勇而狂”的趙穿為何發怒。當兩軍對峙之時,秦國遠征作戰企圖速戰速決,而晉國采用謀慮,布置“坐陣”,進可“起而攻之”,退可“據地防守”。而當由晉奔秦的士會識破此計后,偷襲晉國上軍,希望引敵出戰,自然只有不知計謀的趙穿會“追之不及”;當趙穿返回,看見一個個準備好干糧、布置好“坐陣”的士兵卻不同自己一起追擊秦兵,于是發“裹糧坐甲”之怒問。
當從古代兵書文獻中了解到“坐陣”的實際用途,并且了解到“著甲跪坐于地”這一行為的合理性與在實戰中的必要性(圖3的跪坐兵馬俑或正是“坐陣”之隊形)后,相比之下,后兩種觀點“披甲、持甲”與“積聚鎧甲”自然顯得不恰當。
5.“坐甲”一詞后世用法梳理
后世文獻往往脫離了具體的對話語境,同時“坐陣”的備戰方式也逐漸不用,若不加考慮全部將“坐甲”分析為“著甲跪坐(列陣)”,則會使文意顯得齟齬,故有必要考察該詞語在后世的用法。
當描述兩軍對壘或者進行戰術布置,尤其是一方為奔襲進攻、一方為防守待敵之時,“坐甲”一詞即“披甲坐地”的“坐陣”之義:
(10)軍行十數里,乃率淄、青、兗州步騎四萬余人,逾橋掩其后,乘風縱火,鼓噪而進。燧乃坐甲①此句點校本《舊唐書·馬燧傳》為:“燧乃坐,申令無動。”但此《十一家注孫子》為宋刻本(今上海圖書館藏),較點校本《舊唐書》所用底本(道光岑氏懼盈齋本)早,且前文有“聞賊至,則止為陣”,判斷這便是言說“坐陣”戰法,可知點校本《舊唐書》“申”字或為“甲”字傳抄訛誤讀入下句,故用《十一家注孫子》之注文“燧乃坐甲,令無動”而不從點校本《舊唐書》之文。,令無動。命前除草,斬荊棘,廣百步以為陳,募勇力得五千余人,分為前列以俟賊至。(《孫子·虛實篇》何氏注)
(11)及城被圍,開承明門出戰。子一及弟尚書左丞子四、東宮直殿主帥子五并力戰直前,賊坐甲不起。子一引矟撞之,賊縱突騎,眾并縮。子一刺其騎,騎倒矟折,賊解其肩,時年六十二。(唐李延壽《南史·江子一傳》)
(12)大王今欲親率猛銳,先據成皋之險,訓兵坐甲,當彼疲弊之眾,一戰必克。(唐杜佑《通典·兵十二》)
(13)詔入內內侍省使臣四十人被甲守內東門,殿前諸軍指揮使六十人坐甲于內東門之外。(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五百二十)
以上四例,尤其是第一、二兩例,因為上下文敘述語境詳細,可印證“坐陣”確實為待敵防守的陣型。第一例是記載如何布置“坐陣”戰法待敵而至的具體戰例。第二例是進攻“坐甲”之陣而失敗的具體例證,可見“坐陣”的防守能力很強,這也是秦軍偷襲晉軍上軍不會成功的原因。如果徑將“坐甲”訓為“披甲”,第一例中在行軍作戰,哪有戰事中途再披上鎧甲的道理?并且“令無動”更證明乃是布置“坐陣”。第四例中,前已有“被甲守”一語,而后言“坐甲于東門之外”,正表明列陣先備防守。
當“坐甲”一詞不運用于具體的戰術布置時,在后世文獻中可引申為多種意義,往往是省略“坐陣”的含義,而直接表示“披甲作戰、武裝守備”這一行為:
(14)而興師遼陽,坐甲江甸,皆以國乏經用,胡可勝言。(唐房玄齡等《晉書·食貨志》)
(15)天子新即位,我坐甲于此,以備非常。(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百五十三)
(16)命衛士坐甲東門三日。(元馬端臨《文獻通考·王禮考·國恤》)
也可直接釋為“披甲、全副武裝”之義:
(17)而擁大軍御侮于外,不宜遠露怯弱之形以虧大勢,故秣馬坐甲,每見吞并之威。(《世說新語·方正》劉孝標注引《晉陽秋》)
(18)守天渡,屯賈山,令平水陸路絕,將坐甲而擒之。(北齊魏收《魏書·羌姚興傳》)
(19)募兵出戰,出城門數十步,皆坐甲而歸。(梁蕭子顯《南齊書·東昏侯本紀》)
(20)今將坐甲待敵,則師老財殫,日就困弊。(元脫脫《金史·完顏仲元傳》)
(21)司馬懿坐甲不出城,相拒半年。(《三國志平話》卷下)
進而可引申為“全副武裝的軍隊、戰士”:
(22)今坐甲十萬,糧用自竭。(《全梁文·答蕭穎胄書》)
(23)四壁皆三衙諸軍,周廬坐甲,軍幕旌旗,布列前后。(宋周密《武林舊事》)
以上例句中“坐甲”的使用較為活泛,此時動詞義“披”并非來源于“坐”,而是通過上下文語境產生。在“枕戈坐甲”“頓兵坐甲”“坐甲安邊”等詞中亦是如此,不可因此認為“裹糧坐甲”之“坐”可訓為“披”,因為前文已經證明,這在訓詁上是沒有依據的,且于《左傳·文公十二年》中文意也非妥帖。
6.結論
通過上述討論,可知春秋時期的士兵身著鎧甲裝束可以完成“坐”這一動作,在戰爭中也有“坐陣”之法,故有“著甲坐地”之必要性。《左傳·文公十二年》中“坐甲”一詞應當釋為“著甲跪坐于地”的“坐陣”之法,是一種臨敵備戰的隊列陣型。后世文獻中,“坐甲”一詞可引申為“披甲作戰,武裝守備、鎮守”,或直接釋為“披甲、全副武裝”,再可引申為“全副武裝的甲士、軍隊”。
有趣的是,隨著“坐”由“跪坐”變為“垂腳坐”,或以臀部著地的各類姿勢都可以稱為“坐”時,“坐甲”一詞果有“脫下鎧甲坐于其上”的直接含義。《遼陽州志》卷二十八:“檄下仆旗息鼓,坐甲解櫜鞬。”《董解元西廂記》卷三:“把那弓箭解,刀斧撇,旌旗鞍馬都不藉。”“又曰:‘軍中不叛者,東向棄仗坐甲,叛者西向作隊,以備死戰。’言訖,軍眾皆棄仗向東坐甲。”
引用書目
《帛書老子校注》,高明,中華書局1996年。《楚辭》,[漢]劉向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春秋左傳識小錄》,[清]朱駿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董解元西廂記》,明嘉靖刻本。《廣雅疏證》,[清]王念孫,江蘇古籍出版社1984年。《建康實錄》,[唐]許嵩,南京出版社2010年。《金史》,[元]脫脫,中華書局1975年。《晉書》,[唐]房玄齡等,中華書局1974年。《老子道德經注校釋》,[魏]王弼注,樓宇烈校釋,中華書局2008年。《遼陽州志》,民國遼海叢書本。《呂氏春秋集釋》,許維遹,中華書局2016年。《南齊書》,[梁]蕭子顯,中華書局1972年。《南史》,[唐]李延壽,中華書局1975年。《全梁文》,[清]嚴可均輯,馮瑞生審定,商務印書館1999年。《三國志平話》,古典文學出版社1955年。《施氏七書講義》,金程宇編,鳳凰出版社2012年。《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刊本),[清]阮元校刻,中華書局2009年。《十一家注孫子》,中華書局1961年。《世說新語》,[南朝梁]劉孝標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說文解字》,汲古閣本。《說文通訓定聲》,[清]朱駿聲,中華書局1984年。《司馬法集釋》,王震,中華書局2018年。《宋本廣韻》,[宋]陳彭年等編,江蘇教育出版社2008年。《宋會要輯稿》,[清]徐松,中華書局1957年。《孫臏兵法》,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文物出版社1975年。《太平御覽》,[宋]李昉等撰,中華書局1960年。《通典》,[唐]杜佑,中華書局1984年。《魏書》,[北齊]魏收,中華書局1974年。《文獻通考》,[元]馬端臨,中華書局1986年。《武經七書》,廣陵書社2010年。《武經七書直解》,[明]劉寅直解,岳麓書社1992年。《武經總要》,[宋]曾公亮等著,商務印書館2017年。《武林舊事》,[宋]周密,中華書局1991年。《續資治通鑒長編》,[宋]李燾,中華書局1992年。《晏子春秋》,[清]孫星衍、黃以周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一切經音義三種校本合刊》(修訂本),徐時儀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莊子集解》,[清]王先謙,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