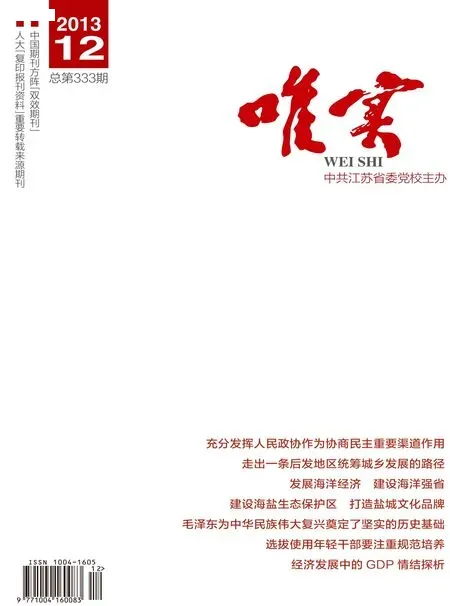世界上最早的城市
陳仲丹

城市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它的出現往往被看成是文明產生的標志之一。根據美國學者的意見,衡量一個居民點能否稱為城市有五個標準:其一,城市與農村相比,是有大量人口的居民點;其二,城市居民密度大于農村;其三,城市的基本功能是分配;其四,城市是交通中心;其五,城市是需求中心。而按照比利時學者亨利·皮朗的說法,最早的城市起源于人類經濟活動的市場或軍事活動的要塞。城市與鄉村不同的地方在于,它要在相對狹小的空間容納較多的設施,以滿足城里居民的各種需要。為滿足居民安全防衛的需要,城市就要有城墻和堡壘;為滿足居民宗教信仰的需要,城市就要有神廟和祭壇;為滿足居民經濟生活的需要,城市就要有市場和作坊;為滿足居民公共活動的需要,城市就要有休閑的場所和市政管理機構。依照這些標準,讓我們按地域和時序來考察世界上最早出現的一些城市。有趣的是,這些早期城市都出現在東方。
土耳其的恰塔爾休于有可能是人類最早建立的城市,距今已有8000年之久。這座城里有1000多座土磚砌的房屋,人口超過6000。每幢房屋規格統一,由一間起居室和幾個附屬房間組成,彼此有低矮的門洞相通。屋內有木梯、爐灶以及放燃料的柜子,另有平臺和長凳以供坐臥。房屋之間都緊緊地挨著,排得密密麻麻,以致城里沒有街道,人們就用房頂作通道。這些房屋的底層不開門窗,只在二樓開個小門,住戶靠木梯從底層上二樓。這樣安排可能是為了抵御水災,也有可能是為了自衛,當出入的梯子收起來后,各個房間自成防御體系,并共同構成一個大的防御體。住戶的內室都不大,不少人家墻壁上裝飾壁畫、灰泥浮雕和獸頭(主要是牛頭)。恰塔爾休于沒有城墻和其他公共設施,嚴格說來它至多只是個大居民點,還算不上真正的城市。
比恰塔爾休于要晚些時間出現的耶利哥(又譯杰里科)在今天巴勒斯坦境內,有人認為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圣經》里記載,耶利哥是以色列人離開埃及回歸故地渡過約旦河后攻占的第一座城市。傳說古以色列人在這里抬著上帝的約柜每天繞城一圈,到第七天耶利哥的城墻竟被號角聲震塌。耶利哥的地理位置很好,附近有源自約旦河的一汪清泉。這座城有堅固的石砌城墻,在城墻外有一條大溝,類似護城壕。城內建有一座直徑10米、高9米的圓錐形塔樓,樓內有階梯直通頂端。城里有些以木柱支撐的泥磚房子。這些房屋皆泥抹地面,半圓頂,沒有窗戶,向下進入低于地面的房間。當地居民還雕刻了數量眾多的塑像和頭像,可能是出于祖先崇拜。但對耶利哥能否算城市,學者們看法不一,否定的意見認為圍墻內的居民數量不多,稱它為軍事要塞更為合適。
距今5000年前在西亞兩河流域南部(稱蘇美爾)出現了十多個城邦國家。它們地處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流域沖積平原,土地肥沃松軟,有利于農業生產。這些城邦大多建有城墻、宮殿和神廟,有的塔形神廟還造得巍峨壯觀,被認定是城市應無疑問。這些城市以在今伊拉克南部的烏爾和烏魯克為代表。
烏爾是兩河流域最富庶的貿易中心。其城墻長約2000米,城里擁擠的房屋和整潔的街道都圍繞巨大的塔形神廟而建。有兩條運河把烏爾與附近的幼發拉底河連接起來。運河不僅有助于城市發展海上貿易,還給附近的農村提供了充足的水源。考古學家在這里多年工作挖出了王陵和塔廟。參與過這一地區考古的英國人倫納德·伍利認為,這些古代城市的外觀很像北非那些有城墻的城市:狹窄的街道構成了同樣的交通網絡,街面寬不超過3米,街旁同樣是兩三層的房屋,同樣有可利用的屋頂、同樣的庭院,還有陡峭的角錐狀高塔聳立在這一切之上。每個居民都分別隸屬于某個神廟。由于不重視衛生,居民清掃屋內的垃圾會傾倒在街道上,使得街道的地面逐漸升高。
離烏爾不遠的烏魯克是傳說中英雄吉爾伽美什的故鄉。在《吉爾伽美什》史詩中有對建造烏魯克城的生動描繪:“他(吉爾伽美什)建造了森嚴壁壘的烏魯克城,看它的外墻,那飛檐有如銅鑄,看它的內城,世上絕妙無雙!”據這部史詩記載,烏魯克由三個“薩爾”和一處圣界組成。這些“薩爾”,“一個是指城市,一個是指果園,還有一個是指邊界地帶(可能是菜園一類的綠化地)”。圣界是神廟所在的區域,建有兩座神廟,分別是供奉天神安努的“白廟”和供奉豐收女神伊南娜的“天之屋”。20世紀初,德國考古隊來這里發掘,挖出了神廟和宮殿建筑遺址,還出土了泥板、印章、石雕等精美藝術品。在這里出土的彩釉浮雕磚反映了當地的建筑水平之高,各種工藝品在技藝上已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因而現代學者認為烏魯克文化是“高度發達的文明”。但這兩座城市就功能而言與后來印度的摩亨佐·達羅相比就顯得有些不足了。
20世紀20年代,英國考古學家馬歇爾在印度河流域(今屬巴基斯坦)發現了一座古城,這就是約在4000年前出現的摩亨佐·達羅。馬歇爾在考古報告中稱:“在摩亨佐·達羅的發掘已經表明有一個早期的城市存在。最上層的建筑物分為兩類:一類是廟宇,一類是私人住房。廟宇的廳室很小而墻壁很厚,說明這些廟宇有好幾層樓高。私人住房結構精良,有浴室、壁爐、磚砌地面和良好的下水道。這一切都說明居民有高度的文明。”按這座城市的規模推算,城內居民約有4萬人。這座城市的建造肯定經過了精心的規劃,以建立在人工土丘上的城堡為核心,四周環繞的低地分布著市區。城堡和市區之間隔有人工溝渠。城堡內的工事堅固,且功能齊備。市區分為東西兩部分,東城呈長方形,兩條并行大街由南向北穿城而過。城里大街小巷基本按東西或南北方向整齊排列,縱橫延展皆以直角相交,整個城區如同一個大棋盤。這里的主要建筑材料是用黏土燒制的方磚。這種土黃色泥磚不但被用來蓋房,也用來鋪路、砌排水溝。東城主要的房屋是民居,大多沿街而建。由于不用木頭框架,磚墻砌得很厚。摩亨佐·達羅雖然沒有專門的工商業區,但有些房屋的主人顯然是專門從事某項手工業,他們在屋內畫上了這個行業崇拜的神靈,也有些房子比較寬大,可能是商店。
與同一時期的其他城市相比,摩亨佐·達羅的優越之處在于其有完善的公共建筑和設施。街道下面有連通各家的排水系統,樓上的污水經垂直的水管通向地下溝道,雨水和污水通過溝道流進大河。為了防止渣滓淤塞溝道,支溝進入主溝處有污水坑,主溝每隔一定距離也有水坑,人們可以檢修溝道,清除污物。城里有幾眼為居民提供用水的大水井,幾乎每一家都有自備水井。東城西邊有個高臺,高臺上最引人注目的是大浴池。池壁和池底砌磚,磚縫中填滿石灰漿,上面涂一層瀝青,防止漏水。這里可能是舉行大型祭祀活動的場所,人們就用池中的水潔凈身體。像這樣注重整體規劃的城市當時在世界各地還很少見,要等到1000多年后羅馬人統治地中海區域時才有類似的城市。
在中國,城市起源也很早。目前發現最早的城是距今6300年的城頭山遺址,它位于湖南常德澧縣。這座遺址呈圓形,有寬闊的護城河、高大的城墻。圓形遺址中央有座城,東西南北分別開有城門。城內功能區劃明晰規整,分為居住區、制陶作坊區、墓葬區等。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單位組成的聯合考古隊發掘出的城河遺址(屬于屈家嶺文化)則是一座5000年前的古城。該城位于今湖北沙洋縣西部的城河村。它有體量宏大的城垣、規則有序的水系、引人注目的大型院落建筑和葬俗獨特的墓地。城墻外側有完備的護城河,最寬處達60米,最深處有6米以上。城墻三處設立水門,城外河水經水門進入城內,再經人工溝渠排至城外的自然河流。這樣既保證了城內大量人口的生產生活用水,又避免了旱澇之災,體現了嫻熟的水資源利用和管理水平。城內有大型墓地位于遺址的最高地。在高崗埋葬死者既不占用城內寶貴的土地資源,影響生者的生活,又能讓先祖處在制高點,“俯瞰”全城,佑護子孫,體現了“生死有別”的理念。
在中國古代早期城市中更為典型的是位于今浙江杭州市余杭區的良渚古城。早在1936年,當時在西湖博物館任職的施昕就發現了良渚遺址。最近十幾年在遺址范圍不斷有重要的發現,2007年發現圍繞中心土臺和王墓的大型城墻,2015年確認遺址群周圍有大型水壩等水利系統。根據其功能和類型,良渚古城遺址可分為三類:城址,包括中心的宮殿區、內城、外城;外圍水利系統,包括谷口高壩、平原低壩和山前長堤;不同等級的墓地。整個良渚古城呈圓角長方形,總面積近300萬平方米,比四個故宮的面積還要大一些,是同時期中國規模最大的古城。古城城墻總長約6公里,以草裹泥的方式修筑。這座古城的發現以確鑿的證據證明中華文明擁有5000年的歷史。2019年良渚古城遺址成為“世界文化遺產”。
傳說距今4000年時,夏朝最早的國王啟的祖父鯀曾“作三仞之城”,“三仞”是指城市的外壕、城墻和內壕。以后夏朝的都城開始以宮殿為中心來設計布局。商周時代的城市除仍注重軍事、政治功能外,也開始對城市的經濟和文化功能有所考慮。宮殿和宗廟是都城的主體建筑,城里有了手工作坊區。到春秋戰國時期,天下紛爭,筑城成了“國之大事”,城市也就蜂擁而起。在城市布局上,棋盤形格局初步形成。都城有了城、郭之分,內城為城,外城為郭,“筑城以衛君,造郭以守民”,有了功能的分工。手工作坊開始固定在宮殿周圍,市場在城內也有了固定位置。筑城方法是先用版筑夯土城墻,但因為夯土易受雨水沖刷,后來就用磚石包夯土墻,使城墻牢固程度大大增強。在今江蘇常州的古城淹城至今基本輪廓還保存完好,這是春秋時淹君的駐地。該城有土墻三重,分為子城、內城和外城。每座城都有護城河,由三城三河相套而成,形制獨特。城墻系用開挖城河之土堆筑。外城是不規則的圓形,內城和子城近似方形,房屋建筑現已不存,城內有幾個高高的土丘,可能是昔日樓臺的遺跡。
(作者系南京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責任編輯:彭安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