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傳記中“審父”與“審母”情結探析
——以《我和父親季羨林》與《我的母親楊沫》為例
魏 雪 全 展
荊楚理工學院
內容提要:“審父”情結是西方文學中的一個經典母題,中國現當代文學中“審父”敘事也是屢見不鮮。但是作為傳記而言,“審父”是一個并不多見的現象,“審母”則更為罕見。季承的《我和父親季羨林》采用“父與子”的模式展開敘事,為讀者呈現了國學大師季羨林的另一面。老鬼的《我的母親楊沫》則站在更加另類的“母與子”視角,真誠地對母親楊沫進行剖析。兩部傳記具有一些共同特征:都從親情的泯滅、母性或父性的淡薄、父母的婚姻悲劇等方面為我們展現了季羨林和楊沫的真實家庭生活。但是兩位作者的創作目的、敘事風格、對父母的理解等方面各具特點,其中暗含了作家不同的成長經歷以及相異的個性特征。“審母”相對于“審父”而言,無疑是對當代作家傳記在真實性以及敘事倫理等方面更進一步的發展。
審父”情結是西方文學中的一個經典母題,父親代表著傳統,代表著權威,“審父”意味著對傳統權威的顛覆,文學創作中主要體現為子女對父親由傳統的仰視視角轉變為平視視角。隨著現代社會女權主義運動對父權制的顛覆,婚姻功能和家庭角色發生轉變,母親與父親共同承載著家庭的責任與義務,成為子女們的權威對象,因此本文將“審母”作為一個與“審父”并提的概念。傳記文學中“審父”與“審母”指的是傳記作者拋棄了對傳主父母的仰視視角,以一種與父母平等對話的姿態對父親或母親進行審視,對傳主身份的父母形象進行還原。傳記文學中的“審父”與“審母”充分發揮了傳記作者的主體性,以子女的身份、平等審視的角度,對傳主進行解釋,從而實現傳記作品的真實性,凸顯傳主獨特的人格特征。季承的《我和父親季羨林》與老鬼的《我的母親楊沫》可謂中國當代傳記中“審父”與“審母”的經典代表。
正如盧梭在《懺悔錄》第一章里面所寫的“我要把一個人的真實面目赤裸裸地揭露在世人面前”一樣,季承在《我和父親季羨林》的扉頁寫道:“通過里面講述的故事,我祈愿讀者朋友們能更多、更真實地了解我們這個家庭,特別是我的父親季羨林先生。”[2]同樣,作家老鬼也在《我的母親楊沫》前記中寫下了這樣的文字:“我遵循母親的愿望,盡量客觀地把母親一生中我所認為的重大經歷記錄下來,盡可能大膽地再現出一個真實的,并非完美無缺的楊沫。”季承和老鬼都不約而同地在傳記的正文之前表達了自己的寫作意圖:展現真實的父母形象,讓讀者更加逼近一個真實而非高大完美的形象,傳記的真實性成為了作者寫作中的首要考慮因素,“不虛美、不隱惡”。伍爾夫認為傳記的問題“一方面是真實性,另一方面是人的品性。假如我們把真實性看作是某種堅如磐石的東西,把人格看作是捉摸不定的彩虹,因而認為傳記的目的就是把二者天衣無縫地融為一體”。季承和老鬼的傳記正是通過對父親和母親鮮為人知的真實面的揭示,去掉父親和母親頭上的名人光環,給讀者展現了傳主普通平凡的一面,同時對父母的行為進行分析解釋,從而實現了傳主季羨林和楊沫的人格重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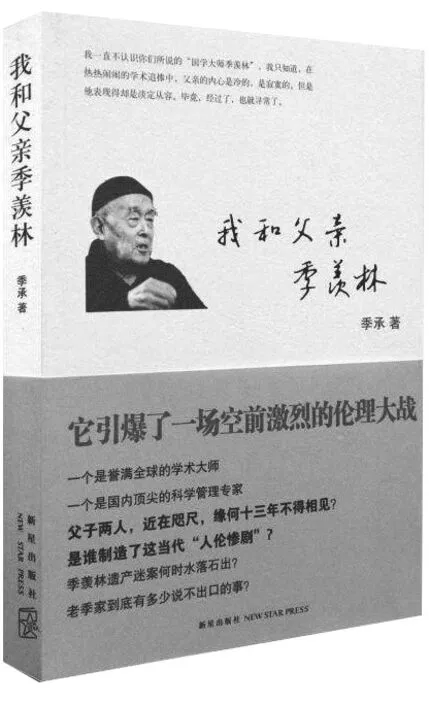
季承著《我和父親季羨林》
《我和父親季羨林》與《我的母親楊沫》都是從傳主父母的出生寫到去世。縱向時間維度上描寫了父親季羨林與母親楊沫的童年時代、青年時代、成年時代、老年時代,涵蓋了傳主一生的主要經歷。在橫向敘述傳主人生每一階段的經歷時,作者主要通過描寫傳主的矛盾沖突來體現強烈的“審父”與“審母”意識。這些矛盾沖突主要涉及到季羨林和楊沫的家庭生活,兩部傳記都從親情的泯滅、父性或母性的淡薄、父母的婚姻悲劇等方面為讀者展現了季羨林和楊沫的真實個性。“兩位作者真實得近乎‘殘忍’的背后,并沒有結論為‘冷酷的背叛’,而是一種深含摯愛之心、泣血之愛的體驗,這份大愛與真、善、美有關,亦與寫作者的文化‘良知’有關。他們都希望還原一個真實的‘人’的形象,也希望讀者能夠接受一個有缺陷的楊沫,一個有缺陷的季羨林。”

青年楊沫
老鬼寫童年時期的楊沫雖然出身大戶人家,卻生活在一個缺少溫暖的家庭,“雖然有親生父母,事實上卻好像是個孤兒。衣服破了,沒人縫;生病了,沒人照料;身上長了虱子,沒人管;季節變化,該換衣服了,沒人提醒……平時吃飯、睡覺都和傭人在一起。她衣衫襤褸,處境還不如闊人家里的一條小狗。”楊沫母親的嚴酷無情給她的童年留下了終生難忘的印象,老鬼受到弗洛伊德的啟發,解釋了楊沫成年后對子女漠不關心的重要原因是楊沫的童年時代缺少母愛與父愛。季承寫父親季羨林的童年生活時著重寫了他6歲被過繼給叔父,被迫“要拋別父母,受人歧視,寄人籬下”。跟老鬼如出一轍,季承指出了童年這段時期的生活,給季羨林情感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甚至影響了一生。兩位傳記作者不約而同地指出:童年時期親情的泯滅導致了傳主母性或父性的淡漠。季承在傳記中著重寫了自己與父親情感上的隔閡,父親在闊別家鄉12年后回家,作者記憶中留下的是“記得父親在摸了我的頭發之后,立刻去水缸里掏舀了一瓢水沖手,使我感到新奇。但他從來沒有親過我或拉過我的手”的印象。在《我的母親楊沫》中也有類似的情節,楊沫“5個孩子有4個是找別人帶的——我和哥哥一輩子不知道在母親面前撒嬌是什么滋味——孩子得病,也不著急……事業型女性,缺少親情意識”。令人驚嘆的是,兩部傳記中,同時出現了因為親情淡漠關系惡化而導致的父母與子女直接決裂的事件。《我和父親季羨林》中出現了父子隔絕13年的事件,《我的母親楊沫》中描寫母子多次斷絕關系。而且斷絕關系的重要原因除了傳主本身父性或母性淡漠之外,皆有外部因素從中破壞導致的感情隔絕。當然,兩部傳記也都寫到了在父母晚年,父子、母子和好,冰封的關系釋然。

老鬼著《我的母親楊沫》
傳主的婚姻悲劇也是傳記作者“審母”與“審父”的重要內容。老鬼寫自己的父親與母親長期分居,各自猜疑對方,到“文革”時互相揭發導致關系徹底惡化,楊沫的婚姻名存實亡、貌合神離。“兩個人只剩下歷史上的關系,因襲的習慣。……沒有離婚,卻一直分居。”老鬼在傳記中詳細地寫出了父母關系惡化的經過,老鬼在書中還大量呈現了母親楊沫的日記,以及父母的通信,向讀者如實展現了楊沫婚姻關系惡化的事實。季承在書中則多次提到其父親對母親的冷漠:“我和你媽沒有感情。”“我父親和母親是沒有感情的,他并不情愿和自己的妻子生活在一起,他們的結合是勉強的、機械的,他們的婚姻和生活是悲劇,他們的家庭也只是形式上的圓滿或美好。只有不了解情況的人,才把父親的家庭說成是美滿的。”季承在傳記中多次寫到父親的冷酷和母親的落寞。
兩部傳記除了通過親情的泯滅、父性或母性的淡薄、父母的婚姻悲劇這些傳主家庭關系的沖突來體現“審父”與“審母”之外,還從傳主與社會關系的沖突視角以及傳主自身人格的矛盾性來實現審視父母。《我和父親季羨林》與《我的母親楊沫》都涉及到秘書事件。季羨林在家庭關系惡化時被所謂的女秘書李玉潔乘虛而入,被其操控導致了巨大損失;楊沫在家庭關系惡化時被所謂的男秘書小羅乘虛而入,也被其蒙蔽導致了巨大損失。而且與秘書關系的結束也正是修復父子關系與母子關系的開始。兩位作者分別對秘書事件作了分析。季承認為:“一位男人在他進入人生末期的時候是需要有人照顧的,特別需要女性的照顧。”于是李玉潔乘虛而入。老鬼的分析則是:“母親找這么一個與她各方面差距極為懸殊的人做親密助手,可能有一種報復父親的心理。”此分析不論正確深刻與否,都是傳記作者對父母的一種審視。
除了寫秘書事件之外,兩部傳記都寫到了傳主的另一個共同點:對家人小氣,對外人大方。老鬼在書中寫自己的母親對兄弟姐妹都非常苛刻,困難時期孩子們回家吃不飽飯,必須交糧票。善待外人,從沒有苛責過家里的保姆,匯款單被人冒領聽之任之,給人300元買皮大衣,一次借給海默500元等。同樣,季承寫父親季羨林對家里人“吝嗇”,對外人“俠氣”:“父親每月給母親一定數目的錢做生活費,要她記賬,至于夠不夠,他不再問。因為他不肯再掏錢,母親也不敢再向他要錢。缺了就拿自己的積蓄彌補。母親常為此而為難。我和姐姐去北大的家,父親是不拿錢出來的,都由我和姐姐貼補。”對別人的贊助和捐贈很大方,但是從來不對家人和親屬“捐贈”。這種對內和對外的行為差異體現了傳主個性中的內在矛盾沖突,豐富了傳記寫作的內在空間。
無論是家庭關系的激烈沖突還是傳主個性的內在矛盾沖突,兩部傳記都進行了真實的呈現,達到了使讀者印象深刻的效果。這種揭示是真實的、豐富的,同時又是尖銳的。與其他的當代作家傳記有意無意回避傳主經歷的沖突、隱蔽傳主的一些隱秘事件相比,其精神是可貴的。尤其是與諸如劉可風的《柳青傳》、梁秋川的《曾經的艷陽天:我的父親浩然》等子女以仰視的視角寫父母的傳記相比較,《我和父親季羨林》與《我的母親楊沫》無疑實現了在充分的沖突中再現傳主形象。“傳記家同傳主的關系,是傳記寫作的核心問題,傳記的成敗與此有關。”傳記作者與傳主身為子女與父母的關系,一方面有利于具有先天優勢可以更好地從近距離角度對傳主進行觀察描寫,但另一方面,子女往往也是最容易考慮到切身利益,對父母傳主進行避諱的。尤其是在敘述家庭關系的矛盾沖突時,季承和老鬼在傳記中將自己的作者身份放置在平視與審視的視角,展現的這些矛盾沖突是坦然的、直白的、震撼人心的。當然,我們對比這兩種寫作視角的傳記人物關系會發現:子女以仰視視角來寫父母的傳記,作者本身與父母的關系是非常融洽的,父母對子女也是和藹可親的,現實中沒有出現“審父”“審母”視角的傳記作者與父母之間巨大的矛盾和隔閡,所以也未嘗不是另外一種真實。

晚年季羨林
老鬼和季承的傳記不僅直白地描寫了傳主的家庭矛盾沖突與傳主的個性沖突,還都從作者與傳主親子關系的視點,用自己的理解對母親和父親的行為及個性作了分析解釋,為讀者重新闡釋兩位名人的形象。傳記作者不滿足于一般的傳主事跡敘述,讓讀者看到傳主怎么樣,還想讓讀者清楚為什么這樣,甚至讓讀者清晰知道自己的想法,可謂一種執著不懈地追求傳記真實性的精神。這種反思精神可以讓讀者更深刻地了解傳主,豐富傳記作品的內涵。關于傳主親子關系的淡漠,老鬼在傳記中進行了反思:“我常常思忖,為什么母親對孩子缺少愛?”作品中歸結為以下幾個方面:“與長期以來大批資產階級人性論有關。從解放初期到‘文革’,全社會不提倡母性、母愛。這被認為是一種資產階級人性論而大加討伐。”“另外,與她早年受鄧肯的影響有關,崇尚叛逆女性……連基本人性也叛逆。如血緣意識、母性本能等全都否定。以為重親情落后陳腐,平庸世俗;母性是動物本能,格調不高……”接著老鬼繼續分析:“也恐怕有她生理上的原因……她自己就是個病人,需要別人照顧,自然對孩子缺少耐心和關愛。”“還有,與父親關系不好,父親對孩子的冷漠傳染了她。”最后,老鬼分析道:“不過,據我看,與母親的遺傳有很大關系。她母親丁鳳儀就不是一個很疼孩子,很母性的女人。——母愛能遺傳,少母愛也能遺傳。”老鬼的解釋不可謂不細致全面,用當時的生活條件來說明母親的個性,將楊沫的生存環境和歷史背景同其人格聯系起來進行考察,用遺傳學、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解釋楊沫的童年經歷對其后來個性的形成產生的影響。無獨有偶,季承也在傳記中通過童年敘事對其個性的形成造成影響來進行了解釋。“生活在叔父和嬸母的照顧下,令父親感到極端的拘謹。”“這段時期的生活,給幼年的父親感情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甚至影響一生。”關于季羨林的愛情婚姻悲劇,季承在傳記中進行了詳盡的解釋:“這里我想談一談父親對于愛情及其實踐的看法”,“父親則把愛情的態度分為兩大流派:理性主義和現實主義。而他把自己歸到現實主義一派”。“對于婚姻,父親沒有明確的論述,他認為婚姻只不過是緣分而已,和愛情并沒有多大干系。既沒有愛情,那婚姻也就談不上是愛情的結束或開始。”季承從蒙田對季羨林愛情觀的影響解釋了季羨林的愛情婚姻觀,季羨林內心的思想矛盾構成了季羨林愛情婚姻的悲劇。“其所以如此,我認為是受他自己的理論,也就是所謂的現實主義的指導,讓他成為愛情和婚姻的冷血兒。”但是這種分析并沒有進一步地深入進行,也不及老鬼對于母親剖析的深刻。“至于是什么原因使他有了他的理論,他的理論是否正確,只可能是智者見智,仁者見仁了。” 此分析點到為止。從傳記寫作的角度來看,傳記解釋有“歷史解釋、直覺解釋、精神分析解釋和綜合解釋”[7]四種主要解釋方法。作者季承還可以應用這些解釋方法對傳主季羨林愛情婚姻悲劇的成因進行深入分析和解釋,提升作品的內涵層次。
兩部傳記相比較,作品都從親情的泯滅、母性或父性的淡薄、父母的婚姻悲劇等方面為我們展現了季羨林和楊沫的真實家庭生活沖突,也都寫到在傳主晚年人性復歸,家庭親子關系得到緩和。從“審父”和“審母”的角度給讀者展示了傳記寫作的真實性。但是兩位作者都比較注重表現傳主外在的人際關系沖突及其成因的解釋,對傳主內心的矛盾沖突挖掘不夠,這方面似乎《我和父親季羨林》比《我的母親楊沫》的創作缺陷更甚。導致這一現象的原因可能與傳記作者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個性氣質有關系。老鬼是作家出身,推崇盧梭的精神氣質,《血色黃昏》就體現了坦然的真實和深刻的揭示。季承則是科學界人士,對人文科學涉獵可能不及老鬼深入,所以其傳記中從社會人文角度進行的分析和解釋也相對少一些,站在科學的角度分析人文主義者季羨林顯然不及作家老鬼分析楊沫的全面,寫作值得提升的空間也更大。另外,縱觀季承寫書前后,季羨林遺產案件沸沸揚揚,季承在父親去世8個月出版此書,其中可能也有在現實方面為父親和自己正名的考慮,其中不可避免地摻雜了一部分現實功利性。與此相比,老鬼的《我的母親楊沫》寫作環境更單純:“一個真實的楊沫,比虛假的楊沫能更久遠地活在人們的心中。”老鬼秉承著盧梭《懺悔錄》的精神和母親的遺愿,寫作目的更純粹,敘事也更豐富全面。傳記涉及到楊沫的生活、工作和創作的方方面面,甚至對“文革”中的楊沫也進行了真實詳細的敘述。《我和父親季羨林》敘述涉及的內容要狹窄很多,對季羨林的學術成就、季羨林“文革”中的遭遇等人生中的重要方面都幾乎未詳細提及。“審父”這一母題借鑒于西方,作為中國當代作家傳記而言,“審父”是一個并不多見的現象,“審母”則更為罕見。“審母”相對于“審父”而言,無疑是對當代作家傳記在真實性以及敘事倫理等方面更進一步的發展。
注釋:
[1] [法]盧梭:《懺悔錄》,黎星、范希衡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3頁。
[2] 季承:《我和父親季羨林》,新星出版社,2010年5月版,第1頁。
[3] 老鬼:《我的母親楊沫》,同心出版社,2011年6月版,第1頁。
[4] [英]弗吉尼亞·伍爾芙:《伍爾夫隨筆全集:花崗巖與彩虹》,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4月版,第1700頁。
[5] 全展:《傳記文學:觀察與思考》,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12月版,第129頁。
[6] 袁祺編:《巖石與彩虹:楊正潤傳記論文集》,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7月版,第396頁。
[7] 楊正潤:《現代傳記學》,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5月版,第129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