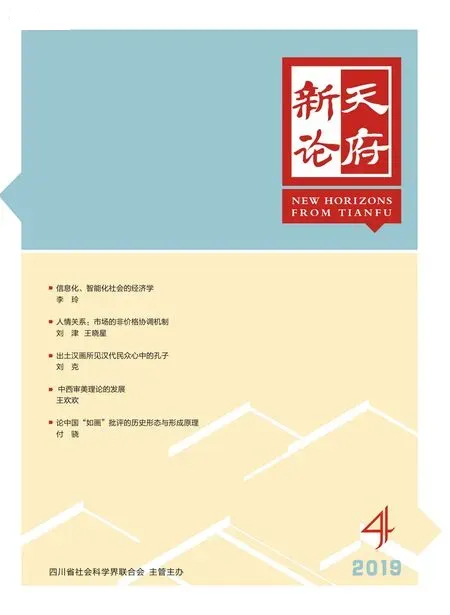《四書》“學習”之義淺說
丁 紀
一、夫子曰
《論語》明引《詩》、《書》、執禮之例,固夫子之所雅言,茲且姑置不論。亦有暗引者,如“巧言令色”引《書》,而以“鮮矣仁”斷之;“無違”或引自常禮,而以“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釋之;“祭如在”亦或引自常禮,而以“祭神如神在”釋之;“敏而好學,不恥下問”引謚法,而以“是以謂之文也”斷之;“克己復禮為仁”或引古史之語,而以“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釋之。此類對于六經等之引用,大概皆屬夫子之“自引”,并不影響《論語》作為經之地位,不會使其淪為“次一級”之典籍。其他如“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與其媚于奧,寧媚于灶”(王孫賈語)等,引用時諺,亦略無芥蒂,此類雖非雅言之屬,乃有以見其耳順之德。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此句平白說出,然自一定意義而言,其實亦是一種引用。朱子有曰:“六經說‘學’字,自傅說方說起來。”[注]黎靖德:《朱子語類》,中華書局,1994年,第153頁。又,參見同條,林夔孫錄作:“自古未有人說‘學’字,自傅說說起。”卷七九“尚書二·說命”,條一二:“經籍古人言‘學’字,方自《說命》始有。”(第2037頁)呂東萊亦云。[注]東萊曰:“自古至《說命》方說‘學’。”見《東萊集·外集》卷六《雜說》,四庫全書本。或問:“‘習,鳥數飛也’,如何是‘數飛’之意?”朱子曰:“此是《說文》‘習’字‘從羽’、《月令》‘鷹乃學習’,只是飛來飛去也。”[注]黎靖德:《朱子語類》,中華書局,1994年,第449頁。又,參見條八(第447頁)、條五五(第456頁)等。此意尚只是在指點“學”、“習”二字出處。然《尚書》與《月令》以及《說文》等意義固不同,非止于兩方面地位之有別而已,蓋《論語》之首章所取于《尚書·說命下》者大,一章之旨,無非本于《說命下》之篇。一篇《說命下》,實可稱作儒家之“學習經”也。
《說命下》傅說所以言“學習”者,為下文論說方便,析作三句,引之如下:
(一)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二)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
(三)惟斅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
其第二句“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中,“惟學遜志”乃言“學”,“務時敏”乃言“時習”,惟“厥修乃來”故“不亦說乎”,然則謂“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只是自《說命下》此句中翻出,或只是融泄《說命下》此句之義而成,抑亦可矣。不但于此,“允懷于茲”則見得“有朋自遠方來”之義,“道積于厥躬”則見得“不亦君子乎”之義,《論語》首章全章,蓋只是隱括得《說命下》一句在其中而已。
“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歷來讀之者,頗有幾處尚費分說,今以《書》視《論》,兩相映照,則:學什么、習什么?曰:“學于古訓乃有獲。”“時習”之“時”,究竟其義為“時時”、為“按時”?曰:既“遜志”而后乃有以“務時敏”,固非時時務此不可,否則,是不敏也。“說”又是“說”個什么?曰:悅其“厥修乃來”也。然則或以謂學習之事使人不悅反苦,則其必無“厥修乃來”之益,且亦無所“遜志”,兼以所習蕪雜,此情此況,不亦可知乎?得《書》 《論》互證,此等疑惑乃可一掃凈矣。
又不止于“學而時習之”一句或《論語》首章全章,凡夫子說“學習”處,皆可以得所照應,其義因得以隨處發明。
如“學而時習之”固是學古訓,而“行有余力,則以學文”(《論語》總章六),亦當是學古訓;“君子博學于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論語》總章一四四),亦當是學古訓;《大學》言格物致知,讀書乃格物之一事,亦當是學古訓。惟子貢以夫子為“多學而識之”,夫子必曰“非也”,而告以“予一以貫之”(《論語》總章三八○)者,蓋若以“多學而識之”當“博學于文”,似僅差卻個“約之以禮”,故曰“予一以貫之”意似僅在于補此“約之以禮”之不足;然“多學而識之”之所以不能至于“約之以禮”、“一以貫之”者,自《說命下》第一句而觀,恐亦有非專于學古訓之憾,故無時時進修之益,其既不能隨所博而約、隨其學之進洵至于弗畔之地,此其病自非于“多學而識之”后添一段“一以貫之”事即可以救藥之者。《說命下》第一句,恰以“人求多聞,時惟建事”與“學于古訓乃有獲”相對為言,蔡九峰注曰:“求多聞者資之人,學古訓者反之己。古訓者,古先圣王之訓,載修身治天下之道,二典三謨之類是也。”[注]蔡沈:《書集傳》,錢宗武、錢忠弼整理,鳳凰出版社,2010年,第113頁,第113頁。“人求多聞,時惟建事”,亦即“多學而識之”之類。學者一旦務其見聞之多,終不免于多事之雜沓,故求多聞與學古訓,至有為人、為己學問異趨之辨。然求多聞與學古訓之分,始亦不必如為人、為己之截然,故蔡注繼曰:“人求多聞者,是惟立事;然必學古訓,深識義理,然后有得。”[注]蔡沈:《書集傳》,錢宗武、錢忠弼整理,鳳凰出版社,2010年,第113頁,第113頁。此較前稍做退步言。人若以求多聞,甫立一個肯事乎事、“必有事焉”之志,才欲求多聞,即去學古訓,而不徒然自滿于閑聞見、閑知識之多,將來至于業精德熟,其所就固非求多聞之可限,然謂其非自求多聞之初志而來亦不得,惟其初或有資人、為人之嫌,亦可以銷釋于學古訓而不終為憾矣。故以“多學而識之”則“非也”,然能勿泥于求多聞,而更自勉于學古訓,“一以貫之”豈不可望乎?
夫子往往備言此義,如《易》大畜卦之象辭亦以言此,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程伊川傳之曰:“人之蘊畜,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圣賢之言與行,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畜成其德,乃大畜之義也。”[注]程顥,程頤:《二程集》(下),中華書局,2004年,第828-829頁。“多識前言往行”倘泛泛以“多學而識之”為解,將無以畜德。要必落實于“前古圣賢之言與行”,然后惟古訓之學、惟往圣言行之識,則有“厥修乃來”之益,乃可以“畜成其德”,乃能臻于“一以貫之”而“以克永世”也。
“多學而識之”其義若此,其與夫子自謂“多見而識之”(《論語》總章一七四)者語近而義別:“多學而識之”,夫子于子貢,不深取乎此而更有以振作之;“多見而識之”,乃夫子不自居生知之列,退以學知之次者自處也。然子貢之所以以“多學而識之”視夫子者,亦必有由,以其嘗聞夫子自言“多見而識之”之故乎?夫子乃曰:我雖非“不知而作之者”,而得乎多聞見矣,然“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如此其至也,“不知而作之者”我果無是乎?適為“予一以貫之”之義。此與以“多聞闕疑”、“多見闕殆”教子張者(《論語》總章三四)又不同:子張所問者卑,又不足與乎多聞見矣,故教之以寡尤悔之道,寡尤悔則須慎言行,慎言行則須闕疑殆,闕疑殆乃不得不先以多聞見之為事,夫然后乃可以“祿在其中”;至于“多見而識之”,若亦以“在其中”之法言之,須是曰“一以貫之、不知而作之者在其中”矣。
如“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論語》總章二七),常解往往以“溫故而知新”若當“學而時習之”者,亦即惟以為學者學習之事也。然章內既曰“可以為師矣”,自亦言教之事矣,此義不可虛卻。朱子注此章曰:“溫,尋繹也。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為人師。”[注]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1983年,第57頁。“故”者既是“舊所聞”、“溫故”既是“時習舊聞”,以“學而時習之”言,卻是“時習而學之”也。蓋“新”者之為“今所得”,固為“溫故”、“時習”之所得,亦奚不可曰“學”之所得,乃至“溫故”、“時習”之后一段“新學”哉?惟朱子此解,亦重在論學者學習之事,于教之事只虛虛帶過,與常解大段無不同。此章既有以言教之事,照應《說命下》第三句“惟斅學半”之語,似得曰:“溫故”者,學之事;“知新”者,教之事。“溫故”乃溫我之故,“知新”則新人之知也。惟“斅學半”,“溫故”與“知新”亦相為半,“溫故而知新”乃教、學各半其事,如此,“可以為師矣”其義乃得不虛。
然“斅學半”,蔡注云:“言教人居學之半。”亦惟以教居學之半,而不以學居教之半,且又甚言以學居教之半者事關某種新巧學風,此詳下文第三節所論。又于“念終始典于學”,蔡注云:“始之自學,學也;終之教人,亦學也。一念終始常在于學、無少間斷,則德之所修,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注]蔡沈:《書集傳》,錢宗武、錢忠弼整理,鳳凰出版社,2010年,第114頁。亦惟以“終始”者言一念在學。然既謂“始之自學”、“終之教人”,則亦一事而已,教、學各半其事而后竟成一事之始終,固可言矣。雖然,無論始之事也,抑其終之事也,學者皆當繼力盡心、無所逃責,然其念之所在,亦惟在于學而已,學亦學,教亦學,雖足以勝任其教,而猶自以為學力之不足,然后有不言之教行乎其中;不然,倘念亦半在于教,其有不貽為“好為人師”之患(《孟子》總章八四)者乎?此以學者之心言,固是“一念終始常在于學”;惟以其事言,亦須是有教、有學,一事乃得以有其首尾始終。一事以學言,教是學之半;一事以教言,學是教之半。由此而言,“溫故”與“知新”,亦相半而成一事之始終;惟一念常在于“溫故”,“知新”只在“溫故”中,則雖不“好為人師”,其實已“可以為師矣”。至于“溫故”之“故”,則不但言其既已在我者,亦言古訓之類而已矣。
然此教學相半之說既或犯新巧,則凜之慎之,于“溫故”、“知新”各半其事之說不敢必其為的解。且如“斅學半”,教為學之半、學為教之半,彼此各為“半事”;若“學而時習之”,學而后習也,習而后又學也,如此相與先后、更替進益,彼此乃互為“后事”;又若“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論語》總章三一),乃言學以思而成、思以學而成,不思而得以成其學者未之有也,不學而得以成其思者未之有也,此既非得言“學思半”,亦非得言“學而時思之”者,以“半”言之則裂,以“后”言之則外,外亦裂也,學之與思,乃彼此在事中為事,事中事則為“全事”,學中全是思之事、思中全是學之事,須臾離不得。“半事”、“后事”、“全事”之形態既異,則教與學、學與習、學與思之關系自不得一律齊。而“溫故”與“知新”,乃有在乎教與學、學與習、學與思之間者,如此,雖非有得乎原義之一,乃有以見理解之多歧、解釋之須相參取也:以“半事”言,“溫故”、“知新”正如教、學之相半;以“后事”言,“溫故”、“知新”卻如學、習,惟“學而時習之”以“知新而溫故”則習在學后,“溫故而知新”以“時習而學之”則習后更進學之不已也;至于“溫故”不“知新”則其故不得其溫、“知新”不“溫故”則其新非新而為不足知,“溫故”以“知新”成、“知新”以“溫故”成,二者之間不亦得作“全事”觀乎?乃若學與習之相先后,學而不習者有矣夫,不妨其為學,非好學者而已矣;又若教與學之相半,學而不獲執教柄者有矣夫,不妨其為學,豈無美玉韞櫝之憾乎?
二、諸子曰
夫子既教人以“博學于文,約之以禮”,顏子乃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論語》總章二一五)蓋直承夫子之教也。在夫子,則“吾與回言終日”(《論語》總章二五),誨之而不倦;在顏子,則“語之而不惰”(《論語》總章二二四)、“于吾言無所不說”(《論語》總章二五五)。故博文約禮之旨,最可于顏子一身驗之。“博學于文”,乃“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中庸》章八)、“不遷怒,不貳過”(《論語》總章一二一)、“以能問于不能,以多問于寡”(《論語》總章一八九)、“聞一以知十”(《論語》總章一○○),至于問仁則曰“天下歸仁焉”(《論語》總章二七八)、問為邦則得聞四代之政,博之極矣;“約之以禮”,則非禮勿視聽言動“請事斯語”(同上)、“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論語》總章一八九)、“無伐善,無施勞”(《論語》總章一一七),至于“回也其庶乎,屢空”(《論語》總章二七○)、“其心三月不違仁”(《論語》總章一二四),約之至矣。大概孔門諸子之中,以顏子為具體而微,其所得最全、所見最正,又最不著手腳,故夫子之所言于顏子者,亦最少對治之意。雖然,“于吾言無所不說”之前先出“回也非助我者也”之意,不掩喜慰之情,其實顏子亦最善發明。如夫子謂人一旦從事乎博文約禮,僅以“弗畔”言之;至于顏子,“既竭吾才”之余,乃以“如有所立卓爾”之益自下證驗,夫子亦稱“其庶乎”,可知所謂“弗畔”也者,豈果然輕以言之乎?蓋不至于卓然自立,終不能無所叛也。既曰“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論語》總章二五),即已謂其能發明矣;惟其所發明,不以言、乃以行,不以智、乃以愚,不以止、乃以進(《論語》總章二二五),人欲獲其助者亦匪易而已。又以《學記》所謂“時學必有正業,退居必有游息”(《禮記·學記第十八》)[注]《學記》自是一篇“學習記”,篇中凡三引《說命下》,由此得以略見“學習經”與“學習記”之關系。其引傅說之第二語,作“敬遜務時敏,厥修乃來”,或以傳本之有異也。《大學》乃在乎經與傳或記之間,《大學》多引《詩》,而《學記》多引《書》,經與傳記之相脈絡承傳,亦由此而有可加推想者。言之,“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是“時學必有正業”,“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則是“退居必有游息”;此亦顏子之“學而時習之”也,時學正業則有時而學,退居游息則時時而習。時學則“于吾言無所不說”,故“不違如愚”,見其“回也非助我者也”;退居則德至行備,故謂其“亦足以發”者,豈必“時學”之“時”哉?“發”必于“時習”上發,而不于“時學”上發,則前謂“溫故而知新”若曰“時習而學之”者,“溫故”雖可當“時習”,然“知新”卻似當不得個“學”字,此亦可知也。
博文約禮乃孔門之通教,又非施于顏子一人者。如上節所論夫子教子張以多聞多見,教子貢以一貫,其究無非博文約禮,惟其材之異,或有干祿之卑下,或有多聞之流濫,教之之法因以異,至于趣向則不殊,故終能成其為“見危致命,見得思義”(《論語》總章四七一)、執德弘而信道篤(《論語》總章四七二),以及得與聞乎“夫子之言性與天道”(《論語》總章一○四)、得企望乎“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論語》總章一○三)與“博施于民而能濟眾”(《論語》總章一四七)者也。要之,四科十哲皆由文學入,即其始皆受“博學于文”之教。文學者,古訓是也;然后見諸行,為言語、為政事;然后成之功,乃為德行。由乎“博學于文”者,皆加“約之以禮”之功,言語、政事亦非不約也,而惟德行之成,約禮之功臻于極盡;其有不“約之以禮”者,非夫子所謂“博學于文”者也。周子曰:“圣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注]周敦頤:《周敦頤集》,中華書局,2009年,第40頁。入乎耳不能存乎心,存乎心不能蘊為德行,蘊乎德行不能發為事業,不但文辭之陋,亦功利之陋,人一有此,則不足以立乎孔子之門矣。
如曾子亦同受博文約禮之教,而“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注]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1983年,第48頁。。曾子先從“約之以禮”上得力,工夫常在“吾日三省吾身”(《論語》總章四),于其中養得個忠信之理分明牢固,與孟施舍雖有“守氣”、“守約”之不同,然“孟施舍似曾子”,曾子亦似孟施舍,非有他故,則或僅能勇過孟施舍、北宮黝,而更先于告子之不動心而已矣(《孟子》總章二五)。故夫子教以“吾道一以貫之”(《論語》總章八一),此與教子貢“予一以貫之”者不同:子貢多聞而識,一貫以約之;曾子“吾日三省吾身”,一貫以開廣之。故對子貢,“一以貫之”,“一”是重字;對曾子,“一以貫之”,“貫”是重字。“一”是重字,一貫以收拾其零散;“貫”是重字,一貫以救濟其偏枯也。曾子一“唯”而覺,對以“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乃其本事,即“為人謀而不忠乎”之“忠”,聞教之下,乃知有“恕”之一段新鮮事,故以“恕”為重,“一以貫之”則“忠以恕之”,則雖三省以養忠,然若不能恕而及物,忠終難成。一分忠有所不得力,固是一分恕有所不能及;然亦惟恕到十分,則俯仰無愧怍、所反無不縮,十分之忠,不待勉強而何有于我哉?想曾子為人言“吾嘗聞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之時,亦何嘗不自慊于守約養勇去此“自反而縮”之大勇既在乎未達一間,然又“雖欲從之,末由也已”?遽料要害所在,乃不但在于忠,更且在于恕;不但要與人較“不動心”孰為早到,且要隨其分之宜而隨時發為“動心忍性”之“動心”也。曾子與顏子,“擇乎中庸”則一,惟是中庸之“不可能”(《中庸》章九),皆須盡其“可能”而至。
子思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中庸》章二○)[注]此語,通行本亦屬之“子曰”。朱子章句此章,較以《孔子家語》,而曰:“‘博學之’以下,《家語》無之,意彼有闕文,抑此或子思所補也與?”則亦未必不以為子思語也。朱子章句曰:“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為知,學而知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為仁,利而行也。”蓋將此專置于學知利行一端,與生知安行、困知勉行對照而言之也。“學而時習之”、“博學于文,約之以禮”等限以學知利行方面固非不可,然以夫子此兩語衡之,“博學之”固“學”、固“博學于文”也,“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在前所謂學與思之間則可當個“思”字,在學與習之間卻已當不得個“習”字。而朱子更廣“學”字之義,謂此皆學以知之之事;又引程子“五者廢其一,非學也”之語,“篤行之”本為行之事,乃以“學”兼“行”義,“學”之義愈廣。然則子思此語所言者學,于其中,“思”字固得以特精其義,卻終似漏落個“習”字,尤其欠說“約之以禮”一節事。
至于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孟子》總章一○四)“詳說之”乃括子思“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而為言,亦不當個“習”字。[注]據楊伯峻《論語詞典》 《孟子詞典》,“習”字《論語》三見、《孟子》僅一見,此與“習”字之義理地位頗不相當。適成對照者,“學”字《論語》六十四見、《孟子》三十見。參見楊伯峻:《論語譯注》,中華書局,1980年;楊伯峻:《孟子譯注》,中華書局,2010年。孟子此語卻說到“約”字,然朱子注此章曰:“言所以博學于文而詳說其理者,非欲以夸多而斗靡也,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學非欲其徒博,而亦不可以徑約也。”“說約”乃是“說到至約之地”,則第一,此“說約”之義似又為“詳說之”所兼;第二,若以此為“約之以禮”之事,約禮之事只在博學詳說中做,與夫子之所教、顏子之所領會若彼之相對相當、均衡周全而約禮亦實自有其事者,乃若有所不吻也。
大概自顏子而下,諸子于夫子博文約禮之教各下證驗,雖皆能有所發明繼承,然說得來疏密徐疾各有偏重,亦見體會之不必盡同也。韓文公所謂“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遍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注]韓愈:《韓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92頁。,其間幾分歸性情、幾分屬學力,尚待細論,惟若以為夫子之道竟爾可使諸弟子引而各自助長其性情之偏,則失其旨遠矣。韓文公本意,乃欲言夫子身后儒家學問“原遠而末益分”之況;然若謂門弟子各以其天資稟賦之所擅長,以就夫子廣大溥博之學,如有好勇過我、好讓過我、好言過我之類,使夫子各加取裁而無不歸于正,則有以見夫子之道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此則可矣。又,錢穆先生有謂“孔門晚年文勝之風”[注]錢穆:《論語新解》,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第277頁。,似又未盡然。蓋孔門早年,非不以文學教;顏、曾早晚高弟,不但絕無文勝之弊,且曾子尤趨于質。子思、孟子固稍遜于言“習”,而欲涵“約之以禮”于“博學于文”中,然此皆非所謂“文勝”。惟詳其由,雖得曾子傳學,或不無親炙與私淑不同之故也。而孔門晚年之中,如子夏既以“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論語》總章四七五)為好學,又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論語》總章四七六),“切問”、“近思”適以當“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詳說之”者,則子思、孟子亦非不有所源自,然其志篤、其問切、其思近,此皆約之之功,既曰“仁在其中矣”,而謂之“文勝”哉?
周子曰:“學顏子之所學。”(《通書·志學第十》)揚子云亦曰:“睎驥之馬,亦驥之乘也;睎顏之人,亦顏之徒也。”[注]汪榮寶:《法言義疏》,中華書局,1987年,第28頁。此段以下所引,分別出自第28頁、第13頁、第15頁、第9頁。然非學顏子之學,學顏子之所學。而“顏嘗睎夫子矣”、“顏淵,習孔子者也”,顏子終得以為顏子,亦“孔子鑄顏淵矣”;七十子之徒蓋莫不與顏子同一其志,故“七十子之肖仲尼也”。孔門諸子典型在瞻,不但向夫子學古訓、學藝業、學德行,亦向夫子學習“學習”。則前謂《說命下》乃一篇“學習經”也者,在孔門,則夫子一身當之,不煩更求之遠;在儒家后學,則亦得以《論語》一書為新出之“學習經”,而以此底定根基也。于此可見經典嬗遞或轉移之一斑。[注]三月廿六日,楊儒賓教授來講《紂王與文王:三千年前的一場精神革命》,其間論及《尚書·酒誥》,曰:“《酒誥》是禁酒令的代表作,義正辭嚴,理據充足……(周初先王)在改革社會風氣方面,最醒目的改革是當時嚴令禁酒,集體酗酒所受的懲罰更為嚴酷。”當時,有知情者以目目我,無牙而笑。稍后得間,我乃從容言曰:“《酒誥》固是一篇‘酒經’,然我之‘酒經’,卻只用‘惟酒無量,不及亂’一句。”此語戲出,然似亦可為經典轉移之一例,故記之于此。楊教授固非惟以《酒誥》為“酒經”也,故其又以《尚書·微子》 《詩經·大雅·蕩》等篇相支持,而其中又有如《詩經·小雅·賓之初筵》所詠“飲酒孔嘉,維其令儀”,乃至“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仙仙”,醉亦不亂者。惟既有《論語》,凡此似皆得以稍隱替之而已。惟是后學典型又遠,征引須多,于是雖七十子皆身通六藝,而《中庸》 《孟子》說向《詩》 《書》處反而較多,亦不得已也。
《莊子·德充符》有寓言曰: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子之于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為?彼且蘄以諔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己桎梏邪?”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可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注]郭慶藩:《莊子集釋》,中華書局,2004年,第202-205頁。
此雖寓言,然以“務學”、“賓賓以學子為”,以及“一條”、“一貫”之所謂條貫者言,猶未失孔門風教之真。惟謂“蘄以諔詭幻怪之名聞”,則不知者言也。又謂賓賓學習之事為“天刑”,其固不知儒者適以學習之事為“天賞”;倘或果有“天刑”如此,則必甘受之者為儒,而逃者失其為儒矣。以此知彼以“學而時習之”為“不亦苦乎”者,未必不出此“天刑”之言也。儒者必不然,故荀子有曰:“學也者,固學止之也。惡乎止之?曰:止諸至足。曷謂至足?曰:圣也。圣也者,盡倫者也;王也者,盡制者也。兩盡者,足以為天下極矣。故學者以圣王為師,案以圣王之制為法,法其法,以求其統類,以務象效其人。向是而務,士也;類是而幾,君子也;知之,圣人也。”[注]王先謙:《荀子集解》,中華書局,1988年,第406-407頁。
三、朱子曰
典型又遠,故朱子一面勤勤于《四書》,一面又回向五經,以求前圣、后圣之相印證。《語類》一條論及《說命下》,編者取林夔孫所錄為正文:
……傅說云:“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古訓何消讀他做甚?蓋圣賢說出,道理都在里,必學乎此,而后可以有得。又云:“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斅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自古未有人說“學”字,自傅說說起。他這幾句,水潑不入,便是說得密!若“終始典于學”,則其德不知不覺自進也。
而以黃義剛所錄附后。其實,義剛錄意味尤好:
人如何不博學得!若不博學,說道修身行己,也猛撞做不得。《大學》“誠意”,只是說“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及到說修身處時,已自寬了,到后面也自無甚事。其大本,只是理會致知格物。若是不致知格物,便要誠意正心修身,氣質純底,將來只便成一個無見識底呆人;若是意思高廣底,將來遏不下,便都顛了……六經說“學”字,自傅說方說起來:“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先生至此,諷誦“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曰:“這數句只恁地說,而其曲折意思甚密。便是學時,自不知不覺其德自修。而今不去講學,要修身,身如何地修!”[注]黎靖德:《朱子語類》,中華書局,1994年,第153頁。
諷誦贊嘆,可見玩味之深。此處最須注意者,乃以《大學》與《說命下》相比觀:“學”則以致知格物予以落實,“厥修”、“厥德”、“道積”乃是誠意正心修身之事,惟是“厥德修罔覺”,故自誠意以至于修身處皆說得寬、不甚有事,工夫密處只在于學。
《語類》卷七八數條,亦皆以《大學》說《尚書》:或問讀《尚書》,曰“不如且讀《大學》”;或問致知讀書之序,曰“須先看《大學》”;有以“《尚書》難讀,蓋無許大心胸”之語為問者,則告之曰:“他書卻有次第,且如《大學》,自格物致知以至平天下,有多少節次!《尚書》只合下便大,如《堯典》自‘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至‘黎民於變時雍’,展開是大小大!分命四時成歲,便是心中包一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底天,方見得恁地。若不得一個大底心胸,如何了得!”[注]黎靖德:《朱子語類》,中華書局,1994年,第1982頁。問者以“《尚書》難讀”句屬程子,然此橫渠語也,見《經學理窟·詩書》條一一,其曰:“《尚書》難看,蓋難得胸臆如此之大。只欲解義,則無難也。”(《張載集》,中華書局,1978年,第256頁。《近思錄》亦以此條入之,見卷三條七三)又謂天官、太宰之職等皆須大其心胸方看得,可參見。《尚書》 《大學》所以讀之有先后之序,以《尚書》高明渾化、“合下便大”;于學者,卻有待循一片條理次第“展開”,《大學》即開示此條理次第無所紊矣。
前謂以《書》視《論》,可以釋所疑。此則以《大學》 《四書》視《書》,亦可以證得《書》之地位于不倒。如《說命》之篇,其為“今文無,古文有”,然其既與《四書》義理無一不吻以至于“水潑不入”,雖欲謂之“偽書”,彼作偽者亦何能若是哉?
大概《尚書》今古真偽之爭,與理學關系絕大者有三。一為《大禹謨》之篇,蔣伯潛曰:“李氏(巨來)更指出,偽《大禹謨》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二語,宋儒所崇為道學淵源者,乃出于《荀子·解蔽篇》之引道經,其言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變,惟明君子而后能知之’。《荀子》凡引《詩》 《書》,皆稱‘《詩》云’、‘《書》云’,此獨稱‘道經曰’,則秦火之前,荀子所見之《尚書》并無此語可知。”[注]蔣伯潛:《十三經概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98頁。以《荀子·解蔽篇》引經為例:引“鳳凰秋秋”謂“《詩》曰”,王先謙注曰“逸《詩》也”;引“采采卷耳”謂“《詩》云”,注曰“《周南·卷耳》之篇”;引“墨以為明”謂“《詩》云”,注曰“逸《詩》”;引“明明在下”謂“《詩》曰”,注曰“《大雅·大明》之篇”;又引“知賢之謂明,輔賢之謂能”、“天下有二:非察是,是察非”、“析辭而為察”等,皆謂之“傳曰”,亦皆無注。以此數例而言,首先,《荀子》多引逸《詩》,《詩》既如此,《書》豈不然?其次,其所謂“傳”,往往難知其確指。據此,引“人心之危,道心之微”而謂“道經曰”,既亦不能確知“道經”之所指,反謂其必非指《書》,恐其說亦非密。一為《泰誓》之篇,蔣氏曰:“今存《泰誓》則顯為偽書,與《牧誓》辭氣語意全不相類,且從天地萬物父母遙遠說起,極似魏晉文章發端;數紂之惡,皆以后世暴君之事想象匯集而成……”[注]蔣伯潛:《十三經概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04頁。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惟以今文二十九篇是取,對《大禹謨》 《說命》二篇徑以偽作斥去;而對《泰誓》一篇,處理較為復雜,乃于經傳中輯取散見之句撮合成文,又于《書序》中附其難以連綴成篇者十六條,然此十六條中與其所謂“偽書”相通者頗有之,卻又不肯加以正視。參見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中華書局,2004年。蔣氏有謂:“宋人注書,揣摩語意,實勝漢唐;而其憑主觀以亂事實,則頗與經生態度未合。”(第104頁)朱子評蘇東坡《書解》,亦嘗曰“他看得文勢好”、“文義得處較多”(《朱子語類》卷七八,條四一、條四二),雖文勢好、文義好亦是好,然惟于此等處用心,卻是文人之儒,非是理學之儒,于此固須辨別得下。不足與論乎理學家之志,乃惟以“揣摩語意”視之,然如謂《泰誓》 《牧誓》“辭氣語意全不相類”、“極似魏晉文章發端”之類,譖乎人者,己不有以先中之乎?至如謂“數紂之惡,皆以后世暴君之事想象匯集而成”,楊儒賓教授此來適亦及此,猶不至謂紂惡全出后世想象匯集而無其事實。然則僅憑“揣摩語意”而“憑主觀以亂事實”者亦果有人矣,惟理學家不與焉。而與本文論題直接相關者,則《說命》之篇也。舉凡此等,“偽《古》”之斷幾以為定論。迨自“清華簡”出,其最重要代表性之內容有《傅說之命》,雖迄今所發布相關消息頗相舛歧,如李學勤以為“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三篇簡文(《傅說之命》)的內容與東晉時期出現的偽古文《尚書》的《說命》篇完全不同……它再一次證明,傳世的《偽古文尚書》確系后人偽造……”,廖名春則以為“(傳本)《說命》當是《傅說之命》的縮寫”,陸建初則以為“《傅說之命》實為《尚書》誤傳劣本,但遺諸多類似”、“古簡該文檔大體同于傳本,尤三篇體制同傳本,而可推定古文《尚書》非出偽造”、“《傅說之命》三十余枚,估計有千字,較《說命》多百余字,亦合《孔序》言夫子筆削、剪裁浮辭云”、“傳本《說命》通篇道理宏達、文質相稱,鏘鏘鳳鳴,信如朱熹言及《孔傳》載篇乃三代上廷辭臣所為,蓋正冊自見本色爾”[注]陸建初:《清華簡〈傅說之命〉亟證〈孔傳〉為真本》,《〈尚書〉史詩考》,學林出版社,2010年。其余參見陸氏《清華簡〈傅說之命〉被曲解而正識何在》,以及2013年1月5日“新華網”李學勤訪談等網文。其中,陸氏亦曰:“此事又涉《泰誓》三篇真偽之爭。”,其間是非雖尚紛紜,至少欲以一“偽《古》”之篇定《說命》之性質地位者已難乎一概論,則前所以為幾乎定論者為翻案矣。
朱子謂壁中書皆平易、伏生所傳皆難讀,其所謂易讀者,每及《大禹謨》 《泰誓》,亦一二及于《說命》[注]黎靖德:《朱子語類》,中華書局,1994年,第1978頁,第1979頁,第2039頁,第1981頁,第2036-2038頁。。然于《大禹謨》,則曰“其間大體義理固可推索,但于不可曉處闕之,而意義深遠處自當推究玩索之也”[注]黎靖德:《朱子語類》,中華書局,1994年,第1978頁,第1979頁,第2039頁,第1981頁,第2036-2038頁。;于《說命下》則曰“水潑不入”;于《泰誓》,亦每申發其“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以及“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之義[注]黎靖德:《朱子語類》,中華書局,1994年,第1978頁,第1979頁,第2039頁,第1981頁,第2036-2038頁。。皆不以偽作疑之。故今之論者有曰:“宋人吳棫先言《尚書》古文篇皆易讀,今文篇則難讀。朱熹認可,且又采一說:易讀者出于辭臣編修,難讀者則直錄王言。朱子言其然也,并未因之疑古文(先典征引《尚書》,絕多為易讀句,朱子深知,怎可等‘易’為‘偽’?)”又曰:“宋儒疏經,無論舊派何家,唯義理是衡,實際輒暗合古學,何嘗偽疑《孔傳》?”[注]陸建初:《清華簡〈傅說之命〉亟證〈孔傳〉為真本》,《〈尚書〉史詩考》,學林出版社,2010年。“古學”是否能“唯義理是衡”且不論,以言理學,則足以當之。“唯義理是衡”較之考訂為尤實,然道理一重又一重,可以鉆研無窮、不竭其澤,總有商討之余地,卻不似今學、古學一味依賴地上和地下“事實”之發現而已。
或者嘗請朱子著《尚書》之書,朱子答以“焉知后來無人”[注]黎靖德:《朱子語類》,中華書局,1994年,第1978頁,第1979頁,第2039頁,第1981頁,第2036-2038頁。。孰知后來之人唯以《書》之今古真偽為“大問題”,如此,謂之于六經之中倒了《尚書》亦可,此豈在先賢所可料哉!惟朱門之中,則無惑于此今古真偽之問題矣。《語類》論《說命下》諸條,朱子之所見,并皆為蔡九峰采入《書傳》。如,《書》“臺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遁于荒野”句,東坡創為“甘盤遁于荒野”之說,《語類》卷七九條一一駁之,以《無逸》證殷高宗遁于荒野,而以“臺小子”之語脈推為高宗自言,此說《書傳》用之;又如,《書》“惟斅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句,《語類》卷七九條一三謂自學為學、教人亦學,而指葛氏、俞子才及某士子等以“我教你者,只是一半事,那一半,要你自去行取”解此者有新巧之病,“全似禪語”(條一六作“教只斅得一半,學只學得一半,那一半,教人自理會”,且謂呂東萊亦主此說),此說《書傳》亦用之。[注]黎靖德:《朱子語類》,中華書局,1994年,第1978頁,第1979頁,第2039頁,第1981頁,第2036-2038頁。皆一一詳推其義理,而一毫不格于今古矣;而朱子、九峰師弟于《書傳》之作,其傳習授受之實,亦由此可見一斑。朱子既手著《書說》 《書傳》不成,因九峰“《尚書》文義通貫猶是第二義,直須見得二帝三王之心,而通其所可通,毋強通其所難通”一語[注]《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三《答蔡仲默》之六,《朱子全書》第二十五冊,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717頁。而知其可相托付,遂將所思所作盡行付之,命以著述之事,九峰“先生文公令沈作《書集傳》……《集傳》本先生所命”皆據實言之,其謂“微辭奧旨,多述舊聞”既非出謙辭,至其“凡引用師說,不復識別”[注]蔡沈:《書集傳》,錢宗武、錢忠弼整理,鳳凰出版社,2010年,序第1頁、第2頁,第114頁。者,循此亦皆略可識而別之矣。
惟于此所引關乎新巧學風者,似尚不能無說。蓋于“斅學半”,若僅謂學是學之半、教亦是學之半,則似惟偏主于學,空卻“斅”字。故前文嘗試解作學是教之半、教亦是學之半,教固非可廢之事,則寓教于學,亦寓學于教,此猶“學而優則仕”而亦“仕而優則學”,以為若此乃可以無所偏廢而兩相成就也。其于朱子所辟“我教你者,只是一半事,那一半,要你自去行取”或“教只斅得一半,學只學得一半,那一半,教人自理會”之見固自有異,然以朱子“全似禪語”之斷甚重,不能不深自警切。《書傳》亦曰:“或曰:受教亦曰斅,斅于為學之道半之,半須自得。此說極為新巧,但古人論學語皆平正的實,此章句數非一,不應中間一語獨爾巧險。此蓋后世釋教機權,而誤以為論圣賢之學也。”[注]蔡沈:《書集傳》,錢宗武、錢忠弼整理,鳳凰出版社,2010年,序第1頁、第2頁,第114頁。去新巧而就平實、辟邪守正,此固儒家學者本分之所在,前解倘有犯之,在所可凜可懼!惟以涉入新巧為戒,亦得無過苛煩,苛則失其正矣。“不憤不啟,不悱不發”、“引而不發,躍如也”,自是儒門正大之教,以言憤悱者乃為學之半、啟發躍如者乃為教之半,不亦可乎?如邵康節從學于師之時,每曰:“愿先生微開其端,毋竟其說。”此即“教一半”之意,朱子乃稱其善學,而欲學者似之[注]黎靖德:《朱子語類》,中華書局,1994年,第2542頁,第2037頁。,不以為新巧、機權之忌也。
又于“惟學遜志”之解,亦稍獻一疑。朱子曰:“遜志者,遜順其志,捺下這志入那事中,子細低心下意與它理會;若高氣不伏,以為無緊要,不能入細理會得,則其修亦不來矣。”又曰:“‘遜志’,則無所墜落。志不低,則必有漏落在下面。”[注]黎靖德:《朱子語類》,中華書局,1994年,第2542頁,第2037頁。以“遜志”為“遜順其志”,固無所可議;然謂須先“捺下這志”,而后方得“入那事中”,亦即入那學之事中,卻似將“惟學遜志”讀向“惟遜志乃學”去。《書傳》曰“遜,謙抑也……遜其志,如有所不能”,乃以“虛以受人”解此句[注]蔡沈:《書集傳》,錢宗武、錢忠弼整理,鳳凰出版社,2010年,第113頁。,雖未盡取師說,然先“虛”后“受”,亦大段無改。然更詳此語意,“惟學”,只一味從事于學;“遜志”,其志乃遜。則似當曰:“惟學遜志”,惟學乃為正當事,欲遜其志者,一惟在于學中,不在于學之先,尤不在于學之外。人甫從事于學古訓,見得事事不如古人,其志自遜;學之既久,深造而自得,其志乃能無所不順乎理,順乎理,其為遜志之至乎?學至于遜志務時敏,其修不來自來,斯乃真可以為弗畔也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