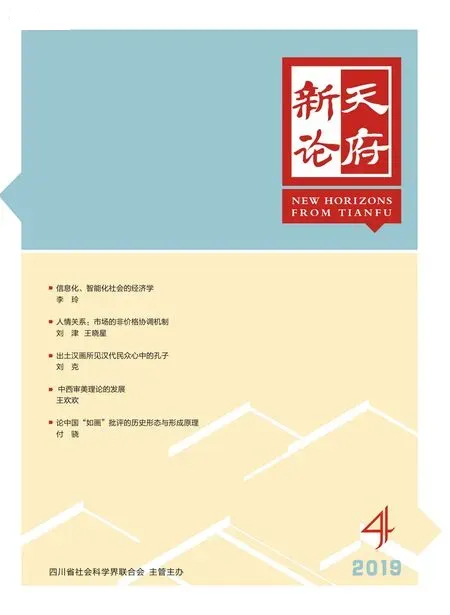美好生活的五個實現條件
王 濤
中共十九大報告對新時代人民的利益做了新的表述,即用美好生活需要來替換物質文化需要,并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確立為黨執政興國的奮斗目標。什么是美好生活(the good life)?這是一個非常古老的話題。在亞里士多德看來,人的善就是人的靈魂合乎(尤其是那種最好、最完全的)德性的生活。[注]亞里士多德:《尼各馬可倫理學》,廖申白譯,商務印書館,2010年,第20頁。人最優越的地方在于靈魂,人向往的美好生活或者說追求的幸福就是靈魂符合德性的活動。德性(靈魂的善)無待于外、自足于內,所帶來的幸福是最為穩定而持久的。盡管古希臘哲人對何謂美好生活存在爭議,但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哲學家都承認,美好生活有著恒定不移的特性,不會隨著時間變遷和空間變換而改變。然而,現代社會是多元化的社會,關于什么是美好生活,不同的人通常會得出不同的答案。現代人相信,在這個問題上無法通過求助某種哲學理論來取得共識。關于美好生活,正如羅爾斯所言,人們能夠確定的事實僅僅是每一個人都有“形成、修正和合理追求一種善觀念的道德能力”[注]約翰·羅爾斯:《政治自由主義》,萬俊人譯,譯林出版社,2011年,第27頁。。善的觀念就是美好生活的觀念。從具備掌握一種善的觀念的道德能力這個方面來看,人不同于只會被動地屈從于內心自然欲望的動物,人是自由的,能夠自己選擇自己向往的生活。作為由自由的人結成的合作體系,現代社會往往鼓勵每一個社會成員自主地追求自己向往的美好生活,而政府的職責則是為這種追求提供基本的物質保障與公平的機會。總之,美好生活的實現離不開每一個人的拼搏和奮斗,它是人們在實現對美好生活向往的不懈努力中創造出來的。在這個過程中,對發展中的中國而言,以下五個方面的條件是不可或缺的。
一、堅強有力的政黨領導
人類的美好生活只有在群體生活中才能得以實現,即便是離群索居的個人,也無法與群體完全隔離。確保群體秩序的安定,保障個人的人身安全,便構成了美好生活的首要前提。人類社會發展體現人多元的價值訴求,諸如秩序、正義、平等、自由等,實現了這些價值的社會,才能稱作美好社會。人在這個世界上生存,所追求的并不是單純要活著,還要活得好。通常,上述這些價值就是我們評判生活好與不好的標準。在人所珍視的各項價值中,秩序又是實現其他價值的先決條件。“如果某個公民不論在自己家中還是家庭以外,都無法相信自己是安全的、可以不受他人的攻擊和傷害,那么,對他侈談什么公平、自由,都是毫無意義的。”[注]彼得·斯坦,約翰·香德:《西方社會的法律價值》,王獻平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05年,第47頁。可見,人類群體生活可以有秩序而不那么美好,卻絕不可能美好而無秩序,因為無秩序的美好生活在邏輯上自相矛盾,在現實中根本就不存在。17世紀的英國政治思想家托馬斯·霍布斯,設想了一種恐怖的前(政治)社會狀態,在那里,人類群體生活的秩序得不到維系,個人的人身安全得不到維護。他所描述的自然狀態,是一種“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狀態。“在這種狀況下,產業是無法存在的,因為其成果不穩定。這樣一來,舉凡土地的栽培、航海、外洋進口商品的運用、舒適的建筑、移動與卸除須費巨大力量的物體的工具、地貌的知識、時間的記載、文藝、文學、社會等都將不存在。最糟糕的是人們不斷處于暴力死亡的恐懼和危險中,人的生活孤獨、貧困、卑污、殘忍而短壽。”[注]霍布斯:《利維坦》,黎思復、黎廷弼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94-95頁。在霍布斯式的自然狀態下,文明在沒有積累之前就已經毀壞了,人人隨時隨地都處于他人的暴力威脅之下,根本無暇去向往和想象、追求和創造美好生活。
近代早期以來,隨著資本主義和現代國家在西方的崛起,世界越來越聯結為一個關系緊密的整體,并演化為資本擴張和國家競技的舞臺。由于現代世界政治經濟體系是激烈競爭的結果,它的結構更加等級森嚴。最后,世界上各類政治實體無不被納入這一體系,從中心到邊緣依次排列。一個國家在發展的時間序列上越靠后,它的現代化條件越不利,就越有可能滑向世界等級體系的末端。如果一個落后大國想要提升自己的國際地位,改變身處邊緣的被動局面,就應該積極創造條件,通過模仿中心國家來推進自身的現代化。但是,后發現代化國家擁有的條件往往非常不利,阻礙發展的守舊勢力也通常比較強大,在推動現代化時,面臨的內外環境異常苛刻。比如,20世紀爆發社會主義革命的俄國和中國,不但內部的守舊勢力十分強大,而且外部的列強也蠢蠢欲動,隨時準備干預和圍剿。因此,一個國家越是后發展,就越不能夠脫離堅強有力的領導核心,只有這樣才能集中有限的資源來應對各種內外挑戰。歷史已經證明,相對于其他的政治主體,無產階級政黨能夠成為維護社會政治秩序、領導后發國家現代化的更加有效的權威。一方面,黨的綱領為社會發展指明了方向,成為凝聚廣大人民群眾、聯合各革命階級共同奮斗的一面旗幟;另一方面,黨的組織體系為贏得各方面的支持、推動政策的執行提供了權力機構和運作機制,成為讓政治制度和國家領導的工業建設運轉起來的關鍵動力。辛亥革命推翻了兩千余年的封建帝制,但殘酷的現實令中國的有識之士認識到,革命后秩序的實現有賴于具有高度動員和組織能力的政黨。20世紀上半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結束了清末以來的長期戰亂,建立了穩固的政治制度(尤其是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實現了中國的安定與團結。1949年新中國的建立,標志著中國現代化進入新的階段。改革開放前,中國現代化的重點是工業化尤其是重工業的建設。新中國的工業建設是在一窮二白的條件下起步的。工業化需要投資,但資金從哪里來?工業化的資金來源不外乎外援、外資、外債、外貿和提取農業剩余五種渠道。建政初期我國采取了“一邊倒”的外交戰略,從社會主義國家陣營尤其是蘇聯獲得了一定的外部資金,但后來又逐漸放棄了這一戰略。中國農村本來人多地少,加上經歷了長期戰亂,建政初期幾乎沒有農業剩余可供提取。正是在黨的領導下,依靠黨組織強大的動員能力,借助國家政權的力量,中國農村和城市的人口都被組織起來,農民和工人的剩余勞動為新中國工業化的起飛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經濟進入騰飛階段,現代化進程持續加速。中國經濟實現了由計劃到市場的轉型,中國的社會結構更加優化,社會主義制度日趨完備,國家實力顯著增強,而這一切都是黨運用國家政權的力量領導改革和現代化的結果。如果沒有黨堅強有力的領導,中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會失去靈魂、失去主心骨,永遠無法實現了。
二、社會合作體系
中國社會的進步不僅體現在社會結構優化上,還體現在人的素質提升方面。現代化的最終目的還是人的進步。人有理性,人憑這一點能夠判定自己有自由。所以說自由是一個理性事實,而不是一個經驗事實。“自由是我們先天地知道其可能性卻仍然不理解的唯一理念,因為它是我們所知道的道德法則的條件。”[注]康德:《實踐理性批判》,韓水法譯,商務印書館,2001年,第3頁。人有理性,即有自由,所以能夠對自己下命令,要求自己做正確的事。但評價一個人是不是好人,可能還須蓋棺才能夠定論。因為按照康德的看法,激勵人一生持續做好事的兩大“懸設”,也就是“靈魂不朽”和“上帝”,作為純粹理性的單純實踐應用的條件,其可能性既無法被人先天地確定,又絕非人可以理解。但在道德實踐中,一個人可能會對這兩個“懸設”產生疑惑。如果靈魂離開肉體就會湮滅,還有什么比肉體上的享樂更富有意義?如果經常見到壞人春風得意,好人卻沒有好報,為什么不去多干壞事?人若既不確定靈魂是否不朽,又懷疑上帝能否給予絕對公正的裁判,他就非但不能夠持續地做好事,反而可能會隨波逐流,縱情聲色享樂,甚至干起壞事來了。但不管什么時候,自由的人的內心總不至于甘愿把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奉為社會行動的金科玉律。這樣的自由人愿意用自己的理性能夠同意、認可和支持的原則來調節他們的社會關系,并把自己參加的社會當成“自由的人的合作體系”。“自由的人的合作體系”具有兩個方面的含義。首先,個人總是社會中的個人,無論是個人的生存和發展,還是個人自由的實現,都離不開各種類型的社會團體以及由不同社會主體所構成的整個社會。其次,組成社會的人是自由的和平等的,視彼此為合作伙伴,由于命運緊密關聯,在他們中間能夠產生出一種愿意相互分擔不幸、關照弱勢者(主要指在社會合作中遇到自己無法克服的阻力而陷入困境的人)的正義感。
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表達了人類合作體系的最高形式——“自由的人的聯合體”。“當階級差別在發展進程中已經消失而全部生產集中在聯合起來的個人的手中的時候,公共權力就失去政治性質”,“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注]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9-50頁。不過,在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帶領人民不斷奮斗,實現共產主義的遠大目標和最高理想、最高目標之前,即便是在廢除了奴役性分工和經濟剝削的社會主義社會,也總還是存在一些少數的、局部的人民內部的利益矛盾,社會關系還需要正義的協調才能達到和諧的狀態。那么,正義何以可能呢?正義的社會基礎是把全體社會成員連接成命運共同體的那種堅韌紐帶。正義不能建立在社會中一部分善良人士的憐憫之上,更不能建立在少數富人的施舍之上。一個社會若沒有一種命運休戚與共的覺悟、一種普遍的尊重人的道德情操,它的社會成員若缺乏對弱勢者的同情、同甘共苦和分擔厄運的意愿,正義也是不可能的。毫無疑問,在生產力還不夠發達、社會還沒有發展到能夠根除一切利益沖突的階段,正義對優良社會秩序的實現而言是至關重要的。正如古希臘人所強調的那樣,人不能離開社會而獨善其身,個人的幸福和善只有在社會正義得以充分實現的情況下才是可能的。一個無法避免利益沖突的社會若是缺少了正義,人民的幸福和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會淪為泡影。中國社會正義的實現同樣離不開黨的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注]中共中央宣傳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三十講》,學習出版社,2018年,第74頁。中國共產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政黨,始終把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不斷增強人民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執政興國的立足點。我們可以說,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無產階級政黨是實現正義和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的組織保障,而正義則是黨帶領人民創造美好生活的社會條件。
三、自由與民主權利
正義是人類社會生產力有了一定發展,但集體財富的一切源泉尚不能充分涌流的時代(這一時代涵蓋了所有類型的階級社會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產物。正義與物品(goods)的分配有關,滿足人們各種需要的物品只能在人類群體生活的組織中才能創造出來,所以正義總是與某種社會團體形式結合在一起的。傳統社會的生產社會化程度和社會交往水平發展有限。中國傳統社會私人領域家族化,社會關系實際上就是家族關系的投射,只有社會性,缺乏公共性,公共領域高度缺失;古代希臘城邦公民的私人交往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政治生活的延伸,社會與國家沒有完全分離。工業革命以后產生的現代社會與傳統社會有著根本性的區別。圍繞物質生產活動而展開的社會交往,形成了具有有限的公共性、相對獨立于國家的新型的社會私人領域。在這個領域中,人的個性發展受到推崇,個人的自由得到提倡。社會主義社會是在現代工業社會的基礎之上發展起來的,它倡導的集體主義精神,是對自私自利的資產階級孜孜于私人的狹隘利益和排他性的個人權利的超越。但是馬克思主義同樣高度強調人的自由。“馬克思主義的最高命題或根本命題,就是‘一切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注]閆健:《民主是個好東西——俞可平訪談錄》,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第5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也認為,自由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組成部分。“在當代中國,我們的民族、我們的國家應該堅守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就是黨的十八大提出要倡導的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把涉及國家、社會、公民三個層面的價值要求融為一體,深入回答了我們要建設什么樣的國家、建設什么樣的社會、培養什么樣的公民的重大問題。”[注]中共中央宣傳部:《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讀本》,學習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89-190頁。自由與其他的核心價值一道支撐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大廈。與上層建筑的其他部分相比,價值觀是更加柔軟的力量,但是從長遠看卻要比剛性的法律和其他制度規范更加堅韌。因為一旦在人的內心埋下信念的種子,它們就會生根發芽,并在社會主義的土壤中茁壯成長為能夠托起和諧社會以及更高社會理想的參天大樹。
自由的人的合作體系的出現意味著社會成員的主體意識已經普遍覺醒,每一位社會合作的參與者都是自由的和平等的。平等主要是指具有相同道德人格的自由人的平等。在現代社會,平等主要表現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及保障人的生存和發展的各項社會權利要求的平等。具有相同道德人格的人同時也是自由的。在法治社會中,人的自由表現為人的權利(right)。所謂權利,就是法律規定的自由。當人類物質生產發展到社會化大生產階段,在人的生存需要能夠得到確定無疑的保障之后,自由權(liberties)就成為了體現和維護人的自由和尊嚴的首要的和基礎的權利。自由權往往通過法律明確規定的公民權利予以確認,所以法律并不限制自由,反而是實現自由的條件。對于體現和維護人的自由和尊嚴而言,自由權的重要價值是顯而易見的。但是對于不同的人來說,它們的價值大小是有區別的,比如與一般人相比,遷徙自由權對跑長途運輸的卡車司機就具有更大的價值;又如思想和言論、選舉等民主權利,對富人和窮人而言也具有不同的價值。在所有公民權利中,尤其需要確保民主權利的價值對于所有公民都是公平的。因為民主既能夠實現社會平等和正義,又能夠保障基本自由權和其他社會權利。而且,感覺自己沒有被排斥在外,確信自己有能力影響政治生活,體驗履行社會義務或公共職責而產生的自我實現感,本身也是一種重要形式的人類善。如果經濟上處于劣勢的公民,在政治參與比如說投票的時候得不到有力的保障,那他眼中的民主權利的價值就要大打折扣了。資產階級民主的虛偽性就在于,它僅僅從形式上賦予人民平等的政治參與權,但是卻刻意掩蓋經濟地位的不平等對民主權利真實價值的影響。受壓迫的工人,不僅在經濟上要服從資本家的統治,而且在政治上同樣要服從資本家的統治。如果他們想要解放自身,就得先取得政治上的統治權。因為若非如此,在選舉中反對資本家提出的候選人,工人首先就得付出被解雇的經濟代價。
四、基本的生活保障
為什么社會中的一部分人貧窮,而另一部分人富裕呢?傳統的觀點認為,一部分人之所以富裕,是因為對社會財富的創造做出了更大的貢獻;一部分人之所以貧窮,則是因為個人的懶惰、不良心態或壞習慣、無能。也就是說,貧富皆可以歸因于個人的責任。但是,大量的理論研究和實證調查卻表明,在工業化的現代社會中,貧窮主要不是由于個人的惡習和無能等個人原因導致的。在大多數情況下,貧窮是由不平等和不公平的社會環境造成的。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工人之所以貧窮,從表面上看是因為他們缺乏勞動技能和進取心,但主要是因為具有壓迫性的、不平等和不公平的社會環境使然。有些人從一出生就面臨資源極其匱乏的生存環境,而且社會也沒有為他們提供參與公平競爭的機會和條件,以至于無法通過個人努力改變命運,而只能接受別人的經濟奴役。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描述了工業革命時期英國工人惡劣的生存環境、貧困潦倒的生活狀態、在死亡線上掙扎的慘景,他正確地指出導致工人苦難的主要原因是資本家的剝削,是資本主義的剝削制度。馬克思深入研究了資本運動的規律,揭示出資本家剝削工人剩余勞動和剩余價值的秘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都沒有把工業社會中受剝削階級的種種不幸僅僅歸因于個人,而主要是從資本主義的社會環境和制度中尋找根本的原因。資本主義國家中的一些有識之士也意識到了這一點,試圖依靠政權的力量推進可以接受的社會改良來更好地維護資產階級的整體利益。無論是1601年英國的《伊麗莎白濟貧法》,還是1883年德國俾斯麥政府的《疾病保險法》,都是統治階級緩和階級沖突、防止貧民社會動亂的措施和手段。在意識形態方面,從19世紀中后期開始,發源于西方工業社會的進步主義倫理觀念,強調社會是一個有機體,對人性總體上持樂觀的態度。通過強調社會的各個組成部分相互關聯——組成一個合作體系——的事實,試圖激發起社會主體分擔彼此命運的意愿。這樣的社會有機體也構成了現代意義上的“分配正義”的基礎。“現代意義上的‘分配正義’,要求國家保證財產在全社會分配,以便讓每一個人都得到一定的物質手段。分配正義的辯論往往集中在可以保證的手段的數量,以及保證這些手段的分配得到執行所需要的國家干預程度。”[注]塞繆爾·弗萊施哈克爾:《分配正義簡史》,吳萬偉譯,鳳凰出版集團、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5頁。
近代以來,生存作為人的一種最基本的權利的觀念逐漸深入人心。最初,這種權利主要針對的是那些尚不具備或者喪失勞動能力的人,如兒童、懷孕的婦女、殘疾人和老人,而有能力工作的人則被排斥在外。隨著工業革命的開展,社會財富的豐裕以及社會觀念的進步,基本的生存權利最終覆蓋了國家中的所有居民。現代正義包含著這樣的要求,即不考慮一個人工作與否,僅僅因為是人就讓他有權獲得維持生存所需的物質保障。人們在失業或者未就業時有權得到政府發放的補助,窮人家的父母在無法為孩子提供食物、衣服和住所時,這些家庭的孩子應該得到國家的救濟,乃至獲得免費的教育和健康保健。1941年,時任美國總統的富蘭克林·羅斯福在致國會的咨文中提出了著名的“四項人類基本自由”(four essential human freedoms),分別是發表言論和表達意見的自由、選擇自己宗教信仰的自由、不虞匱乏的自由、免除恐懼的自由。其中,不虞匱乏的自由(freedom from want)顯然是一種非傳統的新型自由。通過追求經濟上的融洽關系,它力求讓所有國民都過上一種健全的、和平時期該有的生活。在現代世界中,生存權是最基本的人權,為人民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已經成為所有國家都接受的一個不爭的共識。改革開放以來,在中國共產黨的帶領下,中國人民解決了過去幾千年沒有解決的溫飽問題,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40年間,中國貧困人口由最初的7.7億人降至2018年末的1660萬人,中國扶貧事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效。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一大批惠民舉措紛紛落地實施。“脫貧攻堅戰取得決定性的進展,六千萬貧困人口穩定脫貧,貧困發生率從百分之十點二下降到百分之四以下”,“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基本建立,人民健康和醫療衛生水平大幅提高,保障性住房建設穩步推進”[注]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頁。。人民生活有了保障,獲得感顯著增強。只有在生活有了保障以后,人民才有機會向往更加美好的生活。隨著物質生活水平的不斷提升,人民期望的美好生活的內涵還會變得越來越豐富。所以,基本生活保障僅僅是作為美好生活必要而不充分的條件而存在的。
五、公平的選擇機會
除了基本生活保障以外,人民向往的美好生活最終得以實現,還離不開其他的一些保障,諸如同伴給予的幫助、鼓勵個人選擇的文化氛圍、職位和地位向所有人開放、政府確保的人身安全等。人民不僅應當擁有選擇、確定和追求他們向往的美好生活的權利,而且應當擁有公平的機會去實現他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這就要求,防止過度的社會與經濟的不平等,用有保障的自由權來代替純形式的自由權,以確保自由權對于所有人而言都是有價值的。必須建立和完善如下制度:第一,擔負公民行使民主權利的公共經費和確保他們對有關政策問題公共信息的有效獲取;第二,確定的機會均等,尤其是教育和培訓的機會均等;第三,適當的收入和財富分配,確保公民獲得實現基本自由權所需的高于基本生活保障的其他手段;第四,產生有利于創造新的工作機會的經濟政策或社會政策;第五,覆蓋國家中的所有居民的醫療保障體系。對黨和政府來說,就是要在積極推進經濟的高質量發展,為人民期待的美好生活創造更豐厚的物質基礎的同時,還要尊重人民的主體地位,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持續地改善民生,努力促進社會關系的和諧,鼓勵積極進取、開放包容的社會主義文化。在這個過程中,政府必須實時對社會進行適當的干預,以確保社會各個領域的協調發展和社會整體的良性運行。政治權力對社會各領域的均衡作用的意義何在?邁克爾·沃爾澤認為,平等主義的目標是不受支配的社會。要避免支配的社會,就要防止出現一種“充當或能夠充當支配的手段”的社會物品(social goods)[注]邁克爾·沃爾澤:《正義諸領域:為多元主義與平等一辯》,褚松燕譯,鳳凰出版集團、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年,序言第4頁,序言第5頁。。現代社會普遍接受平等,權利平等是適用于社會各個領域的要求。但正義是具體的,貫穿于人類生活的各個領域。可供分配的社會物品是多樣化的,每個領域都有特定的社會物品,應當遵循不同的分配原則。其實踐的可能性“早已扎根在我們對社會物品共享的認識中了”[注]邁克爾·沃爾澤:《正義諸領域:為多元主義與平等一辯》,褚松燕譯,鳳凰出版集團、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年,序言第4頁,序言第5頁。。商人可以在生意場上通過公平交易追逐金錢利益;知識分子可以在學術圈中發揮聰明才智進行研究創造;運動員可以在體育競技中依靠奮力拼搏贏得桂冠。社會各個領域保持相互獨立,就不會產生某種支配性的社會價值。均衡就意味著社會領域和社會價值的多元化。在不同的社會領域里,人們可以各展所長,各得其所。由于各個領域的價值標準是多元的,一個領域中的失敗者,在其他領域卻可以獲得成功。在非支配的社會中,沒有人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都總是失敗者。
但不得不承認,人類社會存在大量的弱勢群體,比如那些隨意被解雇、被拒絕的低端勞動力,那些生活在社會邊緣不受重視的人群。一些人看起來沒有任何才能,他們對任何領域都不擅長,在任何領域都算得上是失敗者。然而沃爾澤宣稱,他并不相信這些人實際上確實是那樣的人,他認為這種現象的出現恰好是社會均衡遭到破壞的結果。“如果人們在每個領域都失敗了,我們就應該把這看作一種不能把各領域分開并保持它們自治的系統性失敗的一個標志:某種才能或某一組才能,某種善或某一組善,支配著所有其他的才能或善。”[注]邁克爾·沃爾澤:《正義諸領域:為多元主義與平等一辯》,褚松燕譯,鳳凰出版集團、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年,中文版序第2頁。如果能夠打破這種支配的局面,人們也許就會發現,所謂的失敗者在我們意想不到的方面有所擅長并且可以獲得成功。正是這種支配的局面使得人們無法進行有意義的選擇。在一個社會中,如果一種物品占據了支配地位,無論它是權力、金錢,還是血統、神寵,那么,誰擁有了這種物品,誰就會在每個地方都取得成功,但這其實也阻礙了他選擇更有意義的生活;誰不擁有這種物品,誰就會在所有的地方都遭到失敗,他的選擇余地將會更加有限。在社會轉型時期,尤其值得警惕的是資本與政治權力這兩種社會物品。如果不受限制,它們都有可能像藤蔓一樣在社會中肆意生長。前者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說的那樣:“(占有資本的)資產階級在它已經取得統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園詩般的關系都破壞了……它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系,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系了”,“資產階級抹去了一切向來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職業的神圣光環。它把醫生、律師、教士、詩人和學者變成了它出錢招雇的雇傭勞動者”,“資產階級撕下了罩在家庭關系上的溫情脈脈的面紗,把這種關系變成了純粹的金錢關系。”[注]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0頁。政治權力這種物品具有特殊的價值,因為我們需要政治權力來捍衛不同社會領域和社會價值的邊界。但政治權力本身也是擴張性的。在中國漫長的封建專制主義時代,政治權力支配社會的格局一直沒有被打破,這催生了超經濟強制,擠壓了社會公共領域的生長空間,阻礙了中國社會的健康發展。這種格局在維護封建統治階級特殊利益的同時,使得農民長時間地處于被壓迫、被剝削的狀態。在文化觀念上,這種格局還扭曲了社會價值觀,造成了封建官場的腐敗滋生,產生了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意識。不管是資本,還是政治權力,無論哪一種物品取得了絕對支配的地位,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將淪為天方夜譚。
總之,美好生活要得以可能,首先離不開秩序和發展,堅強有力的政黨領導構成了實現美好生活的根本前提。人們在一個正義的社會中才能夠自主地創造美好生活,社會合作體系構成了實現美好生活的社會基礎。在工業化的現代社會中,社會與國家相互分離,自由與民主權利成為實現美好生活的法治要求;物質生產水平極大提高,基本的生活保障成為實現美好生活的社會權利;人際關系趨向疏離,社會分化變得嚴重,財富的影響力四處擴張,權力分配容易失衡,公平的選擇機會成為實現美好生活的重要規范和結構性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