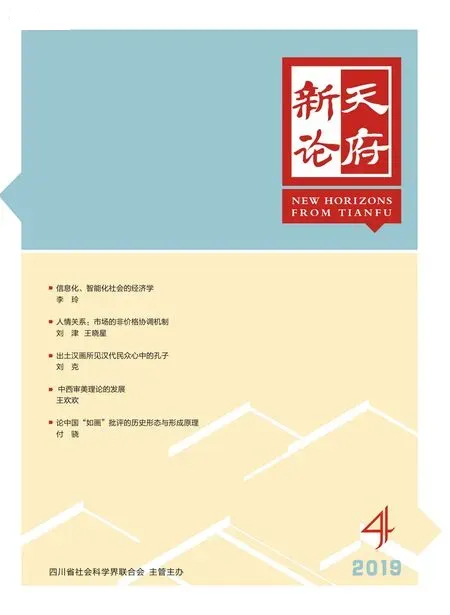中西審美理論的發展
——評楊春時《作為第一哲學的美學:存在、現象與審美》與馬丁·澤爾《顯現美學》
王歡歡
自從美學譯介入中國之后,基于特殊的文化背景和政治背景,相比于哲學中的其他學科,美學研究一直是比較活躍的“部分”。從王國維、朱光潛、宗白華,到狄爾泰、蔡儀、李澤厚、周來祥、蔣孔陽等,從西方美學的翻譯和介紹,到美學理論的創新,從20世紀50年代的美學大討論到20世紀80年代的美學熱,從實踐美學到后實踐美學,無一不顯示了美學研究在中國的活躍度。在大學的學科設置上,從中文系的文藝學專業,哲學的美學專業,到藝術學的藝術學理論專業,它們無不是“寬泛意義上美學”的研究。因而,有學者稱美學研究的重心將會從西方轉到中國。這不是沒有道理的。雖然,新時期以來,伴隨著社會文化生活的巨大改變,純粹美學的研究熱潮已經退去,演化為生態美學、身體美學、文化研究等,以至于有學者認為“我們需要新的美學,這種新的美學,不是回到康德的二元論美學,也不是回到審美無功利和藝術自律。我們承認一種‘雜美學’,容納各種有功利的美,非自律的藝術”[注]高建平:《美學的超越與回歸》,《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1期。。但這并不意味著純粹美學的研究已經偃旗息鼓,也不意味著純粹美學的研究沒有意義。2015年10月,楊春時的《作為第一哲學的美學:存在、現象與審美》在人民出版社出版,隨后,2016年3月,由楊震翻譯的德國當代美學家馬丁·澤爾的《顯現美學》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楊春時的這本著作是其數十年來研究的集大成,而馬丁·澤爾的《顯現美學》是10年前出版的學術著作,其后哲學思想的發展與此書又有很大的關聯。令筆者感興趣的是,《作為第一哲學的美學:存在、現象與審美》的核心思想是建立在對西方現象學的繼承、改造和批判之上的,不過其中又有很強烈的中華傳統美學的印跡,而《顯現美學》的核心思想是建立在西方傳統美學之上,卻又有自己的獨特創新。從二人的美學思想上來看,他們賦予美學很重要的地位,但這種“賦予”又有很大的差異。二人美學思想關注的重點不同,卻又隱含地具有某種相似性。
一、美學的核心:顯現還是存在?
在柏拉圖的美學思想中,存在兩種似乎相反的傾向:一種是對藝術的貶低,認為藝術只是假象,是“實在”的影子的影子,與真理隔著兩層;一種是認為存在美的理念,人應該從認識美的事物開始,逐步升華,直到去感受純粹的美的理念。柏拉圖美學中的這兩種思想深刻影響著后來的西方美學。無論是贊成還是反對,都逃不過柏拉圖的這兩種美學思想。對于馬丁·澤爾而言,他的美學是建立在反對柏拉圖美學思想的基礎之上的。在《顯現美學》這本書的導言中,他明確說:“這本書提議:美學不以‘實際’或‘假象’概念為起始,而是以‘顯現’這個概念為起始。這本書提到的顯現,是所有審美對象共有的一種現實性,盡管它們在其他方面可能各不相同。”[注]馬丁·澤爾:《顯現美學》,楊震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第1頁,第27頁,第36頁,第40頁,第34頁。所謂“實際”美學或者“假象”美學是“審美意識要么充當朝向更高現實的途徑,要么拒絕現實原則——要么同時實現兩種運動”[注]馬丁·澤爾:《顯現美學》(中文版前言),楊震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第1頁,第1頁。。馬丁·澤爾認為這種美學范式使得“審美感知被設想為對生活現象性當下的逃逸”[注]馬丁·澤爾:《顯現美學》(中文版前言),楊震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第1頁,第1頁。。而他的顯現美學卻恰好與此相反,要專注于生活現象性的當下。那么,顯現美學是如何與生活現象性的當下進行聯系呢?他又是如何構筑不同于柏拉圖《實際》或《假象》的顯現美學呢?
馬丁·澤爾說:“將處于顯現中的某物以其顯現為目的來感受——這是所有審美感知的重點。”[注]馬丁·澤爾:《顯現美學》,楊震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第1頁,第27頁,第36頁,第40頁,第34頁。這句話有兩個部分:一是顯現中的某物,二是以其顯現為目的來感受。“顯現中的某物”是包括審美意識在內的一般感性意識都具有的,而“以其顯現為目的來感受”則是審美意識所獨自具有的,或者說,這才是審美意識的本質。“顯現美學之所以得名,其基本區分就在于對‘感性實際’和審美顯現作出區分。二者都是一個對象的經驗現象得到體驗的方式。審美顯現是某物的感性出場方式的一種模式。”[注]馬丁·澤爾:《顯現美學》,楊震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第1頁,第27頁,第36頁,第40頁,第34頁。那么,這樣的一種獨特出場方式或者“以其顯現為目的來感受”是什么意思呢?馬丁·澤爾認為一般意識在接納事物的顯現時,往往從認知性、概念性以及實踐性的確定性角度來思考事物的顯現,并不關注事物的顯現;而審美顯現不同,審美意識超越對于事物的認知性、概念性和實踐性的考慮,僅僅以事物的顯現為目的來進行感知。需要注意的是,審美顯現并不完全“超越”一般概念意識,而是以這種一般概念意識為前提,“審美感知的前提是對概念上確定的某物進行感知的能力。因為只有能感受到某種確定之物的人,才能超越這種確定性,或者更確切地說:超越對這種確定性固定”[注]馬丁·澤爾:《顯現美學》,楊震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第1頁,第27頁,第36頁,第40頁,第34頁。。
其次,這種特殊的感性模式——審美顯現——是通過一種特殊的時間和空間實現的。馬丁·澤爾認為審美顯現之所以不是關于事物的概念性、命題性認識,主要是因為在審美中,人們的感知沉浸于對事物現象的“當下”之中。“審美關系的基本特征,就是我們在其中獲得了目前時間,即使是以完全不同的節奏展開。”[注]馬丁·澤爾:《顯現美學》,楊震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第1頁,第27頁,第36頁,第40頁,第34頁。這種審美的當下—目前—具有兩個內涵:一是同時性,一是瞬時性。同時性是指事物不同方面在事物顯現中共同存在,相互作用,“對對象的單個屬性的把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這些屬性在此地以及此時(通過這種光照,處于視角或者視角的轉換)實現的相互作用”[注]馬丁·澤爾:《顯現美學》,楊震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第43頁,第43頁。。瞬時性是指對事物不同顯象的當下關注,并不指涉過去和未來,而是僅僅沉浸于事物顯現的當下—瞬時之中。兩個內涵共同作用,構成審美感知的當下直觀。另外,需要注意,馬丁·澤爾雖然沒有直接說審美顯現中空間性的重要性,但并不意味著空間在審美顯現中沒有發生作用。他對審美顯現中同時性的界定中其實已經包括了空間考量,比如視角轉換中顯象的變化已經蘊含空間性,“感知對象的這種當下卻也——就像它的顯象全體一樣,在本質上——不是包羅萬象的,而只是通過各自視角變得可感。因為這種感受是通過一種身體位置發生的。只能從特定向度來理解對象(對所有感官活動,情況都是一樣的)”[注]馬丁·澤爾:《顯現美學》,楊震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第43頁,第43頁。。可以說,沒有這種身體—視角的改變,顯現的豐富性或者顯象的游戲就不可能完成。當然,在馬丁·澤爾的思想中,空間性考量是包含于時間性之中的,因為身體視角的轉換最終是通達同時性的。
如果說馬丁·澤爾建立了以顯現為核心的顯現美學,那么,楊春時則建構了以存在為核心的存在論美學。他在《作為第一哲學的美學:存在、現象與審美》的后記中寫道:“確認了存在為哲學本體論范疇,也是美學的本體論范疇,從而真正地建立起存在論美學。”[注]楊春時:《作為第一哲學的美學:存在、現象與審美》,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512頁,第83頁,第95頁,第110頁,第206頁。那么,楊春時是如何確立存在,又是如何基于此建立存在論美學呢。首先,他認為存在是哲學的邏輯起點,是最抽象的、最一般的概念,是一種絕對,不能被經驗所把握。因而,要想把握存在,就必須通過特殊的體驗方式。這種特殊的體驗方式是什么呢?在此,他改造了胡塞爾的現象學,提出了缺席體現象學。他認為胡塞爾的現象學并不具有合理性,存在者的本質并不能在先驗純粹意識中得到把握,但現象學的本質直觀方法可以被用來改造以把握存在,“現象學并不是關于存在者本質的科學,而是關于存在意義顯現的哲學方法論”[注]楊春時:《作為第一哲學的美學:存在、現象與審美》,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512頁,第83頁,第95頁,第110頁,第206頁。。這種論述明顯受到海德格爾的影響,因為海德格爾認為現象學不是探索意識,而是探索存在。“現象學的現象概念意指這樣的顯現者:存在者的存在和這種存在的意義、變式和衍化物。”[注]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陳嘉映、王慶節合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年,第42頁。楊春時認為生存中的一些極端體驗,如痛苦、焦慮、虛無,使得我們隱約感受到存在的召喚。“缺失體驗使不在場的存在獲得了一種被給予性, 從而成為一種現象。”“在缺失體驗中,存在雖然沒有在場,但卻被暗示著、呼喚著,我們也能感受到它的呼聲和召喚。”[注]楊春時:《作為第一哲學的美學:存在、現象與審美》,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512頁,第83頁,第95頁,第110頁,第206頁。可以說,通過缺席體驗,我們推定了存在,使其不再是一種虛無。
其次,通過缺席體驗推斷了存在之后,楊春時又以此演繹了存在論美學。他認為存在具有兩個規定:一是本真性,二是同一性。存在的本真性是指存在超越現實生存,是生存的根據,現實生存是非本真的存在。存在的同一性是指我與世界的共在,“我與世界的共在,不是我與世界的分立,也不是我支配世界或世界支配我,而是我與世界同一”[注]楊春時:《作為第一哲學的美學:存在、現象與審美》,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512頁,第83頁,第95頁,第110頁,第206頁。。存在既然是生存的根據,而現實生存乃是非本真的存在,那么生存就要回歸存在,回到存在的本真性和同一性。這種返回的途徑就是審美,或者說審美體驗。楊春時認為審美并不是生存的現實體驗,而是對現實生存的超越。“審美體驗是不同于現實體驗的獨立的體驗方式。審美體驗已經與現實體驗相隔絕,進入了與現實不同的意義世界。”[注]楊春時:《作為第一哲學的美學:存在、現象與審美》,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512頁,第83頁,第95頁,第110頁,第206頁。通過這樣的一種方式,審美使得生存回到了存在的本真性。另外,審美并不是主體性的,而是主體間性的。在審美體驗中,對象或者世界不再是作為客體與我對立,而是成為了像我一樣的主體,與之對話、交流。“審美不是主體對客體的構造和克服,而是自我主體與對象主體間的自由交往,和諧共
存。……審美對象不是僵死的現實或文本,而是活的審美形象——人;不是客體,而是另一個我。”[注]楊春時:《作為第一哲學的美學:存在、現象與審美》,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77頁。通過審美的主體間性,就回到了存在的同一性。如此,審美就成了回歸存在的一種超越性的體驗方式。審美的體驗就是存在的體驗。審美就是存在之學。
二、美學的構成:審美情境還是審美現象?
對于馬丁·澤爾而言,顯現是審美意識的本質、審美構成的必要條件,正是顯現使得審美意識不同于普通意識。進一步而言,顯現乃是審美情境的核心。審美情境由審美對象和審美感知共同構成。“美學所研究的是一種情境,在這種情境中,某物或者一切都轉化成一種獨特的(客觀的)感知事件,因為發生的是一種獨特的(主觀)的感知事件。”[注]馬丁·澤爾:《顯現美學》,楊震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第77頁,第35頁,第35頁,第80頁,第82頁,第82頁,第83頁,第94頁,第94頁,第100頁。在審美顯現中,審美感知使得對象得以在顯象中游戲,發生審美事件;而審美之所以可能,是因為發生著一種不同于普通意識的審美感知行為。二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二者所指出的是一個共同體的不同方面,這個共同體正是審美感知情境。審美對象的基本狀況只有通過它的潛在感知才能得到理解,審美感知的基本狀況只有通過它的潛在對象才能得到理解。”[注]馬丁·澤爾:《顯現美學》,楊震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第77頁,第35頁,第35頁,第80頁,第82頁,第82頁,第83頁,第94頁,第94頁,第100頁。也就是說,審美情境是馬丁·澤爾探討審美經驗的基本構成,“我們的討論將始終圍繞審美感知的總體情境來展開”[注]馬丁·澤爾:《顯現美學》,楊震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第77頁,第35頁,第35頁,第80頁,第82頁,第82頁,第83頁,第94頁,第94頁,第100頁。。
以事物的顯現為目的來感受事物標示著審美感知的基本特征,不過這種分析處理的對象是現實中的事物在意識中的顯現。若僅停留于此,那么豐富的審美經驗就沒辦法完全解釋。因而,馬丁·澤爾認為審美情境必須要處理假象的問題,即意識中呈現的并不是感性在場的事物。這里有兩種情況:第一,“對于審美假象,可以把它理解成感性偽裝,它在感知情境中并不符合現象性的現實”[注]馬丁·澤爾:《顯現美學》,楊震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第77頁,第35頁,第35頁,第80頁,第82頁,第82頁,第83頁,第94頁,第94頁,第100頁。,審美假象和普通意識假象不同。對于普通意識而言,假象本身并不會被肯定。而在審美意識中,假象恰好被肯定、被歡迎。“發現欺騙都會導致糾正。此前的感知馬上就會被否定,被一種以為是正確的想法替代。……與此不同,在審美感知中,對欺騙性的發現并不導致對這種感知的糾正:在其他方面屬于欺騙性的假象在這里可以支持一張具有積極價值的感知。”[注]馬丁·澤爾:《顯現美學》,楊震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第77頁,第35頁,第35頁,第80頁,第82頁,第82頁,第83頁,第94頁,第94頁,第100頁。在馬丁·澤爾看來,假象非但不會破壞顯現在審美情境中的核心地位,相反,它還進一步強化了顯現這個要素,“它豐富了對象身上可感的顯象之間的游戲”[注]馬丁·澤爾:《顯現美學》,楊震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第77頁,第35頁,第35頁,第80頁,第82頁,第82頁,第83頁,第94頁,第94頁,第100頁。。 “審美假象豐富了審美顯現,使其擁有了更多方面。”[注]馬丁·澤爾:《顯現美學》,楊震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第77頁,第35頁,第35頁,第80頁,第82頁,第82頁,第83頁,第94頁,第94頁,第100頁。第二,審美想象。如果說假象在意識中呈現的是與現實現象性不同的當下,那么想象呈現的是不同于現實現象性的另一種當下。無論是虛構中的小說人物,還是回憶過去發生的事情以及展望未來的事物,想象使得不在場的事物得以在場,“在進行想象的意識中,我們通過某種有點清晰或者有點復雜的感性構造,把某種不存在的對象和情境看作是在場的”[注]馬丁·澤爾:《顯現美學》,楊震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第77頁,第35頁,第35頁,第80頁,第82頁,第82頁,第83頁,第94頁,第94頁,第100頁。。馬丁·澤爾認為,正如審美感知是感知的一種特殊模式,審美想象也是想象的一種特殊方式,審美想象關注的是想象中感性事物的顯現,“審美想象與非審美想象的區別恰好在于:通過審美想象,感性對象得以在它們的顯現中呈現出來”[注]馬丁·澤爾:《顯現美學》,楊震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第77頁,第35頁,第35頁,第80頁,第82頁,第82頁,第83頁,第94頁,第94頁,第100頁。。與假象類似,審美想象通過不在場事物的在場化,豐富、加強了顯現。在某種程度上來說,審美想象比審美感知和審美假象更加重要,因為其進一步解放了意識,“它不需要每次都有一個外在契機,以便進入夢想的王國。它滿足了我們對假象的需求,進一步逾越了所有經驗存在和假象的界限”[注]馬丁·澤爾:《顯現美學》,楊震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第77頁,第35頁,第35頁,第80頁,第82頁,第82頁,第83頁,第94頁,第94頁,第100頁。。不過,需要注意的是,在馬丁·澤爾看來,無論是審美假象,還是審美想象,都是審美感知情境的變種。
假象與想象雖然豐富了對審美情境的理解,但審美情境本身更為復雜。對此,馬丁·澤爾還區分了顯現的三種模式:純粹顯現、氣氛式顯現和藝術顯現。所謂純粹顯現就是完全沉浸于事物的顯現當中,沒有反思,也沒有想象,“當我們完全局限在某物的感性當下性中,它就以一種純粹顯現進入感知”。而當一個對象的顯現中勾連著與生活的關系,則就是氣氛式顯現,“氣氛是一種感性上以及情感上可覺察的從而是生存論上有意義的對已經實現或未實現的生活可能性的表達”[注]馬丁·澤爾:《顯現美學》,楊震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第117頁,第100頁。。而如果感知對象被當作一種中介,當作其他意義的一種表現符號,那么這種顯現就是藝術顯現,“如果感知對象被當作一種特殊的(主要是想象性的)表現,那么,我們所面對的就是一種藝術性顯現的形式”[注]馬丁·澤爾:《顯現美學》,楊震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第117頁,第100頁。。假如我們面前有一個水池,假如我們沉浸于水池的水光漣漪之中,不作他想,那么就屬于純粹顯現;假如在顯現中,還想到這個水池乃是我幼童時就存在的,與我相伴幾十年了,那么就屬于氣氛式顯現;假如把這個水池當成大自然的雕塑,是其神力的象征,那么就屬于藝術顯現。需要注意的是,同一個對象,可以彼此分屬不同的顯現模式,而不同的顯現模式本身也是可以相互交融的。如此,自然審美、藝術審美和生活審美都被審美情境所容納。
如果說基于顯現的審美情境是馬丁·澤爾分析審美經驗的基本要素,那么楊春時則把審美的現象性當成審美經驗的基本構成。從邏輯上來說,楊春時認為存在能夠作為現象顯現,存在現象化的途徑就是審美經驗。他說:“對現象學而言,要使存在作為現象呈現出來,關鍵問題有三個:一是如何克服經驗自我,經驗意識的有限性,從而把握超驗的存在意義;二是如何克服經驗對象的有限性,從而有可能面對存在者整體,使存在本身現身;三是如何克服表象和概念的有限性,使存在作為現象呈現。”[注]楊春時:《作為第一哲學的美學:存在、現象與審美》,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23-324頁,第324頁,第327頁,第327頁,第328頁,第317頁,第317頁,第337頁。他認為,審美經驗恰好滿足上述條件,使得存在現象化、在場化。第一,審美意識既不是感性意識,也不是知性意識,而是超越性意識、自由意識,“超越了現實主體和經驗意識的局限”[注]楊春時:《作為第一哲學的美學:存在、現象與審美》,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23-324頁,第324頁,第327頁,第327頁,第328頁,第317頁,第317頁,第337頁。,因而能夠把握存在的意義。第二,審美對象不是現實中的對象,而是世界本身,“我們進入審美體驗后,對象世界以外的現實世界就不復存在,它被審美注意所消解、屏蔽,被虛無化了,只有審美對象作為整個世界與我交往”[注]楊春時:《作為第一哲學的美學:存在、現象與審美》,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23-324頁,第324頁,第327頁,第327頁,第328頁,第317頁,第317頁,第337頁。。也就是說,在審美中,有限的經驗對象成了世界整體,“這個審美對象可能是一山一水,但它就是整個世界、整個宇宙,與我完全同一”[注]楊春時:《作為第一哲學的美學:存在、現象與審美》,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23-324頁,第324頁,第327頁,第327頁,第328頁,第317頁,第317頁,第337頁。。第三,現實生存中的意識是自覺意識,以表象和概念來思維世界,而審美意識則超越了現實意識,以作為非自覺意識的意象來面對世界,克服了表象思維和概念思維。如此,基于以上三點,“審美意象使對象回到存在領域,而這就是現象。任何審美現象、藝術形象,都不是生活的復制或還原,而是對生活本質的把握,這就是存在的意義”[注]楊春時:《作為第一哲學的美學:存在、現象與審美》,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23-324頁,第324頁,第327頁,第327頁,第328頁,第317頁,第317頁,第337頁。。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楊春時深化了“現象學美學”的研究。他認為“在美學諸分支中,存在著一種現象學美學,它用現象學的方法研究美或藝術的本質”[注]楊春時:《作為第一哲學的美學:存在、現象與審美》,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23-324頁,第324頁,第327頁,第327頁,第328頁,第317頁,第317頁,第337頁。。 “在現象學諸分支中,也存在著一種審美現象學,這就是把審美當作一種現象學還原來考察,用以獲取存在的意義。”[注]楊春時:《作為第一哲學的美學:存在、現象與審美》,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23-324頁,第324頁,第327頁,第327頁,第328頁,第317頁,第317頁,第337頁。審美現象學的提出標志著他對于現象學的改造和發展進入了深度階段。假如胡塞爾的現象學具備現象還原、意向性分析、本質還原的話,那么審美經驗也具有類似的特征。第一,楊春時認為胡塞爾意義上的純粹意識在現實經驗中并不可能獲取,但審美經驗的“還原”卻是可行的,“審美注意隔離、排除了現實世界,使主體憑借審美想象和直覺而專注于審美對象,而且消除對象的‘自動化’,使感性意象突破表象的糾纏而獨立運作,進而升華為超越水平的意象——審美意象”[注]楊春時:《作為第一哲學的美學:存在、現象與審美》,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23-324頁,第324頁,第327頁,第327頁,第328頁,第317頁,第317頁,第337頁。。但與現象學不同的是,審美意象不是通過還原,而是通過超越獲得的。現象學意義上的還原成了審美意義上的超越。第二,楊春時認為意識的意向性并不是最原初的,而是還應該有所奠基,意向性應該是我和世界共在的結構,而不是意識單向對事物的指向,“全面的意向性理論應該建立在存在論的基礎上,它是主體間性的,雙向的,既是我對世界的指向,也是世界對我的指向”[注]楊春時:《作為第一哲學的美學:存在、現象與審美》,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37頁。。而唯有審美體驗才真正符合這一點。審美意識既是我對世界的指向,也是世界對我的指向,二者是交融互生的。審美體驗消除了主體和對象的對立,審美主體和審美對象互為主體,彼此圓融不分。第三,現象學的本質直觀演變成審美直觀、審美體驗。如果說現象學的本質直觀獲得是事物的本質,那么審美體驗獲得的本質乃是存在的意義:自由。總之,在吸收胡塞爾現象學的基礎上,楊春時繼續改造了現象學,提出了審美現象學,認為審美經驗具有現象學的性質,審美意象就是現象學意義上的現象。對此,有學者評價其基于現象學的美學研究:“楊春時幾乎顛覆了整個現行的哲學、美學體系,做出了全新的理論建構。”[注]毛宣國:《‘意象’與中國當代美學的現象學闡釋》,《學術月刊》2017年第6期。
三、美學的界定:感性美學還是生存美學?
馬丁·澤爾認為他構造的顯現美學突破了“存在美學”和“假象美學”的二元區分。這是有道理的。雖然有學者認為:“他其實并不贊同美學回到鮑姆伽登意義上的‘感性學’那里去。”[注]劉悅笛:《氣氛美學、超逾美學與顯現美學——當今德國的“生活美學”取向》,《山東社會科學》2015年第10期。但是,我們有理由相信,他的美學并沒有脫離西方感性美學的傳統。
第一,如果說胡塞爾通過現象學還原,對現實經驗意識進行中止,以達到純粹意識的話,那么馬丁·澤爾對審美的界定并沒有逾越現實經驗意識,還停留在意識的感性水平上。他雖然區分了感性實際和審美顯現,但是通過上文的論述,我們也知道,普通感性顯現和審美顯現的區分主要在于審美顯現把關注的重點放在事物的顯現上,而不是事物的認知性、實踐性上。審美顯現不過是事物感性出場的一種特殊方式。無論是事物的實際(Sosein)還是事物的審美顯現,這種意識都處于感知之中。因此,馬丁·澤爾才說:“審美直觀中的球和刑事偵查中的那個對象以及足踢的那個對象是同一個對象。它有著同樣的感受狀態。”[注]馬丁·澤爾:《顯現美學》,楊震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第67頁,第87頁,第94頁,第95頁。同屬感性范疇,只不過關注的是感性事物的不同方面,由此,我們可說:顯現美學還是屬于感性美學范疇。
第二,他對于審美情境的界定也突出了感知的重要性。如果說審美假象不過是審美感知的一種變種,而審美感知乃是感知的一種模式,那么審美假象終究不過是感知的一種模式。在上文中,馬丁·澤爾認為審美假象自身不符合自身,但審美假象本身屬于一種感性的偽裝。感性意識還是其發生的場所。更重要的在于,雖然假象呈現的不是事物真實具備的,但這種假象的呈現本身對于感性意識來說是真實的,“不管涉及的顯象多么不真實,這種顯象的呈現卻是普遍可感的現實”[注]馬丁·澤爾:《顯現美學》,楊震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第67頁,第87頁,第94頁,第95頁。。海市蜃樓雖然呈現的不是真實的事物,但海市蜃樓本身對于我們來說是感性真實的。審美想象雖然指向另一個世界或者虛構的世界,但想象本身依舊屬于感性意識。“在進行想象的意識中,我們通過某種有點清晰或者有點復雜的感性構造,把某種不存在的對象和情境看作是在場的。”[注]馬丁·澤爾:《顯現美學》,楊震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第67頁,第87頁,第94頁,第95頁。審美想象極大地擴展了感知的范圍,但感知依舊在審美的想象中處于核心地位:“感知及其對象事實上構成了審美的核心領域,即使盡管審美想象經常并且喜歡拋棄這個領域。”[注]馬丁·澤爾:《顯現美學》,楊震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第67頁,第87頁,第94頁,第95頁。總之,在馬丁·澤爾看來,審美假象和審美想象乃是感知的一種變種。正因如此,他才說審美感知是審美感知情境中的一種典范式情境。雖然審美假象和審美想象極大地擴展了我們的審美意識,但對于審美感知的重視明顯地顯現于他的論述當中。若是把他對于審美感知的強調與薩特對于想象的強調進行對比,我們也就明白了為何稱他的美學還是感性美學。
美學之所以被界定為感性學是與西方哲學中的主體與客體、感性與理性、身體與靈魂的二元劃分具有內在聯系的。因而,在中華古典美學思想中,由于缺乏這樣的二元對立,人們對審美的界定往往并不是從感性的角度,而多是從生存的角度來思考審美。從這個角度來說,楊春時書中的理論看似受到西方美學的影響,但其理論的核心應該是繼承了中華古典美學的精神。雖然他認為自己的學說是從實踐美學走向生存論美學再走向存在論美學,但生存的意義才是他學說關注的真正重點。
第一,從邏輯上來說,存在問題的發現和存在問題的解決都是基于生存。存在問題的發現是基于生存的缺失體驗,反過來說,若生存中沒有缺失體驗,那么存在就不可能被推定存在。這就是說,生存乃是存在推定的必要條件。正因為有了生存,存在才不是虛無。存在問題的解決更是依賴于生存。生存的現實性使得人生活于現實生活中,而生存的超越性使得生存超越殘缺的生存的現實性。而生存超越性的最真切的方式就是審美。審美中的自由體驗和超越體驗使得存在現象化。這也就是說,存在問題的解決其實還是依賴于生存。若是生存不具有超越性,那么存在本身也不可能被直觀。雖然說在生存/存在的二元對立中,存在是本體論的,是支配性的,但恰如德里達解構主義的思想所言,中心其實也是依賴于邊緣的,存在本身也是依賴于生存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楊春時所構造的存在美學其實還是為生存服務的,本質上是一種生存美學。
第二,楊春時明確地把審美界定為一種生存方式。叔本華認為審美可以破除表象性的欲望性存在,他雖然注重審美的超越性,但并沒明確提出審美是一種生存方式。在同樣的意義上,尼采的美學具有類似性。楊春時認為存在雖然是邏輯的設定,但存在本身也在歷史中展開,生存就是存在的現實歷史性形式。生存具有三種形式:第一種是自然的生存方式。 “自然的生存方式是原始人類的生存方式,它是建立在人類自身的生存基礎上的”[注]楊春時:《作為第一哲學的美學:存在、現象與審美》,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70頁,第171頁,第173頁,第218頁。。這種生存方式就是原始人的生存方式。第二種是現實的生存方式。“所謂現實的生存方式是指文明社會人類的實際的生存方式,它是建立在物質生產的基礎上的。”[注]楊春時:《作為第一哲學的美學:存在、現象與審美》,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70頁,第171頁,第173頁,第218頁。第三種形式是自由的生存方式。“自由的生存方式是建立在精神生存為主導的基礎上的,是超越現實存在的精神生活。”[注]楊春時:《作為第一哲學的美學:存在、現象與審美》,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70頁,第171頁,第173頁,第218頁。審美就是這樣一種最真切的自由生存方式。他認為審美是獨立的、完整的生存體驗,本身不依賴于現實的生存。審美是純粹的精神生活,本身也不依賴于物質生產。審美中的自由浪漫的體驗(自由的我和自由的世界、自由的時間和自由的空間)也標示著審美的獨立性、自足性。總之,審美就是一種每一個人可以真實感受到了、真實不虛的生存方式。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種劃分依舊是一種邏輯的劃分。自由的生存方式其實并不具備現實性的自足自立。人不可能完全生活在自由的生存方式、審美創造或審美體驗中,因為若是不繁衍自身和進行物質生產,精神生活本身、審美本身也不可能存在。但是,其美學的意義恰好就在于通過這樣的一種界定,突出了審美作為一種生存體驗的重要性。正因如此,審美的感性特征在其美學中不像在馬丁·澤爾那里那么重要。如果說馬丁·澤爾繼續突出了審美的感性特征的話,那么楊春時的美學則是完全逾越了感性美學,出離了感性學的范圍。所以他才說:“審美具有兩重性,一是超感性,這是本質的屬性;二是即感性,這是非本質的屬性。”[注]楊春時:《作為第一哲學的美學:存在、現象與審美》,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70頁,第171頁,第173頁,第218頁。如果感性學在某種意義上屬于德國古典美學的話,那么楊春時的生存美學則逾越了這一傳統。無怪乎代迅把其美學思想界定為“走出德國古典美學”[注]代迅:《走出古典美學,中國美學發展的時代主題》,《學術月刊》2016年第9期。。
四、美學的地位:哲學的校正還是第一哲學?
康德在《判斷力批判》中認為,如果只有純粹理性和實踐理性的話,那么二者如何溝通就成了一個沒有辦法回避的問題。由此,他開啟了對審美的研究,并賦予美學一個獨立的且溝通二者的作用。馬丁·澤爾的美學具有這樣一種類似的意義。他在《顯現美學》的中文版前言中說:“我所注重的是,闡明美學在哲學中的核心角色。它扮演的角色,是對理論哲學與實踐哲學不可或缺的校正。”[注]馬丁·澤爾:《顯現美學》(中文版前言),楊震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第1頁,第2頁,第2-3頁,第3頁,第3頁。那么,他是如何界定這種“校正”呢?這種“校正”如何不同于康德的美學呢?
馬丁·澤爾認為,事物的審美顯現是事物向我們的意識呈現的一種獨特方式,它逾越認知性的和實踐性的要求,“若要某物進入審美關注,完全不必尋求它在理論上以及實踐上的明確性和規定性”[注]馬丁·澤爾:《顯現美學》,楊震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第42頁,第49頁,第170頁,第29頁,第29頁,第30頁。。從另一方面來說,審美顯現在遠離這種概念固定性的情況下,開啟了一個自身獨特的世界。在時間上,審美顯現僅僅是當下的時間,無論它是否利用記憶或者想象。審美顯現不關注事物的普遍性,而僅僅把事物的個別性、獨特性呈現于意識之中。審美感知本身創立了一種獨特的當下景觀。而“當下是一種開放的——也因此是不可預見、不可理解和不可掌控的——視野。”[注]馬丁·澤爾:《顯現美學》,楊震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第42頁,第49頁,第170頁,第29頁,第29頁,第30頁。可以說,作為顯象游戲的顯現本身開啟了一種無限的可能性、一種無限的不可確定性,“審美直觀揭示了對無限可能性進行當下關照的契機……審美對象是一種通過不確定性得到體驗的對象,審美情境是向其世界以及所有世界的不確定性敞開的情境”[注]馬丁·澤爾:《顯現美學》,楊震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第42頁,第49頁,第170頁,第29頁,第29頁,第30頁。。如果說事物的實際是確定性、規定性的話,那么審美顯現就是不確定性、欠規定性。相比于確定性,不確定性更加重要。不確定性擴展著事物的確定性,推進著我們的認知和實踐。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丁·澤爾認為:“美學對于其他哲學領域——對于哲學本身亦然——是不可或缺的,因為它所研究的是世界和生活不可化約的方面。”[注]馬丁·澤爾:《顯現美學》,楊震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第42頁,第49頁,第170頁,第29頁,第29頁,第30頁。因此,無論是理論哲學,還是實踐哲學,本身都依賴于美學的研究:“從理論哲學的角度看,美學承擔著一種不可或缺的任務,因為它揭示了現實的一個維度,這個維度避免了認識性的固定,但卻是可認識現實的一個方面。”[注]馬丁·澤爾:《顯現美學》,楊震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第42頁,第49頁,第170頁,第29頁,第29頁,第30頁。“從實踐哲學的角度來看,美學承擔了不可或缺的任務,因為它研究的是人類的一種生活可能性,這種可能性為人類敞開了自身此在的一種獨特的、自成目的的當下性。”[注]馬丁·澤爾:《顯現美學》,楊震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第42頁,第49頁,第170頁,第29頁,第29頁,第30頁。美學這樣的一種核心地位在他未來的研究中得到了更進一步的深化。如他自己所言:“跟確定性與不確定性兩極密不可分的,是一種更深遠的、對人類生活形式來說相當獨特的兩極關系,也就是:受規定性與能規定性之間的兩極關系。”[注]馬丁·澤爾:《顯現美學》(中文版前言),楊震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第1頁,第2頁,第2-3頁,第3頁,第3頁。受規定和能規定則是其研究人類生活的一種基本結構,“相對于一種不動的運動者的波瀾不驚,人類生活始終一再地被看成是處于對立兩極之間不可解的緊張中——作為運動與靜止、緊張與松弛之間的持續轉換,作為痛苦與無聊之間的擺動,作為快樂原則與死亡驅動之間的對抗”[注]馬丁·澤爾:《顯現美學》(中文版前言),楊震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第1頁,第2頁,第2-3頁,第3頁,第3頁。。人類生活的這樣的一種基本結構在審美中得到最確切的感受:“它們給予被規定性與能規定性之間人類的地位以格外的強調。”[注]馬丁·澤爾:《顯現美學》(中文版前言),楊震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第1頁,第2頁,第2-3頁,第3頁,第3頁。一方面,“在審美感受中,我們能夠以一種罕見的方式品嘗我們此在的消極方面”。另一方面,“這其中存在著審美實踐與其他實踐之間的不連續性:它促成了對我們消極性的積極考察”[注]馬丁·澤爾:《顯現美學》(中文版前言),楊震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第1頁,第2頁,第2-3頁,第3頁,第3頁。。審美不僅僅是審美,更是顯現人類生活本質的一個獨特形式。
不過,正如康德不把美學當成其學說的核心,美學在馬丁·澤爾思想中的地位仍然受到很大的限定。他說:“沒有理由讓美學在地位上提升為哲學的首要領域。若把審美關系闡述為人類可能性的高峰,也是沒有根據的。通過審美感知,人類感知的可能性能夠擴展到幾乎所有領域——這就夠了。”[注]馬丁·澤爾:《顯現美學》,楊震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第30頁,第74頁。美學雖然是獨立的領域,雖然可以矯正理論哲學和實踐哲學,甚至代表了人類生活的可能性。但它永遠不過是感性學,不過是一種哲學的修正。因而,馬丁·澤爾拒絕認為他的顯現美學可以昭示本體論的存在。他說:“通過關注這種顯現,也不是為了進入一種前概念的領域,不是為了遭遇一種‘初級存在’,也不是為了認識一種隱藏在所有形式背后的統治性的‘混沌’。這種或那種基礎主義的解釋面對這種簡單的情況就要落空。”[注]馬丁·澤爾:《顯現美學》,楊震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第30頁,第74頁。他的這樣一種拒斥形而上學的觀點遭到了該書中文翻譯者的質疑:“審美經驗所凸顯的人類存在以及世界的‘不可規定性’意義的強調,其意義何在?通過顯現,我們除了強化自己的在場感、時間意識、自我意識,還能實現什么?”[注]楊震:《重建當代‘感性學’如何可能——馬丁·澤爾《顯現美學》的啟示》,《文藝研究》2016年第5期。實際上,感性學的界定本身已經暗示了美學在其思想中的地位。這樣的一種思想在楊春時的美學中完全得到了逆轉,美學成了第一哲學,成了最為本質、為一切奠基的存在學說。
楊春時認為在哲學中應該區分兩種邏輯:一是發現的邏輯,二是證明的邏輯。缺席現象學通過缺席性的認知和情感體驗只是推定了存在。缺席現象學雖然也發現了存在,但這種發現本身并不明晰。而審美作為自由的生存方式和超越的體驗方式,克服了現實生存的異化,使得我們直接感受到存在,領會其意義。相比于缺席體驗,審美體驗發現并且確定了存在。用現象學的術語來說,缺席體驗只是對于存在的意向,而審美體驗不僅是對存在的意向,而且是對存在的直觀。但審美的體驗僅僅是發現的邏輯,還不是證明的邏輯。這個證明的邏輯就是哲學。在其思想中,這個證明的邏輯由邏輯-歷史進行推演證明。哲學論證進一步證明、充實了審美的發現。從邏輯上來說,先有美學,再有哲學。只有先進行審美體驗,而后的哲學思考才能進行。一個哲學家必須首先具備深切的審美和藝術修養。正是基于這個意義,楊春時才說:“審美意義或存在的意義即審美體驗的反思,哲學思維不過是審美體驗的反思形式,只有在審美體驗的基礎上,哲學反思才能進行;只有在美學的基礎上,哲學論證才能展開。一個哲學家必須對世界人生有深切的體驗,而這種體驗的最充分形式就是審美。對社會人生的審美體驗就是領會了存在的意義,再反思這一體驗,就形成了哲學思考。總之,審美體驗是哲學思辨的基礎和源頭,哲學不過是審美體驗的反思和邏輯證明。”[注]楊春時:《作為第一哲學的美學:存在、現象與審美》,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79頁。
其實,在他把美學界定為超越學的那一刻,就注定了其美學不同于西方的感性美學,也注定了其對美學的重視。囿于感性美學的窠臼,美學的地位本身不會置于哲學思考的頂端。只有超越這一感性學界定,美學的地位才會發生改變。可以說,美學在哲學學科中地位的反轉早就隱含在他的美學思想中。近年來,他對現象學和存在論的研究,只不過是邏輯地把這一點凸顯出來罷了。因而,相比于馬丁·澤爾,他思想中美學的地位更高,美學不是對哲學的校正,而是第一哲學。美學不是感性學,而是存在學。美學不是經驗性的學理,而是純粹哲學的探討。馬丁·澤爾認為,在德語哲學史中,美學的地位一直是很重要的。其實,在中國文化中,美學更加重要。李澤厚認為審美乃是中華文化的核心,“中國哲學的趨向和頂峰不是宗教,而是美學。中國哲學思想的道路不是由認識、道德到宗教,而是由它們到審美”[注]李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論》,讀書·生活·新知三聯出版社,2008年,第226頁。。蔡元培更是提出要以美育代宗教。不像德國人那樣把美學當成一種感性的學說,美學在中國文化中是與人的生命緊緊相連的一種學問。所以,方東美認為:“凡是中國的藝術品,不論他們是任何形式,都是充分的表現這種盎然生意。一切藝術都是從體貼生命之偉大處得來的,我認為這是所有中國藝術的基本原則。”[注]方東美:《生生之美》,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295頁。不像德國人那樣把美學當成一種理論和實踐的中介,美學在中國文化中就是哲學本身。因而,楊春時把美學當成第一哲學也就不那么令人詫異了。
雖然二者的美學思想差異很大,但并不意味著二者的思想中沒有任何相通之處。馬丁·澤爾對于顯象游戲的強調與楊春時對審美經驗中主體間性的關注有異曲同工之妙。審美情境中的不確定性難道不也是生存的超越性的一個維度嗎?審美對象中的同時性和瞬時性不也類似于楊春時界定的永恒性和當下性嗎?不過,囿于西方感性美學傳統,馬丁·澤爾雖然以顯現為核心構造了新的美學理論,但并沒有真正逾越感性學的范圍。又因為受到分析哲學的影響,對形而上學也是拒斥的。楊春時則顯然更傾向于傳統哲學的本體論,構造了一個類似于黑格爾意義上的形而上學美學。不過,這種美學是東方式的生存超越的,不是感性學的。也許,正如繪畫的美在西方以油畫人物為典型形式進行顯現,而在中國則以水墨山水進行顯示,但二者本身并不窮盡繪畫的美,無論是把審美界定為感性學、顯現學,還是把審美界定為存在學、超越學,二者本身都沒有窮盡美的理論本身。但二者美學的意義在于向我們提供了理解美這一現象的新的角度、新的思維。這是他們做出的不可磨滅的貢獻,卻也激勵著我們繼續思考美這一人類社會中最重要、最不可缺少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