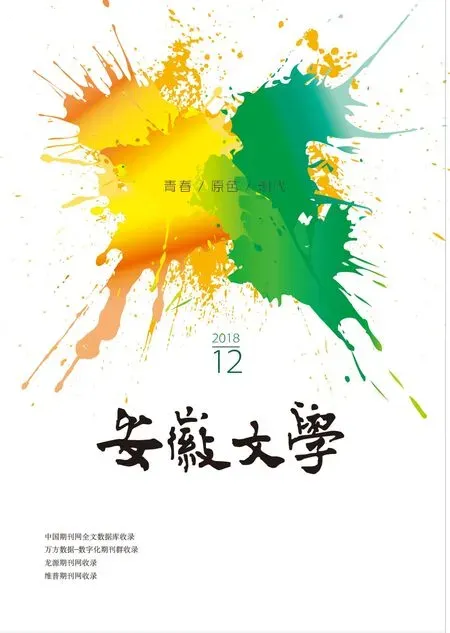中日兩國審美意識比較
——以“天人合一”和“物哀”為例
郭梓燁
中國傳媒大學(xué)外國語學(xué)院
一、中國“天人合一”的審美意識
一直以來,“天人合一”的思想主要用于哲學(xué)領(lǐng)域,是中國哲學(xué)史上的重要命題之一。中國著名哲學(xué)家馮友蘭(1998)曾說“天人合一”是中國哲學(xué)所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中華思想大辭典》(1991)說:“主張‘天人合一’,強(qiáng)調(diào)天與人的和諧一致是中國古代哲學(xué)的主要基調(diào)”。這一哲學(xué)思想起源于春秋時期,經(jīng)歷儒家與道家學(xué)說的發(fā)展后在漢代董仲舒時期達(dá)到頂峰。不僅如此,在經(jīng)歷了幾千年的延續(xù)后,時至今日它仍可以作為解決當(dāng)今全球生態(tài)環(huán)境問題的重要理念。例如,美國物理學(xué)家卡撥勒曾高度評價過老子的哲學(xué)思想,并將其與現(xiàn)代物理進(jìn)行比較。因此,我們不得不承認(rèn)這一哲學(xué)理念已經(jīng)滲透到中國人社會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對我們的影響無處不在,這其中自然也包括中國古代以及現(xiàn)代的各類藝術(shù)。由于審美意識是一種對藝術(shù)的能動反映,因此,我們也可以將“天人合一”這一哲學(xué)理念作為一種審美意識進(jìn)行研究。馮友蘭(2017)先生在其著作中介紹老莊哲學(xué)時也曾說道“莊子的天人合一境界更多地具有審美意義。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深厚的審美意蘊主要源于莊子的‘天人合一’思想。”
(一)“天人合一”思想的發(fā)展歷程
在“天人合一”的思想中,不同的時代以及不同的思想流派對其的解讀都各不相同。這其中,各個時代儒家與道家對天人觀的發(fā)展做出的貢獻(xiàn)最為顯著,也是我們研究“天人合一”思想的主要來源之一。天人合一中的“天”有著多種釋義,在儒道兩家的學(xué)說中“天”既是字面意義的自然或萬物,也是抽象意義或哲學(xué)意義上的天理或自然規(guī)律。
早在“天人合一”的思想出現(xiàn)形成之前,神人關(guān)系是其發(fā)展的歷史源頭。“人類在漫長的歷史進(jìn)化中,必然要在自己的思索中成長,而思索的第一個對象無疑是與人的生存最密切相關(guān)的自然界”(帥松林,2013:36)。早在遠(yuǎn)古時代,原始宗教中就出現(xiàn)了“神人交通”。到了殷商時期,“天王和一”的觀念逐漸形成。到了周代,隨著奴隸與奴隸主之間階級矛盾的不斷加劇,周公提出了新的政治綱領(lǐng),即“敬德保民,以德配天”,這種“依天命”來“敬德”的思想使得“天”作為至上之神的宗教色彩逐漸淡化,也為日后儒家“天命觀”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礎(chǔ)。重視德行必然反思主體,所以,春秋時期倫理德目的豐富發(fā)展,為“人”的進(jìn)一步發(fā)展提供了基礎(chǔ)。(耿云志,1994)隨著東周的衰落、春秋時期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以及社會變革的出現(xiàn),人們得以開始重新思索“天”與“人”的關(guān)系。隨著春秋時期鐵器的普及,人們改造自然的能力也逐步提高。在這一時期,老子和孔子分別對“天”與“人”的關(guān)系做出了新的解讀。
1.儒家思想中的“天人合一”
作為儒家學(xué)派的創(chuàng)始人,我們可以從孔子的言論中首先提煉出關(guān)于“天人合一”的思想。在孔子的天人觀中,“天”更多地被表述為“命”。在《論語·季氏》中寫道“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天”已不再是宗教色彩濃厚的具有超自然力量的神,而是一種哲學(xué)意義上的不為人力所支配的規(guī)律,具有一定的道德屬性。孔子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圣人晏然體逝而終矣!”而“人”既可以指個人,也可以指由個體的人所組成的社會。對于個人而言,“天人合一”意味著加強(qiáng)個人的道德修養(yǎng)使其言行更加符合“天命”。對于社會而言,“天人合一”可以通過行仁政來實現(xiàn)。“克己復(fù)禮為仁。一日克己復(fù)禮,天下歸仁焉。”(《顏淵》)通過“克己復(fù)禮”,建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會秩序,從而使社會中充滿愛,最終達(dá)到人與自然社會的和諧統(tǒng)一。
孟子繼承并發(fā)展了孔子的天人觀,孟子認(rèn)為天即“義理之天”,賦予了“天”道德的屬性。《孟子·離婁上》中就有寫道“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即天擁有誠信的屬性,追求誠信就是遵循天道。此外,孟子認(rèn)為人性本善,預(yù)想達(dá)到天人合一必須修身養(yǎng)性。“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yǎng)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盡心上》);只有通過不斷地“修善”才能達(dá)到天與人合而為一的高尚境界。
漢代唯心主義哲學(xué)家董仲舒改造并發(fā)展了傳統(tǒng)儒學(xué),融合了陰陽五行及各家的學(xué)說,提出了“天人感應(yīng)”。董仲舒認(rèn)為天是“群物之祖”、“百神之大君”,是主宰萬物的至上神。他的這一觀點具有濃厚的宗教色彩,繼承了商周時期人們對“天”的理解。他認(rèn)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即天與人之間是相互感應(yīng),互相影響的。天可以干預(yù)人事,人亦可以感應(yīng)上天。
2.道家思想中的“天人合一”
作為道家思想的創(chuàng)始人,老子與莊子最先確立了道家學(xué)派中“天人合一”的思想。在儒家思想中,“天”更多的是一種道德之天、義理之天,而在道家學(xué)說中,“天”是自然主義的天,較少有人倫道德的含義。老子認(rèn)為世界的本源是“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天人合一”的思想在老子這里就是道與人合二為一,與道為一則“無為”,也就是對萬物順其自然不加干涉。
“莊子在老子道論的基礎(chǔ)上,更多地講人的精神境界”。(馮友蘭,2017:20)莊子說“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天”指自然,人與自然萬物合為一體就是莊子的“天人合一”境界。“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意思是說究極的認(rèn)識是知道自然的作為并了解人的作為,可見在莊子的學(xué)說中,人與天同樣具有重要的意義。“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dá)萬物之理。世故至人無為,大圣不作,關(guān)于天地之謂也。”(《莊子·知北游》)意思是天地萬物有它自己運行的規(guī)律,這是大美,圣人要想通曉世間萬物的哲理就要順應(yīng)自然。這也是馮友蘭先生認(rèn)為莊子的“天人合一”境界更多地具有審美意義的緣故。道家提倡“無為”,這是其天人思想的重要特征,也就是人要順應(yīng)自然,順應(yīng)“道”,“無為”就是“無不為”。
(二)“天人合一”審美意識的影響
可以說“天人合一”審美意識的影響在某種意義上說就是儒家及道家等學(xué)派長期以來對社會生活的影響。因為這些學(xué)派無一不是把天人問題作為其哲學(xué)的根本問題進(jìn)行探討,“儒家和墨家從人道契入,必然涉及天道;道家從天道契入,必然涉及人道。這樣一來,儒、墨、道三家都把哲學(xué)思考的焦點聚到天道與人道哲學(xué)關(guān)系的問題上來了”。(陳博,李慧萍,2015)而儒家和道家又都在不同的方面開創(chuàng)并發(fā)展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尤其是道家,儒家思想的“天人合一”更多地帶有入世的色彩,道家思想中的“天人合一”更加出世,也更具有審美情趣。因此我們可以說“天人合一”的思想無論作為哲學(xué)命題還是一種審美意識,它對中國人社會生活的影響是方方面面的,尤其是對中國傳統(tǒng)藝術(shù)以及國民心理的影響。
1.天人合一”審美意識在文學(xué)方面的體現(xiàn)——以古詩詞為例
第一,“天人合一”的審美意識在古詩詞方面的體現(xiàn)主要是通過對“天”也就是“自然”的描寫來表達(dá)“人”的所思所想所感,從而達(dá)到主客交融、情景交融、物我兩忘的境地。以山水田園派詩人的作品為例。唐代著名山水田園詩人王維在《終南別業(yè)》中寫道:“行到水窮處,坐看云起時。偶然值林叟,談笑無還期。”這首詩描寫的是作者隱居在終南山時的所見所感。作者人到中年厭惡世俗,希望隱居田園。流水與白云無時無刻不在發(fā)生著變化,這里寫到的水與云,表現(xiàn)的是詩人一種渴望無拘無束、自由自在心境。詩人在山林之中通過一行、一坐一看得到頓悟與釋懷,達(dá)到了物我兩忘、天人合一的境地。從藝術(shù)手法上來說,這兩句詩就是一幅山水畫,是名副其實的“詩中有畫”。
其次就是通過托物言志的表現(xiàn)手法,運用“比德”的自然審美觀,將人比德于自然,從而實現(xiàn)自然與人合而為一的境界。北宋周敦頤的《愛蓮說》中就把蓮花比喻為“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的君子。在他的眼里蓮花擁有挺拔秀麗的外形,清新的香氣,只可在遠(yuǎn)處欣賞不能輕易玩弄。結(jié)合周敦頤自身的身世我們可以知道,他性格樸實,為官清廉,不貪慕錢財,可以說是在黑暗的官場中始終保持著自己高潔的品格。蓮花這種“出淤泥而不染”的特性正是他自身不愿同流合污的志向和理想。因此,這種“托物言志”的表達(dá)我們也可以說是受到了“天人合一”審美意識的影響。
2.“天人合一”審美意識在傳統(tǒng)文化中的體現(xiàn)
除去古詩詞及文學(xué)層面,“天人合一”的審美意識還體現(xiàn)在中國傳統(tǒng)建筑、園林設(shè)計、書法、繪畫等諸多方面。
第一,“天人合一”建筑觀所展現(xiàn)的是“自然與精神的統(tǒng)一”。(汪秀芳,2015)盡管中國傳統(tǒng)建筑的類型豐富多樣,但其在選材、風(fēng)格、選址及布局上體現(xiàn)的“天人合一”理念卻有共同性。就建筑選材來說,中國的古建筑是世界上唯一以木結(jié)構(gòu)為主的建筑體系。木材是純天然的建筑材料,給人以挺拔、深沉的自然之美,十分符合中國人的文化性格。它有許多優(yōu)點,取材便利、易于加工,最重要的是可以讓人足不出戶就感受到自然的氣息。在選址與布局方面,中國古代建筑普遍存在“天人感應(yīng)”以及“陰陽五行”等建筑意識,也就是我們所說的“風(fēng)水”之說。“其宗旨是勘察自然、順應(yīng)自然,又節(jié)制地利用和改造自然,選擇和創(chuàng)造出適合于人的身心健康及其行為需求的最佳建筑環(huán)境,使其達(dá)到陰陽之和、天人之和、身心之和的完美境界。”(姚翔翔,2015:98)
第二,中國傳統(tǒng)園林融合了儒家、道家、佛家等多種思想以及建筑、雕塑、文學(xué)、書法、繪畫等多種藝術(shù)手段。“天人合一”的審美意識在中國傳統(tǒng)園林中的體現(xiàn)主要是儒家“天人感應(yīng)”加強(qiáng)中央集權(quán)的觀念以及道家最求“自然式”園林的建筑風(fēng)格。首先,儒家的強(qiáng)調(diào)皇權(quán)至高無上與君臣禮制的觀念與皇家園林布局中中心與軸線對稱的思想是一致的。著名的皇家園林圓明園和頤和園都是這樣的形式。圓明園由三園構(gòu)成分別是圓明園、長春園和綺春園。其建設(shè)也是嚴(yán)仿紫禁城中軸對稱的形式。其次,對于道家來說,道家崇尚自然,渴望與自然合而為一的思想對傳統(tǒng)園林有很大的影響。“雖說山水創(chuàng)作不是因道家才有,園林審美的自然觀卻是道家的總結(jié)。”(潘偉、樸永吉,2010:9)計成在中國第一部園林藝術(shù)理論專著《園冶》中說道:“市井不可園也;如園之,必向幽偏可筑,鄰雖近俗,門掩無嘩。”意思是園林不可建在鬧市區(qū),如果一定要建在市中心的位置,也要盡量在靠近邊緣的位置,因為那里遠(yuǎn)離喧囂,更加親近自然。在他看來只有親近自然才能造出“雖由人作,宛自天開”的園林。而縱觀計成的一生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他一生艱辛坎坷,為此他寫下“歷盡風(fēng)塵,業(yè)游已倦,少有林下風(fēng)趣,逃名丘壑中,隱心皆然,甘為桃源溪口人。”這樣的詩句,這與陶淵明“久在樊籠里,復(fù)得返自然”的想法不謀而合。可見,他也在某種程度上受到了道家更為出世的 “天人合一”與“無為而治”思想的影響。除此之外,傳統(tǒng)園林中的空間布局以及障景、假山以及光與影的運用等方法也無一不體現(xiàn)了“天人合一”的創(chuàng)作理念。
第三,中國古代繪畫中“天人合一”的審美意識主要體現(xiàn)在國畫“君子比德”觀與“形神兼?zhèn)洹闭f中。正如古詩詞中會運用托物言志的手法一樣,“君子比德”的思想也是中國畫論的重要內(nèi)容之一。比如,在中國畫中一個永恒的題材就是“歲寒三友”。“歲寒三友”指的是松、竹、梅這三種植物,宋朝林景熙的《王云梅舍記》中最早出現(xiàn)了這一詞:“即其居累土為山,種梅百本,與喬松修篁為歲寒友。”這三種植物都有不畏嚴(yán)寒、在凜冽的寒冬中仍能保持旺盛生命力的特性,用于暗喻君子高尚的人格,即潔身自好、不趨炎附勢。“歲寒三友”的主題是“君子比德”思想在中國畫中最典型的應(yīng)用之一,也是“天人合一”審美意識在中國傳統(tǒng)繪畫中的重要體現(xiàn)。
除此之外,中國畫中“形神兼?zhèn)洹钡奶攸c也是“天人合一”審美意識的體現(xiàn)。古代中國畫主要有三個門類,分別是人物畫、花鳥畫和山水畫。“形”來源于畫家對現(xiàn)實世界的觀察;“神”指的是藝術(shù)家運用自己獨特的審美以及創(chuàng)作理念使得繪畫中表現(xiàn)出了帶有自身特色的神韻。正如莊子所說“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無論是人還是自然界的花鳥蟲魚,畫家從天地萬物中汲取創(chuàng)作的靈感,之后加入了自己的理解再創(chuàng)作為了藝術(shù)作品,這實質(zhì)上就是“天人合一”審美意識的體現(xiàn)。
二、日本“物哀”的審美意識
與中國“天人合一”的審美意識相對,日本也有貫穿其傳統(tǒng)文化的審美意識,那就是“物哀”。“物哀”源于日語的“物の哀”(もののあわれ)一詞,最早由日本江戶時代的國學(xué)家本居宣長提出。意思是通過敏銳的感受力,體察自然、人心及萬事萬物。這是一種沒有目的性的純粹的感受,是一種真情的流露。正如本居宣長在《初山踏》中說:“凡是人,都應(yīng)該理解風(fēng)雅之趣。不解情趣就是不知物哀,就是不通人情。”“物哀”作為日本傳統(tǒng)文學(xué)、詩學(xué)、美學(xué)理論中的重要概念之一,其形成經(jīng)歷了一個較長的歷史時期,它的影響也體現(xiàn)在了日本社會文化的方方面面。
“天人合一”審美意識的雛形萌芽于遠(yuǎn)古時期的神人關(guān)系,繼而生出“天”與“人”的關(guān)系;反觀日本,“物哀”審美意識的雛形萌芽于《古事記》和《日本書紀(jì)》中記載的古代神話中,也同樣是遠(yuǎn)古時期。“物哀”最初由“真實”(まこと)與“哀”(あわれ)發(fā)展而來,“關(guān)于‘哀’的審美意識的萌發(fā),齋部廣成在《古語拾遺》(807)中從原始歌謠中的阿波禮(あはれ)來考察,認(rèn)為這個用極其簡單的句所形成的歌節(jié)‘阿波禮’,是由‘啊’(あ)和‘呦’(はれ)這兩個感動詞組合而成的,最初是表現(xiàn)人的感動而發(fā)出的聲音。”(葉渭渠,2009:172)
與“天人合一”的審美意識不同,“物哀”的審美意識主要形成于日本對外來文化的吸收與發(fā)展和口頭文學(xué)到文字文學(xué)的發(fā)展歷程中,是從文論范疇中衍生而出的。王向遠(yuǎn)(2010)在本居宣長《日本物哀》一書的序中說道,產(chǎn)生于日本近世(17世紀(jì)后的江戶時代)的相關(guān)概念屬于日本本土性的文論范疇,“物哀”便是其中之一。而前者主要形成于中國古代的哲學(xué)家們對世界本源問題的探索歷程中,是從哲學(xué)范疇中衍生而出的。但其共同點就是都貫穿了兩國傳統(tǒng)文化的始終,在藝術(shù)層面和社會文化層面都產(chǎn)生了一定的影響,并在一定程度上體現(xiàn)在了兩國國民的國民性中。
(一)“物哀”審美意識的形成
第一,“物哀”的審美意識發(fā)源于日本古代審美中的“真·實”。中國古人對于世界的探索著眼于“天”與“人”的關(guān)系,而日本古人對于世界的探索則著眼于“天”、“人”與“神”的關(guān)系。“真·實”的審美意識發(fā)源于日本神道教。《日本書紀(jì)》(1963:13)中寫道:“古天地未刨,陰陽不分,混沌如雞子,溟涬而含牙,及其清陽者,薄靡而為天,重濁者,淹滯而為地,精妙之合博易,重濁之凝竭難,故天先成而地后定,然后,神圣生其中焉。”意思是在混沌的宇宙中,無論是有生命的還是無生命的東西、無論是人還是神都是由自然天地生成的。因此,出于對神靈以及自然的崇拜,日本先民開始了對自然精靈和祖先神明的祭祀,神道教由此產(chǎn)生。而神道教的本質(zhì)和宗旨就是“真·實”。日本文獻(xiàn)《神衹訓(xùn)》中說道:“神道以誠(まこと)為本”。(葉渭渠,2009:171)這里的“誠”就是“真·實”的意思。也就是說無論是《古事記》、《日本書紀(jì)》,還是其他由國家編撰的記錄日本古代神話傳說及歷史的著作都強(qiáng)調(diào)的是被神化了的現(xiàn)實。因此,“真·實”的美意識從日本文化的萌芽期開始,就扎根于日本先民對于“天、人、神”關(guān)系的思考中,成為“物哀”審美意識的源頭。
第二,以“真·實”審美意識為根底形成了“哀”的美意識。“哀”最初是人們?yōu)楸磉_(dá)感動而發(fā)出的聲音,相當(dāng)于中文的“啊“和“呦”。“哀”是一種基于“真·實”的集體的感動,是“物心合一”的結(jié)果。在《古事記》中的一首古代歌謠中寫道“我的愛妻,哀!(あはれ)”這里的“哀”表達(dá)的是對妻子的愛與哀傷;《記·紀(jì)》中共同記載的一首歌謠是“這一顆松,哀!(あはれ)”此處“哀”表達(dá)的是對松的親愛之情。由此可見,“哀”的審美意識形成于日本古人對于具有“真·實”特性之物的愛憐之情中。
第三,佛教思想的傳入與“物哀”審美意識的形成。對于儒家思想中的“天人合一”來說,其最終的形成離不開儒家思想對其他學(xué)派的吸收與融合。“物哀”的審美意識亦是如此,盡管“物哀”作為文論被正式提出是在18世紀(jì),但“物哀”精神最早體現(xiàn)在11世紀(jì)紫式部所著的《源氏物語》中,這與佛教思想在平安時代開始盛行有著密切的關(guān)系。佛教開始受到日本貴族的推崇要追溯到圣德太子時期。“日本從圣德太子在十七條憲法中規(guī)定‘篤信三寶’以來,歷朝天皇和貴族都十分崇信佛教,佛教在社會政治、文化上占有很高的地位。”(楊曾文,2008:114)到了平安時代,統(tǒng)治者為了打壓傳統(tǒng)佛教在朝廷中的勢力,遷都之后天皇便大力扶植空海創(chuàng)立的真言宗和最澄創(chuàng)立的天臺宗,佛教開始全面盛行。
佛教思想中對“物哀”的審美意識影響最為深遠(yuǎn)的便是“無常觀”。佛教經(jīng)典《涅槃經(jīng)》中云:“一切眾生跡中,象跡為上;是無常想亦復(fù)如是,于諸想中最為第一。”意思是說,在一切眾生的腳印中,大象的腳印是最好的;在一切思想中,無常的思想也是最好的。能夠敏銳感知“無常”的人,看到花開花落、四季變換便會思考輪回與生死。本居宣長認(rèn)為,這種可以感知“物心人情”的人就是“知物哀”的人。由此,這種帶有宗教世界觀的“無常”思想與日本本土基于神道教的美意識“哀”碰撞融合后便形成了“物哀”——這一不再是單純地感嘆,而是融合了佛教和日本本土神道教、含有贊賞、親愛、共鳴、同情等廣泛含義的審美意識。
《源氏物語》的作者紫式部自幼信仰佛教,后仕于上東門院,是宮中的女官,可以說自幼就深受佛教影響。因此《源氏物語》中也經(jīng)常可以看到“菩提即煩惱”、“善惡不二”等佛學(xué)思想出現(xiàn)。但紫式部的美學(xué)論是神佛思想融合的產(chǎn)物,她并沒有著重宣揚佛教的善惡觀,而是將其作為表,用無常的思想結(jié)合日本本土的“真實”與“哀”的思想,從而發(fā)展出“物哀”的美意識。
(二)“物哀”審美意識的影響
“物哀”審美意識自形成開始便逐漸成為了日本審美意識的主流。川端康成曾多次強(qiáng)調(diào):“平安朝的‘物哀’成為日本美的源流。”正如中國“天人合一”的審美意識體現(xiàn)在中國傳統(tǒng)藝術(shù)以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一樣,日本“物哀”的審美意識亦是如此。
1.“物哀”的審美意識在文學(xué)中的體現(xiàn)——以《源氏物語》為例
我們可以說“哀”以及“物哀”的審美意識貫穿了日本文學(xué)的始終。據(jù)統(tǒng)計,日本書面文學(xué)的開端《萬葉集》中共有9首歌使用了“哀”一詞。奈良時期的《懷風(fēng)藻》以及平安初期的《凌云集》中都出現(xiàn)了帶有“可憐”一詞的歌。紀(jì)貫之在《土佐日記》中最初提及了“物之悲”,清少納言的《枕草子》中最早出現(xiàn)了帶有“知物哀”一詞的句子。
但古代審美思想由“哀”到“物哀”的演進(jìn),是經(jīng)紫式部之手完成的。據(jù)日本學(xué)者統(tǒng)計,《源氏物語》一書出現(xiàn)的“哀”多達(dá) 1044次,出現(xiàn)“物哀”13次。(葉渭渠,2009:177)可見,“物哀”精神是《源氏物語》的寫作宗旨及整體基調(diào)。
《源氏物語》是一部描寫貴族男女戀情的小說。作者在文中反復(fù)強(qiáng)調(diào),“女流之輩,不敢奢談天下大事”。因此《源氏物語》盡管書寫的是不倫之戀的故事,但作者并沒有用勸善懲惡的道德觀來評價小說中各個人物的對錯,而是以“感知物哀”為第一要義。“無論是哪部物語中,都多寫男女戀情,無論在哪部和歌集中,戀歌都是最多的。沒有比男女戀情更關(guān)涉人情的幽微之處了。”(本居宣長,2010:19)作者借源氏之口寫道“對于好人,就專寫他的好事……對于惡事,則專取那些稀奇的事情來寫。”寫好事的目的就是為了讓讀者“感動”。“感動”不僅僅是傷感,覺得有趣、可笑、可憎、可愛等一切心理活動都是 “感動”。作者把這些事物不帶有個人評價地寫出來,就是為了讓讀者感知“物之哀”;而寫出惡事也并不是讓讀者引以為戒,而是讓讀者感受到惡事的稀奇有趣。
本居宣長認(rèn)為“物語就是將世上的好事、壞事、稀奇的事、有趣的事、可笑的事、可感動的事,用無拘無束的假名文字寫下來,并且配上插圖,使人閱讀時排遣無聊與寂寞,或者尋求開心,或者撫慰憂傷。”(本居宣長,010:19)因此,可以體現(xiàn)“物哀”的情感就是好的,不能體現(xiàn)“物哀”的情感就是惡的。盡管源氏的行為違背了道德,但是是非對錯并不需要物語來表現(xiàn)。因此,我們可以說“物哀”的審美意識是《源氏物語》的整體基調(diào),“知物哀”是其創(chuàng)作的宗旨。
2.物哀”的審美意識在傳統(tǒng)文化中的體現(xiàn)
“物哀”的審美意識體現(xiàn)在日本傳統(tǒng)文化的諸多方面。枯山水的園林建筑、日本傳統(tǒng)繪畫浮世繪中都可以看到“物哀”審美意識的影子。
第一,日本縮微式園林枯山水中體現(xiàn)了濃厚的“物哀”美意識。枯山水是日本特有的園林藝術(shù),屬于禪宗園林。公元13世紀(jì)榮西正式將禪宗傳入日本。禪宗主張“即心是佛”,重自修自悟。寺院園林因接受了禪宗的思想,逐漸將園林建造為無山無水的枯山水形式,以反映禪宗的自律從而達(dá)到自我修行的目的。枯山水庭園中只放置石頭、白砂和苔蘚等物。用石頭象征山巒和島嶼、用白砂象征湖海,再用苔蘚、常綠樹進(jìn)行點綴,以達(dá)到“無相及有相”的境界。
中國的園林建筑主要是通過與自然融為一體的園林風(fēng)格與對稱式的整體布局來體現(xiàn)道家與儒家思想中“天人合一”審美意識的,也就是說園林中越是有生機(jī)勃勃的自然景觀越可以體現(xiàn)“天人合一”。而與中國截然相反的是枯山水庭園中“物哀”的審美意識主要體現(xiàn)在通過“枯”來感知“物之心”上。本居宣長認(rèn)為,“物哀”及“知物哀”分為兩個方面,分別是感知“物之心”和感知“事之心”。“物之心”指的是人心對客觀外物的感受;“事之心”主要指通達(dá)人情,兩者合起來就是感知“物心人情”。與中國園林不同,日本枯山水的庭園中多是沒有生命的事物,僅存的植物也并非郁郁蔥蔥的開花植被,第一眼看過去會給人一種空虛與寂寥的感覺。但枯山水式的園林屬于精神的園林,可以感知“物之心”的人,哪怕是沒有生命的石與沙擺在面前,也可以感知花開花落與季節(jié)的變換,仿佛眼前真的有江河湖海在洶涌翻滾。在簡潔與純粹的事物中,也可以感受到宇宙萬物盤踞其中。這就是通過“枯”來感知“物哀”。
第二,產(chǎn)生并興盛于日本江戶時期的版畫藝術(shù)浮世繪中也可以看到“物哀”的情感基調(diào)。首先,從字面意義上來說,“浮世”兩字源于佛語中對煩悶塵世的描述,最早由浮世繪的開創(chuàng)者菱川師宣用于自己的畫作中。也就是說,浮世繪從形成伊始就蘊含著“人生苦短、及時行樂”的現(xiàn)世意義。反觀中國,中國傳統(tǒng)繪畫中“天人合一”的審美意識主要體現(xiàn)在“君子比德”說與“形神兼?zhèn)洹彼枷胫校嗟伢w現(xiàn)在作畫的寓意與技巧上,而浮世繪中“物哀”的審美意識主要體現(xiàn)在其整體的基調(diào)上,也就是通過刻畫美好而領(lǐng)悟悲情。這主要是源于浮世繪產(chǎn)生于江戶時期的平民階層,日本經(jīng)歷“應(yīng)仁之亂”后,政治上的不穩(wěn)定與階級之間斗爭的加劇,使得平民深受其害,于是產(chǎn)生了世事無常、及時行樂的思想,浮世繪這一反應(yīng)無常世道、具有廣泛題材的版畫藝術(shù)也應(yīng)運而生。用浮世繪中美人繪題材舉例,早期的美人繪多是風(fēng)俗畫,其原型為江戶吉原的妓女。喜多川歌磨的美人繪是美人繪題材的集大成者,他的畫作中既通過整體的線條刻畫人物,又通過細(xì)節(jié)刻畫了人物的心理。在這之后,浮世繪逐漸走向了色情,對現(xiàn)世享樂的需求使得浮世繪開始著重表現(xiàn)男女情愛的場面。對于青樓女子的刻畫可以讓人們感知“事之心”,也就是知時代之“物哀”。日本作家永井荷風(fēng)說:“如果說木版畫在溫和的色彩中存在作者的精神,那么這完全是專制時代人心萎靡的反應(yīng)。在這種暗示黑暗時代的恐怖與悲哀中,我仿佛聽到了青樓女隱隱吸泣的聲音,就不能忘記其中的悲哀和無奈的色調(diào)。”(永井荷風(fēng),1997:166)

喜多川歌磨美人繪
三、中日審美意識在國民性上的體現(xiàn)
綜上所述,中日兩國最具代表性的審美意識分別是“天人合一”與“物哀”。這兩種審美意識的形成與發(fā)展既有共同點又有不同點,但因為這兩種審美意識都通過各類傳統(tǒng)文化滲透到了國民生活的諸多方面,而國民性指的是一國大多數(shù)人的文化心理特征,是在價值體系基礎(chǔ)上形成的,所以我們可以說它們對兩國國民的國民性有著一定的影響與塑造。
在這兩種審美意識的熏陶下,中日兩國國民的國民性也有著各自的特點,通過對不同審美意識背景下的兩國國民性的分析,我們可以更好地了解兩國國民的思維方式,從而更好地進(jìn)行跨文化的交際活動。
(一)中國“天人合一”審美意識背景下的國民性
中國“天人合一”審美意識背景下的國民性有兩個特點,第一是綜合性的思維模式。“天人合一”的命題是東方綜合思維模式的最高最完整的體現(xiàn)。“天人合一”的審美意識更加注重人與外界環(huán)境的關(guān)系,注重整體,因此人與人之間的聯(lián)系普遍緊密,集體意識強(qiáng)。中國“天人合一”背景下的人格特質(zhì)使得中國人習(xí)慣于從整體的角度思考問題,從而“自我”的意識相對淡薄。一般而言,人我界限不明朗,中國人的“個體”沒有清晰明朗的“自我”疆界,是一個普遍和突出的表現(xiàn)。(孫隆基,2004:146—169)因此,中國人注重集體的觀念隨處可見。比如家族意識強(qiáng),偏愛群居,更加從眾、注重人際關(guān)系的建立等等。這樣的國民性的優(yōu)點就是擁有強(qiáng)大的凝聚力,使得中華文明延綿幾千年仍然擁有強(qiáng)大的生命力。但缺點就是個體意識及個體權(quán)利意識淡薄,使得“個人發(fā)展”和自我價值的實現(xiàn)受到一定制約。
其次是重視道德與倫理。儒家學(xué)說中自孔子時代起,“天人合一”的“天”就是“義理之天”的意思,也就是通過“克己復(fù)禮”與“施行仁政”來實現(xiàn)“天人合一”的思想,目的是維護(hù)統(tǒng)治秩序,其具體的方式就是建立“三綱五常”的社會規(guī)范。到了董仲舒時期,“天人感應(yīng)”思想的提出使得加強(qiáng)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quán)有了理論上的依據(jù)。這就使得“天人合一”思想在管理國家的時候變成了一種政治秩序,在這種政治秩序下,重視道德與倫理逐漸成為中國國民性中的一部分。
(二)日本“物哀”審美意識背景下的國民性
受“物哀”審美意識影響下的日本國民表現(xiàn)出以下幾個特點,首先,與中國人強(qiáng)調(diào)整體性思維不同的是日本人較為重直感、重細(xì)微。川端康成在其著作中曾說道:“他們對殘缺的月亮、初綻的蓓蕾以及凋零的花朵更為鐘愛,他們認(rèn)為在殘月、蓓蕾以及花朵當(dāng)中蘊藏著一種能夠引發(fā)人哀愁和憐惜的情緒,顯示的是一種悲情之美。這種悲情之美正是深入日本文化當(dāng)中的‘物哀美’的精髓。”(川端康成,1988:49)“物哀”的審美意識強(qiáng)調(diào)感受“物之心”與“事之心”,也就是體味細(xì)微處情趣的能力,以小來見大。日本人在鑒賞自然的過程中偏愛優(yōu)雅精致的山水,這與日本的地理環(huán)境有著密切的關(guān)系,雖然沒有大江大河與平原廣漠的氣度,但專注細(xì)微之處的“物哀”美也別有一番風(fēng)情。日本人執(zhí)著于將死的東西添出生意。比如把某處的風(fēng)景縮小若干分之一形成一個園林、將某一松柏的形態(tài)造一個盆栽等等。這些在直感與細(xì)微中體味生命之美的能力就是“物哀”的審美意識在日本國民性中最好的體現(xiàn)。
其次是不同于中國人重視道德與倫理,日本人比較缺乏理性、更加重視人情,并且有意把人情世界與道德世界等其他領(lǐng)域分開。因為“物哀”與“知物哀”是由外在事物的觸發(fā)引起的種種感情的自然流露,是沒有功利目的,對自然人性的廣泛包容、同情與理解,是無關(guān)道德的。以研究日本國民性著稱的美國人本尼迪克特曾指出:“日本人的人生觀正好包含在其對于忠、孝、義理、仁與人情的規(guī)范之中,他們視‘人生的全部職責(zé)’如地圖上界限分明的不同地域,人生包括‘忠之圈’‘孝之圈’‘仁之圈’和‘人情之圈’等諸多領(lǐng)域。而這幾個“圈子”是相對獨立的。即踏進(jìn)“忠”的圈子可不顧“人情”;踏進(jìn)“人情”的圈子也可不顧忠、孝、義理等道德規(guī)范。(魯斯本尼迪克特,2007:221)
四、結(jié)語
中日兩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核心命題分別是“天人合一”和“物哀”。這兩者作為審美意識都具有十分悠久的歷史。且其根源都可以追溯到原始宗教中的神人關(guān)系,分別是“神人交通”與“真·實”。“天人合一”是從哲學(xué)范疇中衍生出來的審美意識,在某種程度上涉及到了對世界本原問題的探索,因此儒家思想中的“天人合一”作為統(tǒng)治者加強(qiáng)統(tǒng)治的理論依據(jù),通過“三綱五常”的道德規(guī)范被作用于國民身上。其對國民性的影響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而道家思想中的“天人合一”是“自然主義”的天,因此更多地具有審美價值。其側(cè)重點在于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與順應(yīng)自然。道家思想中的“天人合一”對傳統(tǒng)文化的影響更加深遠(yuǎn)也使其更具有美學(xué)價值。對國民性的影響主要表現(xiàn)在強(qiáng)調(diào)整體性的思維方式,人與人之間的聯(lián)系緊密、集體意識較強(qiáng)等。
“物哀”是從文論范疇中衍生出來的審美意識,但其影響不僅限于文學(xué)領(lǐng)域。可以說日本傳統(tǒng)文化的方方面面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物哀”審美意識的影響。由于“物哀”的審美意識強(qiáng)調(diào)感知“物心人情”,也并沒有涉及對世界本原問題的探索,因此相比較中國,“物哀”的審美意識并沒有作為統(tǒng)治者的理論依據(jù)在道德層面上對國民有過多的約束。在長期感知“物心人情”審美意識的熏陶下,使得日本人的國民性中擁有了體味細(xì)微之處不同情趣的能力,也使得日本國民相比較中國人更加注重細(xì)節(jié)。
由此,受到不同審美意識熏陶下的兩國國民,其思維方式也各不相同。這就要求我們在跨文化交際的過程中盡量使用對方可以接受的方式表達(dá)自己的觀點,對于中國人注重整體的規(guī)劃以及日本人過分強(qiáng)調(diào)細(xì)節(jié)的特點予以足夠的尊重,并且可以在處理具體事務(wù)的過程中取長補(bǔ)短,從而更好地促進(jìn)交流,增進(jìn)兩國人民的友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