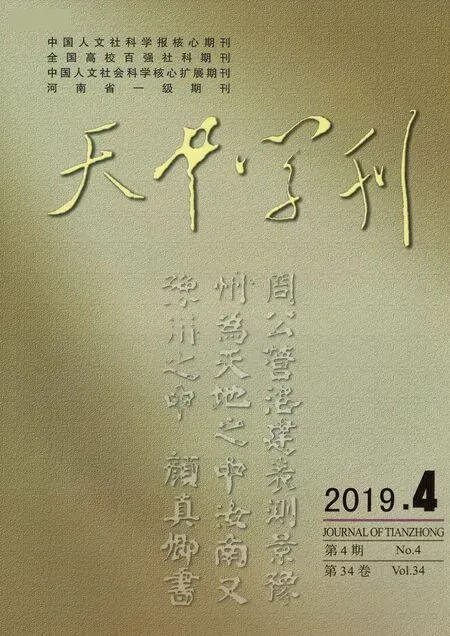郭建勛教授訪談錄
翟 新 明
(湖南大學 文學院,湖南 長沙410082)
郭建勛教授,湖南漣源人,1954年6月出生。福建師范大學文學碩士(1988年)、北京師范大學文學博士(1996年),湖南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同時擔任中國屈原學會副會長、中國辭賦學會副會長、湖南省屈原學會會長、湖南大學辭賦研究所所長等職務,著有《漢魏六朝騷體文學研究》《楚辭與中國古代韻文》《先唐辭賦研究》《辭賦文體研究》等,發表學術論文近百篇。作為郭建勛教授的學生,筆者圍繞求學、治學及教書育人等話題,于2019年4―5月對其進行了兩次采訪。
一、取道靈山
翟新明:郭老師好,很榮幸能夠采訪您。可否先介紹一下您進入學術研究前的學習與工作經歷?
郭建勛教授:我是湖南漣源人,父親是中學教師,當了很多年的中學校長。我1966年小學畢業,1969年下半年初中畢業,然后進了漣源老家的藍田水泥廠。一開始是做木模工,后來做化驗工。當時參加工人夜校學英語,有一個漣源一中的英語老師給我做輔導。到1980年,我調到藍田中學去教英語,再后來考到漣源地區教師進修學院,這個學院又跟婁底師專合并,我就算婁底師專中文科畢業。那時候讀了一些書,對古代文學感興趣,朱東潤的《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除了那些較大篇幅的,我基本都背下來了。上古代文學課的老師看到我都有點發怵,擔心我為難他。1983年畢業,又回到藍田中學,就不教英語了,改教語文,還擔任過語文教研組的組長。
翟:您后來去福建師大跟黃壽祺先生攻讀碩士學位,而且是黃先生的關門弟子。
郭:對。在藍田中學教了兩年,但我是一定要考研究生的。1985年的時候有個不錯的機會,婁底市委宣傳部要我去,我說讓我考一年,沒考上我就去。結果1985年考上研究生了。那時候考研究生,好像有十幾個人考,當時黃壽祺先生是想招不想招的樣子,結果就我一個人上線。我英語考了45 分,剛好上線,一分不多。專業課考得極難,考名詞解釋,什么“一介二南三玄四始五常六義七音八索九流十翼”,這個當時還是挺難的。還考了《山鬼》。沒有原文,要翻譯成現代詩歌,分析它的藝術特色,這也算比較難的,落實到作品就比較難。復試的時候要用文言文寫一篇自傳。面試就我一個人,等于是一定會錄了。這樣就進了福建師大,跟黃壽祺先生讀了三年,一直到1988年。這中間先是幫他做要出版的《周易譯注》的校對,接觸了《易經》的一點皮毛。讀研期間比較重要的事情,一個是讀諸子,上諸子課程,做作業,這篇作業在《福建師大學報》1987年第2期發表了[1],這應該是我發表的第一篇正式的學術論文。當時碩士研究生能在學報上發一篇文章,也是很不容易的,那時候比現在發文章更難。再后來準備寫畢業論文,選題是《〈周易〉之“周”發微——論〈周易〉循環的變化觀》,實際上已經寫了兩三萬字了。沒想到在系里開題沒通過。那時候福建師大中文系碩士答辯通過率都只有50%。沒通過的話,時間就很緊,院里的理由是中文系不能做純哲學題目,匆忙之間便改成了《“楚辭”在漢代的流傳和演變》。我假期回家帶了十幾本書,一個多月寫了三四萬字,不是很長。這個文章,系里看了還可以,黃先生也覺得不錯。我就把被斃掉的那篇《周易》的文章壓縮了一下,投到《中國哲學史研究》發表了[2]。發在頭版頭條,得了198 元的稿費,相當于五個月工資,當時可以買一套《漢語大詞典》。這個文章發表,影響還蠻大。還有一篇,《漢人觀念中的“辭”與“賦”》,是碩士論文的一部分,發表在《文學遺產》1989年第3期,那是研究生時候投的稿,拖了一年多才發出來。碩士研究生能發《文學遺產》《中國哲學史研究》,那時候覺得自己還是挺不錯的,去北大訪學也不怯場。
翟:您是起點高。
郭:黃先生是名家,在學術界很有地位。他是吳檢齋(承仕)和尚秉和先生的學生。尚秉和先生的《易》學堪稱當時天下第一;吳檢齋先生的學問也不用講,而且是章太炎的嫡系傳人。所以后來我考博士的時候,聶先生聽說我是黃先生的學生,那就完全是另眼相看。因為當年整理吳檢齋先生的遺著,北師大專門把黃先生請過去,住在小紅樓。那是1983年,在小紅樓住了幾個月[3]。
翟:您考研的時候為什么會選擇考黃壽祺先生呢?
郭:那時候不懂嘛,覺得自己的水平考名校考不上,考個福建師大總還是有點希望吧。那時候也不知道黃先生是著名教授,否則可能不敢報名。而且那一年只有他招先秦的研究生,完全是意外。我是在一個縣城的中學教書,就想著考個不是很有名的學校,能考上就不錯了。后來順利通過答辯,面臨就業問題。當時我也考慮過考博,準備報考南大程千帆先生的研究生,而且也去了南大,見到了千帆先生。但我回了漣源老家一趟,小孩實在是太可憐了,所以還是選擇了先工作,就去了湖南師大。因為我的碩士論文答辯主席是馬積高先生,馬先生覺得我還不錯。當時馬先生在湖南師大具有很高的威望,就讓我參加試講,講《九辯》。1988年1月,四個人去試講,十幾個人聽課,最后要了我一個。1988年7月,我正式到湖南師大工作。1988 到1989年一年時間,我發了五篇論文,在那個時候是了不得的事,當時的系主任彭丙成教授在大會上表揚我,老一輩的領導看到我都說:小郭,要保重身體啊,寫東西不要那么急。我當時列了一個表,寫了二十個題目,準備兩年內一篇一篇寫完,可惜那年發生了一些很特別的事情,這宏大的計劃也就未能完成,但我1989年還是評上了講師。
翟:當時您還不是講師?
郭:碩士要兩年才能評講師,當時我還是助教,1989年評的講師。后來學校要評“211工程”,鼓勵教師讀博。我當時已經是學校的學術梯隊成員,1993年評了副教授,就去考博,考北師大。那年聶石樵先生只招一個,我主要是擔心英語。最后錄取線50 分,我考了49 分。北師大當時有個不成文的規定,老先生和著名學者可以申請破格錄取,聶先生就打報告申請破格錄取我,所以在北京又讀了三年。1996年畢業后還是回到了湖南師大,1997年評上了教授,我還擔任了文學研究所的所長。到2001年,我就到了湖南大學。那時候湖大還只有人文系,中文、新聞、政管都在一起。2002年10月,文學院正式成立,中間是我在籌備建院。最開始我做文學院常務副院長(2002―2006年),實際上所有事情都是我在處理,教師也是我招進來的。從2003年開始,文學院慢慢形成了一支教師隊伍,學科也慢慢齊全。2004年開始招古代文學的碩士,那時候還沒有自己的本科生,2005年才有自己的本科生讀研。因為沒有博士,所以對碩士論文抓得很緊,要求很嚴,古代文學前面幾屆的碩士論文真的寫得很好。2004年,現當代文學也開始招碩士,到2005年獲批一級學科碩士點,2012年開始招收比較文學專業的博士生。所以我那時候做院長,又要管行政事務,又要做科研,對人的消耗太大了,從2002年一直到2014年,都是超負荷工作。我現在身體不太好,跟那時候的拼命有很大關系。
二、賦海大觀
翟:前面了解到您的求學和工作經歷,接下來是您治學的經歷。您最早的學術研究應該是從《周易》研究開始的。您選擇《周易》研究應該跟黃先生專治《周易》學有一定關系?
郭:緣起就在這里。我在1985年入學之后不久,黃先生和張善文師兄合作的《周易譯注》準備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他拿稿子讓我去校對。那時候還沒電腦,我就背著復印件,做了大概兩個月。就在這個過程中,開始有點興趣。后來黃先生在北師大出了主編的《周易研究論文集》,我也看了一看,當時還沒寫文章。第一篇論文是寫《老子》和《莊子》辯證思想的課程作業,那個是最早的。但是比較系統的研究是從《周易》開始的,因為要選畢業論文,就準備做《〈周易〉之“周”發微》,副標題是《論〈周易〉循環的變化觀》,準備就寫這篇文章,寫了三萬字左右。結果開題沒通過,不能做純哲學的論文。我覺得不能白寫,把這篇文章改了改,投給《中國哲學史研究》,就發表了。
翟:您后來又出版了跟《周易》相關的兩部著作,一部是臺灣三民書局1996年出版的《新譯易經讀本》,一部是廣州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周易譯注》。
郭:后面那個是一個小冊子,沒什么影響力,普及性的。
翟:但三民的那本還是很有影響力的。
郭:對,那個影響比較大,在臺灣影響還蠻大。
翟:這個書稿跟您碩士階段的《周易》研究也是有關系的。
郭:是有一些關系,一些觀點貫徹在里面。但這個再怎么說也是個譯注,不是純學術性質的。實際上我在臺灣三民書局還出版過一本《新譯尚書讀本》,應該是2005年,是三民約的稿。不過我對《尚書》從未有過系統的研究。
翟:您后來轉向了辭賦研究。
郭:后來因為要改論文,碩士論文就改成了《“楚辭”在漢代的流傳和演變》,寫完以后我把其中一個部分投給了《文學遺產》,就是《漢人觀念中的“辭”與“賦”》,大概是1989年收到錄用通知,我當時已在湖南師大工作,于是把作者單位改成了湖南師大。我就這樣開始做“楚辭”,把方向完全改過來了。所謂“‘楚辭’在漢代的流傳和演變”,就包括《楚辭》本身在漢代的流傳,也包括騷體也就是楚辭體在漢代的演變。后來博士論文做騷體文學,也可以說是這個的延展。
翟:黃先生本身也做“楚辭”研究嗎?
郭:也做,他和他的碩士生,梅桐生師兄,出版過一個很流行的本子,叫《楚辭全譯》。
翟:您從《周易》轉到“楚辭”研究的契機是什么呢?
郭:就是改碩士論文選題。
翟:選擇“楚辭”跟您湖南人的身份有關嗎?
郭:應該是有一定關系的。
翟:您的生日是農歷五月初三,恰好在端午節前兩天,跟這個應該也有很大的關聯?
郭:那個當時都沒怎么想,但跟湖南人肯定是有關的。
翟:您碩士畢業后到湖南師大工作,馬積高先生主編的《歷代辭賦總匯》是1991年開始編纂的。
郭:我的碩士論文答辯是馬先生做主席,我到湖南師大跟他也有很大關系。我到湖南師大以后不久,馬先生準備編《歷代辭賦總匯》,把我們幾個青年教師都納入編委會,做分冊的副主編,其實是通過這種方式來培養人。我那時候花了很多精力去做,主要是搜集文獻,各方面的文獻。記得有一個暑假,我在湖南圖書館古籍部查了整整一個月,短褲赤膊,中午關在里面不出來,確實很辛苦。我雖然是做魏晉南北朝這一部分,但是實際上搜集的資料主要是其他時段的。
翟:我看到您之前回憶馬先生的一篇文章,提到您1993年去北京讀書,馬先生還委托您收集跟辭賦相關的材料。[4]
郭:對,在國家圖書館(原北京圖書館),我復印了很多別集的卡片,我記得是用一個旅行包提回長沙,就是摸底。搜集卡片是在老館,我還在新館拍過膠卷,一張張的照片這么拍,因為不準復印。也抄過一些零碎的材料,因為覺得拍照太劃不來了嘛。反正花了不少的精力。
翟:《歷代辭賦總匯》最終在2014年由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了,出版也很坎坷。
郭:有很多不全面的地方嘛,校對也拖了很久。有資金的問題,有文獻不足的問題,校對、排版的問題,非常復雜。2014年出版的時候,在貴陽開全國書博會,《歷代辭賦總匯》新書發行式,我和許結教授都去發了言,他是作為賦學會會長,我是作為編纂委員會的代表。
翟:《歷代辭賦總匯》目前影響蠻大,但也存在一些問題。
郭:錯誤肯定不少,這是避免不了的。像《續修四庫全書》里面的辭賦就沒加進去,我們當時提出來加進去,但來不及了。
翟:您的博士論文題目是自己選的還是聶先生建議的?
郭:自己選的。《漢魏六朝騷體文學研究》,實際上跟碩士論文有關系,另外自己也確實想做一下,做大一點。
翟:1997年,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您的博士論文,可以說是騷體文學研究的開山之作。“騷體文學”的提出有什么契機嗎?
郭:“楚辭”在后世的流變,實際上游國恩先生早就提到過,我就想做“楚辭”的后身。《楚辭》本身就這么幾篇,范圍太窄了,我也想拓展一下。我本來想做一部整個“楚辭體”文學的演變史,但“楚辭體”不是特別好聽,不順口,所以干脆就改叫“騷體”。
翟:這跟前人提出的“騷體賦”也有一定關聯。
郭:有一定關聯。但不僅僅限于騷體賦,整個騷體形式的作品都納入其中。這個概念提出來,慢慢也有不少人去做這個領域的研究,也有一些碩士論文。
翟:您在《漢魏六朝騷體文學研究》的《后記》中提到過,“騷體與其他韻文”本來也是博士論文的一部分,但后來沒有放進去。[5]
郭:覺得太大了,不平衡,當時也沒有精力去全部完成,就沒放進博士論文里面去。所以將收集好的資料留在那里,后來加了一些材料充實,成了另外一部書,就是《楚辭與中國古代韻文》,2001年在湖南師大出版社出版。
翟:這本書在學術界的影響力也是非常大的。
郭:應該說也還有一定影響。
翟:這兩本書可以說是奠定了您在辭賦學界的地位。
郭:如果看引用率,反而是《先唐辭賦研究》比較高一些。
翟:200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先唐辭賦研究》,其實是一本論文集。
郭:對。擇幾個專題,把相關的、自己感覺比較有代表性的論文放進去,做一個集子。
翟:您在《靜一學術論叢總序》里面提到2004年院里出版過一套五本的“側陋論叢”[6],《先唐辭賦研究》應該就是其中之一,但好像封面、版權等信息里都沒有提到“側陋論叢”。
郭:應該是最初有將這本書納入這個論叢的想法,后來因為某種原因卻沒納入了。大概是這樣。
翟:2007年您又在中華書局出版了《辭賦文體研究》,也是“靜一學術論叢”中的一部。
郭:對,這是國家社科基金課題的結題,和陳冠梅(1997 級碩士,湖南大學文學院副教授)、劉偉生(2004 級碩士,湖南工業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教授)合作的,都是課題組的成員。
翟:2017年3月湖南大學辭賦研究所成立,2018年10月又承辦第十三屆國際辭賦學學術研討會,這是學院在辭賦學領域的新發展。您大概從2002年開始,關注到辭賦與詩歌中的女性描寫,申請了兩個湖南省課題,“漢魏六朝詩賦中的女性題材與性別表達”和“魏晉南北朝詩歌之女性書寫研究”。為什么您會從辭賦轉到女性文學研究呢?
郭:契機是因為研究南朝辭賦里面的女性描寫很多,慢慢就轉到這方面來了。也發了一些論文,在《文學評論》發了一篇[7],還全文譯成英文發在《中國文學研究前沿》[8]。這些研究將近有十篇論文。這個領域本來想寫成一本書。我現在有三部書稿是可以出版的。一是《漢魏六朝辭賦史》,已經基本寫完了,三十多萬字,還有一個概論沒有寫;二是給研究生開設的“漢魏六朝文人詩歌研究”課程講義,這是已經大體成型了的;三是《漢魏六朝詩賦中的女性題材與性別表達》,也有十多萬字的東西了。
翟:還可以再出版,學生都可以幫忙校對。
郭:也還沒有完全寫好,所以有很多遺憾的事。
翟:您近期的研究,從辭賦、詩賦中的女性文學又轉向了域外漢學。
郭:這個契機就是文學院好不容易爭取到的比較文學博士點。要帶比較文學的博士生,沒有辦法,不得不向這個方向轉。首先就從康達維教授那里做起。我英語不行,其他方面也還了解一些。最早是鐘達鋒(2012 級博士,現任教于南昌大學外國語學院)做康達維的《文選· 賦》英譯研究,題目是我建議的,材料也幫他收集了一些,寫作還是他自己,他的語言表達能力各方面還不錯的。馮俊(2012 級博士,現任教于湖南大學)也是建議了題目,《英美〈離騷〉翻譯和研究》。因為她跟我聽了一些《楚辭》的課程,又是英國語言文學的碩士,適合做這方面的研究。接下來就是日本文學。李慧(2014級博士生)做林羅山,是因為在外面開會,受到日本人的啟發;邱燕(2015 級博士生)做日本平安時期的辭賦。
翟:您總計指導了7 個博士,有4 個做域外辭賦學研究。
郭:主要是這4 個,辭賦為主體的。其他3 個,剛畢業的范瓊山(2014 級博士)是做越南喃詩傳,涂鴻(2015 級博士生)是做中日耽美文學比較,徐華(2015 級博士生)做蘇軾的海外傳播研究。
翟:您從辭賦研究轉到比較文學,還是比較順利的。
郭:當然也是經過思考的,因為招了比較文學的博士生,還是要向這個方向轉。院里申報這個博士點的時候就已經思考過了,否則的話無法銜接。不過我指導的博士生還是以域外的辭賦研究為主體,與我以前的研究密切相關。
翟:前面是您的學術緣起與轉向。您還出版過一部長篇歷史小說《趙匡胤》,最早是2000年在蘭州大學出版社出版,后來華夏出版社在2007年、2013年兩次再版。為什么會創作這樣一部小說呢?
郭:我博士畢業工作以后,有一段時間對學術極度不感興趣,剛好蘭州大學出版社那邊約稿,計劃出一套歷史小說。方銘教授推薦了我,他本科是蘭州大學畢業的。出版社方面約我寫《趙匡胤》。以前也沒寫過長篇小說,就想寫一寫試試看。我從1996年寫到1998年,中間也有個看史料的過程。好像當時策劃是十本或者八本書,結果有人交稿有人沒交稿,最后收到大概五六部。出版社方面看了之后不滿意,但覺得我那部稿子還不錯,就單獨把我這本出版了,其他的都沒出。
翟:您在之前有過文學創作嗎?
郭:偶爾寫過散文之類的。
翟:發表過嗎?
郭:沒投過稿。
翟:為什么方銘教授會介紹您寫小說呢?
郭:朋友嘛,他覺得我們搞研究的,寫這個應該也可以。后來蘭州大學出版社的社長調到華夏出版社當社長,又派一個編輯跟我聯系,說要出我這部書,放到他們企劃的一套書里面,但是不要這么長的篇幅。我就讓仲瑤(2006 級碩士,現任教于浙江大學人文學院)幫我壓縮,我再過一遍,減了幾萬字。到2013年重新改了一個版式再版。
翟:您后來還寫過小說嗎?
郭:后來沒再寫。
翟:有沒有創作的計劃?
郭:以前是有,以前想寫一個家族小說,退休以后。我退休以后一般不會再做學術,因為我也就這個水平。我受的教育有很大的局限性,讀了初中沒讀高中,大學讀的專科沒讀本科,嚴重的殘缺,不像你們那樣受過完整的、體系性的教育。你別說,這個東西很重要的。另外還有年齡的問題。我碩士讀完已經34 歲,工作幾年去讀博,博士讀完42 歲,接下來為生活奔波,為行政分心,也只能這樣了。文獻方面不是我的所長,理論方面又不是特別厲害,所以想做出一流的東西,說實在的,很困難。
翟:您認為目前國內學術界一流的學者需要哪些方面?
郭:一流的學者,總要有幾個東西。要么做文獻做得很扎實;要么理論方面很突出,能夠創新,腦子很活;要么就是有外語的訓練;要么就是有很厲害的活動能力。反正要有某一方面比較突出,要有所長,但像我這種情況,各個方面都有很大的局限性,所以我說也只能是到這個地步。如果我不做院長,可能會好一點。從2002年一直到2014年,浪費的時間太多了。這十幾年又是精力最旺盛的時候,80%的精力都放在行政上面。學生那里還要放一部分吧,我對學生還是比較負責的。哪還有多少時間去做自己的研究?像我前面說的這三部書,我在這些領域有些想法,也是可以拓展的,但也沒有去做。真正寫得好的文章,下了功夫的,我自己也清楚,就是騷體方面的那些,例如《“七”體的形成發展及其文體特征》《略論楚辭的“兮”字句》《騷體賦的界定及其在賦體文學中的地位》《楚辭與七言詩》《再論楚辭體與七言詩之關系》等等,大概有那么十幾篇吧,應該比較扎實。《人大復印資料》一共復印了我18 篇文章,這還是比較客觀的,也是比較有代表性的。當然,我覺得還是有那么幾篇被遺漏了。
翟:其實對于一個學者來說,有十幾篇論文能夠真正傳世,也是非常難得的。
三、薪火相傳
翟:前面是對您學術和創作的了解,下面再了解一下您對學生的培養。根據我們的統計,您從1997年開始培養研究生,到2016年最后一級,20年的時間,一共培養了61 個碩博士,其中博士7 人,湖南師大時期碩士6 人,湖南大學碩士48 人,還有一個訪問學者。除了本科生,總共62 個學生。聽說您在湖南師大時期培養研究生是帶完一屆再招下一屆。
郭:我是1997年開始招研究生的。第一屆是陳冠梅和玄桂芬。陳冠梅后來去南大跟莫礪鋒教授讀博,現在在院里任教;玄桂芬后來沒做學問了,先去廣州,后調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1998年就沒招了,我說要等到第一屆畢業以后才招。2000年,第一屆畢業,我又招了四個,楊賽、白崇、宋志民、李艷。那時候,讀研的學生一般都是要求考博士的,后來慢慢就沒那么強調了。白崇考上浙大,跟林家驪教授讀博,現在在廣東技術師范大學文學與傳媒學院;楊賽去了上海師大,跟曹旭教授讀博,現在在上海音樂學院,他主持國家藝術基金古譜詩詞傳承人才培養基地,在全國做古譜詩詞創作和音樂推廣,影響還蠻大。宋志民現在在長沙教育學院。
翟:湖南大學時期呢?
郭:我在湖大文學院,一直有很多很別扭的事情。剛開始招收科學學位的研究生,想招多少就可以招多少的時候,我作為院長,覺得招多了太濫,便規定每個導師招研究生不能超過四個名額。所以我每年最多招四個學生,要么就是三個。再后來學校開始限制科學學位研究生的數量,我們院里的招生名額有限,弄得很被動。現在全國都是向專業學位方向走,招專業學位的研究生,科學學位的也就控制得變少了。
翟:湖大文學院是2005年拿到碩士授權點,您最早是在2004年開始招收研究生。
郭:2004年招了四個,劉偉生、羅慧、曾偉偉、榮丹。
翟:您在湖大打破了師大時期帶完一屆再招下一屆的規則。
郭:對。沒有辦法,整個形勢在發展變化,不可能再這樣做的。我在師大的時候,雖然是文學研究所的所長,但行政方面的事情我不負責,可以專心帶學生。
翟:您在湖大培養的研究生,至少有7 人后來繼續讀博,現在在各個高校任教;其他的也大多在教育機構工作。您一般是如何培養研究生呢?
郭:培養學生,首先入學的時候就會跟他們談一次話,告訴他們應該怎么樣去讀書、學習。接下來就是開一些書目,各個方面的,自己選擇精讀、泛讀,每隔一個月聊一次,匯報這個月的讀書情況,有些什么想法、困惑。一般都是這樣的。如果正常的話,要持續一年左右。在第二個學期,就看學生對哪方面感興趣,慢慢選定一個大的研究方向,再確定一個題目。如果學生中有哪個比較不錯,就讓他早點確定題目,或者給一個具體的題目讓他去寫,把這篇文章用一年的時間打磨出來,爭取發表。一般就作為省優秀碩士論文去打磨。我帶了好像四篇省優碩士論文。碩士論文沒有國優,省優就是最高的。師大是楊賽,好像是整個文學院那一年唯一的一個。湖大這邊第一個是毛錦裙(2005 級碩士),接下來是仲瑤,接下來是吳春光(2007 級碩士)。鐘達鋒是國家獎學金和校長獎學金。
翟:現在評省優要發表兩篇C 刊了。
郭:在湖大,兩篇C 刊都不夠,現在要一篇重點期刊,也就是說,碩士生要發表一篇《文學評論》的論文,才有資格出校門參評。太可笑了!
翟:我之前統計過我們院古代文學碩士學位論文的總目。您指導的學生學位論文主要還是側重于歷代辭賦的文本研究,也有辭賦研究述評,以及由辭賦拓展出的其他領域,那面對跳出您專業之外的選題呢?
郭:當然主要還是尊重學生意愿,有些學生有自己的想法,也可以的,像孫磊(2011 級碩士)就是做文論方面的(《論王弼易學對〈文心雕龍〉的影響》)。但做散文研究的就比較少。
翟:其實學生選您做導師的時候,基本就確定以后會做辭賦研究這一方面。
郭:對,學生自然也有這個想法。
翟:今年您有五個學生畢業,最后一屆碩士研究生(2016 級)三人,還有2014 級越南籍博士范瓊山和2012 級博士馮俊。范瓊山應該是您帶的唯一的留學生博士。
郭:之前還有一個馬思清(現任職于美國俄勒岡大學東亞語言文學部),拿的富布賴特獎學金(2011年9月-2012年12月),是訪問學者。
翟:您之前提到我們院最初的研究生培養質量是很高的,近幾年的論文質量有所下降。
郭:不是有所下降,而是下降得很厲害,這種情況已經有五六年了。
翟:您覺得主要原因是什么?
郭:很復雜。首先是大環境,社會就是這樣的。學生來了,大家都是為了完成程序,在湖大讀個碩士,將來找工作好一點,很少有人真的是為了做學術。這是學生方面。老師方面,科研壓力很大,帶的研究生又多,各種類型的,在學生身上花的精力也沒有那么多。
翟:有些碩士連基本的學術規范都做不到,但很多是老師在課上、跟學生聊天的時候都講到過、強調過的。
郭:這個說實在的,實際上老師最要緊,應該在課程里面就涉及這些問題。我以前上研究生課,在課程內容以外,其實已經提供了很多思路、規范這些方面的知識。一門研究生課程不是那么簡單的,往往需要很多年的積累。在一個課程體系里面,至少要有四五門課作為骨干課程,能夠給學生帶來很多方面綜合性的提升,否則的話,課程體系真的是有問題的。不是我自夸,文學院古代文學里,我的兩門研究生課程,真的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也就是“楚辭研究”和“漢魏六朝文人詩歌研究”。在上課的過程中,學生可以學到很多知識,而治學方法是自然而然地在這里面體現出來的。我不搞虛的,通常也不組織討論,因為那樣的話就那么幾個人得益,而更多的同學就混過去了。上課就是傳統的講授,受益面比較廣。如果沒有這么幾門課程作為中堅,效果不好,很多同學就這么飄啊飄的飄過去了。
翟:關于上課,您應該是1988年就開始給學生開課,到現在有30年時間了,您的課也非常受學生歡迎。您覺得上課的秘訣應該是什么?怎么才能把課上得很好?
郭:首先是對自己上課的內容非常熟悉,在上課的范圍里要做過研究,光是拿著教材去上肯定是不行的;第二個是要有比較好的表達方式,因為要去吸引學生聽,要把專業方面的研究通過學生喜歡的方式去表達出來;同時思路要清晰,不要有太多的廢話。
翟:也不要太多的延伸。
郭:延伸倒是可以的,往往學生能夠記住的、印象很深的,就是延伸的部分。但不能無限的延伸,延伸到一定地步要能及時收回來。
翟:您上的研究生課一直是“楚辭研究”和“漢魏六朝文人詩歌研究”這兩門。
郭:主要就是這兩門。《易經》我一直沒有上,就是開講座,給全校本科生開過公選課。因為《易經》這個課,我總覺得,學生讀《易經》能不能真正接受,值得思考。
翟:其實可以作為一門研究性課程來開設。
郭:是,但學生程度一定要好,否則的話開不下去的。我也是想了好久,所以一直沒開。其實也是一門很成熟的課了,我在北大、清華辦的總裁班講了好多年。但在學校開這個課,選的人很多,不過70%的學生真的就是為了要成績,那學《易經》怎么學得下去呢?開始可能還感興趣,后面就沒興趣了,要么就要求你講演卦、風水之類的東西,要么就聽不下去,所以一直沒給研究生開這個課。另外當然跟我一直做行政也有關系,行政方面花的精力太多了。
翟:您上的本科生課程,除了作為核心課程的“古代文學”(先唐段),還開設過其他課程嗎?
郭:開過“中國古代文化與文學”,那是泛泛的,給全校本科生開的。
翟:您基本就是開設比較固定的幾門課。
郭:對,沒多開的。好像還給新聞學院上過一次唐宋文學。
翟:前面涉及您對學生的培養,還想更多了解下您的師長對您的指導。您覺得在您的治學和工作中,對您影響比較大的,有哪幾位先生?
郭:影響比較大的,首先是兩位老師,還有馬先生。
翟:他們對您的影響主要是在哪些方面呢?
郭:影響肯定是綜合性的。治學方面是馬先生影響最大,因為一直跟著他做辭賦研究,時間比較長,交道也打得多,在做人、治學上受他的影響還是比較大的,路子都有點像。但是不管怎么樣,我做人比馬老師差遠了,比黃先生、聶先生都差遠了。人的性格真的是沒法改的,我為人太苛刻,太苛嚴,不管對自己還是對他人。現在想起來對學生、對你們都有點太兇了。對同事也太苛嚴,文學院有的老師看見我都害怕。所以這也是個悲劇,所以就不能平等地與他人交流。
翟:現在好一點了。
郭:現在應該好一點了。
翟:其實您遇到黃先生、聶先生、馬先生的時候,已經是他們的晚年了,所以是性格比較平易的時候。
郭:他們本來就性格平易。
翟:每個人性格不一樣,特別是您在院長這個職位上。
郭:即使不做院長也還是苛嚴,也是這么一個性格,不太愿意跟人打交道,這是很大的局限。
翟:看到黃先生給您寫的“忍默勤”這三個字。
郭:是的,我寫過一篇紀念黃壽祺先生的文章[9]。那是在西安碑林,我陪他去參觀,看到一塊碑上面有這三個字,他就跟我說,這三個字是做人的準則,我只做到了其中的一個字:勤。不能夠忍,忍包括忍受和堅忍。默就更加做不到,好勝。那時候三十來歲,喜歡跟人爭辯,絕不服輸。現在想起來,何苦呢?
翟:您在福建師大和北師大時,除了黃先生、聶先生之外,有沒有跟哪些老先生有過交游?
郭:有一些,不多。福建師大時跟陳祥耀、穆克宏先生,主要是上課,有時候去拜訪,穆先生跟我導師住在一個小區。他們對我也是比較關注的,覺得我在學術方面是可以發展的。北師大跟啟功先生、韓兆琦先生、張俊先生等,多次拜訪過他們,但交往也不是特別多。
翟:啟功先生給您上過課嗎?
郭:沒有。我讀博士的時候,博士專業方面的課程很少用授課的形式,但有必讀的書目,要交課程作業。古代文學就我一個人,也不好上課。
翟:聶先生是怎么指導您呢?
郭:就是不定時地去坐一坐,聊一聊,專業方面的、學界掌故方面的、為人方面的,什么都聊,范圍很廣。聶先生雖不上課,但在這樣的交談中講了很多師門治學風格、尋找問題、論文寫作等方面的問題,聶先生還講了許多做人的道理,受益更甚于古板的、程式化的授課。
翟:您博士論文答辯時有哪些先生參加呢?
郭:褚斌杰先生做主席。我跟褚先生聯系較多,也勉強算是褚門弟子吧。其他答辯老師還有費振剛教授、陸永品研究員、鄧魁英教授、張俊教授、韓兆琦教授和柴劍虹編審。
翟:答辯主席相當于是座師。
郭:是的,另外我也經常去他家里請教。而且褚先生長期做中國屈原學會會長,加上方銘教授的關系,自然交往多一些。
翟:您后來回湖南師大工作,在馬先生之外,像宋祚胤、周秉鈞等老先生有沒有交集?
郭:都見過。宋祚胤先生那里去過幾次,因為做《周易》嘛。周秉鈞先生是做古漢語,交往不多,但也去拜訪過,他也知道我。
翟:您之前提到,在治學方法上受馬先生影響最大。
郭:應該說走辭賦這條路受馬先生影響最大。方法的話,有一些。其實方法最重要的還是在碩士階段。那時候八十年代,讀了一些西方的理論著作和國內一些前輩的研究成果,慢慢在學習和寫作中形成了自己的路子。文獻方面卻沒太注意。
翟:您覺得老師對您的影響主要是通過哪些形式呢?
郭:老師的影響當然有他們的教導和他們的著述,有時候卻是無形的。比如說,我上穆克宏先生的《文心雕龍》課,寫了一篇文章,說由建安時期的重質到西晉時期的重彩,再到劉勰《文心雕龍》把質和彩結合起來,形成情質理論。穆先生看了以后表揚我,說我的思路非常清晰,能夠發現問題。但是黃先生看了卻不以為然,說我是先有想法,再去論證。這個影響就在那里。他說你要從材料得出結論,不能先有想法再去找材料。這篇文章明顯就是這樣的,確實是主觀色彩很強烈,但看上去很漂亮。事實上,想要有論文出來,確實要能發現問題,但要論證得豐滿、成立。老師的影響有時候就是那么幾句話,但給人以很大的啟迪。像馬先生,我記得那時候他生病了,他跟我講到做學術的格局問題,勸我不要在騷體文學上糾結得太久,畢竟那不是文學的主流。意思就是說,你還是要搞到主流文學研究上去。騷體文學研究得再深,那也是個次要的領域。
翟:所以還是強調要做一流的、主流的研究。
郭:對。
翟:那我們采訪就到這里,謝謝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