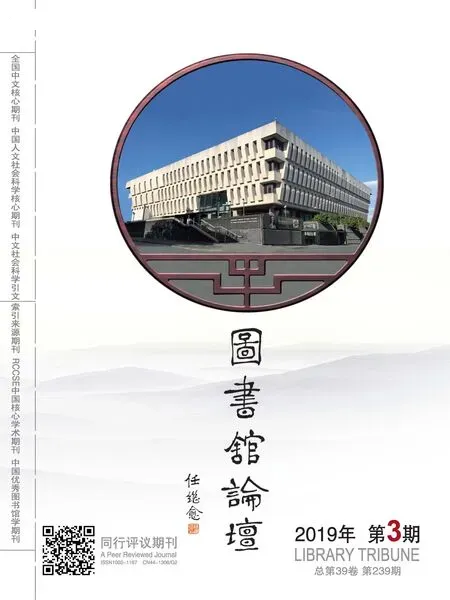創新機制、重心下移、嵌入決策過程: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下半場”*
李 剛
2013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倡議。根據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提出的時間表——到2020年實現總體目標,那么2013年以來的這五年應屬于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上半場”,未來三年應該屬于新型智庫建設的“下半場”。
2016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近年來,哲學社會科學領域建設智庫熱情很高,成果也不少,為各級黨政部門決策提供了有益幫助。同時,有的智庫研究存在重數量、輕質量問題,有的存在重形式傳播、輕內容創新問題,還有的流于搭臺子、請名人、辦論壇等形式主義的做法。”習近平總書記的總結仍然是對五年新型智庫建設切中肯綮的評估。
經過這五年的實踐,我們對新型智庫建設的深遠意義認識得更加清晰。
第一,新型智庫建設成為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抓手和重要路徑。什么樣的國家治理體系才是現代化的?什么樣的治理能力才是現代化的?現代化不光是工具層面的,也應當是價值層面的現代化,現代化的治理體系和現代化的治理能力體現在國家治理的價值、理論、方法、工具所具備的現代性。以人民為中心的法治化、規范化、科學化、協同化、效用化的治理體系才是現代化的治理體系。綜合運用并發揮國家治理體系的最大效用,達成全民福祉的最大化,形成“良好治理”,就是現代化的治理能力。新型智庫無疑是觀察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性的一個重要指標。加強新型智庫建設實質上就是在促進國家治理的現代性成長。
第二,新型智庫建設繼承了儒家“學為政本”傳統,促進了國家治理的科學理性和專業理性。儒家強調“學為政本”,這和黑暗的中世紀歐洲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有思想家說,中國文明是“早熟”的文明,這是與西方傳統對比后得出的結論。秦漢以后,中國就建立了高度理性的非世襲的郡縣制和官員任期制。到隋唐科舉制已經成為官員選拔的主要制度,比近代歐洲文官制度早了數百年。可以這么說,中古以后中國國家治理模式就是建立在知識基礎之上的賢人政治。但是,近代以來,西方逐漸走向了“學為政本”的國家治理法治化和專業化的路向,中國反而陷入積貧積弱、四分五裂的軍閥割據,國家治理不再依賴學術和知識共同體,而是粗鄙的武夫和民粹,學為政本的傳統被迫中斷。現代智庫雖然起源于西方,但卻是為數不多的可以嫁接到中國文化傳統的一種現代西方國家治理架構。現代智庫體現的“學為政本”的賢人政治精神契合中國文化的精神,這就很好地解釋了中國知識界為何對建設新智庫充滿熱情。
第三,新型智庫建設本質是開放言路,建立制度化的“政-知”“政-產”“政-媒”“政-社”意見交通渠道,調動各行業知識精英參與國家治理的積極性。根據我國憲法,人民在國家治理中處于中心地位,但是在國家治理的體系和實踐中,決策體系相對封閉,人民參與國家治理的渠道和機會均有限。實際上,不要說普通群眾,就是高級知識分子參與決策咨詢的選項也不多。新型智庫建設不僅給政府的內腦——各級各類研究室帶來了專業化的決策咨詢工作理念,而且通過外腦——高校研究機構、社科院、黨校行政學院、主流媒體的智庫化轉型,使得理論界、社科界、高等教育界的專家獲得了制度化的建言獻策管道。如果說“內腦”是新型智庫建設中的存量部分,那么“外腦”就是智庫建設中的增量部分。如果說“內腦”是以往決策咨詢的主體,那么現在“外腦”和“內腦”則獲得了對等的主體地位,雖然它們的話語權并不相等。這種不相等并不是由于到決策中樞的距離遠近,而是來自“內腦”和“外腦”的分工和專業素養。在短期和應急決策咨詢上,“內腦”發言權較大,而在長期和基礎的決策咨詢中,也許“外腦”話語權更大。決策咨詢體系增量主體的擴大促進了國家治理體系的開放性、協商性、民主性、包容性。
第四,新型智庫建設促進了有利于開展政策辯論的理性“第二公共政策空間”。互聯網的興起雖然極大地提升了政策辯論的參與度,但是有時候這種參與也是無序的和非理性的,這往往使得正常的政策辯論在網絡空間中無法開展。一方面是由于長期以來民眾接受的政策素養教育嚴重不足,的確不知道如何開展一項嚴肅的政策辯論;另一方面是因為一部分自媒體人和公號的寫手為吸引眼球,無所不用其極,攪亂了正常的政策辯論。而在新型智庫建設過程中,政策共同體的要素和邊界逐漸明晰,形成了包含黨委政府、人大政協、政策研究機構、新型智庫、主流媒體等部門的專家組成的“第二公共政策討論空間”。在這個共同空間中,智庫起到了連接器和催化器的作用,推動了理性的公共政策辯論和協商。
正是因為認識到新型智庫建設是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難得機遇,以天下為己任的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界才懷著滿腔熱情和歷史使命感積極響應中央的號召,努力推動新型智庫建設。
如果從新型智庫實體建設來說,取得了巨大的成績。據中國智庫索引(CTTI)統計,截至2017年底,我國已有九大類604家智庫,分布于50多個戰略和政策領域。根據規模和研究能力,這些智庫分為國家高端智庫、省級重點智庫和普通專業智庫三個層次,其中還包括一些按照“民非”、社團或者企業形式運行的社會智庫。另外,在智庫的制度建設和運營管理上也探索出不少有益的經驗,涌現出很多可圈可點的案例。
2017年,南京大學中國智庫研究與評價中心和光明日報智庫研究與發布中心征集評選了一系列值得重視的新型智庫建設案例,例如“復旦發展研究院:始終堅持國際化路徑促進傳統論壇轉型為智庫論壇”“同濟大學財經研究所:智庫研究要抓重大現實問題要突出前瞻性——《重新認識和準確定義新時期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北京市信訪矛盾分析中心:智庫實證研究的佳作——《社會矛盾指數研究》”“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三十年專注農村社會調查——從走村串戶到構建大數據智庫調查服務平臺”“浙江師范大學非洲研究院近年來立足中非合作實踐需要,成功探索出了一條學科、智庫、媒體三位一體的發展路徑”“江南大學食品安全風險治理研究院旨在打造小而專、小而精、小而強,國際化視野的高校專業智庫”“長江教育研究院:充分利用人大政協渠道,搭建一流專業論壇,十年如一日專注中國教育現代化”等等。
對照《關于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提出的到2020年要實現的總體目標,新型智庫建設上半場沒有解決好的問題有以下幾點。
第一,我國智庫產業集中度和產業集群性很低。實體數量的增長并不意味著新型智庫就形成了“黨政部門、社科院、黨校行政學院、高校、軍隊、科研院所和企業、社會智庫協調發展”的局面,以及“定位明晰、特色鮮明、規模適度、布局合理的中國特色新型智庫體系”。總體上說,我國智庫機構“散”“弱”“小”的局面并未發生根本改變,其實由于數量增加了,智庫類機構“散”“弱”“小”的總體情況可能反而更嚴重,這導致我國智庫產業集中度和產業集群性很低。
相較而言,美國智庫產業的集中度和集群性很高。華盛頓智庫街上的近400家美國智庫,三分之一以上的全職研究員和職員都在百人左右。美國西海岸的蘭德公司有員工1850人,芝加哥大學的全美輿情研究中心(NORC)有全職研究員和職員600余人。可以說,美國智庫不僅多,而且單個規模大、研究咨詢力量強、影響力大。反觀我們的智庫,雖然中國社科院全院總人數4200多人,有科研業務人員3200多人,但這些研究人員分屬31個研究所、45個研究中心和120個學科,每個研究所(中心)擁有的研究人員平均起來不過42人。更關鍵的在于,這些研究所和研究中心都是獨立行政單元,跨所(中心)的協同合作非常困難。這種現象不僅中國社科院存在,不少省級社科院也是如此。至于高校智庫,“小”“弱”“散”的現象則更嚴重。“C9聯盟”中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機構動輒數百個,但是其中絕大多數都屬非實體非法人的教授課題組,往往會因為教授“轉會”或者退休而“人亡政息”,形成大量“僵尸機構”。可以說,我國智庫體系中雜牌軍多、正規軍少,業余選手多、專業選手少,新智庫多、老牌智庫少。因此,中央抓國家高端智庫建設、省市抓重點智庫建設是非常必要的。如果不能把有限的經費和專家資源集中到一起,還是分散發展,那就不可能迅速改變新型智庫體系“小”“弱”“散”的特點。
我國的主要專家資源集中在高校系統,但是高校過于重視學科建設,把主要資源都投入到了學科建設。決定學科建設能否進入一流的主要指標主要包括縱向的項目、學位點、重點實驗室、戴帽子的各類人才數量、高水平論文和各類獎項等,遺憾的是新型智庫的質量和數量并不在其中,這就導致大部分高校對新型智庫建設都不夠重視,不愿意投入真金白銀。國家在一流高校里認定了14家高端智庫(含培育智庫),有些智庫的確發揮了智庫的功能,比如北大國發院、人大國發院和復旦中國研究院;但也有一些智庫還是以教學研究為主,轉型腳步慢了半拍;還有的高校雖然拿到了國家高端智庫建設的入場券,但是并未引起足夠的重視。
第二,新型智庫建設未能有效突破體制上的“三明治陷阱”。實體數量的增長并不意味著智庫研究質量的同步提升和新型體制機制的落地生根,我國智庫的治理體制當前難以突破“三明治陷阱”。2018年3月,黃坤明同志在國家高端智庫理事會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試點工作以來,中央和有關部門在經費管理、人員出國、獎勵激勵、會議管理等方面出臺了一系列含金量很高的政策,賦予試點單位很大的自主權和政策空間,但不少單位承接、落實還不到位,很多政策仍然懸置,人員管理、薪酬待遇、職稱評定、財務管理等方面的掣肘比較突出。
產生這種現象的根本原因是大部分智庫都是附屬型智庫。根據中國智庫索引的數據,我國智庫體系中95%的智庫都是母體機構下屬的非法人的實體智庫和非法人掛靠性質智庫。這些智庫外部治理結構類似三明治,三明治的上層是國家/省市部委智庫管理部門,中間是母體單位(比如高校、社科院),下層才是智庫。之所以稱之為智庫治理的“三明治陷阱”,是因為國家/省市部委智庫管理部門根本無法直接管理到這些母體單位下屬的非獨立智庫,而是要通過母體單位(也可以叫平臺單位)才能作用到智庫。母體單位(平臺單位)就像三明治的中間層,隔絕了國家/省市部委智庫管理部門和非獨立智庫之間的直接治理聯系,國家/省市部委智庫管理部門任何政策落地都需要母體單位(平臺單位)制定實施細則,或者經過母體單位(平臺單位)的認可同意配套相應的落地政策。比如,中央出臺的增加經費中專家勞務費用支出比例的意見,如果未經母體單位(平臺單位)認可并制定相應的實施細則和財務審批的流程,那么中央含金量很高的意見就不可能作用到非獨立智庫(三明治下層),非獨立智庫望眼欲穿的好政策由于三明治中間層的梗阻就無法落地,政策紅利也就無法釋放出來。
對于母體單位(平臺單位)來說,下屬智庫只是眾多業務單元之一,是否值得為中央/省市部委智庫管理部門的政策落實制定配套的細則和流程,還有許多其他考量。以高校為例,學科建設是主要任務,不可或缺,而智庫建設屬于錦上添花,可有可無。如果要中央/省市部委智庫管理部門的政策落實制定細則、配套資源,就會存在是否會激怒主體院系的問題。如果同意智庫增加經費中專家勞務費用支出比例,那么非智庫單位要比照執行怎么辦?不同意的話,非智庫單位會援例爭吵;如果同意的話,科研經費中學校分成勢必減少,傷及自身利益。因此,大部分高校都會對中央出臺的增加經費中專家勞務費用支出比例的文件采取置之不理的做法。三明治中間層對智庫宏觀治理影響巨大,可以說對非獨立智庫而言,母體單位(平臺單位)的智庫治理才是最直接最關鍵的,中央/省市部委智庫管理部門的智庫治理屬于天高皇帝遠、鞭長莫及。如何破解智庫宏觀治理中的三明治陷阱呢?根本解決方法是把非獨立智庫變成獨立法人實體機構。比如,南京大學為化解智庫治理的“三明治陷阱”,就讓下屬的兩家省級重點智庫——長江產經研究院和紫金傳媒智庫在省民政廳注冊為“民非”法人實體智庫,這樣一來三明治陷阱的中間層就不存在了。獨立的法人實體智庫可以直接執行中央/省市部委智庫管理部門的有關智庫治理的政策文件,學校內部其他院系和研究中心也無法援引這兩家智庫享受的政策紅利。為了讓這兩家智庫同時利用學校資源,南京大學還發文成立了南京大學長江產經研究院和南京大學紫金傳媒智庫。南京大學通過一個法人實體兩個牌子的方式成功化解了智庫治理的“三明治陷阱”。
第三,智庫的研究咨詢業務過于集中政策過程的前端,業務模式頭重腳輕。政策過程包含議程設置、政策辯論、決策與路演、政策教育、政策評估、政策反饋修正等,這是一個完整的“政策環”,每個環節都需要智庫參加,但是每個環節需要不同層次不同專業的智庫參加。如果從國家政策層面來說,在議程設置階段和政策辯論階段主要需要高層次高端智庫參與,其他層次的智庫由于缺乏全局性的視野和經驗往往就不適合此項工作。可是在政策評估環節,即使是地方智庫也可以從本地區出發對國家政策的執行情況開展評估和反饋。但由于我們智庫考核指標設置的問題——往往給與高層次批示極高的權重,導致幾乎所有智庫都在思考全國性政策議程設置問題,并就此寫內參、寫研究報告。這種定位錯誤,造成了大量的重復勞動和無效勞動,如雪片一樣飛向北京的內參其實大多數是沒有必要的。因此,絕大多數省級智庫不應該把業務重心放到全國性政策議程設置的決策咨詢工作上。
相反,大量的專業智庫應把業務模式重心下移和后置,把主要精力放到政策教育、政策評估和政策反饋上來。專業智庫不應該去當“國師”——為黨委政府出思想、出概念和出思路,而是應該承擔技術性支援工作。專業智庫的主要工作是調查研究,是采集數據、是數據分析、是建模計算,是協助政府腳踏實地的落實政策,是用自己的數據、計算能力評估政策和項目的執行情況并及時反饋給政府。對于專業智庫來說,可能核心能力并非思想力,而是調查、數據、計算、規劃、評估等能力。沒有這些核心能力,智庫只能開展定性研究,靠拍腦袋為政府出主意,那樣業務重心就浮于表面。
第四,智庫和政府內部研究機構是“兩張皮”,供給與需求之間的信息不對稱難以消除。智庫是政府的“外腦”,政府內研究機構是“內腦”。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加強決策部門同智庫的信息共享和互動交流,把黨政部門政策研究同智庫對策研究緊密結合起來,引導和推動智庫建設健康發展、更好發揮作用。”強調的其實是“內腦”和“外腦”的協同。“內腦”要指導、引導和推動“外腦”的對策研究,要解決政策研究和對策研究“兩張皮”的問題,要消除需求和供給之間的信息不對稱。這個問題之所以未得到有效解決,原因很多。首先,我國智庫體系中高校智庫比重過大。根據CTTI數據,全部CTTI來源604家智庫中58%屬于高校智庫。這種情況得到中國社科院評價研究院的《中國智庫綜合評價AMI研究報告》核心智庫目錄的印證。該報告確定了166家核心智庫,其中高校智庫有79家,比重為47%。高校智庫往往由傳統學術研究“翻牌”而來,更擅長的是學術研究而非對策研究。高校智庫因為固有的“師道尊嚴”文化,往往缺乏“客戶第一”的服務精神。智庫是一種高端的決策咨詢服務工作,不管是高端還是低端,只要是服務業,沒有“客戶第一”的服務精神,服務工作就不可能做好。因此,讓高校智庫主動對接政府研究機構,心甘情愿地為政策研究部門做好技術支援性工作——調查研究、采集數據、分析數據、撰寫研究報告初稿,幾乎是不可能的。其次,政府政策研究部門恐怕也未必看得上智庫,更不愿意和智庫共享數據和信息。坦率地說,二者之間也存在競爭關系,政策研究部門也有“教會徒弟餓死師傅”的憂慮。
解決這個問題的主要途徑還是智庫主動采用“嵌入式決策咨詢服務模式”。“嵌入式決策咨詢服務模式”是我們首次歸納的一個學術概念,指的是智庫的對策研究通過嵌入政府政策研究過程解決“外腦”和“內腦”協同問題。嵌入首先說明了智庫和政府政策研究部門之間存在著一定距離,存在一定的區別,嵌入也意味著智庫的對策研究有獨立的價值,有自己獨特的屬性——和政府政策研究部門相比,智庫研究可能更關心中長期問題,更關心基礎問題,更關心前瞻性問題。嵌入式決策咨詢服務包括政策過程的嵌入、決策咨詢流程嵌入、決策咨詢場景的嵌入和政策共同體的圈層嵌入。政策過程嵌入是指智庫應該嵌入一個政策的完整過程,和“內腦”開展緊密合作,從議程設置、政策辯論、決策與推廣、政策執行、政策教育、政策評估和政策反饋全過程的參與和發揮作用,不僅要關心政策文本的產生,還要促進政策文本的落地以及落地后的效果。決策咨詢流程的嵌入是指要在調查研究、數據采集、數據分析、分析研判和撰寫報告等過程中都和內腦緊密合作,充分發揮智庫技術支援的優勢,服務內腦的政策研究。決策咨詢場景的嵌入是指積極參加領導的調研活動、決策咨詢會議和政策路演活動,獲得決策咨詢活動的現場感與語境,如此才能了解政策產生的前因后果。政策共同體的圈層嵌入是指智庫要和政府決策者、政策研究部門形成密切的聯系,產生強烈的互信關系,這是其他三種嵌入的前提,也是結果。當然,政策共同體中并非只有決策者和政策研究者(內腦),還包含其他的要素,智庫要和這些要素之間都形成密切的圈層嵌入。如果智庫能實現四種形式的嵌入,那么就有可能解決對策研究脫離實際、不接地氣、沒有市場的困境,成為黨委政府想得起、用得上、離不開的智庫。
第五,智庫成果認定與激勵的指揮棒設計不合理。成果認定和激勵制度是引導智庫發展的指揮棒,但目前這個指揮棒設計不夠合理,是制約智庫健康發展的主要問題之一。我國智庫成果認定標準非常單一,從我們收集到的各種認定獎勵文本來看,各類智庫都看重批示的行政級別,無論是折算成文章還是直接獎勵金錢,都是行政級別越高的批示得獎越重。這種做法簡單粗暴,必然導致智庫只愿意為決策者服務而不是為決策過程服務,必然導致智庫只原意為高端決策者服務而不是為基層治理服務,必然導致著力揣摩領導意圖的政策研究而不是基于客觀事實基礎上的政策研究。其實,智庫所承擔的大量政策評估、政策宣傳等工作都不會產生批示,但是這些技術支援性工作恰恰是政府更需要的。因此,這些工作都應該納入智庫成果的認定范圍。政策評估等工作政府會以橫向項目的形式交給智庫,而在我們的智庫考核體系中,橫向項目恰恰是最不受重視的。我們認為,對于國家高端智庫和省級重點智庫而言,的確批示的權重應該大一些,因為這些智庫的主要功能是咨政建言。可是對于大多數專業智庫而言,用專業能力為黨委政府提供技術性支援工作往往不會產生批示,對它們而言,批示就不應該是主要考核指標。
五大問題能否解決好,決定了新型智庫建設下半場的成效。新型智庫體系建設要解決智庫產業的集中度和集群性問題,實體化和法人化是解決體制機制創新、克服“三明治陷阱”的重要途徑,業務重心下移和后置是解決智庫浮于表面注重形式傳播問題的重要思路,而推行嵌入式決策咨詢服務模式是解決政策研究與對策研究銜接、發揮內腦和外腦協同研究效應的重要選擇,智庫成果認定與激勵措施的調整則是最重要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