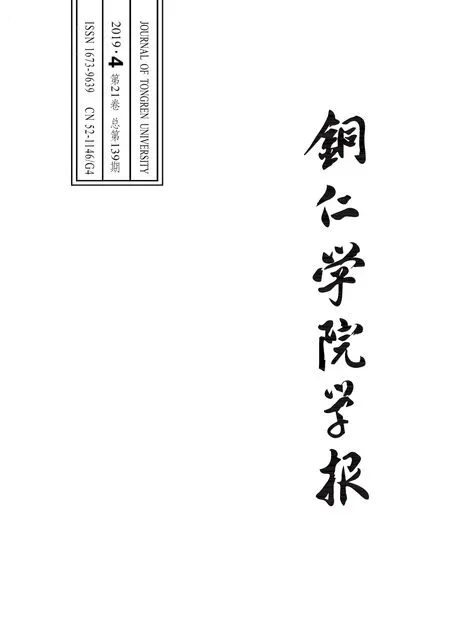《選》學的新境
范子燁
( 中國社會科學院 文學研究所,北京 100732 )
古人說:“《文選》爛,秀才半。”我要說:“《文選》爛,學者半。”熟讀《文選》的人,至少已經是半個學者了。我之所以如此說,是因為此書乃是我國中世紀的文化寶典,研究中古文化之一切問題,均離不開《文選》,對于文學史研究者來說,它更是不可或缺的枕中秘寶。而在祛除了“選學妖孽”的迷霧之后,《文選》受到了空前的推重。《文選》的誦讀之功,今人不如古人,《文選》的研究,今人常常在某些方面超越古人。就當代的《選》學研究而言,明顯分為四線陣營:第一線是關于《文選》本身的研究,包括作家、作品以及相關問題等等;第二線是關于以李善注為代表的古注研究;第三線是關于《文選》的傳播研究;第四線是關于《選學》史的研究,即對《文選》研究的研究。四線互補,氣勢磅礴,構成了一個龐大的涵蓋古今的《選》學體系。
本期梵凈古典學欄目推出的三篇文章,第一篇屬于一線研究,另外兩篇屬于二線研究。
孫少華博士的論文揭示了一個人們很少關注的重要問題,那就是中古文學的“文體流動”現象。“文體流動”是一個很別致很新穎的說法,這意味著任何一種文體都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具有動態特征的;這種動態的特征在于各種文體的深層互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少華對此問題的發現,源于他對《文選》諳熟。他的著眼點是蕭《選》中的吊文以及劉勰對“吊文”分類的認識。少華指出,從文體形式上看,《文選》“吊文”所錄賈誼《吊屈原文》和陸機《吊魏武帝文》,皆可稱其為“賦”,因為陸文屬于賦中常見的“主客問 答”體,但這種“主客問答”體被蕭《選》列入“設論”一類,而《文心雕龍》則列入“雜文”。這種現象說明文體本來就具有“雙重性”特征,即“吊文”從“賦”中析出,其內在的演變機制正如劉勰所說:“華過韻緩,則化而為賦。”這就是本文所說的文體的“流動性”特征。他認為,就“吊文”分類而言,《文選》是從作品內容進行分類,《文心雕龍》則是從作品的具體形式(辭、韻、情、理)上進行分類,二者同樣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顯然,中古文學的這種“文體流動”現象,對深入開展中古文學研究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由此,我也聯想到了中唐時代韓愈的“以文為詩”的問題。少華揭示了文學史中的恒量與變量的關系,他從恒量中看到了變量,從變量中看到了恒量,從而使得這篇短小精悍的論文充滿了辯證法的精神。這是一篇令人回味的好文章,倘若由此視角深挖下去,很可能揭示出我國古代文體演進的隱秘規律。而將《文選》與《文心雕龍》進行比照研究,這種方法也是非常科學的。《文選》學與《雕龍》學應當成為一對親兄弟。焉知曾經擔任東宮通事舍人并且深被昭明太子“愛接”的劉彥和沒有參與過《文選》的編纂工作?
趙建成博士的論文主要考察李善《文選注》所引《易》類文獻和《書》類文獻的問題。他帶著滿滿的自信,立足于當下豐富的《文選》版本材料和傳世文獻,并結合史志目錄與相關典籍中的學術史材料,對相關的文獻進行了徹底的盤點。他參考了前人的相關研究成果,并借助現代的電子檢索手段,最后考定李善《文選注》征引《易》《書》類文獻各12家,并加以適當考證,同時糾正了前人研究中的一些錯漏。李善注是我國古代的四大“名注”之一,其所征引的四百多種文獻大都已經亡佚了,在這種情形之下,這部“名注”就彌足珍貴。就此而言,建成君的研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我期待著他能夠寫出一部氣勢恢宏的“李善《文選注》引書敘錄”,為學界提供一部工具書式的大著作。
當然,近年來,隨著研究的深入,人們對李善《文選注》的學術態度越來越客觀,具體表現就是發現了這部“名注”存在的諸多問題。譬如,臺灣清華大學的朱曉海教授就是其中一位比較勁猛的著名學者。老友力之教授《班固“北地人”說辯證——以文選李善注所引范曄〈后漢書〉為核心》一文,則比較具體地探討了李善注的一個問題。在他看來,這是不可原諒的錯誤。《文選》卷1收錄班孟堅《兩都賦》二首,于“班孟堅”下,李善注云:范曄《后漢書》曰:“班固,字孟堅,北地人也。年九歲,能屬文,長遂博貫載籍。……” 范氏《后漢書》各本均無“北地人也”一語,李善為初唐人,作為文獻學家,他對譜牒文獻并不陌生,何以扶風班氏的家族成員成了“北地人”?北地是秦漢時代的一個郡。《文選》卷9《北征賦》,作者“班叔皮”下,李善注引《漢書》曰:“班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也。”賦中說:“登赤須之長坂,入義渠之舊城。”李善注:“赤須坂,在北地郡。義渠,城名,在北地,王莽改為義溝。酈善長《水經注》曰:‘赤須水出赤須谷,西南流注羅水,然坂因水以得名也。’《漢書》:北地郡有義渠道。”賦曰:“紛吾去此舊都兮,騑遲遲以歷茲。” 李善注:“杜預《左氏傳注》曰:‘紛,亂也。’謂心緒亂也。《楚辭》曰:‘紛吾乘兮玄云。’舊都,北地郡也。”這里足以表現出李善對北地的熟悉。《文選》中的作家,如傅咸、傅玄和傅亮,李善在其名下征引文獻,均有“北地泥陽人也”一語,這是符合實際的。北地泥陽傅氏乃是中古時期的名族。而扶風班氏家族成員,只有漢代的班壹與北地泥陽有關。班彪《北征賦》:“過泥陽而太息兮,悲祖廟之不修。”李善注:“《漢書》:‘北地郡有泥陽縣。’《漢書》曰:‘班壹,始皇之末,避地于樓煩。’故泥 陽有班氏之廟也。”班壹是班氏的先祖,其“避地于樓煩”,說明他不是樓煩人,但曾經在此長期居留,所以這里有班氏廟。至于此廟何人所立,我們不得而知。但班彪賦中稱北地為“舊都”,并且為“祖廟之不修”而感傷,顯然對此地頗有家族的認同感。這或許就是力之兄所說的李善的“潛意識”的起因。他認為,李善注引范曄《后漢書》之所以有“北地人也”四字,“乃其潛意識作怪所致之失,而非別有所本”。換言之,這種潛意識的形成,乃是由于李善太熟悉上述有關班壹的材料了。而“姚鼐、梁章巨、李詳、高步瀛、許巽行諸家關于這一問題之說,或未達一間,或似是而非”,后世關于班固“北地人也”的說法,“或直接或間接本”,皆出自李善此注,而實為“以訛傳訛”。他認為,“既然此前有關這一問題的研究結論皆經不起常識之檢驗,今又別無新‘材料’,則欲有所突破,就得回歸原點再出發,而須在研究方法上著力。類此問題,是否會出在‘潛意’上,這當引起研究者們足夠之重視。”也就是說,當我們已經確認了某種錯誤,而又沒有更多的文獻證據時,我們可以采用科學的具有學理性的思維方法來確認之。這種研究方法乃是校勘學所謂“理校”之法的擴大。因此,盡管力之兄的行文比較晦澀,征引文獻也比較繁瑣,我們還是能夠在他荊棘叢生的文字中捕捉到他那熠熠閃光的見解和多年苦讀形成的獨得之秘。正本清源的工作,本文做得很出色,這也是他治學的一貫風格。力之做學問,一向是打破砂鍋問到底,謹慎而自信。其謹慎出于對學問的敬畏,其自信在于知識的積累。惟其謹慎,故能周章往復,不厭其煩;惟其自信,故能獨具慧眼,超越群倫。這是一種真正的學人所應具備的品格。
讓我們向三位《選》學家致敬!
梵凈山人
2019年6月26日榆林旅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