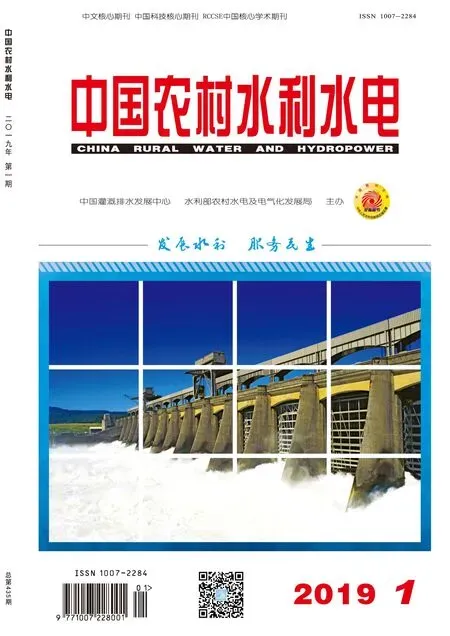基于SWMM模型的低影響開發模式在城市雨洪控制中的研究
王 雷,楊鳳閣,王誠杰,崔建軍,徐 艷,趙國良,霍樹義,金坎輝,路 維
(河北水利電力學院,河北 滄州 061001)
0 引 言
隨著我國城鎮化進程的快速推進,越來越多的綠地被灰色混凝土建筑以及不透水鋪裝取代,這種變化破壞了原有的自然水文生態,在遭遇高強度降雨時,地面降雨能夠短時間內在該區域內形成地表徑流,增加管網排水壓力,極易形成城市內澇[1]。2015年8月31日~9月1日該地區普降特大暴雨,最大降雨強度達到41.6 mm/h,最大降雨量達143.1 mm,造成該地大范圍內澇,嚴重區域水深達到1 m。
低影響開發LID以分散式小規模措施對雨水徑流進行源頭控制,以達到緩解城市內澇,改善城市生態環境的目的。暴雨管理模型SWMM[2]是由美國環境保護署開發的基于水動力學的降雨徑流模擬模型,該模型集成了降雨、徑流等多種模塊,能夠對單場及連續降雨的徑流和排水情況進行動態模擬,LID模塊能夠模擬LID設施影響下的徑流量、峰值流量和蓄水量等參數的變化情況。文章以華北地區某區域為研究對象,通過建立SWMM模型,對不同重現期設計暴雨下的降雨徑流進行模擬計算,為該地區暴雨洪水控制研究提供技術支持。
1 研究區域自然氣候特征
研究區域介于北緯38°16′~38°18′、東經116°46′~116°48′。該區域屬溫帶半濕潤季風氣候,年平均降雨量約600 mm,且分布極不均勻,7、8月份降雨量占到了全年的70%~80%,夏季受太平洋副熱帶高壓影響,極易形成強降雨,具有“降水量大、歷時長、降水集中、強度大”的特點,在這種氣候特征下易形成地表徑流和洪澇災害。
2 研究區域SWMM模型構建及參數確定
2.1 研究區域概況
該研究區域城市化進程快,硬化比例高,用地類型主要為居住用地、教育用地、行政辦公用地、公共文化設施用地以及較少的耕地和綠化用地[3],利用ArcGIS對該區域的DEM數據進行處理,該區域地勢較為平坦,高程7~11 m,坡度0.2°~1.8°。排水為雨污分流制,雨水管網設計標準較低,暴雨設計重現期為0.5~1 a。區域內有小流津河、景觀河、景觀湖,承擔研究區域內雨水排澇任務。
2.2 研究區域模型概化
研究區域總面積約651.5 hm2,平均不透水面積率為50.7%,依據該地區現狀排水管網圖和現場實地踏勘,研究區域概化如下:共劃分子匯水區域109個,面積1.89~9.8 hm2,管段142條,節點143個,出水口16個。研究平面概化圖見圖1。

圖1 研究區域平面概化圖Fig.1 study area plan generalization
2.3 設計雨型及雨量
根據室外排水設計規范[4],中小城市中心城區的重要地區,暴雨設計重現期為3~5 a,人口密集、內澇易發的城鎮宜采用上限。鑒于此,本研究設計重現期設定為1、2、3和5 a 4種;降雨歷時設定為2h;降雨量根據該地暴雨強度公式(1)計算確定;設計雨型采用芝加哥雨型,雨峰相對位置r在0.3~0.5之間[5],本研究取r值為0.4。
(1)
式中:P為設計重現期,a;t為降雨歷時,min;q為暴雨強度,L/(s·hm2)。
2.4 產匯流模型選取及參數率定
地表匯流模型選用非線性水庫模型,產流模型采用Horton入滲模型,水力演算模擬動力波模型。子匯水面積、節點高程等參數通過GIS分析、市政管網資料和現場實地踏勘獲得。曼寧系數、入滲率等參數在參考模型手冊或文獻資料的基礎上根據實際情況進行率定,文章參考劉興坡[6]提出的基于綜合徑流系數的城市降雨徑流模型方法,通過反復迭代試算得到最優參數,再分別以重現期為1 a和2 a的合成降雨檢驗參數率定結果的穩定性。
根據計算得到的該區域不透水面積率,查詢《城市排水手冊》查得綜合徑流系數參考值(表1),可知該區屬于建筑較密的居住區,根據率定結果,得到模型重現期1 a和2 a的綜合徑流系數分別為0.55和0.62,滿足建筑較密的居住區綜合徑流系數0.5~0.7的要求[7]。率定結果見表2。

表1 綜合徑流系數參考值Tab.1 Comprehensive runoff coefficient reference

表2 率定參數表Tab.2 Rate parameter table
3 排水系統現狀能力評估
分別采用1、2、3、5 a 4種設計重現期來對研究區域排水管網系統進行模擬,溢流情況詳見表3。

表3 溢流情況表Tab.3 Overflow table
從模擬結果可以看出隨著降雨強度的增大,管網的溢流節點數量不斷增多,節點溢流量也不斷增大。P=1 a時,積水節點為18個,溢流量均不超過50 m3,基本滿足雨水管道設計規劃要求;P=2 a時,溢流節點數量為61個,占節點總數的42.7%,其中溢流量大于500 m3的節點有2處;P=3 a時,溢流節點數量為77個,占節點總數的53.8%,其中溢流量大于500 m3的節點有6處;P=5 a時,溢流節點數量為89個,占節點總數的62.2%,其中溢流量大于500 m3的節點有11處。可見,除P=1 a外,在2、3和5 a的設計降雨下,研究區域的現狀排水管網系統均出現了多處溢流,且溢流情況嚴重。
4 LID模擬結果及分析
4.1 LID措施參數設置
在借鑒國內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根據研究區域的實際情況,將研究區域內50%的綠地改造為下沉式綠地,50%的硬化廣場及道路改造為透水鋪裝,考慮到綠色屋頂對原屋面承載及防水能力有較高要求,故綠色屋頂的改造比例設為30%,雨水桶按所處理屋面面積的1%的比例計算[8],設置桶高2 000 mm,排水系數25.4 mm/h,排水指數0.5。LID設施主要參數詳見表4。

表4 LID設施主要參數Tab.4 LID facility main parameters
4.2 模擬分析
分別模擬單獨布設雨水桶、單獨布設下凹式綠地、單獨布設透水鋪裝、單獨布設綠色屋頂以及四種LID設施組合布設這五種方案在不同暴雨設計重現期下整個研究區域的降雨徑流過程,如圖2所示。五種方案下不同暴雨設計重現期徑流總量與洪峰流量削減率如圖3所示。
這5種LID布設方案在不同設計重現期下對徑流均有一定的削減作用,在徑流總量削減方面,組合布設LID措施的削減效果顯著,削減率達到76.3%,其后依次是下凹式綠地、透水鋪裝和雨水桶,綠色屋頂的徑流削減效果最差,僅為8.8%;在洪峰流量削減方面,組合布設LID效果顯著,削減率達到75.9%,其后依次是雨水桶、透水鋪裝、下凹式綠地,綠色屋頂最差,僅為6.4%。在延遲峰現時間方面,各方案均能不同程度的推遲了峰現時間,其中單獨布設雨水桶的效果最好。
當暴雨設計重現期由1 a一遇增大到5 a一遇是,透水鋪裝保持20%左右穩定的徑流削減率,這是由于透水鋪裝入滲率較大所致,其他方案徑流總量、洪峰流量的削減率均逐漸下降,這是因為高強度降雨條件下土壤迅速飽和,當降雨強度超過LID設施的下滲和儲蓄能力時,徑流削減效果進一步降低,但仍具有遲滯徑流的作用。


圖2 5種方案在不同暴雨設計重現期下的降雨徑流曲線Fig.2 Rainfall runoff curves of five different scenarios during recurrence periods of different rainstorm designs

圖3 不同暴雨設計重現期徑流總量與洪峰流量削減率Fig.3 Total runoff volume and peak flood flow reduction rate during recurrence of different storm designs
5 結 論
(1)現狀排水管網排水能力不足,僅能滿足1 a暴雨設計重現期水平,一旦該地出現超出設計重現期強度的暴雨,極易發生城市內澇。
(2)5種LID措施布設方案均能不同程度增強雨水系統對徑流的滯留調蓄能力,減少總徑流量并削減洪峰。在徑流總量削減效果上,組合布設LID方案最佳,其后依次是下凹式綠地、透水鋪裝、雨水桶,綠色屋頂最差;在洪峰流量削減效果上,組合布設LID方案最佳,其后依次是雨水桶、透水鋪裝、下凹式綠地,綠色屋頂最差。因此,在進行LID設施布置規劃中,建議采用多種LID措施組合布設,以取得最佳效果。
(3)LID設施在低重現期下徑流削減效果更為顯著,隨著暴雨設計重現期的增大,在高強度降雨作用下,LID設施的徑流削減效果降低,但仍可以起到徑流遲滯作用。
(4)文章著重從技術層面探討低影響開發理論在解決城市內澇問題的可行性,對建設海綿城市具有一定的指導作用,但在進行LID改造時,除考慮LID技術因素外,還需考慮自然因素和成本因素,因地制宜,根據項目實際特點綜合比選方案,避免一味追求多LID設施的堆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