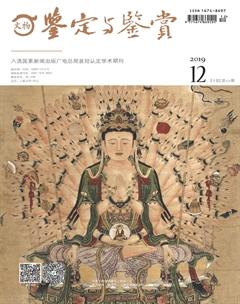清代社會管理的流弊
姚旭
摘 要:道光年間,清朝走向衰勢十分明顯,已無力改善對城鎮的管理,國庫不實,養活不起大批官吏,致使城鎮管理落在“編外”人員的手中,流弊叢生。
關鍵詞:官府;商會;梁山
清代官俸之薄亙古未有,地方辦公經費不足,官、民地位懸殊,官員侵害商民利益的行為時常發生,也為州縣官員收受賄賂、額外勒索大開方便之門[1]。
官府任用“編外”人員維護社會治安,曾是清末在城鎮管理上的一項弊政,內蒙古塞外邊城包頭有許多的事例。其中一次商民告狀竟能勝訴,著實讓我們感到意外,勝訴的原因之一在于官方曾有限制官員、胥吏對商民進行欺詐的紙上明令,第二個原因是包頭商民有告倒德廳主的決心,太原知府不得不如此處理結案。這些事例至今已成為城鎮發展中的珍貴史料,值得整理和研究。
在內蒙古包頭市東河區北梁棚戶區的拆遷工作中,發現清代道光二十三年(1843)一通“嚴絕流弊”石碑,其碑高214厘米,寬80厘米,碑額大字“嚴絕流弊”。從碑文得知,內容是有關城鎮管理的,碑文內容稱包頭鎮(縣級以下行政單位)鋪民(在城鎮開鋪的商人)上告德廳主自蒞任以來,“凡遇毆傷人命,匪情盜案,不以公斷,且向商民強索銀四千六百兩;戶書孟秉昭索銀二百兩”等情況,此案經由山西省巡撫批示,委托太原知府“王大老爺斷案和結”。處理結果是“德廳主離任,門丁發落,戶書孟秉昭斥革衙外”,由新委派的廳主按新立章程辦事。茲后審理匪情盜案不得強索及侵擾鋪民,鋪民勝訴,故刻“嚴絕流弊”石碑向社會警示,以保護鋪戶的合法利益。由于碑文部分字跡已難辨認,且為古代詞語,我們結合其他史料反復試讀,對當年包頭的社會狀況進行說明。
清代包頭城鎮的社會管理存在著許多問題,如商會參政,丐幫管理監獄,官府薩拉齊廳(口外相當縣級單位稱廳)下設的包頭鎮分巡廳(俗稱巡檢衙門)對商會行使權力進行監督,并有守城巡查的任務,出現“多頭”管理的現象。近日見到報紙轉載《南京通史·清代卷》一則史料,獲知南京城也有包頭鎮類似的情況,我們不妨將南京城與包頭鎮進行對比,有助于討論該碑所反映的問題。
南京是省會城市,衙門眾多,人口稠密。包頭是一個塞北小鎮,地方上存在很大的差距,是很難詳加比照的,但有相同點,即南京官府管事的“職官數量十分有限,在管理紛繁復雜的城市事務時,常顯得捉襟見肘……各衙門的具體事務實際上大多由多家經制之外的胥吏(這里指編外的小官)、差役等完成”。由于“官府人手不足,還需借助保甲等城市基層組織來加強對社會的管理與控制,甚至發動普通市民參與巡防”。胥吏和差役“不是國家的正式工作人員,不享受俸祿和升遷待遇,也不接受嚴格的考核。雖然他們只是從百姓中僉派或雇募的差役,但其行為代表官府”,這些“編外”的人員仗官侵害商民的行為時有發生。
包頭鎮所發生的問題,就是因為官府人手不足,經費短缺,致使城鎮管理的具體事務落在官府“編外”人員的手中,這些人具有半官方的身份,凌駕于百姓之上,因而弊端叢生、亂收費問題突出。有權管理包頭鎮社會事務者,要首推民眾組織的商會、官府薩拉齊廳和包頭鎮巡檢衙門。
薩拉齊廳:光緒年間,薩拉齊廳新官到任,各鎮商行例納公費銀1~2萬兩,同知周桂敷到任后,主動裁減,包頭鎮商行交1200兩。例納已是商戶公開的負擔,平日還有其他征稅。
商會:包頭是清代開始形成的一個移民城市,康熙、雍正、乾隆年間,不少山西、陜西、河北、山東等地漢族人先后來包頭墾荒定居,商業由此興起。從事貿易的多是山西人,為了相互關照,維護大家的共同利益,便成立了商會,最早的名稱叫商賈會館,道光元年(1812)改稱大行,大行的負責人稱總領。商會除主管包頭鎮工商業外,并受薩拉齊廳的委托,負責地面之事,如打架斗毆、民事訴訟、支應差傜、迎請官府、攤派款項等事宜,這些都由大行辦理。道光三十年(1850),在今東門大街關帝廟后設大行辦公所。1915年成立包頭鎮商會,以后又有更名,但性質未變。本文行文為了方便均稱商會。道光年間包頭商會內部組織不明,同治年間大行負責人仍稱總領,下設會計、文牘、庶務和辦差人員,又有文武甲頭各1人,總計25~30人。在街上跑雜差的有13人,內部雜役5人,傳達2人,上街收款4人,街頭查辦維修工程2人,共計26名。50多人已是人浮于事,每年花費銀子3500~4000兩[2],儼然是一個兼管城鎮的辦事機構。碑文中言德某人在任內的4年多時間內,強索銀4600兩是接近事實的,廳主指的是職務,或是民間對其職務的俗稱。1913年民國進行改制,裁撤清代所設置的包頭鎮巡檢衙門,成立包頭鎮警務分局,由薩拉齊縣委指派局長1名,共有警察50名,商會管理地方行政事務之權告終。
園行:包頭鎮菜農的行業組織稱園行,道光間加入了大行,同治年間從大行中分出,包頭鎮社會形成大行、園行“共管”的局面,在地面上有所分工,在園行轄管區出了事,由園行直接處理。在大行內設議事機構,由大行出代表4人、園行出代表1人組成,巡檢和巡官對議事機構有監督之責。
巡檢衙門:山西省歸綏道薩拉齊理事廳(管理漢民的縣或稍高于縣在塞外的行政機構)包頭鎮分巡廳,文職稱為巡檢,從九品,武職稱為把總,巡官相當于辦事科員,在大行議事機構中只有監督之責。管理社會的職能在實際上由商會施行,“嚴絕流弊”碑文中稱的“德廳主”,我們只知廳主是職務稱呼,未敢確定他就是巡檢衙門的人,但在當時的包頭鎮卻是一個掌握實權者。孟秉昭屬于胥吏一類人物,這種人依仗官勢,什么壞事都能做得出來,是由廳主雇傭的。
清代商會頭領本是商人出身,是從各行業大商號經理中推選出來的,一旦這些經理在商會掌權,便覺得十分榮耀。有些人修養很差,耀武揚威,在商會內大吃大喝,多吃多占是最為平常之事,出行時坐著轎子,前有虎頭牌、牛皮鞭開道,不是官員卻像似官員,官味更足,經費收支沒有制度管束。大行辦公所具體處理地方各項行政事務,包括審理匪盜、調解民事糾紛等,實權在握。
碑文中的被告人德廳主頗似商會中實際的處理事務的掌權人,地位在總領之下,為什么德廳主很難被告倒,要一直把官司打到省里去,筆者認為他極可能是這樣一類人物,即在官場上有活動能力,有處理社會管理工作的豐富經驗,對上成了商會總領信得住的人,對下有一批胥吏、門丁一類的爪牙可供其驅使,社會上有個被稱作“梁山”的組織可供其利用,白道、黑道結合起來,方可顯示該人的威力和神通。
巡檢衙門官名全稱是包頭鎮分巡廳,巡檢可稱為是該廳的廳主,若有貪污瀆職違法之事,至少有薩拉齊廳長官彈劾他。至于德廳主,我們總認為他不是巡檢衙門的人。
“梁山”:包頭的“梁山”是為商會打下手的,研究社會問題時,對“梁山”不可不知。“梁山”是包頭流氓底層社會的總稱,僅是命名為“梁山”,并沒有《水滸傳》中梁山好漢“替天行道”的思想,在統治階級面前是順民、爪牙、徹底的奴才。這種組織有許多幫派,包頭的“梁山”是由“鎖”“里”兩家聯合組成,“里”家人員以乞丐和打“蓮花落”“數來寶”的行乞藝人為骨干,可以走遍天下到處流浪;“鎖”家以吹鼓手和轎夫為骨干,“梁山”的領導權始終被“鎖”家鼓房所把持。
“梁山”人員行使警察的權力,例如清朝和民國初年,在死人溝(地名,新中國成立后改稱慈人溝)有關押人的“黑房”,凡是在包頭逮捕的人犯,以及五原、東勝和薩拉齊廳后山地區送來的人犯,先押解到包頭由死人溝看管,然后再往薩拉齊監獄解送。“梁山”人員執行警察和特務工作,外邊看“梁山”的人是在為大行、園行辦事,行乞人到處流浪,實際是在充作耳目。他們在賭場、廟會維持秩序,在街道巡查,在春節期間“鬧社火”,歷史上發現有斗毆和交通堵塞的情況,都有“梁山”的人出現,這些不怕死的人,人人見了都害怕。夜間巡邏打更時提著大行的燈籠,可以盤問、檢查、逮捕夜不歸宿的行人,守城門的兵丁離開城門時,甚至把城門房子里掌管的鑰匙交給打更人,打更人便可利用機會營私舞弊,夜間私開城門,放行商旅,獲得銀兩。他們還負責防火救火工作,掩埋無主的死人,協助官府的仵作檢驗尸體,充作法醫破案的助手。做這些服務的工錢統由商會支付。
“梁山”是大社會中的一個小社會,對內管理極嚴,幫有幫規,家有家法。對乞討人和在“梁山”中討生活的人有刑罰生殺之權,且對外封鎖一切有關“梁山”的消息,違者重罰。
清末民初,包頭死人溝東西兩溝住著“鎖”“禮”兩家,“梁山”弟兄有800余人,這是藏龍臥虎的地方,有各種偷盜的能手,有要飯的,這些人都有“頭目”,這些“頭目”都與“鼓扛房”有來往,辦紅白喜事時,派人為雇主抬轎子,以此開工錢,乞丐則到紅白喜事家要錢討吃,新中國成立初期討吃窯只剩下200余人。“梁山”設有“忠義堂”,在門前“掛著大行的虎頭牌和牛皮鞭,閑雜人等都要肅靜回避,在神堂中供有祖師像,并設有囚室、伙房,有專供記賬先生(戶書一類人物)和“把式匠”(會武功的打手)居住的宿舍,“頭兒”出門有保鏢的跟在后邊。他的“兵符”“印綬”是一根木杖,名叫“拐挺”(俗稱打狗棍、桿兒),平時放在祖師牌位后面的供桌上,有事的時候用它行刑打人。“梁山”的人一方面為大行緝盜[3],一方面中飽私囊。
碑文中稱“買空賣空”的句子,文意前后不相連,是被告人反駁原告的話,即不承認被控告的事實。“買空賣空”原是指包頭糧油業資本家搞投機買賣,俗稱“倒糧盤子”,其營業性質是“買空賣空”。交易糧食的時候,一般不動用現糧,只是存有足夠現糧,以應付買主要求付現糧之需,投機者利用糧食漲跌來牟取暴利,有人“買空賣空”大發橫財,有人落得傾家蕩產。“買空賣空”在此處是比喻語,文中所說內外“規禮物色”,指的是對上級官員送財禮、物品進行打點的陳規陋習,即行賄、受賄,為非正常開支,不能將此轉嫁于民。“街巷均立甲頭”是指乾隆八年(1741)在包頭實行的保甲制度,置“牌頭”“總甲”,十戶為牌,十牌為甲,十甲為保,在漢民中實行,從而加強對戶籍的管理,“走西口”的晉陜漢人移居包頭,并在包頭落下戶籍。甲頭有治安巡查之責,像明代的南京那樣。
道光年間,清朝走向衰勢十分明顯,已無力改善對城鎮的管理,國庫不實,養活不起大批官吏,處處保守,已無力改革,碑文所說侵擾商民的流弊卻愈演愈烈,已成為舊社會是無法革除的頑癥。包頭近處的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右旗都存在類此現象。民國時期包頭屢過大軍,糧草由包頭商民無償提供,馮玉祥軍隊向商會墊借過現洋三百五十多萬元,石友山軍隊向商會墊借過一百三十多萬元,這些墊借多是有借無還,商會將此損失交給商戶均攤。■
參考文獻
[1]郝秉鍵.雍正帝:整治陋規 澄清吏治[N].中國文化報,2014-03-24.
[2]中共包頭市委機關.包頭史料薈要(第6輯)[M].包頭:中共包頭市委機關印刷廠,1983.
[3]中共包頭市委機關.包頭史料薈要(第2輯)[M].包頭:中共包頭市委機關印刷廠,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