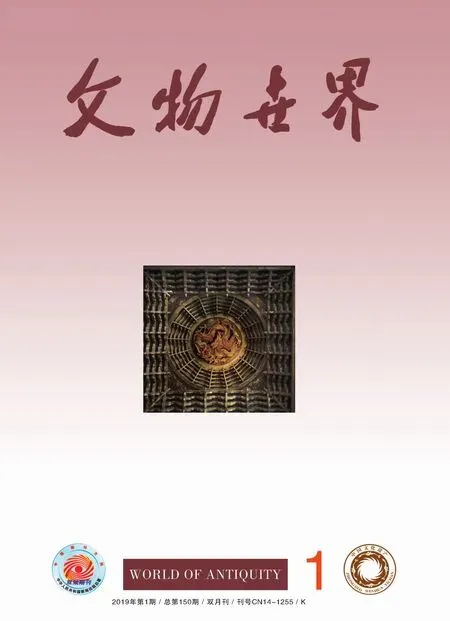論披巾在云岡石窟造像服飾中所起的作用
□ 崔曉霞
服飾,作為見證人類整個文明發展歷程的重要載體,其本身的功能也從最初的防寒遮羞,發展到裝飾人體,繼而體現穿著者的身份、氣質、品味,儼然已經成為了穿著者精神世界對外展示的重要窗口和本身氣質的一種延伸。云岡石窟,這座人類藝術的寶庫中,自然也少不了形式多樣的服飾。它們或華麗或質樸,卻都承載和表現出了雕刻藝術家們登峰造極的藝術和對于雕刻藝術極大的熱忱。云岡石窟造像的服飾元素豐富多樣,而筆者認為,這其中最為出彩的當屬造像所配的飄帶。披巾,作為服飾組成中的重要元素,或飄逸或凝練。由于其出色的可塑性是其他服飾元素所無法比擬的,因此在云岡石窟造像服飾中大量的出現,也成為了人物造像精神特質最為清晰的注解。本文將著重從云岡石窟人物造像所配披巾的敷搭方式,與人物造像的相對位置關系,顏色形態及扭轉狀態的表現等多方面論述其在云岡石窟造像服飾中所發揮的作用。
一、披巾的敷搭方式
披巾作為表現人物狀態的重要裝飾物,在人物不同的狀態下會呈現出不同的敷搭方式。飄帶與飛天的搭配方式最為常見,而飛天的狀態都是極具動感的。云岡石窟中的飛天按人物的性別可以分為兩類。
1.男性裸半身飛天:此類飛天多出現于龕眉,此類飛天多體現出早期西來樣式的樸拙,但也不乏飛天應有的飄逸與動感,人物多側身,前伸臂自然前伸,后揚臂后擺于體側自然延展。中國古代雕刻與繪畫藝術歷來以寫意見長,這一特點在以宗教神話為題材的繪畫和雕刻作品中則更為突出,作為云岡石窟雕刻藝術中飄逸與靈動的化身,飛天佩戴披巾的方式自然也是靈活多樣,以體現人物的空靈。如第6窟中心塔柱下層北面外層龕眉格間裝飾的飛天,披巾與飛天前伸臂的接觸方式為敷搭,并不會纏繞于前臂,繞臂部位多為肘部。后臂的飄帶會繞臂半周。繞臂方式多為由體后敷搭至肘部再繞臂一周,也有少數此類飛天其披巾在后揚臂的繞臂部位下移至手部(圖一)。
2.女性飛天:此類飛天的佩戴方式則有所不同,披巾與身體的接觸部位首先為肩部,經肩部由以后繞至體前,再纏繞于肘部,末端揚起。除了這兩種較為普遍的敷搭方式外,也有一些特例,如9窟前室北壁天宮伎樂列龕中的一逆發形飛天,敷搭于前伸臂的披巾末端并未自由飄動,而是改由后曳臂持握,飄逸中又顯得嚴謹而穩重(圖二)。
此外,呈不同姿勢的造像其披巾的敷搭方式也有所不同。呈跪姿或站姿的造像多為靜態,因此相較飛舞于九天的動態飛天,其飄披巾敷搭方式便略顯莊重。如第10窟主室南壁上層東側胡跪狀供養天,合掌半跪,由于雙手合十,上肢為相對對稱分布。所配披巾于肘部觸臂,繞臂一周后自然下垂,左右兩側飄帶,其敷搭方式及下垂走勢皆為鏡像對稱分布。又如第11窟南壁,尖楣圓拱龕,并坐二佛,左右兩側各一素面冠菩薩(圖三),右手上舉持與愿印,左手自然下垂。雖兩臂姿勢不同,但由于菩薩呈站立狀,因此兩側披巾并未展現出過多的飄逸,而是沿人體中心線呈鏡像對稱分布,大氣端莊。第11窟南壁盝形龕內交腳菩薩(圖四),頭戴化佛冠,袒胸露臂,佩瓔珞,項圈,腰束羊腸大裙,右手上舉持無畏印,披巾于體后繞于肘部后自然下垂,同樣呈鏡像對稱分布。
二、披巾本身的形態、樣式、紋飾及披巾末端紋理的表現形式
第6窟中心塔柱下層北面龕楣格內的飛天樂伎,男性飛天的披巾在其體后部分為半弧形,有些則根據雙臂的延展程度呈一字形展開。且體后部分披巾的高度均低于頭部。形態總體較為圓潤,回轉彎折較為平滑。而旁邊的女性飛天其披巾的體后部分均高于人物發髻(圖五),且整體形態較為突兀,類似于尖銳的橢圓體,繞臂后陡轉上揚,整體形態呈幾字形。造型抑揚陡轉,映襯出女性飛天的動感和飄逸。又如13~18窟頂部兩位飛天舒展自如,披巾線條更加不規則,襯托出女性飛天的瀟灑與曼妙。又如17窟南壁立菩薩袒上身(圖六),佩項圈,短瓔珞,左手持蓮蕾,右手自然下垂。披巾整體并未飄揚,而是大體貼合身體的外廓線,與人體若即若離。過于貼合則無法表現造像的飄逸,過于離散則無法體現人體優美的曲線。披巾下垂部分走勢與造型裙擺外廓線精密契合,靜而不滯,將菩薩瞬息萬變中最美的一刻定格下來,是難得的以靜襯動的佳作。而第8窟主室北壁盝形龕帷幕底部一逆發形夜叉,轉身側望,大眼露齒,背部的飄帶緊貼于體表。神靈的飄逸感頓失,取而代之的是人物的質樸與生動。
三、披巾的紋飾
第6窟中心塔柱下層北面外層龕眉格間的飛天所佩的披巾紋飾比較簡單,只有表面所刻的三條陰刻紋,而披巾末端卻展示出較為豐富的各種表現形式。如第7窟主室南壁6供養天三人一組,半跪相對,披巾繞肩貼胯下行,末端垂于足跟處,末端形如寶劍劍鋒,將披巾的凝練表現得淋漓盡致。又如第13窟明窗東壁一立菩薩(圖七),頭戴素面冠,左手提凈瓶,右手托摩尼寶珠。披巾搭臂翻揚,邊緣飾有多重褶皺,形如綬帶。披巾表面的陰刻線也增多至4道。13窟東壁盝形帷幕龕,龕內雕有一交腳菩薩,兩側各有一脅侍菩薩,所佩披巾末端褶皺更為繁復,立體感頓顯。
四、披巾末端扭結的表現手法
為了表現披巾舞動感,其末端通常會做扭結狀,而表現的手法也是多種多樣。如第8窟窟門西側鳩摩羅天上方的一尊飛天(圖八),人物主體采用淺浮雕手法來表現,而所佩披巾則采用陰刻紋作為表現手法。為了表現出披巾舞動的意境,披巾末端做扭結狀,而扭結的表現手法也非常簡潔和巧妙。披巾表面三根陰刻線在扭結處出現斷點,三條另外的陰刻線從另外的三點再度延伸,并未延續此前披巾正面的三根陰刻線,以此來表示后三條陰刻線所代表的平面為披巾的反面,而正反兩面的出現也證明了披巾發生了扭結,從而增添了披巾和人物的飄逸感。又如第9窟明窗東壁,坐蓮菩薩兩旁各一供養天(圖九),左側一尊供養天所佩披巾,體后部分為扭結狀,扭結后的部分與之前未扭結的部分呈前后交錯狀。同樣在左臂纏繞后下垂的一段披巾也分為前后兩段。飄帶用前后交錯敷搭的表現手法使本是平面的淺浮雕立體感驟增,體現出云岡石窟造像風格寫實的一面,與此前第8窟門拱處飛天所佩披巾的表現手法相比一繁一簡,但都體現出藝術的無比精妙。
五、披巾的雕刻表現手法
云岡石窟造像所佩披巾大多采用淺浮雕雕刻技法,但也有少數特例,如第8窟門拱西側鳩摩羅天上方的一尊飛天,人物主體采用淺浮雕雕刻技法,而所佩披巾則使用陰刻紋來表現,寥寥數條陰刻線將披巾的輕薄曼妙體現到了極致。同時,壁面上的陰刻紋與肘部所刻陰刻紋嚴絲合縫,銜接分毫不差,使得披巾整體的連貫性得到了體現。而披巾下垂部分呈扭結狀,則是以陰刻紋的不連貫性體現出披巾的回轉飛揚。不同類型的陰刻線表現手法相映成輝,和而不同,體現出雕刻藝術的妙不可言。
綜上,本文從披巾的形態,樣式,紋飾以及與人物造像的相對位置關系等幾方面,對這一云岡石窟人物造像中常見的服飾元素進行了論述,表明了披巾在表現云岡石窟人物造像的氣質及精神特質方面所起到的無法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