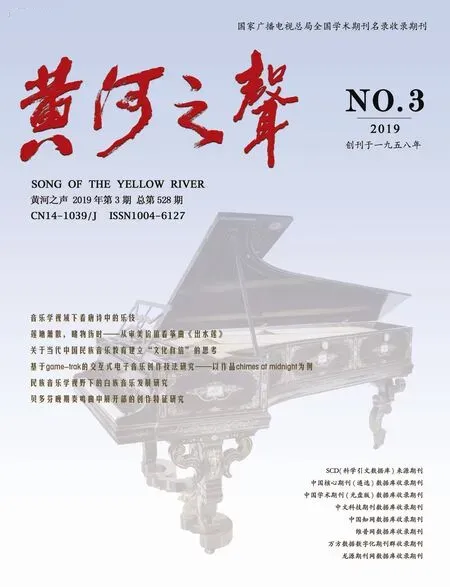蓮塘蕭散,睹物傷時
——從審美價值看箏曲《出水蓮》
張 婧
(肇慶學院音樂學院,廣東 肇慶 526061)
《出水蓮》作為客家箏曲的代表,至今已經擁有較長發展歷史,不僅文化底蘊豐厚,而且也被稱之為客家箏樂中的奇葩。客家人最早生存在黃河流域一代,由于區域重要性突出,自古即是兵家的必爭之地。進入戰亂時期后,加之黃河泛濫,導致客家人不得不為了生存了一路南下,由于客家人秉性耿直,不愿與貪官污吏勾結,在反復被流放情況下,最終在廣東及福建地區落戶,當地人習慣稱這些從北方遷移過來的人群為“客家人”。對于該地區而言,客家人帶來了與眾不同的中原文化及音樂要素,在與當地的藝術風格相融合后,最終形成了舉世聞名的客家漢樂。從根本角度分析,客家漢樂不僅保留了中原地區的傳統文化特征,同時也有典型的廣東地區文化特征,但與純正的廣東音樂又存在一定差異,因為被當地人稱之為“客家音樂”。聆聽《出水蓮》,我們很容易感受到音樂的淳樸,同時又可以看出客家人性格上的孤傲。在《清樂調譜選》中對《出水蓮》的詮釋:“蓋以紅蓮出水,喻樂之初奏,象征其艷嫩也。凡軟線諸調,均可用此調起板。”所以,從歷史發展角度來看,很多名家都演奏過相關曲目,只是在時代不斷發展狀態下,加之不同藝術家對客家文化精神的理解存在較大差異,最終呈現出了不同感覺的《出水蓮》。筆者在文中有對《出水蓮》進行綜述性總結,嘗試從審美特征角度入手,介紹相應藝術意境。該部分元素可以為形態美建設打下堅實基礎。
一、箏曲《出水蓮》演奏風格與客家精神內涵
客家箏曲在客家音樂體系中占據十分關鍵影響地位[1]。客家音樂在藝術領域內也被稱之為廣東漢樂,在整個客家人居住區域十分文明。客家音樂不乏獨立性特征,此外,其也將“中州古樂”的古典、淳樸性特征全面體現出來。客家箏曲也叫做漢樂箏曲,主要包括三種曲調,結構相對十分謹慎,而且每曲六十八板,保留了中原古樂“八板體”的傳統結構模式,例如文章研究的《出水蓮》;“小調少于68板音樂形象并未體現多元化要求。串調則小節連接比價自由,而且很多都是在民間小調基礎上進行調整的。客家箏曲也有相應劃分模式,古代時期就有“三分損益法”的分音階方式。[2]客家箏曲的獨特風格主要體現在演奏技巧方面,傳統演奏方式中,“左手為韻,右手為聲”,曲調的神韻之處包含其中,在滿足大眾欣賞需求基礎上,也不乏高雅之情。
《出水蓮》作為客家箏曲的代表作,發展之初只是在民間進行傳播,而且只包含骨架音一個單一的音色。藝術家在進行相關演奏過程中,通過不斷的變調、變奏等操作,共同打造統一發展整體。現在我們聽到的《出水蓮》已經經過了多次改編,但原曲的一部分結構依然被保留,在不同的技巧處理以后,可以將蓮花的孤傲全面體現出來。在音樂會上,箏曲總是尤其獨特的表演魅力,而且大部分演奏者都是以羅九香或饒寧新的為核心,而且都會適當融入自身對曲調的了解。通過開展相應比較研究活動,上述列舉的兩個曲調版本被演奏的概率相對較高,而且風格十分集中,重點都在闡述蓮花與眾不同的美妙。2001年,羅九香誕辰100年,相關研究會議中,我們聽了很多個不同版本的古箏演奏錄音,很容易就可以發現,對靈活性的不同控制,效果是完全不一樣的。
1.樂曲的開句和樂句結尾的相異
從演奏處理角度分析,羅九香先生在演奏過程中比較善于使用“花指”技巧,中指的不同操作方式能夠將曲目的特殊之處全面體現出來。饒寧新先生使用的是八度“大撮”起板,采用重拍和滑音的技巧演奏方式,對相應音色進行全面控制,余音會給聽眾帶來不一樣的感受,韻味悠長,讓人深陷其中,常常流連忘返。饒寧新先生對每一句的句尾都進行了相應處理,包括音階的連接,在保持良好靈動性基礎上,也將蓮花“出淤泥而不染”的高尚情操體現的淋漓盡致。
2.旋律加花變奏的相異
羅九香、饒寧新兩位箏家在樂曲板數控制方面,除了固有節奏外,不同的變奏加上花樣等,導致曲目的獨立性特征相對較為顯著。羅九香先生的演奏特征即是淳樸、真實,不同的滑音演奏技巧使樂曲內涵相對較為豐富。饒寧新先生的演奏在骨干音階處理方面也十分具有對特征,無論是上方或下方的四度音、二度音作輔助音和經過音,特殊處理以后,整個曲目的韻律都有了顯著增長,同時音樂情感也相對更為突出。
3.裝飾音與節奏運用的相異
羅九香先生的演奏方式在上文中已經有了相應概述,每一個句尾用小的“花指”進行操作,同時在滿足簡潔性需求基礎上,也不包含太多的加花,節奏舒緩、旋律十分優美。饒寧新先生在裝飾音方面,花指相對較長,而且會用特殊的方式保持節奏的緊密性。可以說,饒先生在全面理解《出水蓮》一曲獨特性基礎上,做出了這樣的曲調調整。
4.左手按滑音運用上的相異
從實際演奏過程來看,羅九香和饒寧新兩位箏家都十分注重左手滑音的處理,而且空弦對于整個樂曲而言是十分重要的。饒寧新先生也曾明確表示,樂曲滑音的有效處理是廣東漢樂箏能夠長久流傳的主要原因。從運用方面來看,不同演奏方式都對應相應特征,而且風格各異。羅九香先生的風格即是不同滑音的全面結合,特征被稱之為“緩而不怠,緊則有序”。淳樸音樂之中不乏哀怨,哲理性特征也十分顯著。而饒寧新先生則與之不同,緩慢的按弦方式,處處展現出蓮花的孤傲情懷。
從上文描述過程中我們能夠了解到,關于《出水蓮》演奏頻率較高的兩個版本差異性特征有了全面介紹,但沒有針對演奏細節進行全面性研究,尤其是在左右演奏方式方面,羅九香先生表示,要妥善處理不同演奏技巧,而且要強調空弦對整個樂曲的實際影響作用。饒寧新先生也提出,樂曲滑音部分的處理在廣東漢樂箏藝術領域內占據十分重要發展地位。從運用角度分析,彼此特征較為突出,而且風格各異。王蔚老師分別用蓮之“雅”與“傲”的特征,演繹出兩個不同版本作品。筆者結合相關研究結論,針對饒寧新的曲目特征提出了個人獨到見解。正是因為蓮花喜歡孤芳自賞,高傲之處也顯現出了獨到的凄涼。利用“fa”、“si”表現方式,使觀眾也能體驗到不一樣的悲壯。更為關鍵的即是,蓮花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的境界展示往往十分到位!
《出水蓮》不僅包含了蓮花孤芳自賞的情懷,也體現了客家文化的相應精神。從根本角度分析,客家文化主要包括物質和精神兩方面內容。精神層面多為客家人拼搏進取、不怕困難、勤勞簡約的文化理念。生活中,他們孝敬老人、互相幫助、團結有愛,將客家人的傳統美德不斷發揚光大。這一點在房屋的自身構造方面即有相應體現。客家人有不甘于現狀、不愿服輸的生活態度,自身發展過程中,越來越多的客家人開始向海外轉移,這也體現了他們積極向上的生活態度。“精神是文化中所蘊含的是超越時代的價值理念,在有效集結文化精髓基礎上,確保相關精神特征可以全面體現出來。”[3]從根本角度分析,傳統的客家文化與現代文化之間存在較大矛盾問題,但客家精神的可貴即體現在古代與現代文化的有效融合方面。《出水蓮》則是在強大精神理念作用下,引入了大量時代氣息。截至目前為止,《出水蓮》已經不再是一個古箏作品,而是客家精神文化的重要體現。
二、《出水蓮》的審美價值
美善合在儒家美學思想體系內占據核心發展地位,受儒家文化思想影響,我們嘗試從內心角度對倫理精神進行全面研究,這也是相關研究領域所強調的善的精神。楊雄(漢代文學家)曾經總結“文”與“質”兩方面因素存在表里內外發展關系,其中,“質”的核心體現在品德價值方面,而“文”則是品德的外在表現。而文的美需要依托善來表達,因此,儒家所強調的倫理道德精神往往要遵從于人的內心感受。作為漢民族的分支結構,客家人也受傳統孔孟理念的嚴重限制,這在美學方面也有所體現。《樂記》一書中,美與善元素即很好的結合為一體。由于音樂藝術價值更容易貼近人類心理,因此,在相關音樂審美觀念打造過程中,客觀音樂也會受到不同程度的關注。筆者嘗試從羅小平所提出的“四態說”審美角度入手,對《出水蓮》所具備的審美價值進行全面總結。
“四態”包括形態、情態、意態與風格,嘗試從審美和立美角度入手,也認知和思想為基礎的美稱之為形態美;以心境和意境為基礎的美為意態美;以個性特征為基礎的美為情態美。而《出水蓮》的核心美學特征主要集中在意態和形態美中間。在對上文中所提出的兩個演奏版本進行相應分析基礎上,羅九香先生希望能夠將蓮花所具備的“迎朝陽而不懼,出污泥而不染”主題全面體現出來,蓮花的“雅”比較重要。饒寧新先生則將其老師的演奏為基礎,強調一定要突出《出水蓮》的神韻,在“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的主題影響下,充分展示了蓮花孤傲的情節。這里我們能夠感受的即是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的客家人的生活精神。對于筆者而言,兩個不同的演奏版本正式不同時代的相應體現。羅九香先生作為箏派的創始人,曾在自己的著作中表示,“緩而不殆,緊則有序,古樸淡雅,重在寫意”,他指尖上的《出水蓮》十分暢快的體現了該理念。1930年前后,我國社會發展十分復雜,很多作曲家都開始發起“禮樂救國”運動,羅九香先生也接受了相應教育理念。他在深刻感受到民族危亡基礎上,將悲憤之情體現在了《出水蓮》的演奏過程中,不僅裝飾音十分簡單,而且深刻體現了客家人艱苦樸素的民族文化。對于筆者而言,即便饒寧新的《出水蓮》版本展示了蓮花的孤傲,但也不乏悲涼之情。饒寧新先生生活的年代相對較為安穩,所以,其所演奏的《出水蓮》自然會有當時的社會色彩。該階段,客家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出現了嚴重沖突,在“fa”和“si”中即有所體現。饒寧新的《出水蓮》版本顫滑音運用較多,而且不同音階的“fa”和“si”的顫音也會存在一定差異,這也是體現悲哀之情的一種有效方式。蓮花的孤芳自賞主要是因為沒有伯樂的賞識。這樣的創作思維無疑是時代所造就的,自身經歷往往也發揮十分關鍵的影響作用。
三、《出水蓮》演奏版本的審美感悟
綜上所述,箏曲《出水蓮》有很多不同的演奏版本,筆者自身也聽過很多名家的演奏,自己嘗試對其進行彈奏,而且也有了再度創作的想法。個人比較鐘愛饒寧新先生的演奏版本,主要原因在于演奏神韻與客家人的精神十分貼近,同時曲目也含有淡淡的凄美。不僅如此,客家箏曲的相應特色也體現的淋淋盡致,給人凝重感覺基礎上,也融入了很多當地藝術元素。對細節的巧妙把握正是曲目成功之處。這里所指的“神韻”主要是精神方面的體現,箏樂講究一定要“天人合一”,所以,左手彈奏過程中起到的作用往往十分關鍵。在社會因素影響下,很多情況下,傳統音樂都是以追求優美感為核心,和諧美也最為主要。但是《音樂二度創作的美學思考》中所提出的任何一部作品對應的創作年代都存在較大差異,因此,無論是體裁還是形式方面,都不能相提并論[4]。箏曲《出水蓮》也不例外,不同演奏家對作品的理解不同,而且主觀色彩絕對不能占據主體地位,此種狀態下,音樂也會徹底失去生存的基礎。任何一個版本,展示的都是蓮花高傲的情操,這是永遠都不可動搖的。同時也是對客家人文化精神的重要體現。
四、結語
《出水蓮》演奏過程中,聽眾會被磅礴的音樂氣質所新,同時也能夠將人們潔身自好的生活方式全面出來,追求完美的人格,正像蓮花的“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的情懷,這也是曲目的核心主題與價值理念。從目前發展狀況來看,隨著人們生活節奏的不斷提升,我們已經習慣在快節奏的生活中發展。而《出水蓮》就是焦躁社會中的一片凈土,用音樂來不斷凈化人們的心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