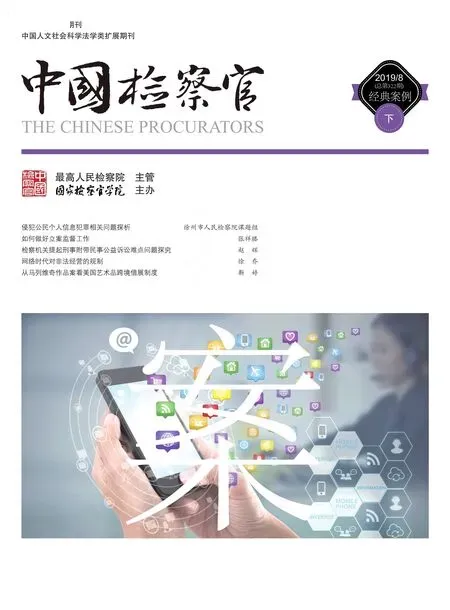如何做好立案監督工作
——以孫某某使用虛假身份證件監督案為視角
●張祥塍 /文
[基本案情]犯罪嫌疑人孫某某于2004 年間在北京市豐臺區小井十隊出租房開小賣部。2004 年7 月2日20 時許,犯罪嫌疑人孫某某因被害人王某某(男,歿年28 歲,河南人)在小賣部對其三嫂丁某某言語輕薄,與王某某發生口角,后孫某某將王某某趕出小賣部,并在小井十隊54 號出租房西側胡同內持水果刀扎刺王某某左大腿一刀,致其死亡。經鑒定,王某某符合被銳器刺傷左大腿,刺破左側股動、靜脈,致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案發后,犯罪嫌疑人孫某某逃跑,并于2018 年3 月5 日被公安機關抓獲歸案。
據孫某某供述,作案后,自2011 年5 月12 日起,花錢通過山西省應縣公安局黨委委員霍某某,應縣公安局下轄的花城派出所制作“吳某某”身份證一張(照片為孫某某本人,身份信息為吳某某的本人信息),其在逃期間使用制作的“吳某某”身份在多地打工,直至被抓獲。
一、監督經過
犯罪嫌疑人孫某某因涉嫌故意傷害罪,于2018 年3 月5 日被北京市公安局豐臺分局刑事拘留,后提請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二分院(以下簡稱“二分院”)審查逮捕,期間,負責審查逮捕工作的檢察官將孫某某涉嫌偽造身份證件的線索移交筆者審查。筆者認為,犯罪嫌疑人孫某某作案后潛逃多年,并購買及使用了“吳某某”身份證,根據現行《刑法》第280 條第3 款規定,構成買賣身份證件罪。因犯罪嫌疑人孫某某的行為發生在2011 年,在《刑法修正案(九)》2015 年出臺之前,因此適用《刑法修正案(九)》之前的規定,按照偽造、變造身份證件罪處罰。
另,該行為的犯罪地為山西應縣,管轄地在山西,但鑒于孫某某的故意傷害行為與偽造、變造身份證行為涉嫌的犯罪屬于關聯犯罪,因此應一并審理,建議提出追加偽造、變造身份證罪,進行立案監督。
2018 年6 月1 日二分院向北京市公安局發出《要求說明不立案理由通知書》,2018 年6 月7 日收到北京市公安局豐臺分局《不立案理由說明》,豐臺分局認為:犯罪嫌疑人孫某某通過制販假證人員辦理“吳某某”的身份證,制證材料真實,并非偽造,有山西應縣公安局金城派出所出具吳某某常住人口登記表、戶口注銷證明等證據在案證實,金城派出所辦理的人員已病故,制販假證人員亦未找到,相關工作無法開展,故不符合立案條件。另管轄應由山西應縣公安局予以立案。
收到公安機關移交的《不立案理由說明》后,筆者仍然認為,公安機關的《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建議對北京市公安局(或豐臺分局)進行監督立案,決定發出《通知立案書》。
公安機關于2018 年6 月28 日決定對孫某某涉嫌偽造、變造身份證件案立案偵查,案件偵辦過程中,筆者結合案件證據,建議偵查機關以孫某某涉嫌使用虛假身份證件罪移送審查起訴,偵查機關采納筆者意見,案件提起公訴后,被告人當庭表示對使用虛假身份證件的犯罪事實認罪,辯護人對此亦無異議,法院判決完全認可檢察機關的意見,本案取得良好的監督效果。
二、法理闡釋
本案立案監督過程中,公安機關與檢察機關的分歧主要有兩個:第一,“吳某某”的身份證是否屬于“偽造”的身份證;第二,針對偽造身份證的該起案件,北京公安機關是否具有管轄權。第二個爭議根據關聯犯罪并案處理的原則即可順利解決,事實上本案爭議的焦點在于“吳某某”的身份證是否屬于偽造的身份證件。
公安機關認為“吳某某”的身份證不屬于偽造的身份證件,理由如下:判斷身份證件是否系偽造的關鍵在于制證主體是否合法。本案中,雖然犯罪嫌疑人孫某某是通過制販假證人員聯系辦理的身份證件,但最終制作身份證件的是有權制作身份證件的公安機關,且制證材料真實,因此“吳某某”的身份證件不能評價為刑法上“偽造”的身份證件。
筆者認為“吳某某”的身份證屬于偽造的身份證,主要理由如下:身份證是由國家有權機關制作的,用以證明當事人身份信息的證件。真實有效的身份證形式上必須由國家有權機關制作,內容上必須為當事人真實的身份信息,二者缺一不可。因此,偽造不僅包括無權制作身份證件的人擅自制作居民身份證件(有形偽造),而且包括有權制作人制作內容虛假的居民身份證件或者違反法律規定的身份證件(無形偽造)[1]。本案即為有權制作人制作內容虛假的居民身份證件,屬于無形偽造的一種,“吳某某”的身份證應認定為“偽造”的身份證件。
單純將制證主體是否合法作為判斷身份證件是否系“偽造”的標準,忽略了身份證件的主要功能在于證明當事人的身份信息,而承擔這一功能的關鍵不僅僅在于制證主體的合法,更在于內容的真實性,某種程度上可以說主體的合法性恰恰是為了保障內容的真實性。因此,公安機關的理由不能成立。
本案中雖然應縣公安局黨委委員霍某某已于2015年6 月去世,但不影響罪名成立。犯罪嫌疑人孫某某為偽造、變造身份證提供了照片,付出9000 元辦理費用,為偽造、變造行為提供了幫助,具有共同故意,系犯罪成立的條件之一,因此應以偽造、變造身份證罪立案監督。
公安機關立案偵查后,因應縣公安局黨委委員霍某某已經去世,孫某某為辦理身份證件聯系的中間人未找到,證明犯罪嫌疑人孫某某偽造身份證件的證據鏈條斷裂,相關證據不足,但證明犯罪嫌疑人使用虛假身份證件的證據充分,故最終檢察機關以使用虛假身份證件罪對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訴,并得到訴訟參與各方一致認可。
三、辦案啟示
結合本案的辦理,筆者認為,新時代作好立案監督工作,要進一步樹立雙贏共贏、主責主業、全程引導等三種監督理念,具體如下:
(一)樹立雙贏共贏的監督理念,形成監督工作合力
從某種意義上說,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屬于一種法律上的“制約”活動,將因“制約”而容易引發的緊張、沖突關系,轉化為雙方的良性互動關系,也就是要樹立共贏的監督理念[2]。在履行立案監督職能過程中,檢察機關與公安機關屬于監督者與被監督者,二者是天然的對立關系,甚至可以說,檢察機關的業績恰恰建立在公安機關錯誤甚至“失職”的基礎之上,因此,公安機關對檢察機關立案監督持有天然排斥甚至對抗的態度則不足為奇。筆者認為,堅持雙贏共贏的監督理念并不是說要通過檢察機關的努力,達到公安機關希望因自身工作不足導致被監督,而是指檢察機關在履行立案監督職能過程中,通過各種方式,盡力削減公安機關對檢察機關的排斥,努力在更高層次上實現檢察機關與公安機關利益的重合,達成雙贏共贏。
本案辦理過程中,首先堅持依靠過硬的專業能力中贏得尊重。檢察機關并不會因為處于監督者的地位而自然贏得被監督者的尊重,“打鐵還需自身硬”,監督者只有在水平不低于被監督者甚至高于被監督者的情況下,才能贏得被監督者的認可。本案中,關于“吳某某”的身份證件是否屬于偽造的證件、北京公安機關是否擁有管轄權等爭議問題,筆者在接到相關訴訟監督線索后,即通過各種形式進行了充分探討和研究,并查閱了相關判例,在確信自身觀點正確的前提下,開始與公安機關進行溝通,這是立案監督工作中檢察機關的底氣所在,案件最終處理結論完全按照筆者預想的進行,這不僅為本次案件的辦理贏得公安機關的尊重,更為以后筆者開展立案監督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其次,通過強化溝通,在服務大局方面贏得公安機關理解。堅持共贏監督理念,要求溝通交流過程中,檢察機關不以監督者自居,尤其不能給公安機關以高人一等的感覺,而應努力通過平等交流實現監督目的。筆者在辦理本案過程中,主動就爭議問題向公安機關闡明立場,并進行詳細說理論證,后公安機關承辦人逐漸認可筆者觀點,但提出,因為孫某某已經涉嫌故意傷害罪且致人死亡,偽造身份證件罪量刑與其相比,幾乎不會對本案的實質處理產生多大影響,因此似沒必要再對此刑事立案。筆者認為,誠然,相較于故意傷害致人重傷而言,偽造身份證件屬于輕罪,但刑罰的功能并不僅僅在于特殊預防,更在于一般預防,因此,對孫某某偽造身份證件的罪行刑事立案,并不僅僅是單純為了對孫某某本人定罪處罰,更重要的向公眾表明刑法對此類犯罪行為的否定評價,尤其是筆者結合近年來媒體報道的多起違法人員利用多張“有效”虛假身份證件從事違法犯罪活動,給社會秩序造成惡劣影響等熱點事件,反復向公安機關說明打擊此類犯罪的重要性,在服務大局方向贏得公安機關的理解。
最后,在幫助公安機關提高辦案水平上贏得公安機關對監督工作的支持。筆者深知,監督工作于檢察機關而言屬于業績,于公安機關而言則屬于工作不夠到位的體現。因此,每辦理一起立案監督案件,筆者都會利用各種場合就案件所涉法理與公安機關充分交流,切實幫助公安機關提高辦案水平,努力讓公安機關整體而言從一起案件中得大于失,為以后順利開展監督工作贏得支持。
(二)樹立主責主業的監督理念,依法主動精準監督
目前,全國檢察機關均已實行“捕訴合一”,除北京市外,各級檢察機關不再設立單獨的偵查監督部門,立案監督工作由承擔審查逮捕、審查起訴的刑事檢察部門檢察官負責,由于受審查逮捕、審查起訴等特定辦案時限的要求,檢察官極容易將絕大部分精力放在審結批捕、起訴案件中,而有意無意地疏忽立案監督等訴訟監督工作,這顯然與檢察機關憲法中法律監督機關的定位不符。筆者認為,為更好履行立案監督職能,檢察官應進一步樹立主責主業的監督意識,切實提升監督能力,依法主動精準監督。
首先,要明確辦案能力不等于監督能力。司法實踐中,很大一部分監督線索均來源于刑事案件辦理過程中,但也不能將“監督”與“辦案”完全等同,比如,無論是審查逮捕還是審查起訴工作,主要表現為被動審查,而立案監督工作則更提倡檢察官的主動意識,這既包括了主動發現線索的意識,也包括了主動要求偵查機關啟動刑事訴訟程序的意識。再比如,由于所處的階段不同,立案所需的證據標準則有別于審查逮捕和審查起訴階段,批捕、起訴階段所需證據標準明顯要高于立案標準,立案監督工作更強調檢察官對案件后續走向的預判能力。
其次,監督能力以辦案能力為前提。立案監督是對公安機關的工作進行監督,除了需要具備基本的案卷審查及法律適用等辦案能力外,還需要對案件立案后通過繼續偵查能否達到最終庭審標準的預判能力,預判能力的養成則需要靠長期的司法實踐和辦案積累。可以說,沒有較長一段時間刑事辦案能力的實踐和積累,監督工作難免缺乏底氣。筆者在辦理孫某某案過程中,之所以敢于要求公安機關以偽造、變造身份證件罪立案偵查,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多年的工作經驗使得筆者堅信,即便最后偽造、變造身份證件罪證據不充分,使用虛假身份證件罪證據也不難查找。
最后,將立案監督事項案件化辦理實現精準監督。案件化的內在表現形式為證據化,就是司法辦案活動必須圍繞證據來展開,需要用一套統一的證據規則體系來保障案件辦理的質量[3]。一言以蔽之,案件化辦理要求嚴格貫徹證據裁判原則。筆者在辦理孫某某立案監督案件時即嚴格貫徹證據裁判原則,并根據不同階段適用不同的證據標準。在收到監督線索后,根據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可初步判斷犯罪嫌疑人通過花錢、提交個人照片等行為參與了虛假身份證件的制作,因此,應將其作為偽造、變造虛假身份證件的共犯來處理,遂要求公安機關以偽造、變造身份證件罪對孫某某立案偵查,案件進入刑事訴訟程序后,由于參與制作假證的公安機關霍某某已經去世,制販假證的中間人客觀上無法找到,證明犯罪嫌疑人參與偽造身份證件的證據主要為犯罪嫌疑人的供述,系孤證,根據孤證不能定案的證據裁判原則,認定孫某某偽造、變造身份證件的證據不足,筆者遂要求偵查機關查找孫某某使用“吳某某”身份證件的相關證據,后公安機關補充了有關證人證言及相關客觀證據,最后決定以使用虛假身份證件罪提起公訴。
(三)樹立全程引導的監督理念,確保立案監督實效
有論者提出,從應然層面,可以將立案監督權運行模式分為程序啟動模式、全程引導模式和追訴控制模式,指出我國檢察機關立案監督權運行模式以程序啟動模式為主,兼具全程引導模式的一些特征,通過分析論證提出,我國的立案監督權運行模式有必要向全程引導模式轉變[4]。筆者認可上述觀點,認為根據現有法律規定及我國檢警關系實際,程序啟動模式難以保障監督取得實效,追訴控制模式似有“越位”之嫌,且不符合檢警既“配合”又“制約”的基本關系,全程引導模式更符合我國司法實踐,能夠較好實現檢察權對偵查權的制約,實現打擊犯罪與保障人權的平衡,這也與北京檢察機關提出的“整合兩項審查、突出實質審查、審查引導偵查”相契合。
筆者在辦理孫某某監督案時,收到監督線索后,在主要依靠犯罪嫌疑人供述的情況下即果斷開展立案監督工作,要求公安機關啟動立案程序;公安機關立案后,并未“撒手不管”,而是及時與偵查機關承辦人溝通,開展引導偵查工作,詳細列明補充偵查事項,要求按照庭審標準來收集證據;在部分證據確實已經湮滅、無法取得的情況下,及時調整引導偵查方向,要求偵查機關重點查找犯罪嫌疑人孫某某使用虛假身份證件的證據。可以說,本案辦理的每一個環節,筆者都堅持跟蹤引導,最終取得良好監督效果。
注釋:
[1] 參見張明楷:《刑法學》,法律出版社2016 年版,第1041 頁。
[2] 參見孫謙:《刑事立案與法律監督》,《中國刑事法雜志》2019 年第3 期。
[3] 參見李辰:《檢察監督視野下重大監督事項案件化辦理制度的建構》,《法學雜志》2018 第8 期。
[4] 參見于昆、姚磊:《檢察機關立案監督權運行模式探析》,《人民檢察》2017 年第20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