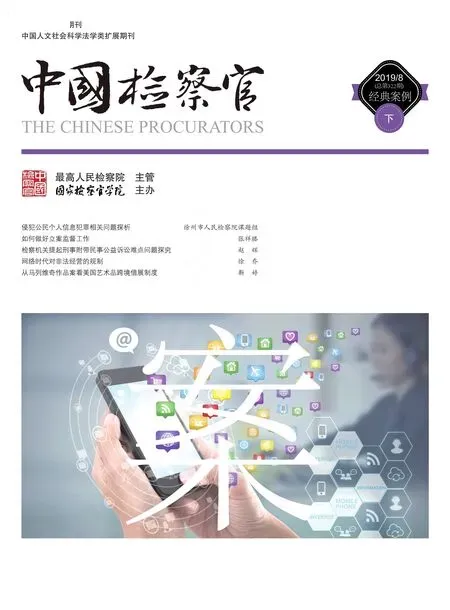暴力襲擊輔警應否從重處罰
●邢小兵 衣艷梅 李德勝/文
一、 基本案情
2018 年11 月28 日15 時許,犯罪嫌疑人奚某違規駕駛客運汽車拉載貨物行駛至北京市大興區某收費站時,遇輔警國某在交警白某的帶領下設卡查處違法車輛,國某將奚某車輛攔停后要求其出示駕照接受檢查。為逃避檢查奚某拒不配合,邊用手掰開國某把住車窗的手邊加速行駛,致國某倒地受傷。后經法醫鑒定,國某受傷程度為輕微傷。奚某被當場抓獲歸案。
二、 分歧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暴力襲警從重處罰條款所保護的首要法益是警察的執法權而非警察的人身權,是否具備“人民警察”身份并非判定是否適用從重處罰條款的關鍵所在。從客觀危害性層面來講,襲擊協助警察執法的輔警自然妨害了公務活動,也嚴重侵犯了警察的執法權,這與襲擊警察所造成的危害后果無本質區別;從主觀惡性層面來講,行為人往往并非故意挑選襲擊對象,而是誰阻攔其行為就侵害誰,襲擊輔警的行為人主觀上具有妨害警察執法權的故意,故沒有必要將從重處罰的對象嚴格限定為“人民警察”,對暴力襲擊依法執行職務的輔警的也應從重處罰,本案犯罪嫌疑人奚某的行為應當適用從重處罰條款予以規制。
第二種意見認為,從文理解釋的角度來講,輔警并不在人民警察的概念范圍內,將輔警解釋為人民警察對行為人予以從重處罰有類推解釋之嫌,違背刑法的解釋原則。輔警相較于人民警察而言,并無獨立的執法權,其輔助人民警察從事執法活動時在身份上擬制為國家工作人員成為妨害公務罪的適用對象,但是在該法律擬制的基礎上,若再將暴力襲擊輔警擬制為暴力襲擊人民警察予以從重處罰,無異于對行為人進行雙重不利評價,有違罪刑相適應的基本原則,故暴力襲擊輔警不宜從重處罰,本案不應適用從重處罰條款。
三、 評析意見
筆者同意第二種處理意見,具體分析如下:
(一)法意探尋:從重條款的法律擬制是立法為回應社會關切而對“人民警察”所作出的特殊保護
《刑法修正案(九)》在妨害公務罪中增設了第5款規定,“暴力襲擊正在依法執行職務的人民警察的,依照第一款的規定從重處罰”,但如何認定并適用該條款卻沒有相應的司法解釋予以細化規定。立法的粗疏及司法解釋的空白,既造成了理論研究的困惑,也導致了司法適用的含混,對暴力襲擊輔警的行為能否適用從重條款進行處罰,實踐中存在不同的主張和做法。筆者從裁判文書網上搜索了暴力襲擊輔警的相關案例,發現部分地方法院在裁判文書中并未對輔警的身份進行任何置喙,在法律適用部分直接落筆為“暴力襲擊正在依法執行職務的人民警察”,從而對行為人進行從重處罰,例如(2018)豫10 刑終246 號裁判文書。也有部分地方法院對該問題采取了回避態度,在裁判文書中并未論證輔警在身份上有別于人民警察的問題,而是直接適用第277 條第1 款的規定進行定罪量刑,例如(2018)津8601 刑初10001 號裁判文書。筆者認為,在具體的司法過程中遇到法律適用爭議時我們不應采取回避的態度,而是應多方面探尋立法本身的真實含義,確保準確地選擇和適用法律,讓法律因應用而精彩。
立法機關將暴力襲警行為明確列舉出來予以從重處罰主要源于兩個層面的現實性考量:一方面,是對人民警察職權的特殊性考量。根據《人民警察法》的規定,人民警察肩負著維護國家安全,保護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財產,保護公共財產,預防、制止和懲治違法犯罪活動的任務,具體執法范圍廣泛,涉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一個和諧安定的社會所呈現出來的良好的公共秩序,背后所仰賴的正是人民警察一項項具體職責的正常開展。“作為一支對內承擔國家安全和社會秩序維護的武裝力量與暴力后盾,如果其執法權得不到有效保障,必將直接影響整個國家和社會的穩定。”[1]可以說,人民警察職權的特殊性需要立法機關對這類公務主體予以特殊保護。
另一方面,是對當前社會矛盾多發、暴力襲警案件頻發的現實性考量。《刑法修正案(九)》在修改草案時,對于暴力襲警行為的處理存在兩種意見,一種意見是主張設立單獨的襲警罪,另一種意見則是將襲警作為妨害公務罪的從重情節并加以嚴格限制。[2]立法機關經過研究后認為,在實踐中我國對襲警行為一直是按照《刑法》第277 條妨害公務罪的規定處理。針對當前社會矛盾多發,暴力襲警案件時有發生的實際情況,在妨害公務罪中將襲警行為明確列舉出來,可以更好的起到震懾和預防犯罪的作用。[3]可以說暴力襲警從重處罰條款的出臺,是立法機關為回應社會關切,秉持審慎的立法理念而作出的立法舉措。人民警察相較于其他公務主體,在執法過程中所面臨的危險更大、承擔的風險更高,對人民警察予以特殊保護,實現法律與社會的良性對接,從功利主義的角度來看符合刑事立法的目的。
本案中,國某作為一名交通輔警,案發時正在交警白某的帶領下,協助采集交通違法信息、查處交通違法行為。雖然從主體適格角度來講,國某具備公務人員的主體資格,但其在身份上畢竟有別于交警白某,不具備獨立的執法權。若人為拔高輔警國某的主體身份,將國某比作人民警察予以特殊保護,恐曲解了暴力襲擊從重處罰條款的立法原意,背離了孵化該條款出臺所立足的社會價值觀念。
(二)解釋限制:將“輔警”解釋為“人民警察”既超出刑法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也有違社會大眾的普遍認知
首先,將“輔警”解釋為“人民警察”超出了刑法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當法律存在疑問或爭議時,司法工作者應當按照一般的解釋原則來消除疑問。具體的法律解釋方法有很多種,包括文理解釋、體系解釋、歷史解釋、目的解釋等,但無論采用哪種解釋方法,均不能超出刑法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如果脫離刑法用語追求所謂‘正義’,人們在具體情況下便沒有預測可能性,刑法本身也喪失安定性,國民的自由便沒有保障,國民的生活便不得安寧。”[4]換言之,完全脫離法律用語,就成了推測而不是解釋。具體到從重處罰條款中能否將輔警解釋為人民警察的問題上,根據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規范公安機關警務輔助人員管理工作的意見》第3 條的規定,“警務輔助人員,是指依法招聘并由公安機關管理使用,履行本辦法所規定職責和勞動合同約定的不具有人民警察身份的人員,主要包括文職、輔警兩類從事警務輔助工作的人員”。根據意見的規定,輔警作為警務輔助人員中的一種,被明文排除在人民警察的概念范圍外。因此,從法律解釋的角度來講,將輔警包含在人民警察的概念范圍內明顯超出了刑法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有類推解釋之嫌,違背了法律解釋的一般原則。
其次,將“輔警”解釋為“人民警察”有違社會大眾的普遍認知。一方面,根據從重處罰條款的規定,“暴力襲擊正在依法執行職務的人民警察,依照第1 款的規定從重處罰”,對該條款中的“人民警察”是理解為一個寬泛的概念,還是理解為一種對身份的強調?筆者認為,從社會大眾的普遍認知出發,答案應當是后者,即此處的“人民警察”應當是立法機關突出對人民警察這一身份的強調,將不具有該身份的公務主體排除在從重處罰條款的適用范圍外,而非泛指一個執法群體。另一方面,社會大眾普遍認知輔警與人民警察在編制、職責權限、福利待遇、武裝性質、可配備警械等方面存在明顯的差別,在日常執法過程中,公眾亦可輕易地從衣著特征等方面辨別輔警與正式在編警察,正如本案被告人奚某在供述中明確表示“我剛要駛出收費站窗口,就看到收費站出口處站著一名身穿執勤制服的輔警人員”。因此,將輔警解釋為人民警察明顯超出了社會公眾的普遍認知。
本案中,若在主體身份的問題上將輔警國某解釋為人民警察,對被告人奚某進行從重處罰,屬于在法律存在疑問或爭議時所作出的不利于被告人的類推解釋,而禁止不利于被告人的類推解釋是罪刑法定原則的基本要求。就具體解釋效果而言,將輔警國某解釋為人民警察會給社會公眾造成一種認識混亂,容易導致刑事司法實踐的混亂。
(三)法理辨析:將暴力襲擊輔警的行為予以從重處罰有違刑法的謙抑性原則
“使用刑罰,如兩刃之劍,不可不慎重,必須基于刑法的謙抑性思想。”[5]筆者認為,刑法的謙抑性原則應當包含兩個層面的內容:第一個層面是入罪層面的審慎,即嚴格控制刑罰處罰的范圍。具體表現為“對于某種危害社會的行為,國家只有在運用民事的、行政的法律手段和措施,仍不足以抗衡時,才能運用刑法的方法,亦即通過刑事立法將其規定為犯罪,處以一定的刑罰,并進而通過相應的刑事司法活動加以解決”。[6]第二個層面則是量刑層面的克制,即應適當把握刑罰處罰的程度,而該目標的實現既需要刑事立法機關在個罪的設置上予以“事先布局”,嚴格遵循罪刑相適應的原則確定法定刑,更需要借助刑事司法機關在個案的刑罰裁量環節予以“具體落實”,除了在法定刑范圍內合理地確定刑罰,使行為人所應承擔的刑事責任與其所犯罪行的社會危害性、人身危險性相適應之外,還應當嚴格把握從重處罰的適用范圍,確保刑罰裁量不任性、不隨意。
在暴力襲擊輔警是否從重處罰的問題上,雖然實踐中一些地方法院在類似案例中存在適用從重條款予以處罰的判例,但立法或司法解釋并未對該問題予以正面回應,在此種情況下,作為司法工作者我們不能盲目跟風而是應當從刑法的基本原理出發,秉持謙抑性的刑法理念,在刑罰裁量環節審慎地解釋和適用法律,嚴格把握從重處罰條款的適用范圍,不可予以擴張使用。具體到本案,若將被告人奚某的行為認定為暴力襲警,對奚某予以從重處罰,從法基礎層面而言是背離刑法基本原則的一種表現,是在刑罰裁量環節對刑法謙抑性理念的一種踐踏和破壞。
綜上分析,筆者認為,暴力襲警從重處罰條款的適用范圍不可盲目擴張,對于暴力襲擊輔警的行為不應適用從重條款進行處罰。本案被告人奚某為逃避交通違法查處而強行駕車沖卡致傷輔警國某的行為,應按照妨害公務罪的基本量刑條款進行定罪量刑。另,本案已由北京市大興區人民法院依法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277 條第1 款的規定對被告人奚某作出有罪判決,判決已生效。
注釋:
[1]葛立剛:《法律擬制,抑或注意規定——“暴力襲警”條款之法律屬性辨析》,《北京警察學院學報》2017 年第4 期。
[2]參見《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審議結果的報告》。
[3]參見《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二次審議稿)〉主要問題的修改情況匯報》。
[4]張明楷:《刑法分則的解釋原理》(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年版,第5 頁。
[5]許福生:《刑事政策學》,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 年版,第416 頁。
[6]陳興良:《刑法哲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9 年版,第8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