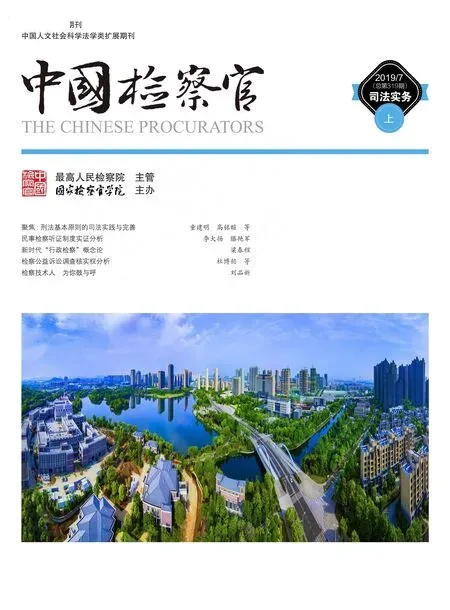罪刑法定原則的中國困境
劉艷紅(東南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罪刑法定原則是刑法的基本原則,也是法治的基本原則。罪刑法定原則應該是當下中國法治一個最大的困境。這個命題看起來似乎很空很大,其實很現實、很具體。因為在具體法治實踐中,我們面臨的現實問題就是罪刑法定原則沒有得到很好地貫徹和堅守。
我國刑法總則中規定了罪刑法定的原則,刑法分則罪名也相對完備。所以,罪刑法定原則在我國刑法中是存在的,但是要把紙面上的法律在實踐中貫徹好、實施好,還需要更多的堅守和反思。現實的情況是,無論是司法理念,還是無論是具體案件的處理,甚至是司法解釋的表述,都存在與罪刑法定原則相沖突之處。
罪刑法定原則要求我們要有“實質出罪”的司法理念。司法實踐中機械僵化理解法條的現象較為突出。比如王力軍收購玉米非法經營案,司法人員機械地認為“無證就是非法”“收購就是經營”,二者相加就是非法經營,進而得出非法經營罪的結論。司法人員沒有從實質上去考量這種行為有無侵害法益、侵害了什么法益,實質上是否符合刑法關于非法經營罪的規定。罪刑法定原則要求我們要注重實質解釋的出罪功能。只有達到了值得處罰的法益侵害性,行為才具有可罰性。符合犯罪構成要件的行為不一定都要處罰,只有其違法性亦即對法益的侵害性達到應受處罰的嚴重程度時,才可能成立犯罪。再比如,實踐中一些賣包子、油條的,查出鋁超標,要不要定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被告人自己也天天吃自己做的這些包子和油條,如果知道有毒有害怎么會自己毒害自己呢?這時候還能不分青紅皂白地定罪處罰嗎?當我們把“刑法之刀”隨意瞄準這些社會最底層弱勢群體的時候,作為法治內核的罪刑法定原則就已經走到了失守的邊緣。
禁止類推是罪刑法定原則的應有之義,但類推解釋的現象并沒有完全禁絕。罪刑法定雖然允許擴大解釋,但是這種擴大解釋是有邊界的,不能超過刑法用語的最大射程范圍,一般來說,應當禁止對被告人不利的擴大解釋。我們的司法解釋也要注意堅守罪刑法定,防止被司法實踐誤解而導致隨意擴大解釋甚至類推解釋。比如,今年4月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聯合印發的《關于辦理惡勢力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關于辦理“套路貸”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關于辦理黑惡勢力刑事案件中財產處置若干問題的意見》《關于辦理實施“軟暴力”的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等4個意見,這些意見對實踐中出現的隨意拔高或降低標準的問題進行了一定程度的糾偏,但是在表述中特別強調“依法嚴懲”就值得進一步推敲。其實,嚴格按照罪刑法定就可以了。這樣的表述在邏輯上有些問題,因為可能暗含著一種傾向,就是依法又傾向于要嚴懲,這會導致實踐中為了嚴懲可能突破依法。實踐中,債主雇傭跳廣場舞的大媽用喇叭對著樓上的住戶喊話催債,結果跳廣場舞的大媽們被當成黑惡勢力成員。再比如,因民間矛盾引發的械斗、因征地拆遷引發的上訪等也被作為黑惡勢力打擊。
司法解釋是對刑法的解釋,并非對刑法的修改。但是實踐中變相把司法解釋理解為對刑法的修改,這是違背罪刑法定的。比如“軟暴力”問題,《關于辦理實施“軟暴力”的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根據不同情形,分別對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強迫交易、敲詐勒索、尋釁滋事、非法侵入住宅等犯罪中的“軟暴力”手段進行了解釋。“軟暴力”手段是否構成這些罪名的根本標準依然是刑法的規定,而不是說“軟暴力”本來不構成尋釁滋事罪,因為有這個司法解釋,所以現在就可以定尋釁滋事罪了。例如,行為人受他人委托進行討債,建立一個微信群,每天在群里催債,被認定為“軟暴力”而定尋釁滋事罪。這有突破罪刑法定之嫌。
罪刑法定原則從寫入我國刑法典到今年已有22年,可是實踐證明,這個支柱性質的原則在中國法治實踐中堅守得不盡如人意。罪刑法定的本來含義是“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不為刑”,我國《刑法》第3條的規定與這一經典表述還存在一定的差異,因為我們在規定“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處刑”之前還規定了“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定罪處刑”,這無非就是“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另一種表述,使得罪刑法定的本質內涵受到沖擊。在這種立法背景下,更需要我們在實踐中堅守罪刑法定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