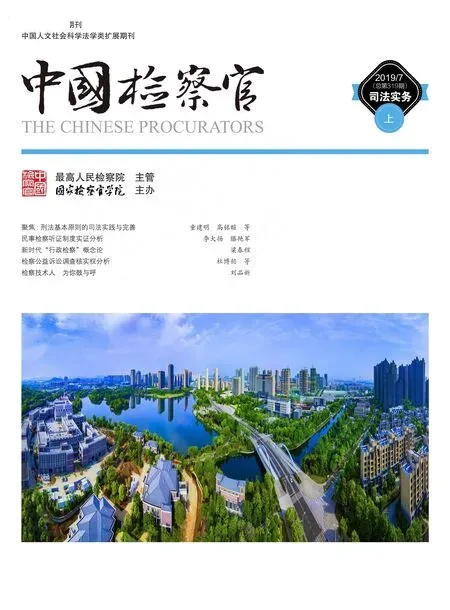謹防司法解釋逾越罪刑法定原則的樊籬
魏昌東(上海市社會科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犯罪學學會副會長)
20世紀70年代以來,世界各國刑法在犯罪規制的類型上,呈現出由以自然犯為中心向以法定犯為中心的歷史轉型,在這一進程中,刑法的修正延遲是任何社會和時代均難以避免的問題,而司法的能動性則在此刻顯現出來,其最直接的表現是,司法解釋是恪守其釋法功能,還是填補法律漏洞以追求社會正義、起“準立法”作用的問題。從當前的司法現狀來看,后者或已成為趨勢。
一、法定犯時代司法解釋擴張適用的問題
在我國,司法解釋被廣泛采用的初衷,一是為了緩解首部刑法典頒布之時即已奉行的“宜粗不宜細”立法指導思想所形成的刑法規制范圍有限、條文抽象的問題。二是為了通過對個罪或類罪作出詳盡的說明或指引,以統一司法部門對犯罪構成要件要素的認知、統一犯罪構成的標準,更好的實現“同案同判”。而在法定犯時代的催化下,司法解釋的數量迅速增加,使得司法部門在刑法適用中形成了對司法解釋的過度依賴。當任何刑法條文都能通過司法解釋來傳遞信息時,司法解釋就已經在實質上取代了刑法,進而成為了審判的依據。
法定犯的時代是犯罪代際更新加速的時代,作為建構性的法律,我國刑法難以達到“判例法”的更新速度,這也就意味著刑法將長期存在滯后性,而司法解釋的存在,則可以化解其與罪刑法定原則之間的沖突,也就不再受到刑法“滯后性”的牽制。實踐中,司法解釋的擴張表現為三種類型:一是行為類型的擴張。以非法經營罪為例,《刑法》第225條的“違反國家規定”的空白罪狀和第4項的“其他嚴重擾亂市場秩序的非法經營行為”的兜底條款,使該罪呈現出雙重不確定性,為此,司法解釋前后公布了17項。但是,如此數量的司法解釋并未能消解掉非法經營罪的“口袋性”,反而是將原來條文邊緣外的行為擴充到了“口袋”內,并依然在解釋中保留了相當大的“口子”。二是對象范圍的擴張。以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為例,2010年出臺的《關于審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對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行為對象的描述,采用的是“資金”一詞,而非“存款”。然而,在金融學的意義上,資金是存款成立的先前條件,具有不確定性,其外延遠遠大于存款。由此可知,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行為對象經過司法解釋的闡釋,已經明顯超出了條文的應然“射程”,逾越了罪刑法定原則的邊界。三是評價強度的加重。以生產、銷售假藥罪為例,該罪在立法上屬于自然犯與法定犯一體化的結構,基本犯是以“違反藥品管理秩序”為核心的法定犯,加重犯是以“違反藥品管理秩序”和“侵害公民身體健康”為核心的復合犯,但是,在2014年《關于辦理危害藥品安全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對加重犯構成要件之一“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列舉,將“生產、銷售金額五十萬元以上”與“致人重度殘疾”“三人以上重傷、中度殘疾或者器官組織損傷導致嚴重功能障礙”等相并列,忽視了加重犯的自然犯性質,片面追求法定犯的標準統一,使得社會危害性較輕的行為被評價為較重的行為。
二、司法解釋逾越罪刑法定原則的根源
傳統司法慣性與法定犯激增是導致司法解釋逾越罪刑法定原則的直接原因,但卻不是根本性原因,其根本原因在于:一是長期以來在國家與社會治理中對刑法的依賴;二是司法解釋的功能定位偏差。
自古以來,民刑合一的法制文化傳統使得刑法成為了法律的代名詞,中國的社會文化環境普遍將刑罰視為調整社會關系最為有效的手段。在傳統觀念影響下,社會對法律的調整方式與譴責力度存在特殊偏好,即定罪處罰,由此造成應然的國家法制體系與實然的國家治理環境之間存在嚴重的不協調。而司法解釋作為指導刑法應用的有權解釋,是溝通實踐與規則的橋梁,便自然地承擔起化解不協調關系的重任。受主客觀原因的影響,司法解釋選擇突破自身職能,追求更實際的社會治理效益。具體而言,在主觀方面,調和社會關系、穩定社會秩序是司法審判的目標,所以審判實踐常會受到民意的影響,滿足社會公眾對譴責力度的需求。在客觀方面,直接運用刑事處罰最具威懾力和實效性,能夠取得良好的社會懲治效果與威懾效果。所以司法解釋更傾向于突破罪刑法定原則的“枷鎖”。
司法解釋在功能定位上存在偏差,最初的原因是受1979年刑法的“類推適用”條文的影響,具有“準立法”的地位,1997年刑法雖確立了“罪刑法定原則”,但是司法解釋的功能定位并未被徹底扭轉,并在法定犯時代繼續發揮著擴展刑法范圍的作用。法定犯時代的特點在于犯罪代際更新的陡然加速,刑法作為法律規范的最后保障,不僅需要考量自身變動后的穩定性,且要衡量變動前后與前置法的關系處理,常常會牽一發而動全身。但是,司法解釋卻具有相當的靈活性,能夠及時跟進犯罪形勢和變化,有效遏制危害現象。然而,這種“及時性”的代價卻可能僭越了罪刑法定原則的底線,是對民主與人權的嚴重侵害。
三、罪刑法定原則下司法解釋的應然發展方向
司法解釋對罪刑法定原則的逾越雖有社會效益,但無異于飲鴆止渴,罪刑法定原則不僅是刑法規范的根基,也是社會穩固的保障。社會主義社會捍衛的兩大內容——民主與人權,也正是罪刑法定原則的根本,因而必須將司法解釋置于罪刑法定原則之下。對此,應當從兩方面入手確立司法解釋的發展方向。
一是轉變社會治理體系的基本理念。社會理念是長期社會實踐形成的,就如“酒駕入刑”,從抵觸到接受再到認同的社會化過程,社會群體在生理上需要逐漸適應新的規則,而社會通念更是需要長期的積淀。同樣,對刑法來說,社會群體對其依賴性一方面源自于傳統思想觀念,另一方面來自于法律規則的實際效果。二者可歸結為,社會治理標準未能良好地實現從一元到多元的轉變。前置法與后盾法是不同位階的法律規范,長期混同適用使得前置法在調整社會關系上不具有獨立自主性,法律規范對后盾法的過度依賴使得刑事法律規范成為前置法調整關系的常規手段,也變相將刑法“由后提前”。因此,應當注重前置法自身保護規則的構建,強化前置法的調整效果,使得前置法能夠滿足社會治理需求,實現社會治理多元化。
二是確立法秩序統一的評價機制。法律規則即為社會框架,不同性質的規則共同搭建起了紛繁復雜卻牢固穩定的社會環境,不同部門法之間應當只有目的不同,不應當存在沖突或對立的狀態,法定犯的核心是行政犯,而行政犯則是以存在前置的行政法律規制為前提的,法秩序統一性原理,要求對法定犯的刑法評價,必須確立“行刑鴻溝”的立法與司法處置理念,堅守“前置法用盡”的原則。因而超出罪刑法定原則范圍的司法解釋,因其天然的規則侵犯性,雖然脫離“解釋”職能的司法解釋或許能實現刑法的目的,但卻將直接造成整體法秩序的動蕩與紊亂。故應確立法秩序統一的評估與檢測機制,將司法解釋置于整體法秩序之中,確立立法部門與行政部門的司法解釋審核權,明確立法部門與行政部門審核流程,只有通過兩部門審核的司法解釋才能夠予以適用。
堅守罪刑法定原則就是堅守社會主義民主與人權。司法解釋的“準立法”性是在歷史原因下形成的,但卻具有副作用與危害性。為此,應當摒棄傳統社會維持的刑法依賴性,確立法秩序統一機制,謹防司法解釋逾越罪刑法定原則的樊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