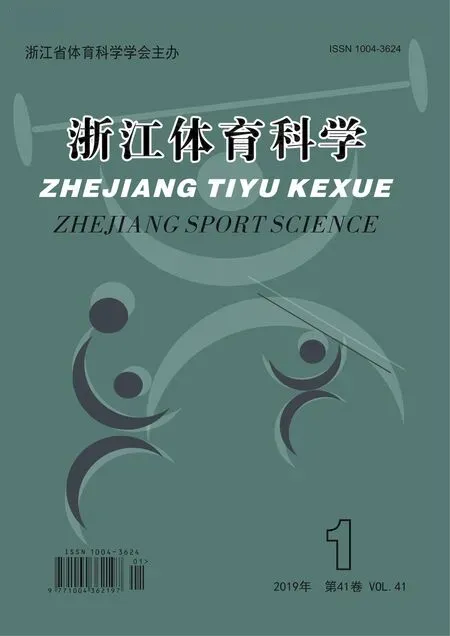時代洪流中的她們
——從代際關系視角看廣場舞鍛煉者
謝晶晶
(寧波大學 體育學院,浙江 寧波 315211)
0 前 言
中老年女性是廣場舞運動的“主力軍”,她們在參與廣場舞的過程中得到身體鍛煉與社交需求的雙重滿足,而較低的門檻則促使這項運動迅速風靡。近年來,隨廣場舞的持續熱潮產生的一些社會問題開始得到有序的組織與處理,但這種趨勢并沒有在全國各地得到完全覆蓋。占用場地、噪音擾民等一直存在的矛盾依然是“廣場舞”和廣場舞者遭致爭議的主要原因。固然,問題產生的根源是社會體育資源無法滿足人民群眾體育需求,但廣場舞鍛煉者與年輕一輩互相不理解產生的矛盾也是廣場舞作為一種社會問題日益加劇的重要原因[1]。
本研究從代際關系的角度展開考察,結合人類學和社會學關于代際關系的相關理論,以“中老年女性廣場舞鍛煉者”為研究對象,對當今社會中的廣場舞沖突形成新思維。
1 代際沖突的理論基礎
1.1 代際問題的提出
社會學家曼海姆指出,“代”是一種社會位置而非實存的群體。作為代際問題的基本概念,“代”的具體涵義有諸多解釋。《社會學簡明詞典》將其釋義為“代——社會一年齡范疇,名義上的群體。屬于同一代的人,其年齡處于某一段,但也并非是不變的。確定代的界限之所以困難,是因為他的社會一生物標準眾多和自相矛盾:青年在生理上的成熟期;結婚的平均年齡;勞動活動開始的時間——這是社會成熟的主要標準;最后,生活方式、行為和價值觀的共同性。”[2]
人是歷史性的存在,這不僅意味著人具有歷史性,生存于歷史之中,它也意味著人不可能超越歷史而存在[3]。同樣,對人的觀察討論也不能脫離社會歷史而存在。若是研究廣場舞問題的視角延伸到代際關系上,那么廣場舞一直以來存在的糾紛可能會有新的解釋。
1.2 代際關系理論的具體內容
自上世紀四十年代代際關系的議題提出以來,學者們對其進行了大量研究與闡述,而在這些論述之中,美國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的理論被公認為經典。她將人類文化以傳遞方式為特征區分為“前喻文化”、“并喻文化”以及“后喻文化”。
前喻文化始于原始社會。數千年前的物質基礎匱乏,人們對祖輩傳遞下來的知識與經驗全盤接受,沒有質疑也就排除了代溝產生的可能。
并喻文化誕生在前喻文化崩潰之際。隨著戰爭導致國家分崩離析、移民帶來了文化沖擊、科學解釋物質世界等各種因素,年長一代不再是年輕一輩的行為楷模,新一代只能自己摸索、仿效同輩,但年長一輩仍然處于支配地位,當兩輩人不可避免的產生矛盾時,就產生了最初的代際沖突。
后喻文化與前喻文化相反,是由年輕一代將知識文化傳遞給前輩。后喻文化是社會的急劇變化所導致的,新一代不再依賴前輩甚至成了前輩的知識傳授者,而老一輩仍然試圖保持權威地位,于是“代溝”問題就凸現出來了。
代溝是指由于時代和環境條件的急劇變化、基本社會化的進程發生中斷或模式發生轉型,而導致不同代之間在社會的擁有方面以及價值觀念、行為取向的選擇方面所出現的差異、隔閡及沖突的社會現象[4]。在不同時代成長的人之間的差異存在在行為方式、價值觀念等各個方面,而當這些差異擴大到普遍個體上時,就出現了“代溝”現象。
在面對代際沖突時,年長一輩將其歸咎于年輕一輩的“叛逆”,卻鮮少反思自身是否落后;而年輕一輩執著于年長一輩的“不理解”與“落伍”,對年長一輩的知識經驗不屑一顧,二者都沒有站在對方的角度思考造成沖突產生的根源。米德對此的理解是:真正的交流應該是一種對話,而這也引導著我們重新審視廣場舞文化的價值與面對沖突的態度。
2 我國廣場舞鍛煉者的現狀
在全民健身戰略與積極老齡化戰略不斷推進的今天,廣場舞作為一項受眾廣、門檻低但又存在社會沖突的群眾體育運動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
一方面,對于當下“有錢有閑”的中老年婦女來說,參與廣場舞是一個很好的體育休閑活動。在合理有序的組織下,參與廣場舞鍛煉不僅能滿足中老年婦女強身健體、防病治病的需求,同時起到休閑娛樂、陶冶情操的作用,以促進社會交往,和諧人際關系,進一步提高中老年婦女的生活質量。
另一方面,對廣場舞鍛煉者的爭議較多集中在時間與空間上。廣場舞爭議的實質是廣場舞愛好者與周邊居民爭奪休閑權和休息權的斗爭[5]。噪音擾民的本質仍是場地不足引起的群體利益的沖突。
其次,廣場舞為參與者帶來眾多益處的同時也為其引來社會污名。媒體或現實生活中的人們提起“廣場舞大媽”時,總帶有一些貶義與偏見。廣場舞被媒體貼上了低俗的標簽,反映并加強了“大媽”群體在社會上的邊緣地位。然而,“品味”本質上是十分可疑的,它只不過是消費時代媒介與商業邏輯合謀產生的幻像而已[6]。
3 廣場舞鍛煉者的代際沖突
3.1 廣場舞鍛煉者的“擾民”沖突
3.1.1 廣場舞的“噪音擾民”是引發一系列社會矛盾的主要原因之一。每個人的作息受到年齡、職業、身體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也許清晨廣場舞鍛煉者們翩翩起舞的時候,正是年輕的創業者徹夜工作后剛準備休息,而傍晚吃完晚飯時的樂聲又被父母們質疑“影響到孩子寫作業”。但是,一直以來,關于權利沖突在法律理論與實踐操作上存在較大的爭議。即使是現有相關法律也沒有給體育活動參與權和城市居民安靜權界定一個清晰的邊界[7]。
3.1.2 “違規占道”也同樣引發矛盾。籃球場等專用場地被廣場舞鍛煉者占用受到批判無可厚非,但在社區與公園等公共場地的分配上卻是各人有各理。如果立足于在公共空間的鍛煉行為對老年人進行批判,顯然是非常片面的。從年齡結構來看,當前中老年人經歷過有著鮮明集體主義的“毛時代”,因而或多或少地內化了那個時代的行為方式,比如在公共場合跳集體舞而當前社會的中青年,則更多受到改革開放后西方文化的影響——強調個人空間權利的重要性[8]。中老年婦女對在公共場地跳廣場舞的訴求真的是不合理的嗎?在當代中國,城市化的建設進程越來越快,被資本層層覆蓋下的城鎮高樓林立,從這個角度看,甚至可以假設公共空間是被擠壓的,“大媽”們跳廣場舞的權益正在被侵犯。
3.2 廣場舞鍛煉者的“觀念”沖突
3.2.1 當傳統的思維方式、行為習慣、生活習慣都變得“不合時宜”時,中老年群體固有的“傳統”和“現代”的價值理念也開始產生沖突。傳統的中國女性承擔撫養后代、照顧家庭的責任,而當下的中老年婦女依賴家庭,依賴子女的傳統觀念開始瓦解,逐漸完善地把注意力不再全部放在家庭與子女身上時,中老年婦女更是開始關注自身的保養。
3.2.2 廣場舞在質疑聲中仍發展迅猛,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在傳統的“熟人社會”向“陌生人社會”轉變過程中,中老年群體能在廣場舞活動中構建“熟人關系”網絡,獲得人生的自信和情感的溫暖,在人際交往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這種思想上的變化,促使中老年婦女群體積極主動地參與廣場舞類的集體活動,在“傳統”與“現代”的沖突中積極主動尋找社會存在感和歸屬感的人生價值。
3.3 廣場舞鍛煉者的“污名”沖突
3.3.1 提起公園里跳廣場舞的大媽,總給人“不合潮流”、“落伍”、“老氣”等等觀感。長期以來,人們賦予逐漸老去的身體的面具有助于將人們固定在有限角色上,比如祖父母輩,不為個體性和多樣性留出什么空間。人們印象中的中老年人是被邊緣化的、被忽視的、日落西山的;而在進行廣場舞的過程中,她們體現出來的是對積極生活和美的追求。這種自我追求和社會期待的沖突,是廣場舞被污名的重要原因。
3.3.2 廣場舞“大媽”在現今似乎已經成為了一種帶有負面意喻的稱呼。在新聞報道和娛樂節目中,不再年輕的女舞者們似乎有各種各樣的麻煩事:和年輕人搶運動場地、影響住宅區居民休息、甚至因為這些矛盾引發砸音響、潑水等進一步沖突;而其音樂、舞蹈動作、舞蹈服飾更是被貼上“土味”、“品味低俗”的標簽,廣場舞鍛煉者們在公眾面前的形象已然變味。
4 結論與建議
4.1 在理解的基礎上平等對話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曾經沸沸揚揚的九零后青年開始注重的“佛系養生”更像一種發現自己不再是時代弄潮兒的自嘲,而慢慢出現“其實廣場舞去跳跳還蠻有意思的”的聲音也算是一種與曾經目空一切的自己握手言和。緩解沖突的關鍵在于新舊兩代人如何共同面對這一人類社會的必然規律。了解是交流的基礎,我們對廣場舞的評價理應建立在對廣場舞客觀辯證的認識以及對廣場舞鍛煉者的基本尊重之上。
4.2 以寬容的態度來對待差異
在社會轉型中出生和成長的兩代人在觀念、文化、行為方式等方面上存在差異是不可避免的,我們可以通過正確了解與處理代際問題來緩解代際矛盾。我們面對廣場舞鍛煉者時要持有寬容的態度并以辯證的目光看待,只要對矛盾的處理得當,能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代際矛盾體現在廣場舞鍛煉上出現的問題的擴大。
4.3 在廣場舞鍛煉上與時俱進
相較于之前的所有中老年人,新一代中老年人有著明顯的不同:他們經歷過國家政權的更替、經濟體制的變革、科技的一次次革命……這些變遷隨著他們生命的歷程,影響了他們的生活環境,重塑了他們的價值體系,也改變了他們的社會參與方式。因此,在當代世界獨特的文化傳遞方式(即后喻方式)中,中老年婦女也要向年輕人學習,吸收當代文化的精粹,融入到廣場舞運動中去,與時俱進,共同發展。
4.4 在媒介輿論上把握好方向
政府部門應加大對群眾文明健身的宣傳與管理,并加強對媒介輿論對于廣場舞報道的的正確引導與管理;媒體應該將輿論導向一個相對平和的角度,對廣場舞沖突的背景與成因進行理性剖析與解讀,而非僅僅將群眾的目光聚集在矛盾沖突的具體事件上,對其進行平面、夸張的報道。
5 結 語
代際問題與每個人都息息相關,因為肉體的衰老是人生必經的過程。如何讓中老年人擁有一個幸福的晚年已經成為成為備受關注的議題,而參與廣場舞極大地充實和豐富了中老年人的生活,有利于提高其自我價值感,在全民健身與健康中國的大背景下是值得推廣與發展的群眾體育項目。解決廣場舞中存在的實際問題是促進和諧社會發展的必要手段,但廣場舞的風靡與隨之而來的爭議中實應折射出更深層次的歷史與社會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