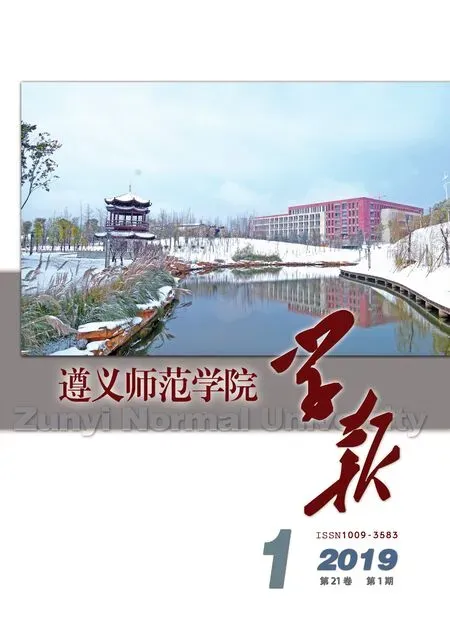從涓生看現代知識分子的心理禁閉
褚連波
(遵義師范學院人文與傳媒學院,貴州遵義563006)
《傷逝》是魯迅唯一的一部描寫愛情的小說,對于這部作品的研究成果集中于以啟蒙為話語核心,以子君和涓生的愛情悲劇及其根源為研究對象,代表性的觀點有以下幾種:一種是結合時代氛圍與魯迅自身經歷,分析社會環境對悲劇產生的影響[1];一種則著重分析子君和涓生的性格弱點,這種分析的結論認為子君的思想退化和對人生的狹隘理解以及涓生的懦弱是造成他們生活悲劇的根本原因[2];還有一種觀點是認為魯迅不是單純的就愛情寫愛情,而是借婚戀的悲劇表達一種和《孤獨者》《酒樓上》等相似的主題,那就是一種普遍彌漫的孤獨感以及魯迅對逃離孤獨之路的探索[3]。此外,一種不很普遍的觀點是周作人在1963年的《知堂回憶錄》中所說的對兄弟之情的哀悼,“《傷逝》不是普通的戀愛小說,乃是假借了男女的死亡來哀悼兄弟恩情的斷絕的,我這樣說,或者世人要以我為妄吧。但是我有我的感覺,深信這是不大會錯的。”周作人的說法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對于《傷逝》的研究,還有一類是從男主人公涓生的角度進行的。這類研究除了揭示子君與涓生愛情悲劇的成因之外,還從現代文化與精神分析的角度對涓生的心理與性格進行了詳細的闡釋,指出其在現代與傳統交替的過程中,所呈現出的矛盾形象。[4]
《傷逝》這篇小說充滿著無限的傷感和內心的酸楚,在情感意蘊上,《傷逝》是魯迅小說中最接近《野草》的風格的,情感的極度壓抑與宣泄使人閱讀起來覺得難以呼吸。如果《傷逝》僅僅是對造成愛情或人生悲劇的社會的控訴,這樣的情感顯然有些過度,如果只是對兄弟反目的痛楚的描述,似乎又難以涵蓋整篇文章的悲苦與激情,因為魯迅是將人生最痛苦的生離死別的體驗融入了《傷逝》的寫作之中的。魯迅是將對啟蒙的反省和對知識分子(包括自身)的批判化為藝術形象融合到作品之中,在這個意義上,涓生的懺悔既是一種有罪的告解也是無罪的辯白,他的自我譴責建立在其自我真實性的袒露之上。《傷逝》中的子君和涓生在他們各自的人生軌跡上偶然相遇并放射出短暫的光亮,此后子君在悲涼中死去,涓生在迷茫中生活,其悲劇根源除了經濟與社會原因之外,還有現代知識分子心理上的問題,即一種極端的心理禁閉。心理禁閉是人在缺乏安全感的環境中所產生的一種自我保護心理,是一種心理上的焦慮、自閉與自戀。
一、焦慮軟弱
涓生逃避現實而又充滿著憤怒的狂躁心理,他的習慣保留且善于保護自己的人格特征躍然紙上。《傷逝》的悲劇不僅僅是男人和女人的愛情或婚姻的悲劇,也不僅僅是孤獨的啟蒙者的悲劇,它是男性知識分子在從傳統到現代的轉型中的性格與人生的悲劇。在最初的示愛中,面對子君的“獨立宣言”——“我是我自己的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涓生當時的反應是震驚,既震驚于子君覺醒速度之快,也震驚于子君的勇氣。因此,在之后的生活中當他發現子君“勇敢”的背后是“虛無”之后,便放棄了對子君的愛與承諾。這是一種退守的策略,涓生時時強調的是子君所給與他的錯覺,那就是他一直以為子君是一個堅強的可以承受一切的女性,和家庭決裂都不怕,何怕再次“出走”——放棄沒有愛的婚姻(其實是同居)呢?直到子君死去,涓生還在逃避著責任。
在和子君的同居生活中,涓生潛意識里是有著強烈的自我保護意識的,他缺乏勇氣,沒有擔當,對現實不滿卻又無力改變。子君要和家庭決裂和他在一起追求自由的愛情時,他認為子君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在求婚的情節中,他一直在回避自己對子君的最熱烈的示愛方式,把跪下的行為看作是對電影鏡頭可笑的模仿,其實這是需要負責的承諾,這個行為也使子君誤入歧途,使她堅信涓生對她的愛是最堅實的。涓生把婚姻的失敗和職業的失去都歸結于不合眾意的同居亦即子君的不肯進取,其實是他逐漸厭倦了婚姻與工作,涓生對他逐漸厭倦的婚姻與早已厭倦的職業的失去,他都看作是子君的錯,認為是子君不懂得人生的要義;他想擺脫子君又怕被子君質問,就拿出娜拉來鼓勵子君走出無愛的婚姻,甚至主動要求子君拋棄自己。
《傷逝》中反復渲染的是涓生對整個感情事件的感受以及他的情緒變化,這種情緒變化不在于如何揭示了悲劇的根源,而在于這一事件不論是怎樣的結局,它本身就是一種悲劇,如果局限于對情感悲劇及其根源的探討,就無法走進魯迅豐富的內心世界和他對于人的豐富性與矛盾性的理解。涓生并沒有認識到自己性格中的弱點,當然也無法意識到自己的心理焦慮。他反復強調的說真話的后果,實際上是為他自己的懦弱與自私的一種開脫,他即使不說真話,按照他對子君的種種也會使子君陷入到精神絕望甚至崩潰的深淵,在他說真話之前他就已經殺死了一個曾經活潑的有著勇氣和無畏精神的子君,一個除了涓生之外毫無依靠的女人。
涓生的性格弱點是他不敢或者無法正視自己的內心世界,雖然在子君死后他有過懺悔,但這種懺悔不過是他借以擺脫罪惡感的一種方式,他把自己的厭倦生活歸咎于子君的改變:子君變胖了,子君的手變粗糙了,子君總是要回憶自己最不愿意記起的一幕,子君沒有高尚的生活情趣,子君沒有對生活更高的追求,總之子君不再是令他心動和愛慕的對象,甚至子君沒有因為生活的苦惱而“瘦損”竟然也成為她的罪過。他把自己的失業也歸咎于子君,但這樣的失業竟然在他們同居幾個月之后,這就不單涓生自己奇怪了。其實是涓生想要逃走了,但他最終發現即使沒有子君,他的生活也不會有新的改變,新的道路只是他逃避現實的卻又無法逃避時候制造的一個幻影。所以他會懷念有子君的日子,他在子君離去后竟然還會幻想子君會在某天不期然地來訪問自己,但子君的死徹底斷絕了他的退路,使他永遠也不會再回到曾經充滿希望的生活。
涓生并沒有給予子君以切實的新生的希望,他最終感到那糾纏自己的新的生路卻沒有自己的一份,這是徹底的絕望和悲哀。涓生始終不敢正視自己的情感,他對自己的過高估計使他把子君對他的愛和眷戀當作他展翅飛翔的最大的障礙,他追求的是一種想象中的生活。但生活是實實在在的東西,雖然沒有理由去譴責涓生對生活的夢想,但把別人作為犧牲對象,鼓勵別人成為娜拉式的叛逆者,僅僅是憑借著一句“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又怎樣去找到自由幸福的生活?一個男人尚且無法謀到職位,一個弱小的女子出走也就只有兩條路:不是墮落就是回來(肉體或精神的死亡)。涓生的懺悔也是他的焦慮情緒的一種表現,這種不滿現狀但又無路可去的悲哀是會糾纏他一生的情結,即使他可以忘卻子君的死亡,他也仍然不會獲得靈魂的安寧。普通的愛情悲劇的抒寫難以達到如此的高度,魯迅的深刻性在于他從涓生的自我辯解的所謂懺悔與自白中發掘了他靈魂之中的卑鄙和怯懦,發現了他的自戀自憐和自我迷失,涓生的焦慮與軟弱也是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心理問題的一種表現。
二、孤獨自閉
魯迅不是一個可以重復自己的作家,茅盾曾說過魯迅是小說形式的先鋒,其實魯迅也是小說主題上不斷創新的作家。《傷逝》這篇小說的形式很特別,一般的日記體小說是屬于作者自傳性質的,如果不是,敘事者是要負責交代日記的來源的,例如《狂人日記》,魯迅就在序言中交代了這篇日記的來源,但是作為僅有的兩篇日記體小說中的另一篇,《傷逝》卻有意忽略了這一點,小說的副標題是“涓生手記”,而且在文章的開始部分有這樣一句話,“如果我能夠,我要寫下我的悔恨和悲哀,為子君,為自己”。既然這是涓生的“手記”為什么又要使用“如果我能夠”這樣的假設句式?而且這篇小說在寫成的那一年并沒公開發表,而是作為小說集《彷徨》中的一篇收入集中,或者可以想象這并不是一篇純粹虛構性質的文本,而是類似于講述故事性質的復述性文本。
將這篇小說和魯迅其他的雙主人公敘事的模式相比較就會發現,涓生和魏連殳、呂韋甫甚至祥林嫂有著極其相似的心理特征,那就是強烈的傾訴欲望與這種欲望的受阻。在魯迅的小說中都存在一個“我”,雖然這個“我”也常常陷入無話可說的境地,但對于魏連殳、呂韋甫和祥林嫂等人的命運還是有著同情的成分,也還可以勉強地敷衍幾句,但在另外的一篇小說《頭發的故事》中,面對N君的牢騷,“我”卻自始至終沒有說過一句話,因此可以把《傷逝》看作是旁觀主體“我”的缺省的敘事文本。由于主人公涓生的激烈的情緒表達,使得作為敘事者的“我”無話可說,而這種無話可說,是由于涓生對于事件的敘述和自我譴責的言說的時間和空間的密度所決定的,也就是說在這樣的文本中,容不下主人公思想流程之外的其他語言和思想的存在。《傷逝》是非常純粹的密度性敘述文本,它是一個嚴密的心理空間,同時也是封閉的心理空間,這個空間又交叉著混亂的時間。在文本的敘述中,涓生的思維中會突然地出現子君的死,“我突然想到她的死”這樣的句子意外地插入涓生對整個事件的敘述中,打亂了文本的時空秩序。子君的死是涓生心理上最難跨越的障礙,對于這樣交織著“死亡”與“彷徨”(認罪的不確定性與懺悔的回轉性)的事件不但是作為旁觀者的“我”,就是作為讀者的任何人都無話可說。
從文本的問題意義來講,子君和涓生的情感悲劇實際上是一個新的生命被滿懷希望地創造又被無情地毀滅的悲劇,這個悲劇既不是社會造成的,也不是周圍環境的壓抑造成的,更不是性格的懦弱和對生活的簡單理解造成的,這是個無人負責的悲劇。涓生真情的懺悔使人感動,但是面對一個曾經熱情鮮活的生命的消失,不是悔恨就可以釋懷的,可以說子君的死亡是涓生永遠的夢魘。
旁觀者縱然沒有權利譴責涓生對待愛情和婚姻時候的懦弱,但是卻無法忽視他在面對責任時候的退縮。涓生常說的振翅高飛,是要在把子君這個對他而言的負擔解除之后,那么在認識子君之前他何以就不能飛翔呢?涓生對子君所說的“攜手同行”其實也是虛妄的,他自己都未必清楚。涓生一生都會在一種追逐的行程之中,得到了就會厭倦了。他用幻想來逃避現實,用子君來驅趕空虛,他沒有確實的行為準則沒有確定的人生目標,他無法腳踏實地像子君一樣地生活。
《傷逝》中有一個耐人尋味的場面——涓生在向子君求婚時下跪,對于這個場景兩個人有著不同的理解:子君認為這是涓生向自己表示了最熱烈最真摯的愛情,因為一個男人為了表達自己的情感竟然會采取最極端的方式;但對涓生而言這卻是最可笑的行為,因為這意味著沒有說出口的最莊嚴的承諾。這是一種認識的錯位,而就是這種錯位預示了他們不可挽回的情感毀滅的悲劇。種種事件的上演都在封閉的空間之內——會所與賃屋,但這個封閉的空間其實是對涓生自閉的心理與性格的一種暗示,當子君的到來打破這種封閉,將涓生從會館帶出,涓生又因為恐懼而逃回會館。
三、自戀自憐
《傷逝》中涓生最顯著的性格特征是焦躁和不自信。他幾乎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即使是在會館中和子君交往的日子也不見他和什么樣的朋友或同事往來。他是一個寄居異地的漂泊者,會館就是提供給那些在外地謀生而居無定所的人暫時的棲身之所,因此涓生比子君更身感著極大的寂寞和空虛。他在不同的人生階段用不同的方式來排解自己的寂寞,書籍、愛情和幻想以及心靈懺悔。排解的方式最初并不是以愛情的形式出現,而是他暫時充當了一個思想啟蒙者,這啟蒙的對象給了他無限的歡樂和極大的自信。可以說是子君的反應暫時滿足了涓生對于被他人承認的欲望,也許在那樣的環境下,除了子君不會再有第二個人對涓生懷著如此崇拜的情感和由此而來的愛戀,子君滿足了涓生需要被肯定的欲望,這種欲望始終貫穿于文本之中。涓生有著傳統知識分子懷才不遇的憤慨,他的自我欣賞與自戀自憐是他悲劇性格的核心。
魯迅在作品中并沒有交代子君為何離開父親的家而來到叔叔的家,但是可以知道的是,子君是一個受過新式教育的女子,但她同時具有傳統的淑女風范與勇敢無畏的現代精神,對雪萊的半身像都不敢正視的她卻能夠與人私奔而毫不畏懼流言,能夠說出“我是我自己的,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這樣的話,也能夠在同居生活中努力做一個賢良的妻子。那句話使涓生震驚更使他深陷入自大的夸張的想象之中——他竟然會認為由此可以見出中國婦女的可以拯救,卻不知道子君是因為愛而勇敢無畏。涓生的欣喜可以說是來源于對自己能力的過高估計,那就是他終于不再是一個天賦頗高卻陷入平凡普通境遇的人。涓生愛上子君其實是愛上了自己,因為只有這個時候,他才能夠從子君的身上找到自我肯定的信心,找到自我力量的確證,由此而來可以推斷,一旦這種內在的纏綿之情隨著時光無情地消散,那么建立在此基礎上的愛情也將消失。
涓生愛子君其實也就是愛他自己作為創造者的身份,他從子君決絕的態度和昂然無畏的姿態上似乎看到了前途的光明,這光明的希望是子君給與的——一個尚在傳統與現代之間徘徊的女子,都能夠無畏地走自己的路,那作為導師的涓生的欣喜是可想而知的。涓生渴望著社會的承認與贊揚,當他和子君一同走路時,他畏縮的表現與其說是一種懦弱,不如說是一種對外在世界規則的趨同。涓生并不想做一個與世隔絕的人,更不想成為一個與眾不同的人,在他的內心世界中孤獨與不愛肯定是他最難以忍受的空虛,他懷念和子君在會館中的爭執,他在子君離去之后去找久已沒有交往的世伯,他注重朋友的冷和子君的冷,都說明了他對熱鬧生活在潛意識中的肯定。涓生幻想的擺脫子君之后的生活,雖然是高貴與低賤混雜的夢幻,但也是一種充滿著熱氣的生活,成為不會被時代拋棄不會被時代遺忘的角色是他的追求。
渴望和社會與人們的期待保持一致是所有人的追求,一旦人感覺到自己脫離了人群,陷入孤獨甚至與他人敵對的境地,就會在心理上感到焦躁不安,“我們成功地說服自己做決定的是我們自己,而事實上,由于懼怕孤立,害怕對我們的生命、自由及舒適的更直接威脅,我們與別人的期望要求保持一致。”[5]涓生和子君的不同之處在于,他們在心理上對于社會承認的渴望程度不同,對于婚姻的理解不同。涓生把愛情、婚姻看作是拯救與鼓勵,他認為婚姻是可以攜手前行的路;子君卻把自由的愛情看作通向美滿婚姻與幸福的路,她認為這場婚姻就是終點,對于愛情與婚姻的認識錯位,來源于他們對于愛情與婚姻的不同的心理期待,也源自于他們不同的性格。子君善于為別人犧牲,她的世界只有涓生和涓生對她的愛,如果失去了這兩者之一,她都會喪失生活的目標,會喪失精神的支柱,她的堅決的宣言也是為了獲得和涓生在一起生活的權利和自由。涓生是了解子君的,他說子君的勇敢是出于愛,就是他看清楚了子君并不是解放了的、覺醒了的女性的代表。除了愛情子君并沒有清醒的自我概念,缺乏自我表現和自我認知的能力,她習慣于犧牲自我,并把這種犧牲的本身看成生活應該有的意義。涓生厭倦的是一種固定不變的、無法與外界交流的生活,愛情的新鮮一旦消逝,他就必然要去尋找另外一種生活來彌補空虛的心靈。涓生常常不滿于生活,但又無力改變周圍的環境,因此他只能在小范圍內改變自己的生活,向子君宣講新的道德觀念和文學家的詩文與生活,這是一種逃避現實卻又肯定自我的方式,和子君戀愛使他暫時逃離了空虛,幾個月幸福的婚姻生活讓他可以抗拒工作的乏味和無聊。涓生的愛不是一種純粹的精神之戀,而是一種手段,當他一旦發現這種手段無法達到他想要的目的——自由、充實與被肯定之后,他內心深處的激情就會很快冷卻并且無可挽回。
涓生在人生的道路上面臨著諸多的生活與心理的困境:婚戀自由后的經濟與精神的痛苦,事業(在職無聊與失業困苦)的抉擇以及對生命與未來的不安。涓生不滿于現實卻又無路可走,他試圖掙扎改變自身的困境,但結局卻是子君在他人的冷眼中死去,自己最終也失去了如魏連殳(《孤獨者》)與呂緯甫(《在酒樓上》)似的茍活者的資格。涓生與巴金、老舍以及沈從文筆下的男性形象,有著強烈的譜系關系,縱觀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無論是男性作家還是女性作家,其筆下所塑造的女性形象,相對于男性而言,其精神與肉體大多具有健康的色彩,她們樂觀、堅韌,尤其是在家庭中擔當了絕大部分的責任,她們敢愛敢恨,她們自強自愛,她們在苦難中支撐起家庭的天空。魯迅通過愛情悲劇的書寫,為我們描述了傳統與現代糾結中的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在心理上的迷茫與彷徨,尤其是男性知識分子責任感的缺失與行動力的匱乏。
1919年,胡適創作了戲劇作品《終身大事》,劇中收到陳先生紙條(“此事與別人無關”“你該自己決斷”)鼓勵的田女士毅然收拾了金銀細軟,坐了陳先生的汽車私奔了,似乎只要有勇氣能決斷,自由戀愛進而私奔同居就必然會有歡樂的結局。1925年,魯迅創作了《傷逝》,其中的子君和涓生卻是除了愛情和勇氣以及雞肋般的工作之外別無其他,更別說汽車和細軟了,悲劇的結局似乎在相愛之前既已注定。但有自由戀愛又有經濟基礎就必然幸福么?這似乎是古往今來的世界性問題,是超越了時間與空間的人類的普遍困惑。《傷逝》是一部充滿詩意與悲情色彩的愛情小說,子君的死亡與涓生的消沉有社會原因,與涓生的心理禁閉也有密切的關系,這種禁閉使他敏感卻又缺乏行動力,使在他終于勇敢地伸出觸角卻不斷碰壁后,又縮回了豐富而瘋狂的內心世界,自我禁錮自我限制。